 |
 |
|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 我为什么会成为余秋雨首选的靶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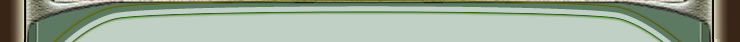 |
 |
|
余秋雨在2002年答多家报纸记者问时说:如此多论敌只选古远清一个人,是因为我发表的媒体最多,遍及北京、天津、广州、合肥、南宁等地,另一原因是我“诽谤内容最具体”。
余秋雨的“情报”工作做得太差,我批评余秋雨的文章除发表在国内外,还在美国、澳大利亚、泰国等国家及香港等地登过。如果他当时知道这个情况,在起诉书中肯定会追加我“道歉”的地区和媒体,或许会将精神损失费涨价至二十万元也说不定。但涨多了,只会增加他的诉讼费,且会引起别人对他更大的反感。
他告我还有一个原因有可能是本人属“独行侠”,在非综合性名牌大学任教。告我至少不会像告别人那样引起名校教授群乃至当地作家群起来助威和声援。
但余秋雨对我似乎不够了解。他把我看作省油的灯,是他犯了在战术上不重视“敌人”这一错误。我虽然是个“小教授”,但我研究“文革文学”与别人不同之处在于主要研究“文革写作组”,且十分注重小处着眼,从史料收集开始。如在《余秋雨与“石一歌”》中,我首次向鲁迅研究界披露了“石一歌”写作组包括余秋雨在内的十一人名单。在《文化名人传记也要打假》中,澄清“花城”出版的《余秋雨的背影》一书中所讲的余秋雨只写过两篇大批判文章这一事实时,首次披露了余秋雨不仅写出了如胡锡涛说过的《走出“彼得堡”》这样轰动一时的文章,并写过用“任犊”笔名发表的《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还参与写作了署名“罗思鼎”的《〈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样的重头文章。在《弄巧反拙 欲盖弥彰——评〈新民周刊〉等媒体联合调查余秋雨“文革问题”》一文中,又披露了原清查上海市委写作组组长夏其言所写的有关余秋雨的结论性意见。这些材料打破了他自己吹嘘的“文革”中没有犯过任何错误的神话,难怪他十分愤怒,以至在答北京《华夏时报》记者问时,含沙射影地把我比作对“当年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做出逆反性指证的“老纳粹”。
比余秋雨年长五岁的我,只是以历史考证者的身份写这些文章,其出发点是纠正有关余秋雨传记和报道中掺假的成分。我在有关文章中从未使用言之过激的诸如“文革余孽”、“‘四人帮’文胆”一类不符合史实的形容词。
余秋雨选中我作靶子另一理由是我“供职的学校名称上似乎有法律印痕”。余秋雨2002年8月21日答《中国青年报》记者问时所使用的“似乎”和“印痕”这两个词,激怒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部分师生,认为这是对我校的嘲笑乃至挑战。因而这所原由司法部后由教育部主管的重点大学,由校长亲自出面请了两位强劲的教授作为我的辩护律师。其中赵家仪博士为我校法学院经济法系主任,他参加过澳门相关法律工作。另一位麻昌华先生,系武汉大学博士,为我校民商法研究所负责人。我校法学院设有“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也许是出于对学校同事的关心和援助吧,这两位代理人不收我的律师费,而余秋雨的律师费却高达每小时三千元。这真应感谢余秋雨,是他告我为我校乃至全国法学界提供了这难得的科学研究新课题,尤其是为舆论监督、文学批评乃至公共(众)知情权与公众人物名誉权、隐私权保护之边界等问题作了探索和实践。
|
|
 
本书由“啃书虫”免费制作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