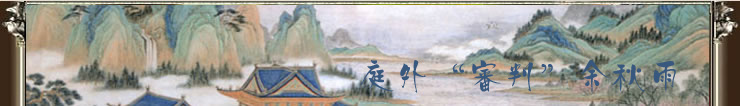 |
 |
|
序言自序 一本由余秋雨惹出来的书
|
 |
 |
|
古远清
原没有准备写这本书,后因余秋雨发表了“法律苦旅”“圆满结束”的声明,撕毁他放弃侵权指控这一具有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书》,再次攻击我研究他的“文革”写作是“造谣”和“诽谤”,这和他早先在《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中,把所有批评他的人归结为嫉妒,并把他们定性为和盗版集团相勾结的“文化杀手”的看法是一致的,因而我觉得有必要把“余古官司”的来龙去脉和一些内幕向读者作一个完整的交待。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余秋雨惹出来的一本书,或者说,是由他出题(起诉),我答辩。
记录这两位文人对簿公堂的精彩镜头和史料——尤其是写得像“文革”大字报的余氏杰作《起诉书》,可看出“文革”并非真的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用历史学的视角看,“文革”早已进了历史博物馆,但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说:“从文化学角度看,‘文革’依然活着。因为‘文革’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它有着深远的封建文化的背景。”(1)余秋雨扬言官司要打它三年五年(犹如一位伟人讲的“文革”七八年又来一次),这本身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一场“小文革”。“余古官司”开展后,余秋雨仍不改当年人品和文风,继续嚣张跋扈,在答记者问时一会儿把我比作“杀人犯”,一会儿又把我比成“老纳粹”,这充分说明“文革”在地面消失后,已转化为余秋雨的精神潜流,这样才会有“罗思鼎”、“石一歌”语言暴力的复活。“这属于当代历史的活化石,正可以时刻警惕我们勿忘‘文革’,也没有什么不好。”(2)写这本书,也算是对当代中国文坛论争史,对余秋雨现象批判,对我乃至对至今仍生活在“文革”阴影中的余秋雨本人回顾反思历史的曲折,从中总结经验教训,都有珍贵的价值。
这次由文学与法律发生的所谓冲突,也是我后中年时期的一种人生记录。
在我心目中,此书是我文学道路上充满挑战性的年轮,是我及广大“支古谴余”的朋友所共同谱就的一支正义之歌。
写这类保留和总结中国文坛十大官司榜首(2002年)的思想文化资源的书,说难也不难。不难在于此系亲身经历,且官司才结束记忆犹新。难在资料的准确性问题。好在有众多清查材料和打官司期间写的日记为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而不敢说任何一件事都叙述得毫无误差,但自信本人严格遵循历史真实,决不敢有半点掺假的地方。
2003年年底,我在台湾出席“两岸诗学国际研讨会”期间,台湾远景出版公司发行人沈登恩先生亲自到我下榻的天成大饭店约我写此书。(3)我不敢怠慢,归来后就加班加点赶写,以至把为我植字的太太累得进了医院,整个春节都没有过好,真对不起她。
一旦写完,便有如释重负之感,好似完成了一张重要的人生答卷,兑现了一个为这场官司探索公众人物名誉权弱化问题的庄严承诺,其欣慰之情,是难以形容的。
在欣慰之余,好心的朋友却替我担心:
此书的出版会不会引来一场新的官司?
我在2004年2月到广西参加台湾作家杨逵研讨会期间,答《桂林晚报》记者刘春问时说过:
“事实和真理在我这边。如果余秋雨再告,除为促销此书做义务广告外,可再次证明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的‘文革’,已无形地潜入他的灵魂和骨髓里。他如不食言把官司进行到底,就有可能把自己的‘文革’问题再让世人重审一遍,这样将再次出现‘庭外审判余秋雨’的壮观场面,让其又一次在历史法庭上充当被告。那时我又可以在余秋雨的‘拿出证据来’的催促声中,找到更多他在‘文革’中劣行的证据,那我就可以再写一本《庭外‘审判’余秋雨》的续集了。”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的编写,得到了著名学者于光远及著名作家董桥等人的支持,他们纷纷寄来了授权书,表示同意将他们的大作收入本书,但也有些作者经多方寻找未果,希望见到此书后与我能联系,以便寄奉样书和簿酬。我的通讯处是:430070湖北武汉市邮政70190192信箱。
2005年春节于武汉
注:
(1) 《“文革”进入了我们的血液》,《随笔》2003年第6期。
(2)邵燕祥:《否定不是抹去》,《文汇读书周报》1995年3月25日。
(3)后因沈登恩先生病故未出成.
|
|
 
本书由“啃书虫”免费制作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