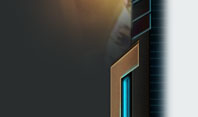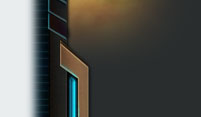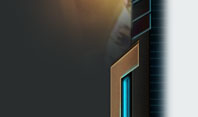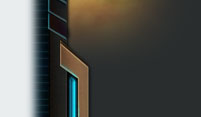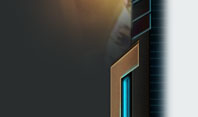 |
|
五 |
|
 |
|
透过半开的百叶窗,正在西沉的太阳将一组菱形的橘黄色条纹投射到卧室的墙上。应该是缕缕的薄云的移动,使光纹暗淡、模糊下去,然后再度明亮、清晰起来。玛丽在醒明白之前已经盯着它们看了整整半分钟。房间的天花板很高,白墙,非常整洁;在她跟科林的床间放了张看起来很脆弱的竹制小桌,桌上是一个石头的水壶和两只玻璃杯;一个饰有雕刻的五斗橱靠在旁边的墙上,橱子上摆一个陶质花瓶,瓶里出人意外地插了一小枝缎英①。干燥的银色叶子在透过半开的窗户吹进房间的温暖气流中微微颤动,瑟瑟有声。地板看来是由一整块间有棕绿杂色的大理石铺就的。玛丽毫不费力就坐起身来,把光脚放在它冰凉的表面上。一扇装有百叶窗的门半开着,通往一个白色瓷砖铺砌的浴室。另一扇门,他们进来的那道门,关着,黄铜钩子上挂了件白色晨衣。玛丽给自己倒了一杯水,睡着之前她已经喝了好几杯了;这次她只是小口地呷着,不再是大口吞咽了,她把身子坐得笔直,把脊椎拉到极限,看着科林。
他跟她一样全身赤裸,也躺在被单上头,腰部以下俯卧着,以上则略有点笨拙地朝她扭过来。他的胳膊胎儿般交叉放在前胸;两条瘦长光滑的大腿略为分开,两只小得反常,就像孩子般的脚朝内弯着:他脊椎上那些纤细的骨节一路下来,在腰背部隐入一道深深的凹槽,而且沿着这一线,在百叶窗透进来的弱光映衬下看得格外清楚,长着一种纤细的茸毛。科林窄窄的腰上有一圈小小的凹痕,就像是牙印儿,印在光滑的雪白肌肤上,那是短裤上的松紧带给勒的。他的两瓣屁股小而紧实,像是小孩子的。玛丽俯下身来想爱抚爱抚他,又改变了主意。反而把水杯放在小桌上,凑得更近些审视他的脸,就像审视一个雕像的脸。
他脸庞的构造真是精致优美,而且具有一种无视惯常比例的独创和精巧。耳朵——只看得到一个——很大而且略有些突出;皮肤如此苍白细腻,简直就是半透明的,耳朵里面的皱褶也比普通人的要多出好多倍来,形成了不可思议的螺旋;耳垂也太长,鼓起来,又细下去,就像是泪滴。科林的眉毛像是粗粗的两条铅笔画出的线条,在鼻梁处逐渐弯曲下来,几乎要连接为一个点。他的眼眶极深,眼睛在睁开时是黑色的,眼下闭着,但见一圈灰色的、穗状花序般的长睫毛。在睡梦中,惯常那弄皱了他眉毛的困惑的蹙额,就连他欢笑时都难得舒展开的,舒展了开来,只留下一个几乎看不见的水印。他的鼻子也像耳朵一样,很长,可是侧面看来却并不突出;相反竟是平平的,沿着脸形延伸下来,在鼻翼处深深地刻进去,就像两个逗号的,是两个极小的鼻孔。科林的嘴挺直而又坚实,微微张开,只隐约看到一点牙齿。他的头发纤细得很不自然,像是婴儿的,纯然黑色,打着卷儿披散在他纤瘦、女性般的脖颈上。
玛丽来到窗前,把百叶窗整个打开。房间正对着西沉的太阳,看起来有四五层楼高,高出周围大部分的建筑。这么强烈的日光直射眼睛的情况下,她很难看清楚底下街道的样子,并由此估计他们所在的位置在旅馆的什么方位。脚步声、电视里的音乐声、餐具与碗盏的磕碰声,狗叫与无数其他的声音混杂在一起,从街道上直冲上来,仿佛出自一个巨大的交响乐团和合唱队。她轻轻地将百叶窗拉上,墙上又重现出那段光纹。受到房间内巨大的空间以及那闪亮的整块大理石地面的吸引,玛丽开始做起了她的瑜伽。屁股着地感受到的冰凉让她喘了口粗气,她端坐地上,两条腿向前伸展开,脊背挺直。她慢慢朝前俯身,长长地呼气,用两只手去够并牢牢抓住脚心,上身沿两条腿的方向趴下来,直到把头抵在小腿上。她将这个姿势保持了有几分钟时间,闭上眼睛,深呼吸。等她直起身来,科林已经坐了起来。
他还没醒明白,从她的空床看到墙上的光影,又转到地板上的玛丽。“我们这是在哪儿?”
玛丽仰面躺下。“我也不太清楚。”
“罗伯特在那儿?”
“我不知道。”她把两腿举过头顶,直到脚尖碰到身后的地板。
科林站起来,几乎立马又坐了回去。“那么,几点了?”
玛丽的声音瓮里瓮气的。“傍晚了。”
“你痒得好些了吗?”
“好了,谢谢。”
科林再度站起来,这次小心翼翼的,四顾打量了一下。他抱起胳膊。“咱们的衣服哪儿去了?”
玛丽说,“我不知道,”说着继续把两条腿向上举,形成肩倒立。
科林有些脚步不稳地走到浴室门前,探头进去看了看。“不在这里。”他把插着缎英的花瓶举起来,把衣橱的顶盖揭开。“也不在这里。”
“是啊,”玛丽道。
他又坐回到床上,看着她。“你不觉得我们该找找吗?你不担心?”
“我觉得挺好,”玛丽道。
科林叹了口气。“好吧,我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玛丽把腿放低一点,朝着天花板道,“门上挂着件晨衣。”她把四肢尽量舒适地在地板上摆好,手掌向上,闭上眼睛,开始通过鼻子进行深呼吸。
几分钟后她听见科林的声音试探性地叫道,“我可不能穿这个。”因为他人在浴室里,嗓音听来像是瓶子里传出的。她睁开眼睛,见他从里面走了出来。“当然可以!”玛丽看着他走过来,觉得奇怪地说。“你看起来别提多可爱了。”她把他的鬈发从带饰边的领口拂开,摸着他衣料下面的身体。“你看着就像尊神一样。我想我一定得把你领到床上去了。”她拽着他的胳膊,但被科林给拽开了。
“这根本就不是件晨衣,”他说。“是件女式睡衣。”他指着胸口位置刺绣的一簇鲜花。
玛丽退后一步。“你不知道穿上这个你看起来有多棒。”
科林开始把那件女式睡衣往下脱。“我可不能穿成这副样子,”他在衣服里面说,“在一个陌生人的家里晃荡。”
“在勃起的时候确实不行,”玛丽说着又回头练她的瑜伽。她双脚并立站好,两手靠在两侧,俯下身用手去够她的大脚趾,然后进一步将身体对折,直到将手和手腕平摊着压在地板上。
科林站着看了她一会儿,那件女式睡衣搭在他胳膊上。“很高兴你一点都不痒了,”他过了一会儿道,玛丽咕哝了一声。等她再度直起身来以后,他走到她跟前。“你得穿上这玩意儿,”他说。“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玛丽腾空一跃,落地时两脚大大地分开。她把身体朝一侧拉伸,直到能用左手抓住左脚踝。她的右手戳在空中,她沿着右手指着的方向望着天花板。科林把睡衣扔在地板上,又躺回到床上去了。十五分钟以后,玛丽才把睡衣捡起来穿上,在浴室的镜子前把头发整理了一下,朝科林嘲弄地一笑,离开了房间。
她小心地缓缓穿过一条陈列着传家宝的长长的走廊,简直就是个家庭博物馆,每一寸空间都被利用了来陈列展品,所有的展品全都富丽堂皇,风格繁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全都是没有用过的、满怀钟爱精心呵护之下的深色桃花心木制作的各种物件,全都雕了花、上了光,八字脚外翻地站立着,但凡可以的全都加了天鹅绒衬垫。两座落地式大摆钟摆在她左手边的一个壁龛里,就像是两个哨兵,并排滴滴答答地走动。就连那些比较小型的物件,像是玻璃罩子里剥制的鸟类标本、各色花瓶、水果盏、灯座,各种无以名状的黄铜和雕花玻璃的什物,也全都显得沉重得搬不动,由时间的重量和失落的历史牢牢地压在各自的位置。西墙上有一连三个窗户,投射出同样的橘红色光纹,正在暗淡下去,不过这里的设计意图被几块陈旧的、摆成一组图案的地毯给破坏了。陈列室的正中摆着张巨大的抛光餐桌,周遭一圈配套的高背椅子。桌子头上是台电话机、便笺簿和一支铅笔。墙上挂了不下十几幅油画,大部分是肖像,也有几幅泛了黄的风景画。所有的肖像一律都黑沉沉的:颜色暗淡的服装,混浊不明的背景,如此映衬之下的脸庞都像是月亮一样闪着微光。有两幅风景,画的都是掉光了叶子的秃树,几乎都看不太清楚了,伸展在黑沉沉的湖面上,湖岸上是举着双臂跳舞的模模糊糊的人影。
陈列室尽头有两扇门,他们就是通过其中的一扇进来的;两扇门全都小得不成比例,没有镶板镶嵌,漆成白色,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广厦被分隔成了小套间。玛丽在一口餐具柜前停下了脚步,餐具柜靠墙立在两个窗户当间儿,简直是个表面锃明瓦亮的大怪物,每个抽屉都有个黄铜的球形把手,还做成了女人头的样子。她试的几个抽屉全都锁着。柜子顶上精心陈列着整套非常讲究的个人用具:一托盘男用发梳和衣服刷子,刷背都是银质的,一只彩绘辉煌的剃须用瓷碗,几把锋利无比、能割断咽喉的剃刀摆成一个扇形,乌木架子上摆了一排烟斗,一根短马鞭,一把苍蝇拍,一个金质的火绒匣子,一块带链子的怀表。这些陈设背后的墙上挂了些运动的照片,大部分是赛马,马匹都四蹄翻飞,骑手都戴着大礼帽。
玛丽已经把整个陈列室都兜了一遍——比较大的物件她都环绕一周,停下来朝一面镀金框的镜子里细看——这才意识到这些展品最突出的特色。西面的墙上有玻璃的拉门通向一个长长的阳台。从她站立的位置望去,因为有几盏枝形吊灯的照明,她很难看透外面半明半暗的景色,不过可以看出有很多开花的植物,还有藤蔓植物和盆栽的小树。玛丽屏住了呼吸,一张苍白的小脸正从阴影中注视着她,一张脱离了躯壳的脸,因为夜晚的天空和屋内的摆设反射在玻璃上的映像使她看不见衣服或头发。那张脸继续注视着她,眼睛眨都不眨,一张完美的椭圆脸庞;然后那张脸后退,斜地里隐入阴影当中,消失不见了。玛丽长吸了一口气。玻璃门打开的时候,房间的映像抖动了一下。一个年轻女人,头发全都朴素地挽在后头,略有些僵硬地走进房间,朝她伸出手来。“到外面来吧,”她说。“更加宜人些。”
几颗星星已然从瘀伤般淡蓝色的天空中突围出来,不过仍旧能够轻易地辨认出大海、泊船的柱子,甚至公墓小岛那黑色的轮廓。阳台的正下方,四十英尺以下,是一个废弃的庭院。密集的盆栽鲜花散发出刺鼻的浓香,浓到几乎令人作呕。那女人在一把帆布椅子上落座,同时痛苦地轻轻喘息了一声。
“是很美,”她说,仿佛玛丽已经开过了口。“我尽可能多待在外面这个阳台上。”玛丽点了点头。阳台足有半个房间那么长。“我叫卡罗琳。罗伯特的妻子。”
玛丽跟她握了握手,自我介绍了,在面对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两人中间有一张白色的小桌子,桌上有一块饼干盛在一个盘子里。覆盖了墙面的常春藤正在开花,藤后面有只蟋蟀在唱歌。卡罗琳再一次注视着玛丽,就像她自己处于隐身状态一样;她的眼睛稳稳地从玛丽的头发看到她的眼睛,再到她的嘴,继续朝下看到桌子挡住了她视线的所在。
“这是你的?”玛丽指着身上那件睡衣的袖口说。
这个问题像是将卡罗琳从白日梦中唤醒了。她在椅子上坐直身体,交叉起双手放在腿上,然后又把腿架起来,仿佛特意摆出一个经过考虑的姿态来用以交谈。她说话的时候,语气有些勉强,音调也比刚才有些高。“是的,我就坐在这里自己做的。我喜欢刺绣。”
玛丽恭维了一番她的巧工,接下来的一阵沉默中卡罗琳显得拼命想找点话头讲。她紧张地一惊之下,意识到玛丽瞥过那块饼干一眼,就立刻把盘子端给了她。“请把它给吃了吧。”
“多谢。”玛丽尽量想把饼干细嚼慢咽。
卡罗琳不安地注视着。“你肯定是饿了。想吃点东西吗?”
“好呀,多谢你。”
可卡罗琳却并没有马上行动,反而说,“我很抱歉罗伯特眼下不在。他请我代为致歉。他去他的酒吧了。当然是公事。今晚上有个新经理开始当班。”
玛丽从空盘子上抬起眼睛。“他的酒吧?”
卡罗琳很艰难地准备站起来,讲话的时候明显很痛苦,冲着想帮她一把的玛丽摇了摇头。“他开了个酒吧。算是种业余爱好吧,我猜。就是他带你们去的那个地方。”
“他从没提到那酒吧是他的,”玛丽说。
卡罗琳拿起空盘子,走向拉门。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得整个身子都转过来,看着玛丽。她就事论事地说,“你对这个酒吧知道得比我多,我从没去过那里。”
十五分钟后,她端着个堆满了三明治的小柳条篮子,还有两杯橙汁回来了。她慢慢地走到阳台上,让玛丽把托盘从她手上接了过去。卡罗琳小心翼翼地在椅子上坐下,玛丽还站在当地。
“你脊背受伤了?”
卡罗琳却只是愉快地说,“吃吧,也给你的朋友留几个。”然后她又迅速地加了一句,“你喜欢你的朋友吗?”
“你是说科林吧,”玛丽道。
卡罗琳讲话的时候非常小心,她的脸绷紧了,仿佛随时等着一声爆炸的巨响。“希望你不会介意。我应该向你坦白,为了公平起见。你看,你们睡觉的时候我进去看过你们。我在那个箱子上坐了有半个钟头。希望你不要生气。”
玛丽一边狼吞虎咽,一边有些半信半疑地说,“不会。”
卡罗琳突然之间像是年轻了许多。她像个尴尬的少女似的摆弄着手指。“我想还是跟你坦白的好。我不想让你觉得我是在暗中窥探你们。你不会那么想吧,对不对?”
玛丽摇了摇头。卡罗琳的声音几乎跟耳语声相差无几。“科林非常美丽。罗伯特跟我说起过的。你当然也是。”
玛丽继续吃她的三明治,一个接着一个,她目光集中在卡罗琳的一双手上。
卡罗琳清了清嗓子。“我想你会认为我简直疯了,而且还很粗鲁。你们两个相爱吗?”
玛丽已经把三明治吃掉了一半,还又多吃了一两个。“呣,是的,我的确爱他,不过你所谓的‘相爱’也许有些不同的意味吧。”她抬头看着她。可卡罗琳还在等她继续往下说。“我不再迷恋他的身体了,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不像当初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不过我信任他。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卡罗琳兴奋地讲起话来,更像个小孩子,连少女都算不上了。“我说的‘相爱’,意思是你会为对方做任何事,而且……”她犹豫了一下。她的眼睛变得格外地明亮。“而且你也会让他们对你做任何事。”
玛丽在椅子上放松下来,两只手捧着空玻璃杯。“任何事可有点夸张了。”
卡罗琳话语中带着挑衅。两只小手紧紧地攥在一起。“你要是真爱上了什么人,你甚至都会甘心让他杀死你,要是必要的话。”
玛丽又拿起一个三明治。“必要?”
卡罗琳都没听见她的话。“这就是我所谓的‘相爱’,”她志得意满地说。
玛丽把三明治推到一边,表示不能再吃了。“如此说来,你也要做好准备把你‘爱’的那个人给杀了?”
“哦没错,如果我是那个男人,就会这么做。”
“那个男人?”玛丽觉得奇怪地说。
可是卡罗琳戏剧化地举起她的食指,还伸长了脖子。“我听到有动静,”她悄声道,开始挣扎着要起来。
门犹犹豫豫地被拉开了,科林颇为小心地走到阳台上来,一只手抓着围在腰际的一块很小的白色手巾。
“这位是卡罗琳,罗伯特的妻子,”玛丽道。“这是科林。”
两人握手的时候,卡罗琳就像刚才打量玛丽一样不错眼地注视着科林;科林则盯着篮子里下剩的三明治。“拖把椅子过来,”卡罗琳道,指着阳台那边一把折叠式帆布椅。科林背朝大海在她们俩中间落座,一只手仍放在腰际,以防毛巾滑落。他在卡罗琳的密切注视之下吃起了三明治。玛丽把椅子往边上挪了挪,为的是能看到天空。有那么一刻谁都没做声。科林把橙汁喝完以后,想捕捉住玛丽的目光。然后卡罗琳再度陷入扭捏的状态,一心想找个话题,就问科林是否喜欢这个城市。“是的,”他答道,冲玛丽微微一笑,“只不过我们总是不断地迷路。”
接着又是一段短暂的沉默。然后卡罗琳突然惊叫一声,把他们吓了一跳,“当然了!你们的衣服。我都忘了。我洗好而且晾干了。就在你们的浴室里那个上了锁的小橱里。”
玛丽仍旧望着夜空中越来越多的星星。“你真是太体贴了。”
卡罗琳冲着科林微笑着。“你知道,我以为你会是个很文静的人呢。”
科林一心想把罩住裆部的毛巾重新整理一下。“你以前听说过我?”
“我们睡觉的时候卡罗琳进去看了我们一会儿,”玛丽解释道,她小心地使自己的语调保持平静超然。
“你是美国人?”科林礼貌地询问。
“是加拿大人,拜托。”
科林迅速地点了点头,仿佛这其间的差别显而易见。
卡罗琳压下一声短笑,举起一把小钥匙。“罗伯特一心希望你们留下跟我们共进晚餐。他告诉我你们如果不赏光的话就不把衣服给你们。”科林礼貌地一笑,玛丽盯着卡罗琳在拇指和食指间摇晃着的钥匙。“我倒是真饿了,”科林说,看着玛丽,玛丽则对卡罗琳说,“我更愿意先拿回我的衣服,然后再作决定。”
“我也是这么想,可罗伯特坚持要这么做。”她突然间严肃起来,俯下身,把手放在玛丽的胳膊上。“拜托赏光留下来吧。客人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太稀罕了。”她在恳求他们,她的目光在科林和玛丽的脸之间打转儿。“你们要是肯赏光,我简直高兴死了。我们吃得很丰盛的,我向你们保证。”然后她又加了一句,“你们要是不肯赏光的话罗伯特会责怪我的。求你们留下来吧。”
“算了,玛丽。”科林道,“咱们就留下吧。”
“求你了!”卡罗琳的语气中带了一丝凶狠。玛丽一惊之下抬起了眼睛,两个女人隔着那张桌子对望着。玛丽点了点头,卡罗琳高兴又如释重负地大叫一声,把钥匙扔给了她。
注释
① 一种欧洲植物(一年生缎花属,一年生缎花),栽培价值在于其紫色芳香的花和扁圆的、银白色的纸质荚果。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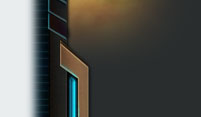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