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天酒地,贼和尚纵情逸乐;死里逃生,孙大圣尘殿探秘..咆哨响马惊家人坠,孙行者搜信,易毒草..
那行者问皇帝出了甚事,皇帝道:“甚事,遭抢也!”行者道:“手头紧那酬银便免了,光天化日之下编派甚抢劫案!”皇帝急道:“寡人虽不富裕,好歹有点私房钱,一百两银子还凑得齐。却要怪圣僧不让寡人乘辇着衮,只好拎着银子微服出行,半道上突冒出一伙歹人,骑快马,衣纨裤,围上便抢银子。手下道:‘圣上在此,休得无礼!’那帮泼皮竟大笑:‘什么“剩上、剩下”,一个子也下给你剩!’朕道:‘便是平民百姓财物,也不该抢。
还有王法么!’那帮人道:‘可笑,可笑!王法大,王法大,不如俺爹一句话!’夺了银子,呼啸而去!”
行者笑道:“不瞒陛下,昨日俺师徒进城,先被那伙人抢去看皇御赐的锡杖、僧帽。俺师父投状府衙,府尹不理;又至大理寺告诉,寺卿却道师父‘诬告’,打入大牢,生死未卜。”皇帝惊道:“有这等事!”行者道:“适才陛下遭抢时,可认得强人是谁?”皇帝道:“朕不认得。”转身问随从:
“你们可认得?”众人吞吞吐吐。皇帝怒道:“莫不是串通一气,有意欺君?”
随从恐惧,一个道:“小人认出两个,一个看似老太师的长孙,一个像是大理寺卿的小儿!”
一人接道:“还有一个像是兵部尚书的侄子!”皇帝听了,脸一阵青一阵白,只叫:“可恶,可恶!朕回去一定嘱有司严加惩办!”行者道:“既如此、俺师父——”皇帝道:“立马便放!”“被抢僧宝?”“一定壁还!”
行者几个自欢喜。皇帝道:“圣僧,寡人之病——”行者道:“圣上之病,勿需针石!昨宵俺曾变化了入你寝宫,所闻所见,知陛下是个清廉之君。
然你既为一国之君,自当为民造福。眼下国中妖魔作祟,人臣在法,盗贼蜂起,民不聊生。陛下虽独善其身,于国何益,于民何益?”
一席话说得皇帝面热心跳,浑身冒汗,搭讪笑道:“圣僧说话忒直,好歹也给寡人留点面子。”行者笑道:“忠亨逆耳利于行’!想你朝中大臣,只甜言蜜语,粉饰太平。令你目昏耳喷,实祸国殃民也!”
皇帝道:“依圣僧之见,朕该如何做?”行者道:“老孙问你:那个金铃大王是个什么东西?值得你们奉为神圣,年年拜献,岁岁贡赋?”皇帝道:
“三年前他驾祥光彩云来到皇宫之上,天坠花雨,果然有神明仙圣模样。他有三个金铃,晃一个便下大雨;晃二个便刮飓风;晃三个便起雾瘴。他道如寡人不依他言,便连下七七四十九天大雨,再刮四十九天大风、起四十九天毒瘴。朕思如此一来,一国君臣黎民命皆休也!无奈,只好对他俯首帖耳,言听计从。”行者道:“那厮近日可曾来过?”皇帝道:“自从朕给他在南山修了金圣宫,却有二年没露面了。只是遣人找中常侍门公公,要钱要人!”
行者道:“陛下自回宫,却不要提敛钱选美之事,待老孙去南山探个明白,回来再做主张!”皇帝道:“圣僧自去,只求别提是寡人差遣!”八戒道:
“老官儿休怕!你不晓得俺大师兄神通,什么金铃大王,禁不住俺师兄一金箍棒!”行者笑道:“呆子,休乱卖弄!”腾云走了。
这厢皇帝要回宫,却下敢再便服出门,遂差人回去叫凤辇仪仗禁卫来。
等候的空儿,八戒将大圣故事一一说与皇帝及随从听,听得众人一惊一咋。
皇上道:“孙长老如此神通,猪长老、沙长老也一定不凡!”八戒牛气道:
“俺与大师兄相比也不过差个三十六变。什么上天入地,吞日吐月,捉妖拿怪,法力却也相仿!”大众听了,齐赞八戒。沙僧有些不自在,道:“猪长老什么妖怪都能降,只是见不得女妖精。见了她们,骨便酥了,手便软了,耙儿便掉了。”众大笑。八戒反稽道:“沙长老好,师父最喜他——师父放个屁,都说是香的!”说得沙僧恼怒,抄起宝杖要打八戒。八戒道:“来真的,好呵!”摸起钉耙,两个叮叮当当打到院子里。觉得施展不开,又腾起云头在半空开战!八戒力猛耙狠,杀了十几个回台,沙僧渐觉不支,便架住八戒兵器道:“二哥息怒!是小弟言语差池,冒犯了。还请宽宥!”八戒也是个直肠子,见沙僧这般。也就收了兵器,道:“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老猪也是个要面子、吃软不吃硬的角色。你既赔了礼,此事便作罢。好歹还是兄弟!”遂收了耙按落云头。皇帝笑道:“二位空中争斗,寡人真开了眼!才不过片时,为何不战了?”沙僧喝道:“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
目今妖怪未灭,我兄弟斗甚!”说得皇帝哑口无忽见太监进门,原来辇驾来了。沙僧道:“陛下回宫,休忘了传令释放师父、擒拿强人,追缴夫物!”
皇帝连声应诺。八戒道:“俺们在此间只吃菜糊糊,甚为清苦,你也摆个酒宴叫老猪打打牙祭!”皇帝推道:“却难为寡人!朕每日也是青菜粗米,三月不知肉味矣!”八戒不依。随从见皇帝为难,出主意道:“陛下休虑、可传旨门公公代为款待。他家山珍海味俱全!”皇帝不信。从人道:“谁敢欺君!”皇帝感叹:“真真想不到!”嘱随行太监:“便着门公公代朕备晚宴款待圣僧!”八戒道:“老诸午斋便不吃了,专候陛下来邀俺兄弟赴宴!”
皇帝不敢不应,起驾回宫。
皇帝返回宫中,临宣政殿,急遣太监分别去召大理寺卿、门公公。中常侍府邪离宫廷甚近,不知为何,等了约半个时辰,不见门公公来。寺卿倒昏头昏脑来到。原来他正与同僚吃酒,已是半醉;闻圣上召,撂酒盅酡红着脸儿来了。皇帝劈头盖脸把寺卿骂一顿,说他尸位素餐,纵容子弟胡作非为,犯上作乱;该捕的不捕,不该拿的乱拿。怒极,竟唤来锦衣校尉,令:“推出午门斩了!”吓得寺卿浑身抖颤,连连告饶。正危急间,幸门公公一步赶到。
门公公居处近为何姗姗来迟?原来早朝时皇帝见了行者、八戒后,匆匆散朝,未言征敛选美之事。门公公心存疑窦,回府即着心腹随从去馆驿打探消息。随从在馆驿门外埋伏下不久,便见皇上微服进了馆驿;又见行者腾云往南而去。随从回禀后,问公公觉事情不妙,便书简帖派人火速送往南山金圣宫。钦差去时,他正候南山回音;便着人招呼钦差在前厅吃茶,却在后庭坐等。片时投书人赶回,看了复简,才陪钦差进宫。一进宣政殿,见皇上要杀大理寺卿,忙代为求情。
皇上道:“这厮读职,几乎害了寡人性命,留他做甚!”门公公道:“强人惊驾,罪当诛杀。盼陛下允寺卿戴罪立功,捕获盗贼。但歹人未必是权贵子弟。我闻那东土妖僧善变化蛊人,难说不是他们幻了相来蒙骗陛下。还是等拿了真强人,审清了再定生杀子夺!”
那皇帝耳朵根软,被门公公一番花言巧语,也就转了心眼,不杀寺卿。
但亦惧怕行者几个神威,令寺卿即刻回衙释放唐僧,捉拿强人,勘明案情,速速报来。寺卿千恩万谢,出殿去了。皇帝又道:“公公,那猪长老要寡人今晚请他吃酒。朕一时无奈,答应下来。却是让爱卿备宴。请勿见怪。”门公公闻言,暗喜:“天助我也!”拜道:“微臣能力圣上分忧,乃是天大的荣幸!岂敢推委!臣这就回去嘱咐厨下办斋、一厢投柬相邀。陛下不嫌弃,届时也请驾临寒舍,以示礼贤下士之意厂皇帝道:“孤身体欠佳,就不去了。
一切烦爱卿操持。那孙长老去南山金圣富打探消息去了,回来也一并下柬帖请了。免他抱怨寡人小气!”门公公道:“圣上放心,老奴保管将东土圣僧一个不剩请到,叫他们吃饱、吃好,醉得一塌糊涂,出不了门儿!”叩辞皇帝,回府操办不提。
却道行者纵祥光离了馆驿,片时便至南山。山不甚高,却也松竹清幽,泉吟鹤鸣。俯看山问,只见金圣宫楼字重叠,鳞次柿比,果然一派庄严景象。
行者降下云头,变作一只白颊蓝羽山雀,一翅飞到大雄宝殿廊下。见正中三世佛与观音并排坐着享受烟火,微微诧异:“这金铃王也是个半瓶醋!若供三世佛,都是观音把后门儿,龙女、善财两旁侍立。他却如此排列!”那欢门前香案上香烟袅袅,莲座四匝酥油灯闪烁,老和尚■■敲着木鱼,小和尚咿咿呀呀念经。行者再瞧不出异常,振翅住后飞,过讲法堂、毗卢殿、方丈室,又见偌大一个后庭,门户森严。行者数了数,竟有九重!那楼堂殿阁,比前头梵宫又要精美:只见金铺玉户,雕梁画栋,极富丽堂皇,却清静无人。
行者正察看,忽闻一缕音乐声自深院传出。行者飞过去,路上见殿堂门额题着“金屋’、“银舍”..心说:“非金即银,俗不俗气!让老孙看看是些什么玩艺!”飞过去,顺窗户眼往里一瞅,不禁惊讶,原是一屋金子,金光灿灿,直堆到梁间。再看,又是盈盈一室银子,耀人目眩。行者骂道:
“好个贪财的妖,多欲的魔!”又往里行,见一华字门匾上写着“偎红斋”,对面一殿是“倚翠堂”。
那乐声便是从偎红斋传出的。行者忖道:“偎红、倚翠,花花公子勾当也。甚神明仙圣!”掠翅自窗上风眼飞进殿堂。里面盆火通红,暖意融融。
一厢乐工调丝弦;当庭宫娥蹈曼舞。席上一个胖大和尚正左右搂着两个美姬吃酒。那和尚脖子上挂着三个金铃。想便是金铃大王。行者细觑那妖,五官长相,一举一动,分明是胎生奶大之人,端的奇怪!想拿了他,又惧他铃儿,正踌躇间,脚蹬下梁间尘土,掉下来迷了那和尚眼目,抬头看见“山雀”,气得泼口大骂,伸手将一个铃儿略晃了晃,行者便觉一股强风袭来,忙嗖的一声,又顺风眼飞跑了。
那风儿将梁间尘土裹成一团浓雾,拂开门帘,吹出房室。起风时却也扬起宫娥裙裾,露出亵衣玉肌,众女子慌得并腿拢裙。和尚淫兴大发,便弓腰过去,垂涎道:“心肝儿,你护怎的?”偏撩人家裙子,又掐又挠,惹得女孩子一片嗔叫。行者外头听得清楚,怒道:“好个贪财好色的妖僧,逼得皇上穿破衣、百姓去截道儿!却在此荒淫无耻!”正要掣棒打进去,忽听一阵脚步响,原来一个小和尚捧着书简慌慌张张跑来,入室叫道:“门公公差人投书来也!”那和尚初不以为然,道:“看老阉人说个甚!”拆信一看,大惊,“原来姓孙的来窥探我家!”悟道:“适才那山雀儿莫不是他变的?—
—小心为妙!”便拂退舞乐姬妾,出堂来,召唤精壮弟子,持弹弓强弩,寻着山雀便打。
行者惊诧,“不知那姓门的是何人,与妖怪勾结,泄了老孙底细!”忙变作一个瓢虫,欲称“花大姐”的,伏在朱柱上。那伙人也没看清。忙乱了一阵,打杀了十几只山雀。金铃怪略放了心,便去前庭,行者一飞叮在那怪僧帽上。那怪进了方丈室,对投书人道:“回去告诉公公,就说我知晓了。
叫他也提防那几个东土僧人。有甚动静,丙来报信!”那人应着,出门上马走了。那怪便打坐养神。行者寻思,“这厮沉溺酒色,临急了抱佛脚,俺却不叫你养神!”便去门外,现了法身,掣出棒来,喝道:“金铃魔头,适间你满世界打弹弓放弯箭要杀老孙!如此爷爷在此,拿出你手段来赌一赌吧!”
那和尚闻言,先是一惊,推门一看,见是一个雷公脸瘦和尚,冷笑道:
“那书简上说你神通广大,我道有三头六臂哩!原是个痨病鬼儿!一姓孙的,我与你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为何上门滋事?”行者道:“泼魔,你与宦官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祸国殃民,该当何罪!”和尚笑道:“那国王自愿奉承老爷,干你屁事!你这瘦猴,‘一把攥着两头不冒’,却僭称什么‘大圣’。
赶紧走你的路!不然惹恼了本王,你小命倾也!”众弟子呵呵大笑。行者怒道:“叵耐这厮,竟敢小觑老孙!”见身旁有一凉亭,将铁棒晃一晃,长得旗杆似的,一下子打断四根住子,那亭子訇然倒塌。
妖僧与众弟子大惊失色。见行者挥棒上前,慌忙将三个铃儿对着行者没命地摇晃!只见狂风骤雨劈头盖脑袭来,大圣全然不惧,顶风冒雨直取那怪;忽又见一股瘴烟扑面吹来,便裹住他头脸,憋不住吸了几口,一刹间便觉头晕眼花,情知不好,正要纵筋斗云逃脱,无奈神昏志迷,念不了咒语,头栽倒在地,昏迷过去。众弟子一拥而上,将行者捆了。那怪大喜,令:“推到金圣殿前斩了,就地埋在菩提树下。多事猴儿就此了账也!”
众弟子得令,将行者抬至第九进院子,绑在大殿前菩提树上。刀剑齐下,乒乒乓乓,那行者脖子红也不红,众僧兵器皆卷了刃。没杀了行者,只把他震醒了。弟子们无奈,只好回禀妖僧,那怪心惊:“这厮果然有些功力!”
令将行者缚牢,又着心腹弟了点起铜炉去煎断肠草,好毒杀行者。
众僧给行者又加了两道绳,捆结实了,抽身锁上院门走了。行者抬头看那金圣殿,见匾上金字无光,廊柱蛛网缠绕,门封窗闭,寂无人声。忽悟道:
“此乃金铃怪正经去处,为何遭此冷落!”便想进去看看。遂使个缩身法儿,抽出身子,又将适才僧人撇下的一把烂刀变作自己模样仍在那儿缚着,方上了台阶。凑门缝一瞅,却一片昏暗,看不清楚。行者又使个遁法,自门隙进了大殿。定下神来,才慢慢看清锦帷彩帘尘封虫噬,鎏金铜炉香残灰冷。宝座上却分明坐着个狮首人身妖精:鬈发披散,眼如铜铃,届若钢针,口似血盆,十分吓人;穿一身黄金锁子甲,左手持一株于巴巴莲花,右手捏一截丝绦带儿。
行者初一惊,以为那怪看见自己了,忙藏在帷幕后,那厮却仿佛睡着一般,毫无动静;再觑,那怪仍坐原处一动不动。忍不住凑前,哧地笑起来,原是个死的!行者便嘻嘻哈哈揪那怪的胡子,拍他的脸,捶他的心窝,忽从嘴里喷出一股臭气,像是肝花肠子腐烂的气味。行者顿悟:“看来这才是真妖怪!不知何时叫那和尚暗算了,将铃儿夺去,仍唇称金铃大王名份作威作福!可悲那一国君臣还蒙在鼓里!”
行者感叹一回,揪下一缕黄澄澄的鬈发,揣在怀里。才出了殿,见几个和尚开庭门进来,其中一个捧着个瓷碗,急闪在廊柱后。见他们逮住自己替身,便灌药。一个笑道:“仙酒来也!不知能否降服这厮?”另个道:“金铃大王法力如何,也叫儿株断肠草送了命!何况这瘦猴子!”又一个道:“就是,就是!这厮头硬。肠子安是铁的!药到命除,没二话!”行者暗自庆幸,心想若是趁自己迷糊时,灌了这药,难说能活着出去!便像拣了便宜,也不惊动众僧,化一阵清风走了。
行者回到馆驿,见师父已放回来。八戒、沙僧迎上道:“猴哥,你可回来了——探妖事如何?”行者道:“已知底细!”问师父:“可吃苦了?”
三藏道:“先时吃些苦,走时又请我吃斋饭。只失物尚未归还。”行者道:
“不拿强人,如何追赃?”起身道:“待俺再去找皇帝老儿催催!”唐僧道:
“听他两个说皇帝是个好人。切勿鲁莽,惊了圣驾!”
行者应着走了。腾云来到宫庭,降下云头,直闯后宫。皇上与皇后才进午膳,饭是黄粱饭。几样素菜,无非是藩菜、蕨菜、萱草花、雪里蕻之类。
毋须侍女,更无乐舞。见行者至,两口儿慌得让座,道:“孙圣僧,回来了。
一堆吃些?”行者笑道:“不吃,不吃!谢了!”又道:“陛下好生清苦,却不知那金铃大王金银满屋,昼夜签歌,亨不尽的荣华富贵!”皇上讷讷道:
“人家是神圣,也是前世修来的。朕不眼馋!”行者叹道:“陛下焉知眼下那‘金铃王’不是什么神圣,其实连妖怪都不是!”皇上不信,道:“孙圣僧你逗寡人呢!那金铃大王朕三年前见过——”行者道:“以后陛下又见过几回?”皇帝、皇后皆摇头。行者摸出金鬈发递给皇帝看:“实话告之,那真金铃怪已被人害死,这是俺扯下的真妖怪的头发。现今却没有什么金铃大王,只一个花和尚住持假冒死大王名义要金银美女。”
皇帝两口儿哪里肯信,道:“不能,不能。倘如此,那门公公早已得知,敢不报来!”行者道:“正是你朝中有人与那花和尚勾结,欺君害民!”皇帝大惊:“是谁?”行者道:“俺在金圣宫探察时,朝中一个老太监送书简给那假妖王,俺听小和尚道:‘门公公差人投书来了!’请问陛下,这宫中几个宦官姓门?”皇帝道:“只一个,乃是中常侍门公公!”行者道:“看来便是那厮一直在蒙骗陛下!”皇帝连连摆手,“你说门公公,打死寡人也不信!他对朕一直忠心耿耿!休乱猜疑,免得我君臣不和!”行者又好气又好笑,“陛下——”皇帝道:”孙长老休再说了。那门公公代寡人备晚斋供养几位圣憎,便在公公府上。见他时,还请孙长老慎言!”
行者想:“这皇帝如此昏庸,难怪能哄他这么久!也罢,待俺得了那阉人与假妖勾结照证,再来羞这老糊涂虫儿!”才要去中常侍府探寻破绽,又道:“老孙还有一事要陛下恩准!”皇帝道:“圣僧请讲!”行者道:“俺家丢失物品至今没下落,究竟伺时能还?”皇帝道:“我已吩咐大理寺卿捉拿盗贼。请圣僧稍候几日!”行者冷笑,“只伯寺卿下不了手!不如请陛下降一道旨,叫他把什么太师的长孙、寺卿的么子、尚书的侄子..先拿了去,打五十大板,叫他皮开肉绽。那公子哥儿捱不过皮肉之苦,自然招供。如此一来可擒获全部贼人,问他们抢劫、惊驾之罪,二亦可追回我家憎宝。”
皇后道:“孙圣僧说的是!那帮恶少被他们爹娘宠惯得无法无天,非老头子你下旨不可了!这般还可讨回咱家的一百两银子——那还是我的私房钱哩!”皇帝本已信门公公之言,听老婆这般说,又转过来了,道:“那帮纨绔子弟实在可恶!竟然不把寡人看在眼里,该拿该打!——孙长老,朕有意委你为钦差大臣,坐镇大理寺,拿犯追赃如何?”行者沉吟道:“俺却不得闲儿,不如让猪师弟代劳!”皇帝道:“是那位耙儿抡得好,却有些好色的长老?”行者笑道:“陛下如何知晓尸皇帝道出八戒与沙僧口角斗胜之事。
行者道:“这帮强人,却无一个裙钗在内,猪长老自然下得手!”
皇帝便书了一道手谕,差黄门官送到馆驿。那八戒本欲罢午斋的,捱不过饥虫钻心,正喝菜糊糊,闻旨,丢了碗,抹抹嘴,扛上耙儿,喜气洋洋辞别师父,在两位公公陪同下,登车赴大理寺做钦差大臣去了。
那行者此时也辞别皇帝,纵祥光来到门公公府邸,砰砰打门。一家丁开了门,却不认得行者,见行者面目凶狠,吓得要跑,叫行者揪住:“门公公在何处,快引老孙见他!”
家人惧他,只好引行者走,三转两拐,进一丽室:外间有锦榻绣枕,壁上嵌金,地下铺玉;又有梨花木隔山。内间传来吭吭哧哧声音。家人道:“老爷在里间出恭,请候片时!”行者见陈设如此富丽,哪儿信这是东厕!便一脚喘开二门.果见门公公正蹲在金铸便盆上解手。公公见行者气势汹汹,忙提上裤子,赔笑脸道:“不知孙神僧驾临,失敬,失敬!”便去外间,问行者来此有何见教?行者道:“听说公公要斋供贫憎,特来瞧瞧。怕的是公公也与陛下一样清贫,岂不难为公公了!”门公公笑道:“吾虽一身廉洁,两袖清风,不过圣上既吩咐下了,一餐饭还是备得起!”行者冷笑:“好个清廉官宦!连茅厕也同宫殿似的!”门公公毕竟老道,只打哈哈笑,笑过,忽道:
“孙神僧去南山金圣宫,可曾看见什么?”行者警觉道:“俺去南山,公公如何知晓?”门公公道:“是圣上告之下官的。”行者道:“老孙见那宫字前庭香火旺盛,还算清净,后庭却不甚干净!”门公公暗惊,道:“敢问神僧,是如何不干净?”行者笑道:“此乃天机,不可轻泄!——老孙告辞了,脯时再来打扰!”拱拱手,昂然出门去。却起在空中,隐了身,看门府有何动静。
行者走后,门公公连声骂:“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老子非灭了你不可!”便去书房,将适间写了一半的书信写完,封上,交给心腹家人,嘱他再赴南山投书。家人去了。行者便纵风跟上。马行得飞快,不消半个时辰,已至金圣梵宫。行者趁家人下马之际,仍变成一个“花大姐”叮在他肩上,径入方丈室,便有人传报进去,一霎,那和尚蹙着眉匆匆进来,展书简便看。
行者也轻悄飞起,落在和尚僧帽上,将书简觑个正清,原来上面写道:
东土四贼僧,节外生事端。
欲设鸿门宴,断肠草为剑!和尚阅后大喜:“那姓孙的弄神通走了,我正发愁!有此机会除他,真是天助我也!”便拿出鱼匙,令身边人去“延寿堂”取断肠草四株,须臾取来,写了回书,皆交来人。
那家人不敢停留,出山门上马便走。行了约五七里,忽听一声嗯哨,原是行者唤马用的——他做过粥马温,管过天马,至今马还听他的——那马闻唤便前蹄腾空,收敛后腿,转首看行者,却把马上的家人猛掀下来,跌个仰八又,头撞在硬地上,登时晕了。行者嘻嘻哈哈,上前在他身上搜出书简与断肠草,见书上写着:“附上断肠草,叫他东土贼僧心肝烂!公公事成后,与尔金圣梵宫共把盏!”行者大笑,“这厮白日做美梦哩!”将书信与毒草都收好、却去向阳山坡上寻了四株茅草嫩根,吹口仙气,变得与断肠草无异,又塞到家人怀里,纵云走了。
一会儿,家人苏醒,挣扎爬起来,见马在一旁啃枯草,气得狠抽了它儿鞭子,摸摸断肠草还在,只不见回书,前后寻了一回,也没寻着,无奈、只好上马赶回府中,将“断肠草”呈上。却不敢说实话,只道:“金铃圣未写回书。只道他晓得了,有事及时通风!”公公一时信了他,不放心别人,亲将“断肠草”熬了,屡入美酒中。
却道行者得了假妖回复门公公信简,又调换了断肠草,想着今宵有好戏看了,喜不自胜。起在半空,想回馆驿报喜,忽又挂牵八戒:不知那呆子做钦差做得如何?便拨云径去大理寺,降下云头、踏入大堂,却鸦雀无声。转入理事内堂,见呆子蹲在雕花椅子上,正与寺卿二少卿并太师的大孙子、寺卿的小儿子、兵部尚书的侄子、中常侍的外甥、司马的妹夫、司空的连襟、御史的内弟、府尹的表兄..围着偌大一张公事案子,飞献走著吃酒。相互拍肩摩膀,“哥”、“弟”乱叫。你一盏我一盅,好不酣畅!席前又肖几个妙龄女子吹拉弹唱,轻歌曼舞。行者大怒:“死呆子,真是狗肉上不了桌子!
俺保你为钦差,正事不干,却与钦犯称兄道弟、推杯换盏起来了!”八戒一骨碌滚下交椅:“哥哥来得正好!
先吃一杯!”那帮人也乖巧,便有人让座、斟酒、添箸。行者怒不可遏,掣出棒来,“叫你吃酒!”一挑将酒桌掀翻,上前便揪八戒。要知他如何收拾八戒,且看下回分解。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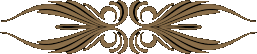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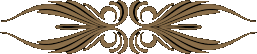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