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第二回 黄衫客一剑诛妖 红线女单身杀盗
|
|
话说黄衫客自飞云洞借土遁法来至混元湖边,湖中忽起大风,来一怪物,张口作浪,急举袍袖拂时,退他不得。看看逼近岸旁,黄衫客忙将两足一登,踏空而起,往下瞧看是何妖物。那怪已似觉察,昂起斗大头颅,两目灼灼,宛如两道金光,直冲霄汉。霎时间,忽又把头向水底一低,支咧咧大吼一声,涌起一阵急浪,足有数十丈高,向黄衫客直淹过来。黄衫客说声“不好”,在着空中使个大鹏展翅之势,滴溜溜向东南方旋了开去。这怪见仍旧淹不着他,又在水中昂起头来,把口对着黄衫客一张,喷出一股冷气,好似雪练般一条,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且此冷气之中,隐隐似有巨灵掌一般大的五个指爪,斜刺里向黄衫客抓来。黄衫客到此地步,暗想:“我因怜这妖魔,不知修炼几千百年始得在此混元湖中仙凡交界之处占穴而居,再数百年,功行到时未必难成正果,所以不忍伤害于他。如今这样肆恶,若再让时,深恐反遭不测。只不知他究竟是个水族中怎么东西,有此怪异,未可轻敌。”遂双手向空打一稽首,说一声:“上苍好生,不是偏我黄衫好杀,但今日水怪兴波,逼人太甚,不得不一开杀戒,愿为当世除妖。”说罢,伸手向袍袖中一招,飕的飞出一把剑来。但见一道寒光,向着那怪口中所喷冷气直冒过去,敌个正住。
其时,半空中恍如有两条白龙在那里厮斗,约有半个时辰,不分胜负,黄衫客见了大怒,起右手并着三个指头向那仙剑一指,口中喝一声:“捷!”说也奇怪,这剑起在空中打了三个盘旋,向那白气中直冲而进。那怪大惊,慌忙把口一闭,收回白气,又将四足向水面用力一伏,窜入波心而去,黄衫客焉肯容他,借着剑光护体,使一个寒鸦扑水之势,把身子往下一逼,跃入水中,紧紧追赶。那怪慌了手脚,只想凫水而逃,又恨被寒光逼住,不敢行动。黄衫客看看将近赶到,拼指向剑光连指数指,这剑望着那怪顶门直劈下来。那怪此时愈加着急,使一个鲤鱼攻水之势,掉转身躯挺着四足,向黄衫客狠命扑来。黄衫客微微一笑,喝声:“孽畜,休得猖獗!”即在丹田穴中运出一股气来,向着那怪一呵。此气乃是先天三昧真火蕴结而成,比着凡火有百倍之热。这怪怎能抵挡得住,顿时在水中缩做一团,动弹不得。黄衫客把手又向剑光一指,这剑直飞下来,将怪腰斩水中,分为两截,鲜血直冒,湖水变红。黄衫客十分过意不去,道声:“善哉,善哉。可惜尔数千百年修持,一旦化为乌有,皆尔不守正道,妄思图害生灵所致。”口说着话,把手扔将袍袖一扬,收回仙剑。因念怪虽斩了,奈在水中,看不出究竟是甚妖邪,十分利害,何不取上岸去瞧个仔细。遂一手提着一截,远远先自撩上岸去,然后将身透出水面,慢慢的踏波而行。果然仙家妙用,衣服冠履,毫无水迹沾濡。逮至到得岸边,定睛向此物看时,并非别的水怪,乃是一只极大白獭。牙长似戟,爪利于钩,身约丈余,毛浓寸许,自头至尾,一白如银,并无半点杂色。黄衫客暗忖道:“原来是这孽畜,怪不道方才口吐白气。那气中如有五个指爪,却是他驱鱼的长技。但白獭髓乃金创中第一圣药,不论如何血流皮破,只须合琥珀屑熬膏敷治,立刻便能止血生肌,将来且无一些斑点。《西阳杂俎》及《拾异记》中载:吴主孙和宠邓夫人,一日和醉,舞玉如意,误击夫人头角,额破血流。太医奏请以重金觅白獭髓和琥珀末敷治始痊,此是明证。惟调敷时因琥珀太多,以致脱痂之后留有一点血痕,殷红夺目,后人相传为獭髓妆,播作美谈。这是下药时铢两未称,乃至于此。否则色泽均匀,可以毫无破绽。况世传獭肝能治肝胃等疾,亦极神验。我今何不把他剖了取作药笼中物,留着医治世人,岂不大妙。”主意定了,甚是欢喜,探手袖中,取出仙剑,先把胸腹割开,取出肝来。大凡飞禽走兽的肝叶,本来皆一叶的,独有獭肝按月而生,一月一叶,此时正在三月,故有三叶之多。黄衫客即取湖水洗涤一过,再运丹田真气向肝连呵数回,把那水湿之气吸干,收入怀中豹皮囊内。又把足骨及头尾各骨敲开,倾出好些髓来,白腻如膏,也用先天真火炙干,一并收入囊中。余下的皮肉等物,依旧抛入水内,任他随波逐流而去。从此为混元湖除了一患,免得后来或有凡间甫经得道之人,欲渡此湖,被其吞噬,且免湖中水族伤残殆尽,其造福却也不小。
黄衫客既将白獭收拾已毕,把豹皮囊揣入怀中,藏好仙剑,起一个穴底擒龙之势,飞身下湖,用水遁法,不多一会渡过仙湖,早登彼岸。但见一片荒郊,绝无人迹,因仍驾着土遁,走有百里之遥,看看红日西沉,依然前不把村后不着店。黄衫客连夜趱程,也不稍歇,直走了一日一夜,不知经过几重恶岭,几道毒泉,始觉渐有人烟,到了登州地界。我且按下慢表。
再说那红线女,自驾金遁与黄衫客分途之后,他虽是往东南去的,却也要过混元湖而行。只因当初共工氏与颛顶争帝,共工头触不周山,天倾西北,地陷东南,后来虽得女蜗氏炼石补天,那地却未曾补得,所以混天湖的湖面东南方西北方有数十倍之大。红线女到得岸边,看见一片汪洋,茫无涯涘,欲使水遁之法,深恐湖面大了,未免费力,故把莲钩一蹬,起在半空,驾着半云半雾而过。俯视湖中,甚是风和浪静。惟西北角隐隐似有一道杀气直冲霄汉,正黄衫客剑斩白獭之时。红线女因急欲趱程,也不去仔细看他。及至渡过湖面,有五百余里沙漠之他,不但人迹不到,连鸟兽树木也是没有。直待过了此处,方见远远的有几点青山,却有大海阻隔。那山乃在大海之东,正是山东曹州境界。红线无心观玩,依旧纵起云光,片刻间过了海面,始慢慢的将身一晃,落下尘埃,款步而行。
其时已是申牌时分,大约又走有三五十里之遥,见有一座高山挡路。这山周围三百余里,共有三十六个高峰,一个个高插云表,所以名截云山,十分险恶。红线见了,心下踌躇。正想再纵云头越过此山,忽听得山凹里有一片哭喊之声,心下大疑,急忙将身一纵,来在一个小小峰头往下瞧看。但见来了一伙大盗,约有二三百人,为首的身长九尺,向外一张锅底脸儿,身穿元色绸软销,腰束黑绩战裙,头上边皂色幞头,足上穿一双元青缎扒山虎薄底快靴,两手提着两把泼风刀,押着一个愁眉泪眼的女子,过山绕道而去。红线暗忖道:“看这光景,分明是伙酒色强徒。但这女子,独自一人来此深山何事。若说他有同行亲属,或被强盗杀了,因何地上不见尸骸,好不令人难解。我今既到红尘,正要行些侠事,何不看个明白。若这女子果有冤情,何妨杀了强盗,救他下山。一来泄个不平,二来可与行人除害。”主意一决,跳下峰来,探手胸前,取出一个胡桃大小的剑丸,临风一晃,化作一道寒光,隐着身形,尾随群盗而去。
抄过了十数个峰头,便是山寨,约有一百余间房屋,也有是瓦盖的,也有是草编的。又转了两个山湾,方是大寨,共是九开间七进高厅,乃依山傍岭而成,所以一进高似一进。
那黑脸的盗,押着女子,直到第七进厅中。红线仍旧借着剑光隐在厅前屋檐之下,举目望厅上看时,只见正中间坐着一人,八尺以外身材,一张淡黄色脸,两道疙瘩眉,一双蜂目,颧高耳陷,口阔鼻低,腮下边一部短髭不到半寸,身披杏黄罩衫,内衬秋葵色短袄,头上戴一顶闹龙扎中,脑后双飘雉尾,腰间悬着一口三尺长的佩剑,足登粉底豹皮靴,分明是个盗首模样。回头,只见那黑脸盗先自上厅,说了几句言语,听不甚楚。这盗首便传女子进厅,高声问道:“看你小小年纪,倒有这般大胆,究竟姓甚名谁,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从实来说,或者免尔一死。”女子只是嘤嘤啜泣,绝不作声。盗首因冷笑道:“你纵不说,我也知道。你来的那一条路,除是往卧虎营去,别处不通,明明是在营中秦大人那里逃出来的。本来你年纪尚轻,貌也不错,可以收留在山。只是大人与我颇有交情,今虽被吴头目拿汝上山,还当着吴头目送汝到卧虎营去,听候大人发落。”这女子不听此言犹可,听了之时,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带泪骂一声:“狗强盗!原来与负国强徒往来。不幸我乍离虎穴,又入龙潭,也是命该如此,只苦的不知我父母生死若何。”话尚未完,看他抢上一步,将头向着盗首的腰间直撞过来,乘着势儿,双手找他佩剑,要想拼一个你死我活。盗首见了,哈哈大笑,喝一声:“贱人,休得无礼。众英雄何在!”猛见厅事两旁来了百数十个人,一个个手持刀械飞奔上来,黑脸的盗也在其内。红线此时再耐不住,将身一现,喊声:“女子休要惊慌,俺来与你杀这一班强徒。”一道剑光向大厅上直逼进来。黑脸盗见半空中飞下一人,好生惊骇。后见也是一个女子,济得甚事,提着泼风刀望红线面门劈来。红线喝一声:“止!”但见剑光一绕,这颗斗大的黑头顿时落地,鲜血直流。众盗见杀了同党,那肯干休,发一声喊,围将拢来。盗首也拔出佩剑,大喊:“何来泼妇,伤我弟兄,休要放他走了,倒了俺郝天彪一世威名。”红线心中暗想:“看此山寨,至少也有数百人,不能杀戮太多,有伤上天好生之德。谚言‘擒贼擒王’,不如先把那自称姓郝的盗首杀了,余盗略略示些儆戒,使他们弃邪归正,岂不是好。”因起三寸金莲,打一个着地扫儿,把群盗跌出丈外,伸手并着两个指头,向剑光连指两指,这光直逼郝天彪顶门而来。
那天彪是一个积盗,惯走江湖,见冷森森一道白光射来,晓得必是剑术十分利害,急将两腿一蹲,使个潜蚊出洞之势,向外飞奔。谁想这剑如生着眼睛一般,呼的一旋,飞也似的跟了出来。天彪大惊,要想回身窜入人丛,或可幸避,奈已不及,只得大叫一声:“我命休矣!”急起佩剑,使一个五花盖顶之势,拼命保住颈项。那晓得耳根后飕的一声,却被红线连剑连人斩于厅前地下。这把佩剑削成两段,落在血泊之中。也是郝天彪为盗半生,奸淫妇女杀害人民,造孽过多,故此只落得这般结果。众盗此时吓得一个个胆战心寒,面如上色,丢下枪刀,一溜烟多想往外逃命。谁知红线又起两个指头,向剑光团中略指一指,那剑望着众盗头上直砍下来,只得共叫一声:“饶命!”一线齐的跪地告求。
正是:蚁蝼尚然知惜命,为人焉有不贪生。
毕竟不知众强盗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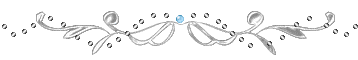
|
|
|
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本书由“云中孤雁”免费制作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