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第十一章 百变千容制群雄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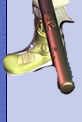 |
|
褚扬苦笑一下,道:“兄弟平生第一次狼狈逃命,好不惭愧!”李不净伸手推他们两人道:“快走,贫道独自留在此地对付就行啦!”
褚、裴二人想想唯有如此,当即分别驰走。李不净提心吊胆的在崖上空地走来走去。
大约过了一个更次,崖边冒起一道人影,落地现身,却是个全身黑衣娇小玲珑的女子,面目丑陋可怕!
李不净心想:“终于来啦!”打起精神,走过去稽首道:“姑娘能够在千仍峭壁上落自如,贫道便晓得不会认错人了!”那黑衣丑女怒声道:“他们呢?”李不净道:
“都趁机逃跑啦!贫道可不敢走开,等着把消息奉告诉姑娘。”
黑衣女子冷哼一声,大有瞧不起的意思,李不净心想你纵是瞧不起我,但为了褚扬的性命,只好逆来顺受。再者辛无痕向来以心肠冷酷,手段毒辣震惊天下,我可犯不着招惹你这等可怕的娘儿!
他故意用奉承的口气说道:“他们心眼坏得很,一个向溧阳逃走,一个向相反的路跑!姑娘赶紧追……”黑衣女子喝道:“住口,追不追是我自己的事!”李不净连忙道:
“姑娘说的是。”黑衣女子冷笑道:“嘿,褚胖子以为他有神行之术就可以逃得掉,简直是做梦,我让他先走十日也追得上他,你信不信?”
李不净不假思索,应道:“信!”黑衣女子道:“放屁,你凭什么相信?”李不净苦笑一下,道:“贫道当真不晓得!”黑衣女子道:“所以我说你是放屁,你听着,家母昔年威震天下,除了轻功武功举世无双之外,还擅长许多妙术;譬如水火不侵,上天入地,不饮不食等等,另外还有追踪绝技,哪怕你逃走了一二十日,仍然可以查出种种线索,路踪追赶。”
李不净初时被她斥喝得十分难过,这时却听得目瞪口呆,忘了心中的难过,道:
“追迹之学贫道也听人讲究过,但水火不侵,上天下地和不饮不食这些妙术,当真骇人听闻……”黑衣女子道:“若无这种种妙术,焉能使对方痛苦得宁愿自杀而死,你真是笨蛋一个!”
这黑衣女子接着又道:“走,我们一块儿去找裴淳算账,找过他之后,便轮到那胖子!”她从地上捡起一根细长木捧,说道:“这就是五异剑之一,你敢不听我的话,我不须对付你,只把此剑送给阴山剑派之人,你崆峒派人就别想活得成!”她把纫长木棒给李不净瞧看,李不净久闻五异剑之名,连忙接过,一按枢纽,杆端吐出一节又薄又长的锋刃,树木石头应剑穿裂,果然锋利无比。
他一生练剑,自然极是识货,这毒蛇信一人手,便已深悉此剑妙用纯在“阴柔毒恶”
四字之上,果然深合阴山剑派的路子。再者此剑落在别人手中毫无用处,也唯有阴山剑派之人才能凭仗此剑横行天下。
那阴山剑派向来最是仇视崆峒派,一则上代结有怨仇;二则两派剑法路数相克,先天上已有水火不容之势;三则崆峒派人才鼎盛,声名显赫,阴山剑派因而为之黯然无光。
这种种原因加在一起,阴山剑派便以打击崆峒嗣派为首要之务,崆峒派之人反而没有这等心思。
李不净向来傲啸江湖,如孤云野鹤,无拘无束,如今却被迫俯首听命于一个怪异女子,心中的难过也就不用提了!
他们一道上路,李不净正愁自己跟着这么一个丑陋奇异的女子赶路,势必使其人人侧目,幸好她一味捡荒村僻壤的路走,穿田度陌,或是翻山越岭,倒也很少碰得到行人。
黑衣女子宛如一团迷雾,李不净暗自这样的想,她的真正面目是不是像面具那么丑陋?她的武功有多高?她的性情如何?她找到了裴淳之时怎生对他?以后再找到褚扬时又如何对付他?她为何要自己跟着?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无法解答,但李不净却深知要知道了她的性情为人,这些问题便不难猜测出一个大概。
他们走得很快,而她似乎对长程远行之道特具专长,越走越快,却不是奔跑,瞧起来从容得很,李不净内伤不曾调治,只是仗精纯内功压制住,这时一段路走下来,便感不支,但他又不肯屡次在这女子面前示弱,一味咬紧牙关忍熬,到了下午时分,已经觉得难以支持。
她却越走越快,似乎可以走上一年半载也用不着休息吃喝,李不净见了更加感到难以抗拒这种无形的压力,意志大有崩溃之势。
他们经过一个村庄,李不净停步向人家讨了一碗茶喝,一转眼问,她已走得无影无踪,李不净喝完那碗茶,精神一振,又咬牙向前奔去,此时只剩下他孤身一人,因此不必装出英雄气概,步履之间大见蹒跚艰难。大约走了十余里路,陡然间一阵酒肉香味直扑鼻端,李不净虽是茹素戒荤之人,但这刻实在饿得急了,所以感到馋涎欲滴,转眼望去,只见一块山石后侧有片草地,一个衣衫槛楼鹑衣百结的中年乞丐正席地炊啖,一大包香喷喷的牛肉和一葫芦美酒,大喝大嚼。
李不净肚子咕噜叫得山响,不由得多望了两眼。那中年叫化招手道:“道爷,到这边来!”他的神情似是有话跟他说,而不是喊他饮酒食肉,李不净怀疑与那黑衣女子有关,便走过去。
叫化说道:“这个给你!”话声中抓起一块牛肉迎面掷去,李不净不知不觉的伸手接住,皱皱眉头,道:“贫道哪能饮酒食肉,老兄别开玩笑。”他见此丐掷牛肉之时手法迅快准确,猜他或者是丐帮好手。
叫化笑道:“一个人若是不吃饱了哪有气力办事?道爷何须拘泥小节?”他把葫芦一举,道:“此酒用药物泡过,专能行气活血,旧疾新伤一概能治,道爷来喝几口。”
这一番话大大的打动了李不净之心,暗想:“这酒若是有此灵效,正是我急需之物。”
但他又晓得自己的毛病,不禁再三踌躇。那叫化起身把葫芦送到他鼻子之下,一阵浓例的酒香直收入鼻,李不净咕一声吞口唾沫,伸手接住葫芦,向口中便倒。
他喝了─大口,但觉酒性极烈,微带辛辣之味,不觉叫一声“好酒”,再往口中倒去,叫化一手抓住,道;“道爷好大的酒量,但须得先吃点东西,不然立即就得醉倒。”
李不净道:“这话极是!”左手那块牛肉向嘴巴送去,堪堪入口,忽然停手,喃喃道:
“难道我数十载修为竟毁于一旦?”
他突然狼钡的丢掉牛肉,把葫芦塞在叫化手中,转身便走,那叫化十分惊愕的瞧着他,随即大声叫道:“道爷,你若是酒瘾发作,忍受不住,可以回转来……”
李不净一口气奔出数里,但觉胸口一团热气盘旋不散,鼻中不断闻到口里喷出的酒味,因此使得他没有片刻忘得掉那一葫芦陈年烈酒,又走了里许。这段路程中他三次停步,想转回去大喝一场。但最后仍然忍住了,一面走一面诅咒的道:“那叫化子定是魔鬼化身,故意拿美酒使我破戒犯誓,哼!他一眼就瞧得出我脏道人有酒瘾,这不是魔鬼是什么?”
又走了一程,到了一个乡镇。李不净见这许久都追不上那黑衣女子,暗念自己言出必践,答应过跟她一道去找裴淳,决不食言。不过目下既追她不上,反正是迟了,何不索性找个地方打坐休息,进点饮食,最要紧的是争取时间治疗内伤,能减轻一分就是一分,此念一决,便买了一些食物,寻到一间破庙,先吃饱了,然后打坐运功。两个时辰之后,天色已黑,李不净睁开双眼,烦躁地叹口气。原来这两个时辰的调息运功,只把真气调匀一点,但胸中那团酒热依旧不散,这使得他心神时时分散,老是感到有酒香朴鼻。
忽然一阵细碎步声向破庙走来,李不净大感惊讶,挪到角落一座石墩上坐着不动。
一个人悄悄入庙,香风阵阵,显然是个少艾女子,李不净初时还不偷看,但过了一会儿,突然嗅到浓烈酒香,还有杯盏碗筷之声,心中大奇,便悄悄窥瞧。
那女子已点燃起一根蜡烛,把她照得清清楚楚,却是个美貌少妇,身量丰腴,面庞圆润,眉目姣美,风情甚荡,她携来一个盒子,此时已从盒中取出两样菜肴和一壶酒,两个酒杯斟满了,杯边各压一双竹筷。
李不净自个儿摇摇头,付道:“这真是邪门得紧,她是谁?杯筷各有两份,等的是谁?这酒是什么地方的名产,如此浓冽,使人馋涎欲滴?”正在想时,忽听那美貌少妇低叹一声,自言自语道:“好狠心的冤家,今宵又失约不来,我只好又独斟独饮了,只是这漫漫长夜,孤枕寒裳的怎生捱得过去……”
她拿起酒杯,一饮而尽,举止之间,甚是放荡,大有空帏独守,难耐寂寞之意。
李不净心绪烦躁之中,骤然碰上此事,不由得心中怦然,脑海中胡思乱想起来,加以酒香扑鼻,把他肠中枯渴已久的酒虫都勾了出来,越发的难以忍熬。不住的问自己道:
“我要不要出去讨杯酒喝?
要是出去了,三杯落肚,面对着这个淫荡美妇,自然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要不要出去?”
那美貌少妇独自饮了几杯,扮颊一片酡红,神态举动更是放荡淫亵。李不净咬一咬牙,缓缓站起身子,那少妇星眼斜飘,见到道人,登时大喜道:“老天爷可怜我伶汀孤独,特地派遣道爷来陪我,道爷快过来喝一杯。”
李不净走出去,眼中光焰流动,伸手抓住她的手腕,就在她手中喝干了杯中之酒。
但觉酒性极烈,烫得肚子十分舒服,同时也勾起了体内另一种火焰。
她媚荡地格格笑道:“好道爷,再喝一杯……”另一只手拿起杯子,李不净也抓住她的手腕,一口吸干。此时,她双手都被李不净抓住,面面相对,她身上的脂粉香气,都扑送人李不净鼻中。
四只眼睛牢牢的对觑着,那美貌少妇一点也不怕他的欲火熊熊的眼光,两声脆响过处,她手中的两只酒杯一齐坠地,跌个粉碎。
这已是行动的时候,李不净缓慢地坚定地把她双手推向背后,以便把她整个抱住。
他的动作很慢,美貌少妇格格荡笑道:“你一定是老天派来安慰我的,不管你是人是鬼,我都甘心……”她甘心什么,无庸说出。
李不净淬然推开了她,口中喃喃道:“魔鬼……魔鬼……”原来她的话触动了他这个意念。须知玄门修真之士,专一讲究烧汞炼丹之道。在修待过程之中,每有幻象侵扰。
道行越高的,遭遇的幻景侵扰更加厉害。是以修真之土,时时刻刻警组戒惧于心,久而久之,定力自比常人深厚得多。
他一推开那美貌少妇,头也不回的奔出庙外,可是奔出不远,便停住脚步。回头一望,庙中烛光犹在,分明不是幻境。他暗暗对自己说道:“天下闻哪有这等离奇的遏合,这少妇一定是魔鬼化身,诱我败道……”想是这么想,可是脚下却不知不觉的向破庙走回去,不一会儿工夫,又回到破庙,并且见到那风情狂荡的美貌少妇。
然而李不净忽然停住脚步,只因那美貌少妇不但没有他预期中送抱投怀的表现,那对美眸中甚且射出冰冷严厉的光芒,这两道限光有如冰拄一般使得他腔中炽热全消,恢复了理智。
但他的肉体却与理智背道而驰,有一种煎熬狂放的冲动,催边他变成野兽。
他痛苦地哼一声,突然运聚真力,贯注掌上,举起来向自家天灵益拍落,掌势落处,半途被一只手拿挡住,原来是那美貌少妇以极快身法移到他身边,伸手架住,她冷冷道:
“喝下那边放着的一杯酒,就没事啦!”李不净本想一举拍碎天灵盖,免得身败名裂,这心意极是坚决,可是目下有了生机,登时软弱下来,过去拿起酒杯,心想这酒杯纵然盛着毒酒,我也不怕!
他一口喝干杯中之酒,发觉酒味与前不同,微带苦涩之味,喝下之后,顿时感到全身一片清凉,欲火尽消,他转眼一瞧。那美貌少妇已经不知去向。他顿足叹口气,忖道:
“我早该醒悟她就是那黑衣女子,唉!只怕午间的那个叫化也是她的化身,即使不是她本人,也是她的同伙无疑。”
想通了这一点,一则因自己曾丑态毕露而感到难为情。二则十分奇怪她为何要如此作弄自己?
这一夜他在破庙内歇宿,等了一夜,都不见那黑衣女子出现,他没有法子能够安睡,心中老大的一个疙瘩使他甚是不安。
直到第三日早上他赶到了溧阳城,在城门碰见了她,这才得知她何故作弄自己。她已改扮为一个男孩子,面貌丑陋,穿的也是黑衣,若不是她先行招呼,李不净根本就认不出来。
她说话时眼睛不大瞧人,流露出不屑的高傲神色,她开口就告诉李不净道:“我碰见了南奸商公直。”
李不净道:“他在哪里?这个人坏透了,姑娘小心别上他的当!”
她道:“我已经上过当啦!”李不净大为惊讶,道:“那么姑娘竞肯放过了他?”
她道:“其实他也坏不到哪儿去,以我瞧来,你们这些男人都差不多,一律视为猪狗也就是了!”
李不净想起前晚破庙中之事,面上一热,不敢做声,她又道:“待会儿你和病僧会合,替我办一件事。”李不净惊道:“病道友也在此地?”她白了一限,道:“自然是我叫他来的,哼!你们两人的定力不相上下,服了我的秘制药酒之后,便把持不住。我告诉你,目下你们虽是一切如常,但其实药力已深入骨髓之内,我只要施展独门手法,你们就立刻失去理智,到处出乖露丑,做出种种恶行,失去理性之时,谁也阻止你们不住,事后你们纵然自杀,可是臭名永远抹除不去。”
李不净背上沁出冷汗,心想原来那是她的圈套,今日这番话不知是真是假?如果当真,除非现在就自杀,否则就得服从她的命令,不得违背。
她两眼望天,又冷冷道:“我跟家慈姓氏,名字不必告诉你们,以后称呼时叫我黑姑便行了,你要不要知道我派你们去干什么事?”
李不净捏着一把冷汗,道:“还请黑姑示知!”辛黑姑道:“我派你们去杀死商公直!”李不净松口气,付道:“商公直虽是不易杀死,可是此事非是伤天害理,还可以服从,若是为非作歹,违背师门禁条之事,我势非立刻自战不可!”
辛黑姑挥动手中的细长木捧,又道:“这个人狡诈得紧,武功也极是高明,不过有你们两人联手合力,谅必可以取他性命!”她绝口不提自己上过什么当,李不净不便出言询问,只好唯唯答应。但料想商公直必定得罪了她,所以她才遣人取他性命。
辛黑姑想了一想,问道:“胡二麻子的武功怎样?”李不净不知病僧、裴淳等人在山洞内碰见胡二麻子之事,讶道:“哪一个胡二麻子?
可是数年前投入元廷领袖群凶的胡二麻于?”辛黑姑点点头,李不净道:“贫道未会过此人,可是听敝派长辈谈过,据说他的大力鹰爪功乃是武林一绝,以他的成就造诣,恐怕远在贫道之上!”辛黑姑道:“若是徒手拼斗,你果真远非其敌,不过你剑上功力不错,还是有得打的,我瞧这人算得上是一把好手,暂时就饶了他的狗命。”
说到这里,忽有三匹快马驰出城外,辛黑姑谈谈道:“来啦!可是已经过了期限,只怕是活不成了!”李不净问道:“哪一个来了?”
辛黑姑道:“裴淳!”接着简略的把朴国男所定期限之事说出。李不净登时忘了探问有关胡二麻子之事,说道:“黑姑对裴淳的生死可是袖手不理?”辛黑姑道:“我理他做甚?”
李不净没话好说,汕汕道:“虽然没有什么渊源瓜葛,但裴淳的武功人品却是当世稀有的,若是毁在朴日升手中,未免可惜!”
辛黑姑道:“可惜?哼!也不过像杀死一头猪一级罢了!”李不净忽然想到一个理由,赶快接口道:“姑娘因胡二麻于武功不错而饶了他的性命。裴淳武功不弱于胡二麻子,为何就不救他?”
辛黑姑仰面想了半天,道:“这话虽是有理,但朴日升势力很大,我包庇胡二麻于的性命已经会有麻烦,再去惹他的话……”她没有说下去,李不净只笑一笑,也不答腔。
她不悦地道:“怎么?难道你以为我怕朴日升?”李不净道:“贫道绝无此意,但姑娘既然免不了跟他交涉,再加上裴淳之事也没有什么!”
她摇摇头,突然凝神倾听了一下,道:“那三骑把裴淳的马车押回来啦!”
李不净却听不到一点声息,心中半信半疑。辛黑姑似是瞧透他心意,淡淡道:“我有天视地听之术,若是环境配合得好,远在于百里外的人事动态,了如指掌,若是环境配合不来,那就只比你们这类武林好手强胜三五倍而已!”
李不净被她唬得目瞪口呆,信也不是,不信也不是,正在心中琢磨推究之时,辛黑姑忍不住笑了几声,道:“这秘密告诉你也不妨,我的确练成天视地听之术,目力耳聪都比你们强得多,但千百里外的事物也不能察知,须得使用另一种天视地听之术,那就是奸细,不过在我来说,那只是我的耳目,不能叫他们做奸细,我把他们供给的资料凑起来研析一番,就可晓得远在千百里以外的事物和动态了。”
李不净却佩服地道:“这种手法,只怕化本身可以修练的功夫,还要难上无数倍,错非姑娘天聪明敏,思虑周详,换作别人,谁也布置不成这等耳目:”
辛黑姑听了心中大为受用,道:“不是我夸口,若是没有我的手段,哪里去找适合的耳目,比方朴日升的手下,哪一个不是武林高手,但步崧、彭逸都已变成我的耳目,如果没有我的手段,他们岂肯屈服?”
李不净再捧她几句之后,才问道:“姑娘知不知道朴日升怎生对付裴淳?”辛黑姑娘道:“详细还不晓得,但有一点可以确信的,那就是林日升为了云秋心之故,终必要杀死裴淳,他会使用种种手段磨折裴淳,以消心中之气,我相信裴淳不会一见朴日升的面就被他杀掉!”
李不净道:“贫道有个奇怪的想法,只不知姑娘可允我说出?”辛黑姑道:“左右闲着没事,你说吧!”李不净道:“要救裴淳性命,一点不难,只须姑娘准许商公直将功赎罪,责成他一定要搭救裴淳,以商公直的诡计多端,此事一定成功!”
辛黑姑却定睛望住他,好一会儿才恢复她原来高傲的态度,道:“此计甚佳,但我却十分奇怪一件事!”李不净道:“什么事?”辛黑姑道:“你本来要取裴淳性命,为何转变得这么快?病僧也是如此。”
李不净细心想了一会儿,道:“他具有一种大仁大义的气度,性情宽厚,从一些微小的言行和事情中可以察觉,使人不知不觉中生出敬佩爱护之心!”
辛黑姑道:“那就是说他用王道赢取人心,我则是用霸道手段,我倒要详细瞧瞧他性格为人,瞧瞧是不是足以值得你们佩服……”
正说之时,一辆马车远远驰来,前后护行的各有六骑之多,尘土高扬,不一会儿就到了城门。
李不净早已躲匿起来,辛黑姑则站在路边瞧热闹,马车从身边擦过,她手中的毒蛇信迅快一挥,随即转身走开。
路边有不少人瞧热闹,她乔装为男孩,因此谁也没有注意她,那辆马车驰到城门边,突然间一只后轮与车子分家,滚了开去,马车随即倾侧倒下。赶车的壮汉身手高明,在这等情况之下仍然勒住马匹才跃落地上。
车厢内钻出一个精灵的红衣喇嘛,紧接着便是裴淳出来。他跳落地上之时,不停的搓摩手腕,似是双腕被缚太久,感到麻木。
那个精灵的红衣喇嘛先向四周一扫,人人都感到好象是电光划过,一个劲装大汉上来禀报道:“轮铀是被极锋利的刀剑砍断的!”红衣喇嘛没有理他,伸手指住人丛中一个汉于,道:“朋友,请过来谈谈。”
那汉子面目黧黑,衣着甚佳,这时毫不迟疑的走到红衣喇嘛的面前,道:“大师有见教?”
红衣喇嘛面色一沉,冷冷道:“是谁弄的手脚?”
那人摇摇头,红衣喇嘛又道:“洒家晓得不是你,你还没有这等功力,到底是谁?”
那汉于又摇摇头,红衣喇嘛怒道:“你最好老老实实说出,反正不会是你们的帮主淳于靖所为,连他也办不到!”
裴淳这时惊异地打量那汉于,这才瞧出果然是丐帮中的一位八袋高手,那汉子也十分惊讶的望住红衣喇嘛,道:“大师眼力果然厉害,一眼就看出在下是丐帮弟于,当真不愧是密宗三太高手之一,这辆马车发生变故,在下也莫名其妙,所以才逗留不走,意欲看个明白。”
裴淳接口道:“古奇大师怎生得知此事非是这位大哥和淳于帮主所为?”
古奇喇嘛道:“车轮被毁之时,车子正在颠簸驶行,所以不曾察觉,但现在回想一下,果然有点异感,但以情理推论,在众目睽睽之下,斩断轮轴,而又不被旁人发觉,洒家也没有这等本领,所以知道决不是他们出的手,这人是谁?必定要查出才行。。
裴淳心中大喜,付道:“莫非是恩师他老人家得知我蒙难道厄,所以亲自前来搭救?”
但他立即转喜为愁,继续想道:“纵是恩师亲自前来也不行!他的本领自然胜得过古奇或札特,可是我今日遭的难不是武力能够解决,只要见到朴日升,我就得动手自则,恩师岂能让我做个背信食言之徒,因此连他也只好眼睁睁的瞧着我死!”
这时护行的一共十二骑劲装大汉已分散查看,但他们这刻哪里还能查出辛黑姑下落,即使见到了,也想不到这么一个孩子有如许本事。
他们纷纷归报古奇,这红衣喇嘛倒也大方得很,挥手命那丐帮高手回去。自己再细心勘查轮轴,并且下令先把马车拖到城墙下,让出道路。
他推究了好久,数骑自城内驰出,却是朴日升闻报亲自赶来,还带来了札特大喇嘛、金元山、步崧、金笛书生彭逸等一道。
他们谈论了一阵,仍然不得要领,札特独自过来跟裴淳说话。他道:“你超过十日期限才回来,已经输了性命,你英年天折,实在太可惜了!”裴淳道:“多蒙大师关怀,但这也无可奈何之事,在下这两日已经懒得多想了。”
札特大喇嘛道:“从车轮被毁之事,可见得有人暗中要搭救你:”
裴淳点头道:“在下也晓得,但天下谁也救我不得!”札特道:“这也不然,令师乃是中原第一等高手,他若是亲自出手,洒家自问毫无取胜把握。”
裴淳道:“家师最重信义二字,岂肯使我变成背信忘义之人?此所以我说天下无人救得了我!”札特点头道:“我们本来都疑惑是令师出手,但这样说来,可知决不是他。
然则放眼天下还有哪一个具有如此身手。那轮轴乃是以精钢特制,纵是宝刀也须用不少气力弄得断,除非是武功极高,擅用巧劲之士,还有利器在手……”他突然停口,裴淳也恍然的啊一声。
两人都猜到必是辛黑姑仗着毒蛇信使的手脚,札持顿时大为放心,过去告诉朴日升他们,裴淳却反而忧虑起来,付道:“这个人十分难缠,我若是当她搭救之时不肯逃走,激怒了她,只怕所有我识得之人都要遭她杀害!”
朴日升缓步走到他面前,道:“请问裴兄,那位夺去毒蛇信的黑衣姑娘高姓芳名?
是什么来历?”原来步、马二人脱困出来之后,马延已身负重伤,当时之事不大清楚。
步松则被辛黑姑慑服,奉命不得说出她的来历,所以朴国男这方面,只知有个武功高不可测的黑衣女子夺去毒蛇信,札特大喇嘛则因他的手铐被毁,所以深信那五异剑之一的毒蛇信真有所毁车轮之威。
裴淳肚中骂一声伪君子,口中应道:“在下也不晓得。”他的为人众所皆知,因此他说不晓得就是不晓得。朴日升沉声道:“她两度出手搭救你,想必渊源甚深,本人渴欲见识天下英雄,也颇想见一见名重武林的五异剑,今日若是把裴兄请到下处,这两个心愿谅必可以如愿。”
裴淳大声道:“在下曾有誓约,须得在国舅面前自杀,在下这就动手便是!”
朴日升反而吃一惊,道:“裴兄使不得!”裴淳道:“大丈夫岂能言而无信?”朴日升道:“此约是我们两人所定,我自然有权解决前约!”裴淳一怔,道:“那么我不用自杀了?”朴国舅道:“不错,但有一点却须得讲明白。你此去打听梁药王不肯出手救人之故,虽是有了答案,但是不是真的还未可知,倘若本人设法求见到辛老前辈,得知此讯不确,则裴兄仍然未达到使命甚为显明。”
裴淳不禁一楞,付道:“这话甚是,倘使此讯不确,自然是我输了。”于是大声道:
“国舅尽管去求证。若是不确,在下自当遵照约定自杀!”
朴日升道:“既是如此,便请裴兄移驾下处,以便听取消息。”于是大伙儿向城内走去。不一会儿回到府中,朴日升安排裴淳跟梁药王同院居住。一晃眼过了数日,裴淳和梁药王都不能出院门一步。幸而两人同院而居,还可以谈话消遣。
裴淳一点不晓得杨岚的情形,也没有丐帮的消息。现就是李师叔的安危,辛黑姑的用心,还有云秋心、薛飞光等人,都时时系念于心,却苦于没处打听。
这一日,朴日升忽然走到院中跟他们见面,裴淳一口气连问十多个问题,朴日升顾左右而言他,都不作答,只道:“本人派遣许多高手打听辛无痕前辈隐居之地,都不得要领,若是打听不出,裴兄找回来的答案无法证实,那就只好委屈两位在此处住一辈子!”
梁药王倒无所谓,但裴淳却大惊失色,一则永远丧失自由想想就够可怕。二则云秋心、李星桥的性命全凭梁药王打救,若是得不到辛无痕允许解除誓言,梁药王永不出手,他们岂不是死定?他对于自己生死还不怎样,但李星桥、云秋心两人的安危,却重要无比,当下自告奋勇的道:“倘若国舅信得过的话,在下出去设法打听打听。”
朴日升道:“裴兄既是自愿前往,那是最好不过的事。”当下讲明裴淳此去不论成功与否,都须在三日之内回来。裴淳踏出院门之时,但觉胸襟顿宽,十分舒畅,不禁联想到牢笼中的飞鸟,不能振翅高飞乃是何等痛苦!
他出了朴府,头也不回地向城外奔去。走过一条街道,忽然有个人转出来拦住去路。
这人身躯颇长,双眉如刀,隐隐透出一股杀气。
裴淳从未见过此人,不禁一怔。那人已经冷冷的道:“你是裴淳不是?”裴淳点点头,那人又道:“你害得我好苦……”裴淳讶道:“大哥贵姓?在下怎会害得你好苦?”
那人又道:“你一身功夫末失,为何自甘被囚在朴府之内,这不是害死人吗?”
裴淳越发莫名其妙,道:“在下与国舅有约在先,所以不能外出。
再说,那两位密宗高僧的武功十分高强,在下斗不过他们。”那人道:“放屁,你逃走就得啦,哪个教你跟他们挤命?还有什么约定不约定全是狗屁!”
裴淳见他十分气恼,心想犯不着惹他生气,便道:“好吧,算我说错了,大哥别生气。”
那人道:“放屁,我焉能不生气呢?除非你告诉我今日怎生出来?为的何事?”
裴淳肚中好笑,想道:“原来他为的此事,故意大发脾气。”他没有说出来,答道:
“好吧,反正这事也不怕别人晓得,我是去打听一位辛老前辈的住处下落。”
那人双眉一挑,更像是两把刀倒坚起来,道:“这一下又坑死我了!”裴淳讶道:
“大哥这话怎说?”那人道:“倘若你打听不出,那就要回到朴府中居住一辈子,假使你探听得出,我和称一齐没命。。
裴淳道:“前一说在下还听得懂,后一说则恕在下无法了悟。”
那人道:“你真是笨瓜一个,试想朴日升是何等心黑手辣之人,只要你探听得出那事,他一则无须再利用你,二则妒忌你的本事,连他也束手无策之事,你一下于就探听明白,他焉能不妒?有这两点原故,他非立刻杀死你不可!”
裴淳道:“大哥说得虽是有理,但在下还有两点不懂,一是大哥怎生猜得出人家心意?二是大哥为何也跟着在下一同送命?”
那人道:“除非像你这等蠢笨之人才猜不出来,至于我死不死,倒不劳你费心!”
裴淳心中微恼,倒不是为了他骂自己蠢笨,因为他压根儿就承认自己愚蠢,却是为了这人不肯坦白说出内情,而自己却一无隐瞒,所以着恼,当下道:“大哥请吧!你别问我,我也不问你!”
那人道:“好吧!我老实告诉称,有人命我非救你不可!因此如果你死了,我也难以活命!”裴淳越听越奇.道:“果真有这等事,那人想必是我的朋友了?”他道:
“不,是你的对头,终必也会杀死你!”
裴淳哈哈一笑,道:“大哥别逗我,我可不信你的话啦!”那人双眉皱起,露出愁容,道:“我没有骗你,真是千真万确之事。若不是这个命我救你之人,终必会杀死你,我决不设法搭救你的!”
裴淳这时又不懂了,道:“原来大哥想让那人取我性命?”
他摇头道:“谁杀死你都是一样。”
裴淳越发胡涂,但也懒得弄明白,当下道:“在下要走啦!”
那人又道:“我陪你去!”口气中好象裴淳决不会拒绝他一般,裴淳果真不好意思硬邦邦说不,只好举步走去,一面筹思拒绝之词。
不一会儿已走到城门,裴淳突然停步,惊讶地左顾右盼。那人道:“怎么啦?找谁?”
裴淳道:“我见不到一个熟人,所以十分奇怪!”
那人道:“哦!原来找穷家帮的人!他们已经迁到别处避祸去啦!”
裴淳讶道:“避祸?朴国男么?”
那人道:“可以说是,又可以说不是,总之,淳于靖这刻自身难保,哪有时间管你的闲事?”
裴淳凛然道:“别的人我不知道,但淳于大哥却是员重义气之人,不错,他一定遭遇大难,才没有派人与我联络。”
那人道:“那倒不是为了劫难临头之事,而是命我救你的人不准他们插手外事,随后穷家帮就发生事故,全帮迁到别处去了。”
裴淳膛目道:“你背后的人到底是谁?”那人骇一跳,极快的连转几转,裴淳失声笑道:“不是有人站在你背后,而是问说幕后命令你办事之人是谁?”
那人才舒一口大气道:“被你这傻瓜把我骇了一路,真真不值!”
斐淳突然叫道:“我知道了,定是那位黑衣姑娘无疑,只有她能够像她母亲一般使天下高手寒心丧胆……”他从这人转身的姿式速度中已瞧出乃是武林高手,所以才突然醇悟,那人低声道:“别嚷!别嚷!她说过不准我让你晓得她是谁的。”
裴淳真想对他说:倘若你不告诉我是谁,我就越发大声的叫嚷。
可是这种用别人害怕的隐私事来威胁人家,他实在做不出来。他踌躇一下,说道:
“请大哥别跟着我!”
那人道:“我陪你去查询那事,倘若查不出来,我就按照原定计策救你离府。如果查得出,我就要改变计策了。”他那双像刀也似的浓眉一直紧皱着,忧色难掩,显然不是说着玩的。
裴淳只好坦直说出心中疑虑,道:“我要去拜见几位老前辈,他们定必问我你是谁,我答不出来,他们一定很不高兴,认为我不该带了陌生的人同往。”
那人道:“有道理,但到时我自会应付,你一万个放心。”裴淳没奈何,只好继续走去,出得城外,沿着一条小河的河岸奔行,不久,已瞧见前面河岸一处高地上有座茅顶木屋,甚是简陋。
他们在木屋附近停步,裴淳寻思片刻,问道:“他们几位老人家耳朵都不大好,说话听不见,怎生是好?”
那人道:“用手势比划!”
裴淳道:“此事不易比划出来,你也是知道的。”
那人道:“若是比划不出,你就以笔墨传达。”
裴淳道:“那儿没有笔墨,为之奈何?”
他道:“这还不容易!你把平坦而微湿的泥地作纸,折根树技当笔。”
这一连串的问答之间毫无片刻停顿,不知内情之人,还以为他们早已编就了这番话,所以对答如流。
裴淳微微一笑,道:“你是商公直大哥,是不是?”那人做出摇头的动作,但只摇到一半就中止了,道:“你怎生知道的?”这话不啻是承认了,裴淳笑道:“只有你的才思如此敏捷,还有就是刚才你转身之时,小弟也瞧出一点儿端倪。”
那人道:“商公直身材肥胖,我却不是。”
裴淳道:“身材易改,面魏难变。不过你以前告诉过我你擅长化装易容之术,所以虽是样貌、身量都不相似,我仍然敢猜是你!”
那人直到此时才点头道:“不错,我就是商公直,现在我才知道你小事胡涂,大事不糊涂。”
裴淳道:“商大哥,你这一向可好?”
商公直道:“好个屁,单是一个你就足够气死我了!或者你宅心仁厚,真的有神灵呵护也说不定。”
裴淳心中明白他话中之意是说屡次三番都害他不死,当下笑道:“商大哥终于也碰上一个使你害伯的人了!”
商公直道:“那小妞儿当真厉害之极,我老奸虽有一肚子诡计,但怎样也甩不掉她的跟踪。我已是精擅易容之术的人,但她似乎比我还要高明……”
裴淳大感兴趣,道:“哦!你们较量过了!”
商公直道:“我们有一日碰上了,我竭尽所能,前后摇身变化七个完全不同的人,她却比我多变五种。但这还不足为异,因为她先天上就占了便宜,譬喻她能变作小丫头、美貌少妇、男童、样貌不同的少女等等,我却无法效步!”
裴淳道:“我明白了,她年纪轻,又是女孩子,所以能够如此,她也可以跟你一样变成老人老妇等等,但你却万万无法变为一个美貌的小姑娘!”
商公直嘲讽地笑一声,道:“聪明得很,果然是这样。但多变几样少变几样都无关紧要,最要命的是她有一种异于常人的观察力,我无论变化成何等样之人,她一眼就瞧破,而她的化装我却瞧不出,所以这回输得惨极,我任何诡计圈套都没有用,因为她一下于就找到我,怎样也躲不掉,所以我们只较量了一日,我就心寒胆落,无法抗拒她的命令了!”
裴淳万分同情地点头道:“这样厉害的人自然使人害怕,何况她的武功十分高明,那是我亲眼见识过的,连九州笑星褚扬大哥,崆峒李不净道长都远不是她的对手。”
商公直冲口道:“何止不是她的对手,瑰下李不净和病僧都得听她吩咐,前日他们联手对付我,险险把我杀死。那是奉了她的命令而来的,若不是她忽然出面阻止,我早就魂归地府了。”
裴淳万万想不到李不净、病僧这等侠士奇人也屈服在她手下,不觉惊讶得说不出话。
商公直一肚子的牢骚,对任何人都不敢讲,唯有这个裴淳最靠得住,所以尽情倾泄,他道:“那小姐儿的武功邪门得紧,尤其是轻功,只要有掩蔽之物,像茂密的山草或者夜色之下的树丛、房舍等,她就能够在你前后左右说话而你决无法发现她的身影,这等功夫真是天下罕见罕闻,我真是打心底不敢惹她!”
他满面俱是懊丧之态,裴淳好心地劝道:“商大哥最好不要多说,尝闻她的喜怒与世人不一样,若是被她听见,你就得有一顿生活好受啦!”
商公直道:“我何尝不知,所以只敢对你说说!”
裴淳道:“她化装之术既然比你还高明,万一变成我的模样,你岂不是上当?”
商公直那么老练刁滑之人,这刻也不由得面色大变,睁大双跟在他面上瞧来瞧去,满面谅恐的神色。裴淳笑道:“别怕,小弟是真的裴淳。”
商公直喃喃道:“难说得很,难说得很……”
裴淳道:“我骗称做什么?咱们一齐在潜山挖掘石坑的事,你还记得么?”他故意提起以前之事,好教商公直相信。
但商公直面色更加惨白惊骇,吶吶道:“那时候你已经出现过一次!”
裴淳莫明其妙地道:“什么一次,我们整天在一块儿!”
商公直却记起那一日见到自己的影子旁边多了一条人影,其时他已在李星桥持有的魔影子辛无痕的令符之前发过誓,所以惊得呆住,忽然感到有一样东西落在头上,抬头一望,恢复神智,迅即回头四瞧,二十丈之内,全是旷朗之地,哪有人踪?因此这条影子定必是魔影子辛无痕或她女儿辛黑姑无疑,她一直跟随着自己,自然晓得挖掘石坑之事。
他若是讲出这件事,并且其后冒险回转查看那一片草地有没有坑洞的用意也说不出来的话,裴淳便会晓得师父曾经命他填平那个土坑的用意了,而以裴淳的淳厚老实,不须几句话就会被商公直弄出真相。可是商公直焉敢再提那条影子之事,只是叹气道:
“罢了……罢了……”
裴淳还以为他已经相信了,便道:“我要去请问那三位老人家啦!”
商公直把心一横,忖道:“我总得瞧个水落石出,反正事到如今,躲也躲不掉的!
于是默然跟着他,一径走到木屋门前。”
只见屋内紧闭,裴淳恭恭敬敬的上去敲门,良久还没有回音。他陡地记起那三位老人家耳朵不行,便伸手推门。门扉应手而开,屋内杏无人迹,裴淳探头瞧了一遍,但见门角的水缸内筋水全无。他曾经替他们挑过一缸水,所以印象甚深,于是进去取起水缸,弃到河边盛满净水,回到屋内,放下水缸之时,忽见地上垫水缸的黑色石板上留有白色的字迹,定睛一看,上面写着的是“我们在金陵武定门外徐家祠”等寥寥数字。
裴淳把水缸放下,恰好盖住字迹。这个水缸甚是破旧,谁也不会动它,果然是秘密留言的好处所。
他也没有细究为何会留言石扳之故,奔出门外,只见商公直已恢复往日的形貌装饰,但面上的笑容却找不到。商公直道:“此处哪得有人居住?”
裴淳道:“原来是穷家三皓隐修之所。”
商公直面上愁云顿时一扫而光,仰天笑道:“原来你真的是裴淳。
裴淳讶道:“商大哥何以有此一说?”
商公直道:“刚才种种举止,除了伤裴淳之外,谁也假装不得,咱们在这儿等侯三皓便是。”
裴淳摇头道:“他们走啦!”
商公直讶道:“他们既然不在,为何又去打满水缸?”
裴淳正在考虑要不要讲出内情,商公直已接着又道:“我明白了,你天生就是这种敬老尊贤之人,不管他们在不在,你都照样服劳执役,我告诉你,他们自然不会在此,穷家帮已经迁回金陵老巢,那儿才是穷家帮创始之地,他们迁回去原不足奇,但据我所知,穷家帮另有重大隐情才会迂回元廷驻有重兵的金陵,这也不过是前几日之事,大概淳于靖自知无法解决,忧急之情溢于言表。”
裴淳讶道:“你跟淳于大哥很有交情么?”
商公直摇摇头道:“没有交情,我们还打了一架,那真是以命相挤,凶险无比!”
装淳更加不解,道:“你们既然不是朋友,他怎肯透露帮中秘密事?”
商公直道:“他没有透露,只是忧形于色,被我骗出一点口气,得知不但于他个人荣辱生死有关,更关系到穷家帮的前途,我老实告诉你吧,那天我是变成你的样貌去见他的,但数言之后,就吃他瞧出破绽,所以才拼斗了一场,尚幸我老奸擅长逃遁之术,不然的话,那穷家五老合围之势一成,我便遏不掉啦!”
裴淳摇头道:“商大哥你这就不对了,你可以作弄任何人,但淳于大哥率领穷家帮暗暗与元廷作对,主持武林公道,这等忠义之士,实在不该作弄!”
商公直听得一怔,道:“这一点我倒是从未想过,不错,天下间尽多供我戏弄之人,何必找到他头上?”
裴淳一点也不晓得这个天下闻名变色的“南奸”,平生不相信任何人,只有现在破例在别人面前赤裸裸的说出自己心意。也就是说,南奸商公直深心之中已确定裴淳是个忠厚正直之人,绝不会蜚长流短,撤弄是非,更不会暗箭伤人,所以在他面前,可以肆无忌惮的流露出心中真情。
裴淳满心欢喜的道:“好极了,你以后不再捉弄他也就是了,以前的事不必放在心上。”
商公直点点头,摹地屡悟过来,怒道:“我老奸做人行事还要你这笨瓜指教不成?
哼!我偏偏要跟自命忠义之士作对。”
裴淳楞了一下,“商大哥,你这又何苦呢?若是矮小弟说得不中听,把小弟教训一顿也就是了,千万不要那样做。”他竟是衷心相信商公直说的话,因此神态十分恳切,几乎近于哀求。
商公直忽发奇想,付道:“我老奸从来少有碰到这等实心眼之人,若说他真是那等愚笨吧!但从他以往的经历上却瞧得出颇有机智,若说他大智若愚,却也不能装得那么的真切,我因要瞧瞧他几时才露出真面目,说不定我老奸今日才碰上势均力敌的斗智对手……”
他越想越觉得这个推论极有道理,深深的注视裴淳一眼,决定以后凡事都以实为虚,只要裴淳不相信自己的话,立刻就会中计吃点苦头。
裴淳哪里得知商公直在这顷刻之间转了这许多的念头?当下道:“小弟这就赶往金陵,唉!可惜现下借不到那匹烟脂宝马!”
商公直心想此马刻下在朴日升手中,无人得知,须得想法子使他不向朴国舅打听,而仅仅向旁人打听此马下落才行,当下使用“以实为虚”的计策,说道:“你何不向朴日升借马?此马现下正是在他手中。”
他想裴淳一定不相信自己的话,便不会去询问朴日升,自然也就只向旁的人打听,这一来,他暂时决计询问不出胭脂宝马的下落。
裴淳点点头,道:“小弟正要回去见朴国舅,因为他限的三日之约太短了。”说时,举步向城内走去。
南奸商公直毫不相信裴淳当真会向朴日升借马,嘻嘻一笑,道:“咱们前路再见!”
说罢径自走了。
商公直健步如飞的从西门官道奔去,这条大道经南渡而折向北行,到句容、汤山才又折西直达金陵。他一口气奔出数十里路,看看已经快到南渡,忽听后面蹄声大作,回头一望,几乎把他气死。原来大道上一匹红马迅疾驰来,马上之人正是裴淳。
裴淳在他身边勒住马匹,道:“商大哥,咱们在金陵见面,恕小弟先走一步。”
商公直肚中直骂自己混蛋,只因穷家帮迁往金陵之事也是自己告诉他的,虽然此事他也可以从朴日升口中打听出来,但裴淳未必就愿意向朴日升打听,以致泄露了行踪机密。
他气得半死地挥手道:“滚你的,我到金陵干什么?”
裴淳一点都不生气,讶道:“那么商大哥打算到什么地方?”
商公直没有好气的随口应道:“我到镇江去……”话一出口,才发觉这话正合“以实为虚,以真作假”的计策。只因那辛黑姑当真说过命他到镇江见面的话。不过此约尚在数日之后,当然他可以先到镇江等侯辛黑姑。
裴淳道:“镇江地方不小,小弟怎生找得到商大哥?”
商公直甚觉奇怪,付道:“你我我干什么?”他越是猜测不透,就越发不肯询问或是露出线毫意思,口中应道:“我投宿在最近西门的客栈之内,你一找就着!”
裴淳道:“是!”举手作别之后,随即纵马驰行,他心中最焦虑的是淳于帮主遭遇危难之事,恨不得插翅赶到金陵。胭脂宝马脚程实在不下于飞鸟,有时候碰到车马阻路,无法疾行之时,往往凌空跃去,飞渡数尺,路人惊视之时,它已经驰去老远。
话休联絮。当日傍晚之际,裴淳已到达金陵地面,那胭脂宝马虽是遍身大汗,但更见神骏雄健,裴淳此时已不须急驰,便缓辔徐行,入得城中,已是万家灯火之时,他找个客栈歇下,询知武定门在城南,于是沫浴更衣,草草用过晚膳,走出店外,天色全黑,街上店铺多半关门安歇了。
他心中琢磨城门已闭,四关都驻有重兵,碰上了这些铁骑,轻则受一场闲气,重则有性命之虞,自然他决计不会被军士杀死,可是那一来全城之人都遭殃。所以他只在大街上走动,并不急于出城拜见穷家三皓。
走了一会儿,忽然有人轻拍肩头,沉声道:“不要回头,放慢脚步,待我前面带路,等到我掉了手中之物,弯腰捡拾之时,你瞧我身躯向哪一边弯,就往哪边走,其时恕我不再引路,人巷之后第三家便是了。”
这人说罢便掠越到前面引路,裴淳瞧时,只是个外表极普通之人,若不是留了心细瞧,实在看不出有丝毫特别,这刻细加注视之下,却隐隐瞧出这人体格坚实有力。
此人的身份来历与及如此诡秘的安排,可教裴淳猜不出一点头绪来,起初裴淳紧紧跟着他走,走了不远,那人头也不回的低声道:“别跟得太紧,明眼人会瞧得出破绽的。”
语调急促,大有紧张之意。
裴淳只好坠后,距离那人背影约有三四丈远。他虽是想不出那人奉谁之命来引路,却悟出自己今日抵达金陵,一定已有别人晓得,而这些人会跟踪着他,所以那个引路之人才如此的紧张和诡秘,他灵机一动,走到适当的地点时,突然间闪人一条小巷之内。
小巷内一边是屋宇,另一边却是花园的围墙,裴淳纵身跳过围墙,贴立墙根,凝神倾听。果然片刻间一阵轻微的步声在巷口徘徊,接着便向巷内奔去。
此时天色已黑,相隔得远就不易瞧得明白。裴淳连忙跃起伸手扣住墙头,只露出一对眼睛循声望去,但见一道人影很快地向巷内奔入,一瞥之下,瞧出那人一身劲装疾服,手中有个长形包裹,似是兵器。
从装束上可瞧不出此人底细,裴淳正要趁机出巷,忽然有悟于心,暂时隐伏不动。
过了片刻,那个劲装汉子从巷底奔回来,裴淳觅准时机,蓦地扑出去,人未到指力先及,但听指风破空哧的一声,那人一声没哼,向前便倒。裴淳不待他倒下,已飘落他身边,伸手扶住。
只见这汉子面目陌生,因是侧身垂头靠在裴淳手臂上,所以瞧见他耳后到颈部有一道长形疤痕。裴淳把他放在地上,摆布成靠墙而坐的姿势。取过长形包裹,抖开一瞧,却是一柄两尺半长的尖刀,刀柄上缠着银丝。
他从兵器上查不出一点线索眉目,便又跃回墙后。过了好一会儿工夫,巷口有人低声道:“你怎么啦?点子呢?”问过之后,见对方不答话,奔到他面前,低头查看,裴淳无声息的从墙头冒起大半截身子,运聚指力向那人颈后的大椎穴隔空点去,哧的微响一声,那人登时扑倒。
他觉得非常的满意,飘落地上,一瞧那人也不认识,却感到此人满面剽悍之气充满眉宇之间,这股神情好象有点熟悉。此时他断定已没有跟踪之人,所以赶快奔出巷外,四下一望,附近虽是还有人走动,可是似乎都是良民百姓。他循原先方向奔去,走到街道岔分之处,不禁踌躇回望。只见黑暗的转角处有个人站着不动,这刻从黑暗中走出,一言不发向前行去。裴淳真想上去跟他说一说刚才的事,但终于没有这样做。
两人一前一后弯弯曲曲的走了一程,那人突然弯低身子捡拾掉落之物,拾起之后迅快地走了,裴淳回头查看了一会儿,确定没有人跟踪,才奔出去,迅速转入巷内。
第三家大门紧紧闭着,他敲动门环,竞没有人出应,裴淳腾身越门而入,但觉里面一片漆黑寂静,似是无人居住。
这时,裴淳不知不觉涌起满腔戒备之心,付道:“这个引路之人身份不明,若是有人布下陷阱,诱我人瓮那才冤枉呢!”于是提功聚力往前探索。
这座屋字甚是深邃,走人第三进之时,与外间声息完全隔住,万籁俱寂,宽大的堂屋内没有灯火,黑暗无比,略略一站,便要举步奔到别处。角落里突然传出语声,道:
“我们候驾已久,难道连话都不讲一句就离开吗?”
裴淳向那角落望去,只见黑漆漆一片,什么都瞧不见。当下道:“阁下是哪一位?”
另一边的角落中传出口音不同的话声,道:“他是黑狱中的游魂……”这个人说话口音比第一个人似乎更加平和没有火气,但语调却很认真,全无调侃玩笑之意。
裴淳讶道:“他是黑狱游魂?你呢?”
另一个角落中又传出第三个人的话声,道:“他也是黑狱游魂,唉!”此人语声甚是熟悉,裴淳怔了一怔,蓦地想起来,道:“你……你不是先前带我来的人么?”
此人默然不应,但别人答道:“不错,就是他了。此屋之中除了你之外,我们四人都是黑狱游魂,当真是可悲可叹……”这个说话之人语气铿锵震耳,内力之深厚强劲,竞掩饰不住!
裴淳惊道;“四位游魂大哥召我来此,不知有何贵干?若是在下能够办得到的事,便请明言。”
第一个人开口道:“我等果然是有事相求。”
裴淳道:“不敢当得相求二字,诸位尽管吩咐。”
第二个人道:“黑狱之中毫无欢趣,唉!”
裴淳大惊忖道:“他们一直悲叹黑狱之苦,这回叫我到此,定与黑狱之事有关无疑……”
第三个人说道:“且休提黑狱之事,小裴淳在等着呢!”他口中这句“小裴淳”大有亲热之意,教裴淳泛起受宠若惊的感觉。
第四个人道:“要说快说,咱们都所剽无多啦!”
|
|
|
|
本书由"云中孤雁"免费制作;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