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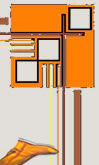 |
 |
|
 |
 |
|
第十五章 真情难得抛红豆 奸诈有心布疑兵
|
|
韦小宝大马金刀,坐在江宁织造曹寅的客厅里,却有一个仆人走了进来,躬身道:“韦爵爷,我家老爷请书房里见。”
达官贵人之中,请客人书房里相见,原本是尊重客人的意思。
韦小宝心里却是大怒,暗骂道:“他奶奶的,曹大花脸好大的臭架子!与老子的品级差了十七二十八截,不拿了手本,站立道边,口报履历,恭迎本爵爷大驾光临,倒是这般作威作福。”
曹寅在书房的门口迎接韦小宝,只是打千道:“卑职参见韦爵爷。”
韦小宝笑嘻嘻的,道:“曹大人,你好啊?”
心里却道:“曹大花脸,你好大的胆子!”
曹寅的书房陈设得极是雅致,一架一架的古书,摆满了四壁。间或点缀着一二幅字画、一二件古玩,粗疏而不流于俗气。
韦小宝心道:“辣块妈妈,曹大花脸的书倒是比老子公爵府的书还要多,大约他也与老子一样,书认得他,他不认得书,装装门面罢。”
曹寅正在赏玩吴道子的一幅画,显是意犹未尽,让座之后,竟将韦小宝引为知音,道:
“韦爵爷,吴道子的佛、道人物,真正登峰造极。你请看,笔迹洒落,势状雄峻,点画之间,时见缺落,有笔不周而意周之妙。诚如苏东坡所言:‘画至吴道子,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手拈胡须,摇头晃脑,哪里是一个武林高手,分明是一个酸儒。
曹寅看到韦小宝一派茫然的神色,不由得心里哑然失笑:“对这等小流氓小无赖奢谈吴道子,老夫不是对牛弹琴么?”
曹寅歉然一笑,道:“韦爵爷甚么不知道?卑职这样夸夸其谈,可谓班门弄斧了。”
韦小宝一惊,付道:“‘关门弄虎’?他奶奶的,曹大花脸要破罐子破摔。乖乖隆的冬,猪油炒大葱,在你曹大花脸面前,老子又是甚么虎了?你再关起门来,不是成了瓮中捉鳖么?”
韦小宝极喜成语,十之八九却是错的,只有“瓮中捉鳖”说得对了。却又常常用在自己身上。
他这样一想,心中倒也忌忡、口气便和缓了,笑道:“曹大人,我察看水情,路过这坐,想着我们俩交情不浅,特意来看看你。”
曹寅忙里偷闲,好不容易有个欣赏名画的空儿,这点雅兴却被韦小宝打断了。面上便有些不豫,恭敬但又淡然地应酬道:“多谢韦爵爷关心。”
韦小宝看出了曹寅是虚与委蛇,心道:“看不起老子么?老子且吓他一一吓。”
便笑道:“不值甚么。曹大人,还有几个朋友向你问好呢!”
曹寅顺口道:“谁啊?”
韦小主板着指头,道,“我师父独臂神尼九难师太,我义弟霹雳掌于阿大,天地会的兄弟玄贞道长他们。还有我的几个不成器的老婆,本来都想来拜访曹大人,我说,织造府何等的威势,是官府衙门,诸位江湖人物下去也罢,他们才听了我的劝。”
在微山岛,曹寅亲眼看到韦小宝说的这一伙人如何地回护于他。心道:“这人说话不尽不实,大不可靠,不过也不得不防。”
曹寅曾亲手与九难师大动手过招,也亲耳领教过于阿大的“狮子吼”神功,这些人若是真的来寻仇,倒是极难应付的。
曹寅笑道:“曹某好大的面子哪!”
韦小宝道:“我说:‘这点儿小事,兴甚么师。动甚么众?我与曹大老爷极有交情,这点面子,他一定会给的。’曹大人,你说是么?”
曹寅道:“韦爵爷的吩咐,卑职定当照办的。不知是甚么事?”
韦小宝慢吞吞道:“我师父九难师太道:‘小宝,如果姓曹的不给面子,你也不必客气。哼哼,他那七成不到、六成多些的大成掌。比起你师父的铁剑门神功,却是差了十七二十八截。他若不服,你便叫他来与我比试比试。’曹大人,这可是我师父她老人家说的,与我可没有干系。”
曹寅鼻孔里“哼”了一声。
韦小主又道:“我的一个老婆是建宁公主,一把揪住了我的耳朵——他奶奶的,她仗着是皇上的妹子,金技王叶,没上没下,常常揪了老子的耳朵说话,不是太过目无长上了么—
—道:‘夫婿,你去告诉那个曹大花脸,乖乖儿的听话罢。若是他不听话,本公主与她到皇帝哥哥面前打官司。’曹大人,他是女流之辈,你也不必与她一般见识。”
曹寅心道:“九难师太武功虽然高强,也奈何不了我,可建宁公主是皇上的妹子,若是胡搅蛮缠,倒是无可奈何了。”
曹寅赔笑道:“公主说笑话了。”
韦小主一番胡说八道,镇住了曹寅,这才轻描淡写道:“曹大人,听说你近日买了个女子?”
曹寅面孔一红,尴尬道:“韦爵爷的消息真是灵通得紧哪。”
韦小宝没想到事情如此简单,一个敲山镇虎,便将老好巨猾的曹大花脸的实话吓唬出来了。
他顿时得意之极,笑道:“我韦小宝没别的能耐,独独在女人身上……”
曹府的一个丫餐进来倒茶,曹寅赶紧咳了一声,打断了韦小宝的话,道:“韦爵爷,请用茶。”待得丫蟹退了出去,曹寅特地关了门,压低了声音,道:“韦爵爷。
卑职不明白你的意思。”
韦小宝道:“哼,你明白得紧哪!”
曹寅想了想,沉声道:“好,既是韦爵爷问到了,卑职也不能不说。是的,卑职是买了个女子。”
韦小宝慢慢道:“是从盐枭手里买的么?”
曹寅道:“大人明鉴。”
韦小宝又问道:“那女子叫双儿,对么?”
曹寅惊诧道:“韦爵爷,你,你甚么都知道了?”
韦小宝掩饰不住得意心情,翘起二郎腿,双眼望天,道:“若是一般平常的女子呢,我也不会来打扰曹大人,只是这女子大有来历……”
说到这里,却又住了口。
曹寅道:“卑职愚鲁,还请韦爵爷明示。”
韦小宝道:“也不用明示、暗示了,咱们打开窗子说亮话罢。双儿不是等闲之人,她是大有来头、大有身份之人。总而言之,她与我师父九难师太、我义弟于阿大、我老婆建宁公主、我大舅子当今皇上,还有神龙教长胡子洪安通教主、丐帮痨病鬼小叫花郑义虎、藏头露尾的黄龙大侠、天地会的玄贞道长……都是大有干系,大有渊源。”
韦小宝信口胡扯,云天雾地。
曹寅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道:“那双儿也就是寻常女子,怎能,怎能……”
韦小宝不耐烦道:“看样子对我说的话,曹大人一定不信啊是不是?你就去一个个地打听去,看我说的是真是假?”
曹寅心道:“你拿了这许多大有来头的人压我,我却哪里打听去?不过,这小流氓虽说一贯地胡说八道,今日找上门来,只怕确实知道了一些蛛丝马迹,倒是不可不防的。”
曹寅为人把细,便赔笑道:“韦爵爷的话,哪能有假?
不说那些人了,就是韦爵爷大驾亲临,卑职也得伺候才是。”
韦小宝道:“你明白就好,赶快交人罢。”
曹寅道:“是,是,卑职这就带了韦爵爷去。”
韦小宝道:“双儿难道不在这里么?”
曹寅忽然如孩童一般面呈忸怩之态,虽在书房之中。
还是四处张望了一下,才低声道:“韦爵爷也不是外人,实不相瞒,家慈规矩极严,而且不时有河东狮吼,卑职实在是……实在是……”
韦小宝心道:“家慈不知是块甚么瓷?河东狮也不知是只甚么狮?将曹大花脸吓成这个样儿,总之是极厉害的瓷、极厉害的狮子。”
韦小宝故意放高了声音,道:“既是有厉害的‘家瓷’、厉害的‘河东狮’,你就不该买人家的女子才是啊?
弄得娘家人找上门来,你怎么说?”
曹寅连连作揖道:“大人低声,大人低声。”
韦小宝大乐:“曹大花脸既是怕了一块瓷、一只狮子,有柄的烧饼老子攥着了,便不怕他,便甚么甚么之中,甚么千里之外。”
韦小宝道:“要我低声,那也容易,你老实告诉我,你将双儿藏在哪里了?”
曹寅颞颥道:“在杏花楼。”
韦小宝奇道:“你将她藏在那里做甚么啊?”
曹寅道:“卑职将她纳做了小星。”
韦小宝生在妓院,常见到有阔佬花了银子为婊子赎身,是以对“小星”这个词儿倒是懂得的。
他顿觉大事不妙,道:“辣块妈妈不开花,你拿双儿做了小老婆了?”
曹寅一迭连声道:“卑职没出息,卑职没出息。”
韦小宝大惊,道:“你,你办事了么?”
曹寅点点头,觉得不妥,问道:“韦爵爷,双儿她到底是……”
韦小宝忽然跳了起来,大骂道:“你奶奶的曹大花脸!
你色胆包天,敢在老虎头上拍苍蝇,叫老子做了货真价实、有假包换的乌龟王八,老子不叫你曹家戴上十七二十八顶绿帽子,老子便不姓韦,跟你姓,叫曹大乌龟,曹大王八!”
曹家虽是武人,但又生在书香人家,哪里待见在自己的家里,被人如泼皮无赖般这等辱骂?那张脸,已自气得紫红了。
然而官制所关,只得跪倒连连叩头,道:“大人息怒,大人息怒。”
韦小宝骂不绝口,道:“息你奶奶的怒!辣块妈妈不开花,老子将你变成一只活乌龟,变成一只活王八,你能息怒么?”
曹寅只是叩头,不敢吭声。
韦小宝提起脚来,想朝曹寅的屁股上踹上一脚,可想到对方的武功实在高强,虽说他不敢还手,暗中使内力反击过来,自己的腿只怕是折了,犹豫了一下,便没有踹下去。
韦小宝喝道:“还不快领老子去见双儿么!”
三拐两拐,曹寅领着韦小宝进了杏花楼。那地方极为隐秘,显是曹寅怕极了家中的“那块瓷”、那只“河东狮”了。
曹寅对丫头、老妈子挥了挥手,带着韦小宝轻轻地上了楼。
就见一个淡妆女子,临窗轻弹琵琶。那背影不是双儿,却又是谁?
那曲子似幽似怨,如位如诉,却是韦小宝在云南的时候,在陈圆圆修行的尼姑庵里,亲耳听得陈圆圆弹唱过的,叫《圆圆曲》。
韦小宝心道:“双儿还会弹小曲儿么?”
韦小宝继而醋意大发,暗暗骂道:“他奶奶的双儿小婊子,在老子面前假正经,连十八摸也不唱,倒在奸夫眼前弹甚么圆圆曲、方方曲的!老子却是看不惯这等作张作势的臭作派!”
曹寅此时声音竟是异常轻柔,道:“双儿,有老朋友看你来了。”
双儿“嗯”了一声,道:“谁啊?”
韦小宝冷笑道:“你亲夫捉——”
双儿口转身来,韦小宝忽然住了嘴。
眼前,是一个十六八岁的少女,哪里是自己的亲亲好老婆双儿?
双儿却连正眼也不着韦小宝,笑盈盈地对曹寅道:“老爷,你来了?”
韦小宝道:“曹大……老爷,她就是双儿么?”
曹寅道:“是啊。”
韦小宝道:“从盐枭的手里买来的双儿?”
曹寅道,“是啊。”
韦小宝忽然哈哈大笑,道:“他奶奶的,我说你曹大人是个极重义气、够朋友的好汉,怎的能叫好朋友戴绿帽子、做乌龟王八?老子的眼光果然没错。曹大人,你果真是一句话值一千两金子,人无信站不起来。兄弟佩服,佩服!”
曹寅一怔,暗道:“甚么叫‘一句话值一千两金子,人无信站不起来’啊?”
韦小主却又道:“小花娘果然美貌,那个落鱼沉雁,那个闭花羞月……不过曹大人。你既是贪花好色,便大大方方的,躲躲藏藏的不是大也委屈了双儿姑娘了么?至于你家里那块厉害之极的瓷啊,还有厉害之极的河东狮啊,交给我来对付。咱们好朋友讲义气,理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曹寅被韦小宝的话弄得糊里糊涂,只得答应了一声“是”。
韦小宝却已拱手道:“兄弟告辞了。”
曹寅道:“韦爵爷……”
韦小宝抢过话头,道:“咱们后会有期。”
说着,竟然施展“神行百变”的功夫,如飞而去,像是怕曹寅捉住一一般。
片刻之间,韦小宝己然来到了大街上,犹自暗笑不止:“老子忒也糊涂得紧,将人家的小老婆认做自己的老婆了,他奶奶的,盐枭的人贩子忒也可恶,卖了一个双儿,又卖了一个双儿。”
看看曹寅并没有追来,不禁自呜得意:“幸亏老子有急智。将曹大花脸糊弄住了。若是他当真起来,计较老子一个诬良为盗的罪,老子倒是有口难辩……又怕甚么了?他倘若真的闹起来,老子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到他家里去,将他家那块极厉害的瓷、那只极厉害的狮子都挑斗起来,大伙儿一拍两散,曹大花脸只怕要退避三舍。
退避六舍了。”
却又百思不得其解:“家慈是块甚么瓷?河东狮是只甚么狮?曹大花脸这样怕了他们?”
韦小宝胡思乱想,自言自语,一抬头,却来到了一座尼姑庵前。
这尼姑庵不大,极是清雅,庵前凡株修竹,极是青翠。老梅横枝,虽是花期早过,然而嫩叶疏落有致,却是另一番情致。
韦小宝粗俗之极,哪里懂得欣赏美景?心中只是奇怪:“这闹市之中,哪里来的一个庵堂?”
又忖道:“天下尼姑是一家,我师父九难师太便住在庵里也说不定。师父对双儿极好,她老人家若是出手寻访双儿,定是马到成功。他奶奶的,这世道太也不成话,老子没了帮手,甚么事也做不成了。”
“韦小宝信步朝庵里走去,却被一个妙龄尼姑合掌挡住:“施主请留步。”
那尼姑也就二十出头,生得眉清目秀,一袭缁衣,虽是宽大,却包裹不住窈窕身材;不施脂粉,更掩饰不了天生丽质。
韦小宝心道:“小花娘俊俏得紧,做甚么尼姑了?若是在扬州我妈妈的丽春院里,一定是嫖客盈门,生意好得紧的。”
韦小宝一双眼睛贼兮兮的,笑嘻嘻他说道:“师妹你好啊?”
尼姑俏脸一红,暗道:“此人无聊之极,素不相识,却又是甚么师兄、师妹了?”
闹市之中,毕竟不是山野之地,那妙龄尼姑见到的泼皮无赖多了,合什道:“施主,万寿庵是家庙。不能请施主随喜,请施主见谅。”
韦小宝道:“这里叫万寿庵么?是谁的家庙啊?”
尼姑道:“江宁织造曹府。”
韦小宝一怔:“曹大花脸?他奶奶的,老子前生作孽,走到哪里都见到大花脸奸臣。”
韦小宝对尼姑道:“师妹,我与你说,我与曹家是数十年的交情,便是那曹大……老爷亲自来,也要请我去庵里随喜的。”
尼姑抿嘴而笑,道:“你有几岁年纪了,能与曹大老爷有数十年的交情?”
浅笑之间,面颊如花。
韦小宝心里痒痒难忍,笑道:“这个么,却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师妹,你请你师兄进去,师兄慢慢地将其中原委说与你,好不好啊?”
尼姑俏脸一板,道:“你这人好生没趣,甚么师甚么师甚么的?请便罢。”
说着,便要关门。
韦小宝身形一晃,人已进了院子,笑道:“来呀,你能捉住我么?”
尼姑急得要哭,只得跺脚。
正在这时,庵门竹帘儿一挑,一个孩童走了出来,道:“妙玉,你和谁说话啊?”
那孩童七八岁年纪,生得面红齿白,粉装玉琢,淡雅的月白衣衫,脖子上戴着金项圈儿。容貌、打扮,胜似女孩儿。
韦小宝眼睛一亮:“这不是曹大花脸的孙子曹小花脸,叫甚么曹雪芹的么?我说这妙玉尼姑怎么高低不让老子进去,原来屋里藏着个小花脸呢。他奶奶的,甚么好东西了?”
韦小宝顿时眉开眼笑,去拉曹雪芹的手,道:“芹哥儿,还认识我么?”
曹雪芹记性甚好,自然记得这位“韦爵爷”。他心里生了厌恶,却因家教甚严,不敢不尊敬长上,这才恭敬地请了个安,道:“韦爵爷吉祥。”
韦小宝笑道:“起来罢,不必多礼了。”乘机便朝庵堂里走去。
曹雪芹却在门前拦住,道:“韦爵爷,我们在外面坐一坐,叫妙玉给我们沏上一壶好茶,咱们坐着看看竹子,你说可好?”
韦小宝嘴上道:“好啊。”
心里却骂道:“几竿破竹子,又有甚么好看的了?曹小花脸也与他爷爷曹大花脸一样,表面上一本正经,满肚子花花肠子。”
便在竹丛边儿石凳上坐了,妙玉一脸的不豫之色,端了茶来,却是两壶,一壶是整个儿竹根雕的,一壶是普通的茶碗。
妙玉将竹根茶壶放在曹雪芹面前,将普通茶碗放在韦小宝面前,韦小宝大怒,暗道:
“老子身份高贵,又是堂堂一表人才,哪里比不上曹小花脸了?连茶碗也分三六九等!”
面上却不显露出来。折腾了这许多的时候,确是口渴了,忙端了茶碗,“咕嘟咕嘟”就是一碗。
韦小宝抹了抹嘴,道:“咱们南方的河水,就是比北方的井水好喝得多了。”
妙玉冷冷一笑,自语道:“真正糟践了我这隔年的大好雨水了。”
韦小宝道:“这是雨水么?我怎么没喝出来?”便要再倒一碗尝尝,哪知一壶茶就这小小的一碗,却再也没有了。
韦小宝道:“师妹忒也小气,师兄大老远的来了,连茶也不管够。”
妙玉正色道:“贫尼与施主素不相识,再也不必说师甚么的话了。”
韦小宝笑道:“师兄也是好混说的么?我……”
妙玉怕他说出甚么无赖的话来,忙道:“茶是没有了,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驴了。’”
她说完,自己也忍不往微微一笑。
韦小宝一肚子的气,被她嫣然一笑笑得无影无踪,心道:“小花娘真是个怪物,气起来好看,笑起来也好看。”
韦小宝伸手便去取曹雪芹的茶壶,笑道:“不管饮牛啊饮驴啊,师妹这个茶好得紧,师兄也要多喝两杯,不辜负师妹的一片心意。”
妙王却豁然色变,猛然娇叱道:“放下!”
韦小宝一怔,道:“怎么啦?”
妙王冷冷道:“这是五年之前,我在蟠香寺的梅花上收的雪,总共得了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施主大富大贵的俗人,却是享受不得这方外至宝。”
韦小宝心里勃然大怒:“辣块妈妈不开花,老子是俗人,曹小花脸便是他妈妈的甚么雅人了?他奶奶的,小花娘欺人太,太也那个了。”
韦小宝脸皮极厚,笑嘻嘻道:“师妹于茶道上,规矩倒是不小,扬州有一家大大有名的茶馆,不知师妹去没去过啊?”
妙玉道:“贫尼方外之人,扬州繁华之地,去不去也没有甚么。”
韦小宝道:“啧啧,若是修行,别的地方不去也罢,扬州是非去不可的,去了扬州,别的景致不看也罢,丽春院是非看不可的。”
妙玉毕竟年轻,禁不住问道:“丽春院?那是甚么地方啊?”韦小宝一惊一乍,道:
“师妹,亏得你还整日的吃斋念佛,连鼎鼎大名的扬州丽春院都不知道,嘿嘿,你哪里能得正果?”
妙玉奇道:“你不是说丽春院是甚么茶馆?与佛门得正果又有甚么干系?”
韦小宝摇头晃脑,道:“当然有干系,大有干系,有干系之至。那可是辣块妈妈不开花,乖乖隆的冬,猪油炒大葱……”
韦小宝一边用扬州土话胡搅蛮缠,一边心里想着如何圆谎:“老子这谎可是撒得远了点儿,倒是怎么才能叫小尼姑相信呢?”
曹雪芹忽然插话道:“我佛有云:‘任你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妙王笑道:“真正难为你了。”
韦小宝听懂了一个“水”字,便道:“是啊,佛经里有水,茶是水煮的,是以大有干系了。师妹若是不信,日后到扬州丽春院去,品一品味儿,嘻嘻,师兄保管你立地成佛。”
妙玉看他贼兮兮的眼睛,心里老大的不舒服,板了脸,发话道:“天已不早,二位在此,多有不便,这便请回罢。”
说着,便打扫起来,将曹雪芹用过的竹根茶杯收拢了,却将韦小宝用过的茶碗,顺手向门口扔去。韦小宝心内大怒:“臭尼姑小花娘!摔东扔西的,不是成心叫老子大大地塌台么?”
正想说几句刻薄话,门口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唉呀,唉呀,讲打么?”
一条威猛汉子,黑塔似的出现在庵门口。
那茶碗无巧不巧,正扔在威猛汉子的身上。
妙玉只是个寻常尼姑,不会丝毫武功;曹雪芹是个孩童,又是富贵人家子弟。这两人吓得退后一步,话都不会说了。
韦小宝却站起身来,道:“喂,你……”
忽然住口,来人不是别人,却是茅十八。
韦小宝道:“茅——”
茅十八道:“毛?还没打,便发毛了么?”
说着,连连向韦小宝使眼色:“老子到处找你,原来你躲在这里与尼姑鬼混哪!你欠着老子的那笔帐,到底还是不还?”
韦小宝虽说不知道茅十八的用意,看他的神色,知道一定大有文章,便道:“好汉做事好汉子当,算帐你找我韦小宝便是,与我的这位师妹和这位曹小……少爷可是没有丝毫瓜葛。”
茅十八一竖大拇指,赞道:“好,韦爷是条汉子,有担待!”
话音未落,茅十八十指如钩,便锁拿韦小宝的咽喉。
韦小宝惊呼道:“喂,你做甚么,敢情是疯了么?”堪堪闪过。
身形相错,茅十八悄声道:“快同我打。”
韦小宝也低声道:“他妈的,真打么?”
茅十八道:“他妈的,打架还有假的么?”
韦小宝莫名其妙道:“茅大哥,你弄甚么玄虚啊?”茅十八却不再理会,一掌一掌,掌风呼呼,迫得韦小宝喘不过气来。
韦小宝一看来了真的,只得展开了“神行百变”的身法,与他游斗。
韦小宝哪里是茅十八的对手?茅十八游刃有余,边打边道:“小白龙韦小宝韦爷的功夫,真正是名不虚传啊。
只是可惜啊可惜!”
韦小宝道:“他奶奶的,老子武功高深莫测,武林泰山北斗,又有甚么可惜不可惜的了?”
茅十八学着韦小宝的腔调,不无讥刺道:“是啊,武功泰山北斗,高深莫测,可惜啊可惜,连他奶奶的老婆都保不住。”
韦小主惊道:“你是说双儿?”
茅十八冷笑道:“你能咽得下这口气,老子这个大舅子可咽不下。”
韦小宝心道:“他奶奶的,你甚么时候又成了我的大舅子了?”
正要说话,茅十八忽然沉声喝道:“看掌!”
掌风飒飒,掠得韦小宝的面孔生疼。
韦小宝除了那个半生不熟的“神行百变”,其余甚么武功也不会,哪里是在江湖上滚了多半辈子的茅十八的对手?
再者韦小宝压根儿也没有想到,茅十八能真刀真枪地与他动真格儿的。
就这么一慌神,茅十八一指点在韦小宝的“膻中”穴上。
韦小宝满眼怒火,朝地上倒去。
茅十八一把抱住了他,扛在肩头。身形晃处,将吓坏了的曹雪芹顺手抄起,抱在怀里,一个“旱地拔葱”,已上了墙头。
茅十八在墙头上转回头来,向籁籁发抖的妙王道:“告诉曹寅,若想要人,拿人来赎!”
茅十八飞身下墙,脚未落地,听得一个声音冷笑道:“这便留下罢!”
茅十八临敌经验甚丰,陡遇强敌,却是不乱,在半空中一提劲,身子落下时便错了尺余,敌人的一招“大成掌”也偏了尺余。
来人正是曹寅。
他的一招“大成掌”当顶击到,眼看着得手,却在间不容发之际被敌人避了开去,也是大感意外。但他并没有犹疑,不等茅十八站稳脚跟,第二招、第三招不停手地递了过去。
茅十八的武功本来不敌曹寅,加上肩头扛了个韦小宝,怀里抱着个曹雪芹,更是捉襟见时,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
曹寅招招不离对手大穴要害,茅十八腾挪闪避,顿时险象环生。
这还是亏得茅十八手中有了曹雪芹与韦小宝两个人质,曹寅投鼠忌器,不敢太过逼迫,茅十八才有了闪避腾挪的余地。
忽然,曹寅双掌相错,灵蛇般绕着茅十八转圈儿。倏地右掌疾拿茅十八的琵琶骨,左手拍向茅十八的“大椎穴”。
茅十八再也无法闪避了。
曹寅暗自庆幸,道:“相好的,留下罢!”
茅十八笑道,“留下就留下。”
一个急转身,茅十八已然将蒲扇大的大手悬在了曹雪芹的头顶,冷笑道:“姓曹的,大伙儿一拍两散,同归于尽罢!”
曹寅怔住了。
双掌齐下,敌人必死无疑。
可敌人临死前的一击,取爱孙的性命,也将是易如反掌。
曹家其时正是“烈火烹油、鲜花著锦”的鼎盛时期,然而子息艰难,数代单传。因此曹雪芹如“老祖宗”的命根子一般,若是有个三长两短,“老祖宗”的性命,只怕也要搭上了。
曹寅是个孝子,上有高堂,下有爱孙,双掌悬在半空,便无法击下。
茅十八极为得意,道:“不敢了么?老子可是要失陪了。”
曹寅双掌作势待发,喝道:“你要怎的?”
茅十八道:“简单之极。以人换人。”
曹寅“哼”了一声,道:“朋友,有本事咱们单打独斗,劫持人质,算甚么英雄好汉!”
茅十八学着曹寅的腔调,笑道:“对极,对极。有本事咱们单打独斗,劫持人质,算甚么英雄好汉?算他奶奶的狗熊王八蛋!”
曹寅气得脸色煞白。
茅十八一招“星换斗移”,已是滑出数武。
万寿庵因是曹家的家庙,当然建在僻静、幽雅之地。
茅十八几个起落,便要来到大街上。
茅十八正在暗自庆幸,不提防背后一股大力突然排山倒海般地袭来!
不管在江湖上,还是在官场中,曹寅都是大有身份之人。眼看着敌人倚仗劫持了人质,肆无忌惮地到了闹市之中,光天化日,他如何能在闹市中与人相斗?那不成了泼皮无赖了么?
情急之下,曹寅不顾爱孙曹雪芹与韦小宝的性命,陡下杀手!
茅十八是条爽直汉子,素无心机,一看曹寅投鼠忌器,便得意忘形,太过托大,没想到敌人孤注一掷,挺而走险。
待得他省悟过来,已是晚了。
背心穴道,已被曹寅的凌厉掌风罩住,便是悬在曹雪芹头顶的手,也无力拍击下来了。
曹寅一招得手,喜出望外,搬运了六成多的大成掌内力,蓄势便朝茅十八的后心穴道拍落,眼看着茅十八便要丧生……
一支拂尘,忽然架在曹寅的手腕上!
曹寅顿感手腕酸麻,这一掌便拍不下去。
茅十八笑道:“姓曹的,若要你这个命根子孙子和朝廷鹰大韦小宝的小命,五日之内,带了我双儿妹子去扬州赎人。晚了,老子便撕肉票了!”
口中说话,脚下飞奔,乘机一溜烟地去了。
曹寅却见面前立着一位独臂女尼,不由得惊呼道:“九难师太!”
九难师太含笑道:“曹大人,你好啊?”
曹寅“嘿嘿”冷笑道:“独臂神尼好大的名头,却与绑票的小贼串通一气么?”
九难师太故作惊讶道:“阿弥陀佛,原来那人是绑票的小贼?贫尼却是不知。”
曹寅的鼻孔里“哼”了一声。
九难师太道:“贫尼只是来与曹大人算一笔旧帐的。
曹大人,你使大成掌将我门下的陶红英伤了,那又该怎么说啊?”
曹寅知道,既是九难师太插手,自己今日着想追上“绑票的小贼”,夺回爱孙,已是难了。
曹寅冷笑连声,道:“哼哼,师太要为门下报仇,便请下手罢!”
转身朝庵内走去。
以九难师大的身份、地位,自然不会朝不还手的敌人出招的了。
九难师太微微一笑,拂尘挥处,瞬间不见了踪影。
韦小宝揉揉眼睛,坐起身来的第一句话,便是大骂茅十八:“茅十八大乌龟,茅十八大王八,他奶奶的谋财害命的茅十八,见色起意的茅十八,杀千刀、下油锅的茅十八!……”
韦小宝出身市井,骂人的话阴损毒辣,并且骂上三天三夜不带重样儿的。、”
正巧茅十八端了一盆鸡汤进来,朝他面前桌子上一放,也骂道:“他奶奶的韦小宝,骂够了没有?老子这盆鸡汤有穿肠的毒药,你敢不敢吃?”
韦小宝道:“你有甚么狗屁毒药了?无非是下三烂、下六烂、下九烂的蒙汗药罢了。老子还怕了你不成?他奶奶的,不吃白不吃。”
肚子饿极,一口气喝了大半盆鸡汤。
韦小宝这才抹抹嘴,笑道:“茅大哥,你这是唱的哪一出戏啊?”
茅十八也笑道:“双儿姑娘落在了曹寅的手里,我便想了个主意,将曹家的宝贝疙瘩命根子掳了来,叫他用双儿来赎。不想你韦兄弟也在那里,老子便顺手牵羊,将你一并绑票啦。”
韦小宝一听,心里也是极为感动,道:“茅大哥,你对韦小宝真好!”
茅十八道:“这算甚么?你茅大哥这条小命是你韦兄弟给的,如今双儿姑娘被劫,你茅大哥再不出力,还算个人么?不过,今日若不是九难师太出手,咱们两个只怕不能全身而退了。”
韦小宝惊喜道:“我师父?她在哪儿?”
茅十八道:“她老人家走了。”
韦小宝失望之极,道:“她走了?师父,你怎么不见弟子一面?”
茅十八道:“他奶奶的韦兄弟,你简直糊涂之极!九难师太何等的身份,岂能搀和在绑肉票这等江猢不齿的下流事里么?”
韦小宝心里却是大不以为然:“动手过招是为了得胜,绑肉票同样是为了得胜,又有甚么上流、下流之分了?师父忒也迁腐得可以。”
嘴上却附和道:“那是,这等下流的事体,自然都是下流的人做的,哪能堕了师父的令名?”
茅十八笑骂道:“他奶奶的韦小宝,你这不是骂你茅大哥自甘下流么?”
韦小宝道:“这又不是,曹寅若是与你茅大哥单打独斗,你即便不敌,拼了性命也要奉陪;如今他劫持了双儿作为人质,却是他下流在先,咱们下流在后……不,是他自甘下流,咱们却是上流,大大的上流。这便叫以甚么之道,还治甚么之身,哈哈!”
二人纵声大笑。
笑了一会儿,韦小宝忽然道:“茅大哥,这事儿只怕有些不妥。”
茅十八道:“有甚么不妥啊?不是以甚么之道,还治甚么之身么?”
韦小宝道:“不是这个不妥,曹大花脸自盐枭手里买的那个双儿我见到了,那双儿可不是这双儿,与老子的老婆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呢!”
茅十八道:“原来是这个。韦兄弟,你可上了曹寅的大当啦。”
韦小宝问道:“她不是双儿么?”
茅十八道:“这倒不是。那个双儿确实也是曹寅买的,也确实是从盐枭的手里买的,更巧的是,她也确实叫双儿。”
韦小宝奇道:“他奶奶的,天下竟有两个双儿?这两个双儿又偏偏碰到了一块?”
茅十八道:“是的。曹寅老好巨猾,花了十万银子,买了双儿姑娘,大约知道你韦兄弟难缠,又花了二千银子,从盐枭手里买了另一个双儿。”
韦小宝笑道:“老子的亲亲好双儿,有闭花羞月之容,落鱼沉雁之貌,卖了十万,值!
那假冒的双儿却是只卖得两千,真是一分钱一分贷,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公道得紧。”
想了想,又问道:“茅大哥,这许多的内情,你怎么知道的?”
茅十八道:“自从那日在丽春院里,我使刀误伤了你之后,又被曹寅击了一掌,养了月余才养好了伤。扬州是我的老窝,我便在扬州东游西荡。
“说来也巧,五天之前的那个夜晚,我到城外想找老财主周扒皮借几两银子使使,碰上了两个盐枭,两位老兄哺哺咕咕,一个道:‘老子拼了性命,掳了双儿那女魔头来,卖了十万两,却只得了二百两银子。他们坐地分赃,却成千成万的拿,太也不公!’“另一个道:
‘你知足罢。你听说过没有?那女魔头的老公是个有名的泼皮无赖。’韦兄弟,那可是盐枭骂你,可不是我。”
韦小宝笑道:“这有甚么?我自己也知道我自己是泼皮无赖小流氓啊?”
茅十八学着那盐枭的话,接着道:“‘小流氓厉害得紧,手眼通天,日后若是寻仇,咱们俩的小命保不保得住,还难说呢。’“先前的那盐枭道:‘你又不是没在场,那小子落在了咱们胡达胡师父的手里,又是卖给丐帮的,他哪里逃得出来?’”
韦小宝心里说道:“两个盐枭既是提到了胡达,这话对样了。”
茅十八又道:“另一个盐枭道:‘丁老三不知从哪里弄了个小婊子双儿,才卖了两千两银子,倒是他一个人独吞了,还有公道么?’“先前那盐枭笑道:‘你想多分银子,倒也不难,也去做龙头老大的小舅子啊?’“另一个盐枭大怒,道:‘他奶奶的,你才是龙头老大的小舅子!’“两人说着变了脸,我一个箭步冲了过去,一只手卡住一个人脖子的大椎穴,笑道:‘两个小舅子,都给老子乖乖地站住了!’”
韦小宝笑道:“两个小舅子落在阎王爷手里,大概也只有乖乖的份儿了。”
奉承得茅十八心中极是熨贴,道:“两个小子顿时傻了。我道:‘你两个将两个双儿的甚么事,一五一十地告诉我,谁说得对了,我赏他二百两银子;哪个要瞒了一句话,老子拧断他的脖子。要银子还是要脖子,哼哼,二位掂量着办罢。’”
韦小宝道:“茅大哥这话问得可不大对头,银子要要,脖子更得要啊。”
茅十八道:“其实我就是吓唬吓唬他们。
“岂知其中的一个经不住吓,筛糠般地籁籁发抖,道:‘我说实话,我说实话。那两个双儿一个是妓院里的小婊子,一个却是大有来头,是甚么鹿鼎公、驴鼎公的老婆。’”
韦小宝哗了一口,道:“鹿鼎公就是鹿鼎公了,哪里又冒出一个驴鼎公来?”
茅十八道:“我当时也没有闲心抓他的话柄,追问道:‘你们将鹿鼎公的夫人卖与谁了?’“他说道:‘这后来的事儿就不是我们兄弟经手的了,听他们说,是卖给了江宁织造曹……,“这时,另一个盐枭却打断了同伙的话,哈哈大笑起来,我道:‘他奶奶的,你笑甚么?’那盐枭冷笑着对同伙道:‘兄弟,不就是二百两银子么,你胡扯一通?同你说,这个你就不如我知道的清楚明白了。’“我道:‘你知道,你来说,银子归你。’“岂知那人却极是强拗,道:‘你这般狠霸霸的做甚么?官老爷审案子么?你松开手,我便老老实实地告诉你,老子赚了你这二百两银子;这般硬逼,老子却是宁死不招!’“俗话说:‘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我的手一搭上两人的脖颈,便知道他二人的武功、内力都是平平,心道:‘老子便放开你,你能跑了不成?’便松了手,道:‘好,你来说。’”
韦小宝叫道:“茅大哥要糟!”
茅十八奇道:“你怎么知道?”
韦小宝道:“这个人八成玩的是甚么缓兵之计,缓将之计。”
心里道:“这有甚么奥妙?老子被迫无奈,连投降的事都做呢。”
茅十八叹息道:“若是韦兄弟在场,那就好了。我的手一松开,那人竟迅疾无比地拔出匕首,一下子插入他伙伴的心窝里。”
茅十八继续道:“我大惊,重又抓住了他的脖颈,喝道:‘你做甚么?’“那人并不反抗,扶住了快要咽气的同伙,幽幽说道:‘兄弟,咱们盐枭虽说在江湖上并不是甚么了不起的帮派,可咱们自己要瞧得起自己。龙头大哥处事确实不公,不过,咱们窝里怎么斗都可以,就是不能借了外人的手来出自己的气。嘿嘿,嘿嘿,那不是忒也叫人家名门正派瞧不起了么?”
“韦兄弟,你是知道的,你茅大哥历来吃软不吃硬的,我敬服他武功不济,倒也是一条汉子,便松开了手,道:‘你走罢,我不难为你。’“那盐枭惨然道:‘谢谢你啦。不过。
我们盐枭的规矩,你也一定知道,那盐毒之苦么,哼哼,哼哼,也是不用提了。’“我常在江淮一带行走,知道盐枭对于叛逆之徒的惩治极为严酷。”
“那盐毒是从盐里炼制而出,将人不论是甚么部位划破了口子,撇了盐毒,便无药可治,浸人体内,苦不堪言,在七天七夜之后才得死去。”
茅十八沉默片刻,道:“说完,那盐枭倒转匕首,猛地插入自己的心窝……”
茅十八一生闯荡江湖,见过多少惨烈的场面?却是不知为甚么,对这两个盐枭之死,心中极为黯然:“他奶奶的,人这东西忒也没味儿了,人家不杀你,你他妈妈的自己抹脖子。”
韦小宝岔开了话头,道:“茅大哥,后来你就找双儿去了?”
茅十八道:“那盐枭说,你也被抓住卖了。我想,韦兄弟是个福将,又是狡猾多端……”
韦小宝笑骂道:“他奶奶的,甚么叫狡猾多端?那叫小白龙韦小宝雄才大略,赛过诸葛之亮,甚么甚么之中,甚么千里之外。”
茅十八道:“我与曹寅交过手,知道那鹰爪孙爪子极硬,又老好巨猾,双儿姑娘落在他的手里,只怕是大大的不妥,便急忙赶了去,却是真的找到了那个小婊子双儿姑娘。”
韦小宝道:“那小婊子我也见着啦,生得也是稀松平常,哪里能值二千两银子?哼哼,曹大花脸色中饿鬼,肯出这等大价钱。”
茅十八不理他胡说八道,接着说道:“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真双儿姑娘的踪迹。我想,江湖上传闻,总是不尽不实的居多,莫非盐枭以讹传讹了?
“然而总是放心不下。
“那一日我乘着黑夜,冒险潜入曹寅的窗下,忽然听得一个粗嗓门道:‘曹大人,快刀斩乱麻,你得痛下重手才是!’“曹寅咕噜咕噜地吸水烟,半晌道:‘唉,我也有我的为难之处。我与韦爵爷一殿为臣,这事儿也不能太过急躁,撕破了面皮,大伙儿无趣。还是谨慎为是,留些相见的余地。’”
韦小宝笑道:“曹大花脸与我交情不浅哪!”
茅十八道:“那人嘿嘿冷笑,道:‘曹大人做事滴水不漏,卑职当真佩服得紧。不过么,若是此事没个痛快了结,上头追究起来,哼哼,大人担当得起,卑职官小职微,却是罪无可赦的。’“曹寅声音极是不乐,道:‘既是上命差遣,咱们理当竭尽全力,同舟共济才是,又分甚么你我了?再者双儿姑娘她软硬不吃,你不是也没有办法了么,怎能都算在我的头上?’”
韦小宝一怔,猛地跳了起来,道:“甚么卑职、大人?
甚么上命差遣?曹大花脸是江宁织造,连江浙巡抚也让他三分,能够差遣他的,除了朝廷,还能有谁?难道是小皇帝叫他抓了双儿?”
茅十八道:“韦兄弟,老哥哥甚么都服了你,就是一件,你对鞑子皇帝不能一刀两断,老哥哥一百二十分地看不惯。那一日,我遇到了顾炎武顾老先生,他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人家真正是有学问的人,这八个字真正对了我的心思。”
韦小宝道:“他奶奶的,他有学问,老子就没有学问了么?”
茅十八笑道:“你的学问大得紧哪!我问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甚么意思?”
韦小宝道:“老子懒得掉书袋。”
茅十八道:“不懂了不是?其实我也不懂,还是顾老先生解释了我才知道的:满清鞑子不是我们汉人,自然不会与我们汉人一个心思。”
韦小宝道:“是我族类,心眼儿就定准不异了么?崇帧皇帝是汉人,怎么杀了忠心耿耿的汉人大忠臣袁崇焕?
李自成是汉人,怎么逼死了崇帧皇帝?”
茅十八一怔,道:“讲歪理儿,老子可不是韦小宝韦爷的对手。不过,人家顾老先生是大有学问的人,总不会错的。依我看哪,鞑子皇帝对你也未必存有甚么好心,你还是小心些的好。”
韦小宝心道:“对老子存了好心的人、又有几个?”便转了话头,道:“我自然明白。
茅老兄,咱们还是接着来说双儿罢。”
茅十八道:“我知道曹寅的狗爪子确实厉害得紧,不敢在窗外等得时间太长,便潜出了曹府,在一个僻静的地方,等待着与曹寅说话的人出来。”
茅十八继续道:“不大一会儿,一个身着夜行衣靠的蒙面男子走了出来,我出其不意,从暗中暴出,伸手便锁拿他的‘命门穴’。”
韦小宝笑道:“茅大哥,偷施暗算么?”
茅十八正色道:“姓茅的虽说武功不济,却是自来不做这等下三烂的勾当。是以在出手之前,已是提前喝了一声:‘好朋友,留下罢!’”
韦小宝心里骂道:“他奶奶的,你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么?”
果然,茅十八苦笑道:“岂知那鹰爪孙极为了得,虽是仓促之间,却是处变不惊,倏地转身,与我对了一掌。
他气态悠闲,站立不动,我却‘噔噔噔’倒退了三步,猛地将后背靠在墙上,心里血气翻滚,‘哇’地喷出了一口鲜血。
“蒙面男子笑道:‘到底谁留下来啊?’“说完,出手如电,径直拍向我的胸脯。我一时真气难续,呼吸也是不喝,哪里能够出手还击?眼瞅着必死无疑,只得闭目待死。
“蒙面男子却倏地转身,将掌力击向了后面。
“原来是九难师大出手救了我。
“蒙面男子仓促一掌,却也将九难师太袭向他背心的拂尘击歪。”
韦小宝武功不高,识见倒是不低,道:“世上有几人能是我师父的对手?想必我师父与你一样,不肯偷施暗算,是以未出全力而已。”
茅十八奇道:“韦兄弟的武功,想是大有精进,确实如你所说的那样。不过那人的武功,也实在是匪夷所思,连你师父九难师太也极是佩服。她当时说道:‘阁下的武功高明得紧哪!’“那人笑道:‘能得九难师大的夸奖,在下三生有幸。
不过若是师太使出全力,这一招“净瓶杨柳”,已是取了在下的性命了。’“九难师太摇摇头,也笑道:‘不,其实贫尼已是输了。’“蒙面汉子愕然,道:‘师太手下留情,在下感激不尽,说输了甚么的,不是羞辱在下么?’“九难师太道:‘阁下能说出贫尼的武功路数,贫尼对阁下的武功却是一无所知,贫尼岂不是已然输了一招了么?’“蒙面汉子沉默一会,道:‘师太见谅,在下本该将师门、来历禀告你老人家,无奈师尊严命,不得泄漏他老人家的名讳。’“九难师太点头道:‘我知道了。不过这位茅十八茅爷,与贫尼倒是有些渊源,阁下看在我的面子上,揭过这段梁子罢!’“蒙面汉子道:‘这个何需师太吩咐。在下也不敢让茅爷为难。师太,在下告辞。’“九难大师微微一笑,道:‘见了老怪物,代贫尼问候他罢。’“蒙面汉子一怔,未置可否,却是极其恭顺地向九难师太躬身行礼,如飞而去。
“我急了,道:“师太,放他不得!’“九难师太道:‘此人身手不凡,强留他也难,不如大方些,让他去罢。’“我道:‘他身上担着极大的干系呢!’“九难师太道:‘不就是双儿那丫头么?此事曹寅做得极为隐秘,解铃还需系铃人。解救双儿,还得找曹寅才是。’“我道:‘就是这事为难,那曹寅是朝廷大官,武功又极高强,我想了许多主意,也没有得到双儿姑娘的真实信息。’“九难师大沉吟道:‘曹寅也是武林成名人物,做事却怎地如此鄙劣?绑肉票么?听说他有个宝贝命根子孙子,将心比心,若是他孙子被人绑票,他的心里如何想法?’“我心中一动,道:‘他奶奶的,有他曹寅初一,就有我茅十八十五!
老子也将他的宝贝孙子劫了,叫他拿双儿姑娘来换。师太……’“我抬头一看,师太不知甚么时候走了。”
韦小宝笑道:“我师父要面子,不愿意搀和到这等绑票公案里去。”
茅十八也笑道:“老子本来也是要面子的,不过为了小王八蛋韦小宝,也只得不顾身份,做上一回绑票的土匪啦。”
虽是说笑,韦小宝心中也着实感激,道:“茅大哥,你将曹雪芹那个小肉票放在哪里了?可得好生保护,让曹大花脸抢了去了,那可大大的不妙。”
茅十八道:“这是在扬州,可不是曹寅的老巢,他要做甚么手脚也难。再说,曹雪芹是他曹家数代单传的命根子,曹寅也不敢太过冒险。”
听说是扬州,韦小宝大喜道:“乖乖隆的冬,猪油炒大葱,老子杀回老家啦,这可是他奶奶的衣甚么还乡了,老子面光得紧。”
说着,韦小宝又道:“茅大哥,你将曹小花脸带了来,让老子扒了他的裤子打屁股,他奶奶的,出出心里的这口恶气!”
茅十八愕然道:“甚么大花脸、小花脸的?”
韦小宝笑道:“就是曹雪芹啊。茅大哥,我告诉你,让你长个见识:他爷爷是曹大花脸,他爹爹是曹中花脸,曹雪芹不就是曹小花脸么?”
茅十八伸手揭开韦小宝床里面的被子,道:“韦兄弟,你看这是谁啊?”
——曹雪芹的身子露了出来。
曹雪芹正在酣睡,脸色红扑扑的,呼吸犹如饮了醇酒一般。
韦小宝捏住了曹雪芹的鼻子,笑道:“小花脸,睡得香么?起来与你爷爷玩玩好么?”
曹雪芹酣睡如故。
韦小宝问道:“茅大哥,这小花脸怎么了?”
茅十八笑道:“没甚么,你茅大哥怕他小孩儿调皮不听话,点了他的昏睡穴。”
韦小宝勃然大怒道:“你奶奶的,咱们也是江湖成名人物是不是?这样折腾一个屁事不懂的小小孩童,还要脸不要啊?”
茅十八也恼羞成怒,道:“你奶奶的,小花脸是你祖宗么?你这等护着他!”
可茅十八骂归骂,尽管心里有气,还是立即出手,解开了曹雪芹的穴道。又从鼻孔里“哼”了一声,掉头走了出去。
过了好一会儿,曹雪芹才醒了过来,一眼看到韦小宝,翻身坐起,迷茫地揉揉眼睛,问道:“前辈,这是在甚么地方啊?”
韦小宝将手指放在唇边,“嘘”了一声,道:“你不要说话,咱们被强盗绑票了。”
曹雪芹道:“甚么叫绑票啊?”
韦小宝道:“就是绑了孩童来卖银子。”
曹雪芹不解道:“卖银子?孩童也不是牲口啊,怎么能买卖。”
韦小宝心道:“他奶奶的,小花脸安富尊荣,甚么也不懂得。”
想了想,说道:“怎么不能?越是富贵人家的孩童,越能卖出个好价钱的。”
曹雪芹道:“前辈,他们将你与我一块儿绑票,你也是富贵人家的孩童么?”
韦小宝笑骂道:“老子是甚么孩童了?更不是甚么富贵……”
忽然心里涌出个念头:“曹大花脸将老子的亲亲好双儿买了去,此时也不知叫老子戴了十七二十八顶绿帽子了,老子也不能善罢甘休。对,老子将他十七二十八代单传的宝贝命根子,弄到花花世界里走上一走,叫他好好长长见识罢。”
眼珠子“骨碌骨碌”地转着,自己盘算了一会,极是得意:“你叫老子戴了绿帽子,老子叫你曹家出一个古往今来、独一无二、天下第一的无行浪子,曹大花脸,你可赚足了便宜哪!哈哈!”
(庸注:数十年之后,中华文学史上出现了一部最大的“淫书”《红楼梦》,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自称是“天下第一淫人”,不知其作者曹雪芹,这次与天下第一小流氓韦小宝结伴的扬州之行有没有关系?只得有待红学家的考证了)心念一动,韦小宝改口道:“我当然更是富贵人家的……出身了。我同你说,我的家里比你们曹家啊,不知富贵了多少倍呢!”
曹雪芹摇头道:“我们曹家有甚么富贵的?不过是面子上的事罢了。我常常听得父亲在背后长吁短叹,说甚么大有大的难处,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宴席,咱们曹家外表上‘烈火烹油、鲜花著锦’,骨子里其实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说完,神色竟是黯然。
韦小宝奇怪道:“曹大花脸的家教,其实也是一塌糊涂,弄得子孙后代也不会说话,说出的话也没有人听得懂。一百只足是甚么虫?蜈蚣么?可哪里有一百只足的蜈蚣?他奶奶的,曹家的蜈蚣生了这许多的足,怪不得曹大花脸总是狠霸霸的。”
想了半日,韦小宝也没有弄清“百足之虫”,便自语道:“反正曹家也不会出甚么好虫,定然是一条大大的坏虫也就是了。”
曹雪芹道:“前辈……”
韦小宝急忙打断他的话,道:“不要吭声,我们俩赶快逃命要紧。待会儿那强盗来了,保不准要将你蒸煮蘸了酱油吃了。”
曹雪芹吓得打了个冷颤,道:“前辈,人,人也是能,能吃的么?”
韦小宝道:“怎么不能?童男童女的肉最嫩,强盗更是喜欢的。”
见将曹雪芹吓得够了,韦小宝又安慰道:“不过你放心,有我在,他们吃不了你。哼哼,老子发起脾气,咱们俩合伙,将强盗蒸煮来吃了也说不定。”
注:韦小宝与曹雪芹在万寿庵遭劫,实有其事。万寿庵是曹雪芹的家庙,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上康熙的奏折中明确提及家庙“万寿庵、水月庵”两处,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有描写。水月庵原址于1980年在今江苏省南京市珠江路大平桥南找到,万寿庵遗址也于1991年3月14日在南京中山东路289号和291号被确证。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