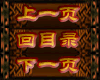|
|
第二章 柔情似水
|
 |
|
|
甘青池将刀切入自己肚腹。
因为事出突然,他动作太快,丁不一和徐温玉都未来得及出手阻拦。
“甘捕头!”丁不一抢过去,扶起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甘青池喘着气道:“请丁总捕头在我娘寿终正寝之前,每月用我的名义给娘寄……”下面的话,已难出口。
丁不一目蕴泪水:“你放心,我一定会的。”
“谢……谢。”甘青池脸上绽出一丝笑。
丁不一责备地道:“我已平安无事,又没有怪你,你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
甘青池陡地张目,猛然拔出切入肚腹的刀,一股鲜血喷溅出来:“沧洲府衙捕快没有叛徒,也不容许有叛徒!”
声断,人亡。
丁不一凝视着甘青池渐渐散乱的目光,久久未动。
徐温玉靠近他的身旁,轻声道:“他已经死了。”
丁不一痴痴地道:“他已经死了,人都会死,你我也是一样。”
涂温玉深沉地道:“死的人,虽死去了,活的人,却仍然要活着。”
丁不一扭转脸。
她澄澈明亮的眸子像星光一样迷人。
他轻声一叹:“也许你说得对。”
她沉静地盯着他道:“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从不为已逝的人和事儿无谓的叹息与伤心,因为叹息是多余的,伤心更无用,还有许多应该要做的事,等待他去做。”
他明白她话中的意思,缓缓地道:“你以为我是真正的男子吗?”
她翘翘嘴道:“你和我一样,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就看自己怎么去认识。”
此时,独脚汉和独眼汉收拾好阎克强和胡毒毒的尸体,回到柴靡院内。
徐温玉向他俩再发命令:“将甘捕头的尸体秘密运送到禹城县衙,不得走露风声。”
独脚汉和独眼汉走到丁不一身旁:“丁总捕头,请将甘捕头交给咱俩。”
他俩的眼里除了徐湿玉之外,没有任何其它主人。
丁不一放开手,退后两步。
独眼又从背囊中取出两只皮囊搁在地上。
独脚汉拐杖一挑,将甘青的刀挑人一只皮囊中,然后弯腰叠起皮囊用细绳系好。
独眼汉打开另一只皮囊,将甘青池套入囊中,扎好囊口素头。
独脚汉从腰囊中取出一个小瓶,往地上洒了一层粉末。
地上的血迹沾上粉末,立即消失。
独眼;又将装着甘青池尸体的皮囊往肩上一搭,撤步就走,独脚汉夹着装刀的皮,紧随其后。
两人动作熟练。配合默契,像是干惯了杀人越货勾当的老手。
他俩没告辞,也没打招呼,就这样大咧咧地走了。
天已经完全黑下。
月亮还未升起。
坪内一片深沉。
丁不一望着黑沉沉的柴靡门外,问道:“他俩是谁?”
徐温玉的目光也盯着柴靡门外:“你不是早已见过他们?”
丁不一沉声道:“不错,但我不知道他们的来历。”
徐温玉凝视着他,默然片刻后,说道:“他们是我从残缺门请来的杀手。”
“残缺门!”丁不一心念一动,不禁脱口而呼。
徐温玉道:“有什么不对吗?”
“没……有。”丁不一急忙道,“我只是没想到,他们居然会是残缺门的人。”
徐温玉淡淡地道:“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他们七人本就是七个残疾人。”七人丁不一又惊呼出口。
侮山七妖也是七人,与残缺门有关,是否与此七人有关?
徐温玉这次没有理会丁不一的反应,犹自继续道:“他们是残门排行第一的七位高手,据说若七人联手,就连残缺门门主董志行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丁不一本想提及郝倚老、甄稽首、柳长青,去残缺门找董志行的事,但强忍着没有开口。
他想起了沈素贞和爹爹丁不伟的警告,这个扮装成分子爷的女人,可不能不防着点。
徐温玉却在坦诚地将她的秘密告诉他:“这七人是黄单眼贾一脚、赵缺鼻,邓癞子,辛金躬、邓无耳、刘少手……”
好奇怪的名字!“这是根据他们身残部位所取的名字,在残缺门里,大伙又叫这七位并排一号的杀手,叫残门七妖。”
“为什么?”
“丁总捕头若有兴趣,请到堂屋里说话。”
徐温玉末等他回话,已转身大步走进了堂屋。
丁不一在犹豫。
他该不该帮徐温玉的报仇?
徐温玉真如沈素贞和爹爹所言,是另有企图?
他完全可以弃她而去,无论是什么企图,都不管用了。
然而,他没走。
不知怎的,他觉得她是可以相信的,这仅是他的感觉,但,他却坚信不移。
他不走。还有一个借口,他该将她的折扇还给她。
此时,堂屋里亮起了灯。
他毅然转身,走向堂屋。
屋内点着一盏油灯。
徐温玉在八仙桌旁的长木凳上坐着。
桌上除了瓦壶、土碗之外,还多了一个小酒壶和两只酒盅。
徐温玉已早有准备!
他踏步进屋,默默地在她对面坐下,目光凝视着她。这是质疑与询问的眼光,十分锐利,似乎要刺穿她的心底。
她斟上一盘酒,送到他面前,缓缓地道:“当年的梅山七妖是由七个江湖采花淫贼结成,七人个个俊逸潇洒,倜傥英伟故江湖上称之为采花七粉郎,当时江湖人只知道采花七粉郎,知道梅山七妖的人极少。”
丁不一眼中闪着游疑的光:“原来梅山七妖就是采花七粉。”
徐温玉点头道:“这是七个俊男儿,而残门七妖却是七个奇丑无比的残疾人,其中几个你已见过了,因此我想他们决不会是当年的梅山七妖。”
“可是有人说梅山七妖与残缺门有关联……”丁不一自知失口,话说一半,猛然顿住。
徐温玉淡淡地道:“钦差大臣徐刚正大人告诉郝倚老,说梅山七妖与残缺门有关,郝倚老、甄稽首和柳长青三人,已去残缺门找董志一了,待他们回来,事情也许会有个眉目。”
丁不一脸上泛起一阵潮红,他为她的坦诚,而感到歉意。
她把自己当成知已,无所不言,自己对她为何不能坦诚相待:
徐温玉端起酒盅:“丁总捕头请。”
丁不一不好意思地笑笑道:“你还是叫我金公子顺耳。”
他化名为金沧海,徐温玉一直对他以金公子相称,他喜欢她这样称呼自己,他觉得“金公子”这个称号来得亲切。
徐温玉略略一顿,随后浅浅笑道:“金公子请。”
她酒盅在唇边碰了碰,便轻轻放下。
丁不一举盅一饮而尽。
“好酒!”他像那日在破庙中,与她对饮进一样,发出一声赞叹。
他是由衷的赞扬,盘中之酒就边京城八仙楼的状元红,也要逊色三分。
她抓起酒壶,替他将盘中酒斟满。
他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没开口。
她放下酒壶,凝视着他道:“你想要说什么,尽管说,不要有顾虑。”
他咬咬下唇;“你与郝倚老是什么关系?”
她没有迟疑,大方地道:“我是他的雇主。”
“雇主?”他睁圆了眼,“万金难雇的太上老君是你扉用的杀手?”
她淡淡地道:“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出钱扉他,他原意应扉,不就成了。”
“可是……”他顿了顿道:“老爷子也雇用了他们,据我所知,江湖三杀手是从不听命于两个雇主的。”
她伸手挑油灯,火苗窜了上来,映亮了她脸。
她盯着火苗光道:“老爷子是通遏聚英庄穆钟仲龄作中保,才请到郝倚老三人的,而穆仲龄这个中保,预先得到了我的同意,所以真正的靡主只有我一个,而郝倚老三人的任务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找到梅山七妖,并杀了他们。”
他想了想道:“为什么一定要杀梅山七妖?”
这是一句明知故问的话,带有几分试探的成份。
他还在试探她的可靠性。
她沉缓地道:“若不杀梅山七妖,隐君庄永远不会消失,我的心愿永远无法实现。”
他瞧着她道:“你认为一定非要摧毁隐君庄不可?”
她蓦然侧头,一双亮眼迎视着他:“到现在人还不能相信我?你以为我向你说的那个家毁人亡的故事,是骗人的鬼话?”
火苗突地窜跳了几下,墙上的影在摇曳。
他能感受到屋内空气的澎湃,和她内胸翻涌的狂涛。
“不,”他深沉地道,“我相信你。”
照他的感觉,他不能不相信她。
“我也相信你。”她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彩,“只是……”
他打断她的话:“你与毕不凡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九鬼对你的折扇如此尊重?毕不凡为什么要让我看九冥神功秘笈还有华士杰……”
一连串的连珠炮的提问,射向徐温玉。
徐温玉耐心地等他问完话,平静地道:“有些问题,我能回答,有些问题,我不能回答,有些问题,我无法回答,但等隐君庄真正被摧毁的一天,一切你全都会明白的。”
他用乞求的口气道:“你能告诉我一些什么?”
徐温五沉思片刻道:“我除了那位救我的恩公外,还有一位师傅,那柄折扇就是他老人家送给我的。”
丁不一目芒一闪:“你师傅是谁?”
徐温玉肃容正色道:“七怪老人松莆子。”
他摇摇头,他从未听过七怪老人松莆子这个名字。
徐温玉低缓地遭:“你可曾听说过梅山的得道高僧天跃大师?”
他惊讶地点点头:“七怪老人松莆子就是七怪堂庙的天、地、日、月、风、雷、灵大高僧中的天厥大师?”
“不错。”她端起酒盅,脸上绽起一团红云,“当年梅山七妖认为是七怪堂庙的人,将他们的消息告诉了关天英,所以逃出天牢后,血洗了七怪堂庙,庙中七十二僧无一逃生。”
他咬紧牙,胸中腾起一股基于正义而泛起的杀心。
“唯有天厥大师幸免于难,但双目已教挖掉,两腿被砍断……”她说到此,声音突然中断。
他瞧着她:“为什么不说了?”
她露出一丝苦笑:“我已经犯了师傅的禁令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他扁扁嘴,抱歉地道:“实在是对不起。”
他觉得已经难为了她,而且下面的事不说,他也自能猜着几分。
他从腰中取出折扇,以手捧着送过桌面:“天厥大师的折扇,难怪鬼魔城的九鬼肯卖这个面子,现在此扇完璧归赵。”
他自认为猜到了,其实,他只是知其一,而不知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这其中蹊跷无数,奥妙无究,在揭开谜底之前,你怎能猜得透?
她伸出白晰的手,在扇杆上轻轻一隔:“这扇你留着吧。”
他愣住了,捧着扇不知所措。
怎能接受她这份重礼?
她浅浅笑道:“你留着它,日后也许还有用处。”
他支吾道:“可是……”
她收起笑容,正色道:“这是我正式送给你的礼物,日后即使没有用处,也可留着做个纪念,除非你不愿意接受它。”
他微微一笑,收回双手:“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我就不客气了。”
他不明白她赠扇的企图,但无法拒绝她的这份礼物。
他收好折扇,端起酒盅道:“谢徐公子这份厚礼,在下无以回报,借花献佛,敬徐公子一杯,以表谢意。”
他虽已认破徐温玉女子之身,而徐温玉心下也自明白,但两人却未说破,心照不宣,故此,他仍以“徐公子”相称。
徐温玉待他饮过酒后,凝视着他道:“金公子,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该讲?”
他瞧着她:“请赐教。”
她凝目道:“情为何物?”
他不觉一怔,不知她为何有此问,想了想道:“情即为色,色即为空,色空情空,万物皆空,若坠情中,葬身火狱,不得出离,受苦长劫。”
她凝视着他,沉声道:“你真是这么想的吗?”
他低下头,沉吟不语。
他只是信口胡说,心思又问尚如此!
她柔声道:“人有情有爱,有相托,有依赖,但总离不了一个缘宇,是缘长相聚,无缘必分离,正如佛门所云:众生无我,苦乐由缘。有些事是勉强不得的。”
他低着头,沉声道:“世间事不离因果,死生生死,离合合离,以及一切寿天、强弱、盈亏、得失、苦乐、成败、循循环环,无休无歇;因因果果,互消互夺,播什么样的因,就会收什么样的果。佛门中不是常常如此说么?我是自食其果,无怨无艾。”
她瞪圆了眼,神情有些惊讶,她没想到,他对佛理也如此深通。
她想了想道:“真性如水,妄念如波。那水本来无波,因乱动就出现波浪。真性本来湛然明净,因无明而妄念颠倒,因此说:‘全真成妄,全水成波’。又说:‘全妄成真,全民水’。”
他突然抬起头,勾勾地望着她。
她深邃的眸子就像一汪平静的潭水,清澈、明亮如镜。
他缓声道:“那波本是水,只要停止动乱,全体原来是水。
妄念本是真性,只要休息下来,全体原来是真性。”
她瞧着他点点头:“你知道就好。”
他皱着眉:“可是,我做不到。”
她轻叹一声道:“须知止与觉为缘,就能返妄归真,比如化波成水,但不到智光显现时,妄情波相一时不能破除。相反来说,乱与昏为缘,就能使真为妄,比如搅水成波,但不到无明现前时,本性湛水不会动摇,可见寂照便觉,失照便昏。”
他端起酒盅一饮而尽,然后走走地瞧着她:“我的事,你全都知道?”
她坦然承认:“可以这么说。”
他眼中进出一抹精芒:“你一直在暗中跟踪我、调查我?”
她供认不讳: “是的。我一直派人在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
他声音低冷:“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她面容冷肃,神情凝重:“因为我关心你。”
他脸上绷紧的肌肉痉挛了一下:“我有什么值得你如此关心的地方?”
她淡然地道:“我曾经说过,你是唯一能帮助我完成复仇的计划的人,因此,我不希望际出什么差错。”
他脸色颇为严肃:“你认为我会出差错?”
她声冷如冰:“如果刚才不是我及时赶到,你就完蛋了。”
他的心陡地一跳。她说的的确是实话。
他没再吭声。
她稍稍一顿,又继续道:“我原以为你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没想到原来是个如此容易为情所困,如此容易意声消沉的男人。我算是看错人了。”
他身子触电似地一抖,胸中激起一股豪气,不觉喷然道:“我认为,我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窝囊。”
她轻噬地笑了一声:“金公子曾在八桥镇,当众脱裤钻人胯挡,难道还不算窝囊?”
他霍地站起,满脸通红,右掌扬在空中。
她端然地坐着,无动于衷。
他忽然例嘴笑笑,缓缓收掌坐下:“徐公子,有话请直说,用不着用这种激将法来激我。”
她芜尔一笑:“你很聪明,并未失照便昏。我已知道你的四个未婚妻皆是公主,皇上已下令接她们回宫,可没想到你居然会变得如此沮丧,意志消沉,以至心死。”
他抓起酒壶,对着壶嘴,猛喝了一口酒,苦兮兮地笑道:“你若是我,你当如何?”
她肃容道:“止觉为缘,就能返璞归真。”
他目透精光:“你是说,我还有望?”
她肯定地道:“一定有望,难道你不觉得她们四人都是真心地爱着你!”
他握注酒壶的手一抖:“可是皇上……”
她沉静地截断他的话:“别说是皇上,就是西天佛祖如来,道教三清老祖,也无法阻挡男女之间真情的爱。”
他抿抿嘴,握紧了酒壶:“可沈素贞和白如水都已向我表示,她们是公主,不能下嫁给我。”
她轻摇头道:“我不知道她俩为什么要这么说,也许是有意考验你,或许还有别的意思,但我知道,她俩是爱你的,女性是一种感情强于理性的动物,一旦她对你动了真感情,无论你是谁,她这一辈子都会跟定你。”
他放下酒壶,猛地抓住她的双手:“谢谢你。”
心中乌云豁然拔散,他显得几分豪爽,几分激动。
她的脸蓦地红了,在灯光下就像一朵姹紫嫣红的夜海棠。
被丁不一捏得变了形的酒壶,在桌面上像是不倒翁似地摇晃。
“请放……开手。”她涨红着脸,竭力想缩回手。
他突然醒悟,意识到她是女人时,不觉也红了脸,急忙松开手:“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只是想……谢谢你的开导。”
他说得很诚恳,神态也很真势,没有半点做作之态。
“没什么,我并没有怪你。”她轻声说着,脸却更红,连颈脖也红透了。
她并没有怪罪他,但她、中腾起的一种崭新的不可言喻的感觉,使她感到惊异、羞涩、喜悦、和阵阵晕眩。
他痴痴地看着她,为自己刚才的失态和鲁蛮,而不知所措。
她深吸口气,竭力压抑下狂跳的心,故意做作的声调道:“情莫大于心狂,哀莫大于心死,你为情所困,心哀似死,柳树林中暗藏的人,你看不到,易容的胡毒毒、尤宝宝夫妇,你辨不出来,连我投石告警,你也无动于衷,结果是什么,你很清楚。”
他歉意地道:“很对不起。”
她正色道:“你重任在身,若不振作起来,仍为情所困,随时都会丧命的。”
他眨了眨皮道:“你怎么知道我会来这里?”
她思忖了一下道:“实话告诉你吧,是沈素贞要我来的。”
“小贞!”他眼中顿时光彩四射,“她现在哪里?”
“在西公馆。”她爽快地道:“自从你和她分手后,你心神不定,她伯你出事,一直在暗中跟着你。今夜她要去西公馆会毕不凡,所以就把你交给我了。”
他弓起身子瞧着她:“原来你与她早已相识。”
她正要答话。
此时,门传来上一阵冷笑声:“我说丁总捕头哪里去了,原来在这乡村别墅与女人风流快活!”
丁不一听到这声音,脸色变了,变得有些苍白。
一阵风刮到,堂屋门洞开。
一线红光坠,一袭红披风展开,华温倩飘然而入。
丁不一呼地站起,厉声道:“华温倩,你来干什么?”
华温倩鼻微微一翘:“我不能来吗?”
丁不一知道她难缠,于是唬起脸道:“我和徐公子在谈公事,请你离开这里。”
华温倩浅浅地一笑:“是怕我坏了你俩的好事?”
“你……”丁不一脸刷地一红,沉声道:“休要胡说!”华温倩清格格地笑着道:“丁总捕头,你别装蒜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徐公子是个女人?”
徐温玉苍白的脸透出一层红绯:“华温倩,你不要……”
“哎!”华温倩挥手堵住她的话,“现在我没有与你说话,我在和丁总捕头说话。”
丁不一咬咬嘴唇:“不得对徐公子无礼!你若在此胡闹,我就对不客气。”
华温倩挺起胸脯跨前一步,一双灼亮的阵子盯着丁不一:“怎么?丁总捕头想杀人灭口?”
丁不一横紧了拳头,复又松开,对这个小梅花妖女,他真是没办法。
花温情翘起美丽的薄唇道:“你在隐君庄对付不了我爹,在这里就想欺辱我,是不是?”
丁不一胸中开起一团怒火:“你以为我不敢动你?我现在就拿你去衙门,让你蹲上几天大牢,看你还这么刁蛮?”
说罢,他衣袖一卷,真要动手。
徐温玉却斜里一格,拽住他的衣袖。
他困惑地看了徐温玉一眼。她为何不让自己动手?
华温倩欺身到丁不一身前,瞪圆明眸道:“你以为我是什么人?你敢让我蹲大牢,我就要让你丢尽脸面!”
丁不一何曾受过这种要挟,浅浅一笑道:“刁蛮的姑娘,你不要以为你爹仗着西宫太后撑,就能一手遮天,你说说看,你到底是什么人,怎样让我丢尽脸面?”
华温倩盈盈一笑道:“徐公子,你也好好听着,我不仅是丁总捕头的救命恩人,而且也是他的女人,他要让我蹲大牢,他的脸面还有什么?”
徐温玉仍是斜身站在他俩人之间,对她的话,没有多大的反应。
丁不一却气败坏地道:“你这小妖女也太不像话了,说是救命恩人我不说,怎么是我的女人?”
华温倩晃晃头,神气地道:“你忘了,你我赤身搂抱在马背上,还在山神庙里共一条被子睡了一夜!”
徐温玉打断她的话道:“那是你点住了他的穴道,强迫他所为,怎能算数?”
丁不一惊愕极了,这种事,徐温玉也能打听得到?
花温情歪着头道:“不管怎么说,我是与他赤身抱过,睡过,除了这个男人之外,你还能嫁给别的男人么?”
徐温玉哑了声。
丁不一愣住了。
这种女人真是天下少有!
花温情对徐温玉翘翘嘴:“到外面来,我有话要对你说。”
她转身就走。
徐温玉略一犹豫,跟了过去。
华温倩在门口扭回头,笑吟吟地对丁不一道:“你不要走。我还有要紧话要对你说。”
|
|
|
本书由“weiweins”收集整理文本,“云中孤雁”免费制作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