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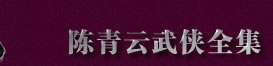 |
|
 |
|
 |
| |
|
第 四 章 情天惊变
|
|
岭顶,松林一片苍郁。
林中,一块岩石上端坐着一个额有刀疤的中年汉子,刀疤是直的,几乎占了整个前额,一道深槽把额头一分为二,使本来就凶恶的面目显得更加狰狞。他身边站了两名骠悍的年轻汉子,肩后斜背厚背鬼头刀,刀柄上垂着红绸,仿佛是待命行刑的刽子手。
韦烈已经来到,他隐身在一块倚松而立的岩石之后。
“香主,没消息如何复命?”一名手下问。
“如果人已入山不会没有消息。”刀疤汉子回答。
“山区如此之大,找人……”
“你少给我泄气。”刀疤汉子凶巴巴地喝阻。
那名手下立即闭嘴不言。
两名汉子来到。
“怎么样?”刀疤汉子迫不及待地问。
“禀香主……没消息。”之一躬身回答。
“哼!”
紧接着,又有两名汉子押着一个山民来到。
韦烈一看大为震惊,这被押的山民赫然正是自己向他打探驼峰所在地的壮年猎户,他怎么会被擒押而来?对方要打探的是什么消息?
“这是什么人?”刀疤汉子问。
“山中猎户,”押人者之一回答。
“问出什么没有?”
“他死不开口。”
“那好办,本香主来问。”熠熠凶光直照在那猎户脸上:“听着,你不想死就乖乖回答大爷的问题,你是否碰到一个长得很俊的年轻武士在山中行走?”
韦烈心中一动,这不是指的自己吗?对方什么来路,竟然要打探自己的行踪?看装束很像是“大刀会”的……
猎户闭口不答,一脸愤色。
“开口!”刀疤汉子大声吼叫。
猎户仍不开口。
刀疤汉子狞笑一声,冷森森地道:“你是要装哑巴,就教你永远开不了口。”头一偏又道:“王虎,逼供你最拿手,弄点辣的给他尝尝。”
原先说话的背刀汉大步上前,“飕!”地一声从腰里拔出一柄短刀,比在猎户眼前连晃,狞声道:“相好的,你知道刀子在嘴里搅是什么滋味吗?嘿!趁早规规矩矩回答,你在山里看到那个没有?”
猎户挣扎,但被扣得很牢,根本无法动弹。
“在这里杀人者死!”猎户终于开口了。
“有意思,谁说的?”
“神仙!”猎户抬头遥注宝塔形的入云尖峰。
韦烈心中又是一动,猎户所指的神仙是冷玉霜他们吗?她说过,上代密谷主人为了避免干扰,曾经在山中制造了许多神迹,使山里人信服。
“什么,神仙说的?哈哈哈……”刀疤汉子暴笑了一阵:“山里居然有神仙替你们立规矩,真有意思。”
“杀人者死!”猎户又说了一遍,神情很严肃。
“王虎,我们就试试看!”
王虎扬起短刀。
猎户并无惊惧,他似乎极为相信心目中的神仙。
韦烈蓄势待发……
王虎一把揪住猎户的头发向后一拉,短刀往心口里……
韦烈正要现身阻止,突见王虎短刀掉地,扭住头发的手缩回,仰面栽了下去,挟持猎户的两名汉子也同时歪了下去,连半点声息都没有。
刀疤汉子从石头上蹦了起来,惊惧四望。
其余三名汉子却吓呆了。
韦烈也大感意外,这太邪门了。
那名猎户朝尖峰方向下跪,拜了一拜,飞奔而去。
刀疤汉子暴吼一声:“拦住他!”
三名手下木立不动,等惊觉要采取行动时,那猎户已没了影子。
三具尸体,竟不知是怎么死的?刀疤汉子上前检视了死者一遍,眼里的凶光变成了骇异,额上的刀疤似乎也是更深了,厉声道:“老子一辈子不信邪,想不到还真他妈的邪门,三条命怎么送的都不知道……”
就在此刻,一条人影奔到,是个山里打扮的小伙子,但从利落的身法来看,又不像是山里的青年。
“副总管!”刀疤汉子迎上前躬身为礼。
“这怎么回事?”
“有……有人偷袭。”
“宋香主!”年轻的副总管架势十足:“你这不像是办事的样子,踩盘踏线是秘密行动,你居然像上阵盘摆出这种谱,成话吗?”
“是,属下知错,请副总管担待。”刀疤汉子又躬身,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一头恶犬变成了驯羊。
“有‘武林公子’的行踪吗?”
“这……还没得到。”
“哼!”副总管重重地哼了一声:“马上处理善后,然后回总舵接受处分。”车转身气冲冲离去。
韦烈大为惊奇,对方怎会追到山里来踩自己的线?
刀疤汉子愣了好一阵,才粗声暴气地道:“他妈的倒楣,——入山便给死鸟在头顶上拉了泡屎,老子就知道非倒楣不可,发什么呆,一个带一个,我们走!”
三名手下各负一具尸体,起步离开。
韦烈正待喝阻,心念一转,放弃拦截,他想到必须保留山里人对神人的崇拜慑伏,自己一现身,刚刚的事实便会走样,变成了是自己暗中偷袭,而且自己正在等洪流和王道,要查因由,王道一出马便可完成。
日头已斜到跟岭顶平行,黄昏即将来临。
一道白色的旗花从山岭下方冲空而起。
韦烈迅速地奔去。
岭下山沟边,横陈了七具尸体,赫然是那刀疤汉子和六名手下,刀疤汉子单独在一边,其他六个各成一双。
韦烈刚到,洪流已现身趋前。
“洪流,是你做的?”
“是,他们先动手。”
“这叫玩刀的碰上了刀祖宗!”王道也现身。
“死者什么来路?”韦烈问。
“大刀会的零碎!”王道不假思索便回答。
“你怎么知道?”
“老早就相识了,江湖上只有他们一律带刀,刀柄上一定击红绸带,跟‘乌衣帮’狼狈为奸,彼此通鼻孔,联手干好事。”
“他们入山是踩我的线。”
“哦!那杀得不冤。”
“现在我们先回垣曲,王道立刻设法查明‘大刀会’盯踪我的原因。”
“公子,好差事,嘻,关于那驼……”
“出山再说,现在不许提。”韦烈大声制止。
王道与洪流齐现出讶异之色,但都不再开口。
垣曲。
时间是傍晚。
韦烈兴冲冲地进入原来投宿的那家客栈,房间没退,竟然还保留着,房饭钱已经预付,算算还有三天不必付费。令他沮丧的是司马茜已经离开了,不知去了哪里,他怅然若失,原先进店时的那股兴头完全消散。
小二送来了酒菜。
“小二,隔壁房的那位女客官走时没留话?”
“没有,不过……”小二欲言又止。
“不过什么?”
“那位女客官走的时候脸色很难看。
“噢!”韦烈心头打了一个结。司马茜难道碰到了什么意外事,她说过要等自己回来的,一个任性好动的女子耐心有限,等烦了先离开不足为怪,她是订过亲的人,方一平也算一表人材,没有理由跟自己牵缠,不解的是她竟然不留片言只字,莫非她的家人已追了来。
转念一想,又觉得自己是何苦,就因为她长得像亡妻小青而勾住了自己的心,但她并不是小青,交往下去注定没结果,而且会带来无尽的痛苦。
“公子!”小二还站在旁边没走。
“你还有话要说?”
“嘻!只是句闲话,垣曲城这几天在闹怪事。”
“什么怪事?”韦烈心不在焉。
“接二连三的命案已经发生了五起,遇害的都是年轻英俊的男人,官府的仵作天天忙着验尸,再下去……。”
“凶手是什么样的人?”
“不知道,听人说……是反采花。”
“哦!”韦烈心中一动:“你说这话的意思……”
“请公子小心些,没别的意思。”
“我会小心。”
小二拉上房门离去。
韦烈一个人在喝闷酒,冷玉霜和司马茜的面影交互在脑海中浮沉挥之不去,最后留下的是司马茜,因为她是小青的影子。本来他已经想透,酒一下肚,他又想不开了,明明知道不会有好结果,但他无法不想,而且更强烈。一杯接一杯,麻醉不了那股刻骨的哀思,他想的是小青,但也是司马茜,真实与虚幻他已分不清了。
司马茜的家凌云山庄是在嵩山南麓,她可能是为了不满与方一平的这桩婚事才离家出走,当然不会回去。洛阳只是她暂时落脚之地,跟方一平那一闹,自然也不会再去,那她去了哪里,韦烈深深地想。
窗门被风吹开,似水月光洒了进来,很美。韦烈突然想到城外的小桥流水,绿丘凉亭,曾经跟司马茜在那里流连过,月夜,那里应该更美。
情思郁结加上酒力摧化,韦烈起身出房离店?
人在这种情况下常常会想到什么做什么。
月如水!
天无尘!
郊外的景色的确美得迷人。
可见亭角飞月,竹影摇风。
浓浓的酒意被风一吹,整个人在迷离中飘飘然。
他沿小路石级登丘。
在将要到达丘顶之际,突然听到人语之声,原来亭子里有人,韦烈登时意兴索然,止步想回头下丘……
“你说你叫紫娘?”男人的声音。
“不错,好听吗?”
“太好了,和你的人一样美!”
“紫娘”两个字把韦烈的脚跟钉住了,酒意也消失了大半,想不到司马茜会和男人在这凉亭里,原来她离开客栈却没离开垣曲,跟她一道的男人是谁?韦烈的情绪不由自主地沸腾起来,他无法忍受,他以往把她当成小青。
话声又传。—“龙少爷,你真的认为我很美?”司马茜嗲声说。
“不仅是我,谁见到你都会这么认为。
“你听说过好景不长吗?天下任何美好的事物都不会长久,正如老天爷常常让红颜女子薄命!”“哈哈哈哈,紫娘姑娘,你太多愁善感,没那样的事,所谓红颜薄命,只因为她是红颜,特别受人注意关切,一旦发生变故,便引来这样的感叹。许多生来丑陋的女子,她们的命更苦,却没有人同情,而她们同样是女人。
“你的口才很好?”
“谬赞!”
“今夜月色很美,但不久就会……”
“对,美景良宵,岂可辜负,紫娘姑娘,我们……,”“不许动手!”
“姑娘孤单一人步月,并未拒绝在下同行,当然是心照不宣,又何必惺惺作态,来吧,别负了月老的美意。”韦烈全身有如火焚,想不到司马茜会是这样的女人,他突然想起客栈房中小二说过的“反采花”故事……
“龙少爷,你先听我说一句话。”“请说,快些。”“你认为一个见色起意,毁人名节的男人该付出什么代价?”
“这……这……说这种话不太杀风景吗?”
“我要你回答。”
“好,我说了,该杀!”
“对了,你说对了,你已经起了邪念,所以该杀!”
韦烈心头一震,司马茜到底在玩什么把戏?
“哈哈哈哈,紫娘,你可能错了,你我初见,引我到这无人的地方,用心不问可知。垣曲城最近一连发生命案死的全县年青俊美的男子,何以如此,瞒不过明眼人人,我‘花间狐’龙生可不是省油灯……”
“哦!你想怎样?”
“我喜欢好花,碰上好花我就一定要采到手!”
“要是采不到呢?”
“宁做风流鬼,如果你有这分能耐的话。”
“很好,就让你如愿做风流鬼。”
接着是交手的声音。
“哈哈哈哈……,”花间狐龙生边出手边笑。
韦烈已经无法再按耐,他不明白司马茜为什么要这样做,听情况花间狐身手要在司马茜之上,所以才那样自得“花间狐”这名号自己并不陌生,他是北方道上大名鼎鼎的花魔,不知糟蹋了多少良家妇女,是该杀之徒。
“啊”司马茜显然不是对手。“看剑!”司马茜已经亮兵刃,她爹司马长啸封为“天下第一剑”,在剑术的造诣她应该差不到哪里。
韦烈又勉强忍住,他想让司马茜亲手杀死这花魔。
花间狐时而中断,搏斗之激烈可以想见。
盏茶时光,只闻剑刃破风之声.没有金铁交鸣,显然“花间狐”是以肉掌对司马茜的利剑。
“啊!”司马茜的惊叫,想来她已经失利。
韦烈正要掠起……
“住手!”暴喝立传。
韦烈又卸了势,不知来的是什么人?
交手之声顿止。
“梅花剑客?”花间狐的声音。
“不错!”
韦烈心头一震,来的是司马茜的未婚夫方一平。心念一转,他偏开步道,从侧方铁林木而上,到视线所及的位置稳住。
亭外草地上,三人鼎足而立,司马茜与方一平自然成了犄角之势,因为对手只有一个,固定是三角的一点。
现在看清了,“花间狐”龙生年纪不到三十,看上去一表人材,除了目光诡利之外,还真是个俊品人物,不知底细的人谁敢相信他会是个邪恶的采花贼。他正视着方一平,意态还是十分地从容。
“方兄有何指教?”花间狐带笑说。
“别跟我称兄道弟,问你想做什么?”
“没什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已!”
“你知道她是谁?”
“叫紫娘没错吧?
“她是……”顿了顿才道:“本人的未婚妻!”
“噢!”花间狐表示很惊讶:“实在想不到,她是方兄的未婚妻,那是误会了,失礼之至,不过……不得不声明一下,小弟是被动的,如果不是还有点微末之技,已经成了神秘血案中的第六个,方兄懂这意思?”
“你放屁!”司马茜厉叱一声,扬剑就要攻出。
“由我来!”方一平抬手止住司马茜:“龙生,你自己是什么德性你自己心里明白,你的魔掌伸到本人未婚妻的头上自然要还出公道。”
“怎么还?”
“你能逃过本人的梅花剑就可以活下去。”
“好大的口气。”
方一平拔剑,亮势。
韦烈静下心来观察,他还没见识过所谓的“梅花剑”,方一平赖此成名,当然有其独到之处。
“花间狐”的脸色沉凝下来,双手在胸前交叉。
双方凝神对峙,空气骤寒,场面冻结。
“呀!”栗叫声中,方一平长剑挥出,剑尖幻出五点精芒,恰似一朵梅花,玄厉诡辣臻于极致,果然名不虚传。梅花同时攻击五个部位,没留任何间隙,而且快极,令人闪避隔架感无从,的确是剑法中的剑法。
“花间狐”速退,上盘左右胸、心窝及两肋明显现出了五个破洞,梅花形。
“龙生,你真的不赖,能在本人剑下不倒!”
“后会有期!”“花间狐”一扭身电闪逸去。
韦烈敏感地心中一动,尾随追去。土丘下的溪边,“花间狐”停下来检视了一下前胸,自言自语地道:“好家伙,果然是上乘手法,连皮都没破,事先我……”说完,一闪而没。
韦烈已经追上,但他没截阻,因为“花间狐”的几句话使他呆住了。原先在现场觉得方一平出剑虚而不实就觉得内有文章,果然不错,两个人在演戏。
方一平为什么要演这场戏?
想以英雄救美的姿态挽回司马茜的心?
对未婚妻玩这一手不是太卑鄙吗?
司马茜怎会落入方一平的设计中?
韦烈深深地想,觉得此中大有蹊跷,因为司马茜诱杀好色者是事实,方一平是将机就什么。
原先以为方一平是个可交的对象,想不到他是只披羊皮的狼,司马茜不喜欢他是看穿了此人的心地吗?要不是动念跟了下来,由“花间狐”自己说破,还真难以发觉这秘密,该不该管呢?能插手管别人的私事吗?
他又想起了小青,即使是小青的影子也不容许伤害。要管,非管不可。心意一决,他又返身悄然掩上土丘。
月下。
方一平与司马茜依然对立着。
“师妹,你真的不肯跟我回去?”方一平温婉地说。
“我不回去!”司马茜语意坚决。
“可是……师父他老人家已经择定了吉日……”
“这辈子我不会嫁给你。”
“师妹……”
“你就只当我们没认识,司马茜已经死了,我叫紫娘,我根本不认得你,这样说得够明白了吧?”
“你连父母也不要?”
“那是我自己的事,谁也管不着。”
方一平脸色很难看,沉默了好一阵子。
“垣曲城新近发生的血腥艳闻真是你做的?”
“我不否认,我恨透了见色起意的畜生。”
“要是师父和师母知道了……”“你可以去告密,我不在乎。”
“嗯!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
“你看上了‘武林公子’韦烈对不对?”
“又怎样?”
“又怎样”三个字等于是承认了,这使得暗中的韦烈内心起了极大的震撼,这难道是真的?
小青藉着司马茜复活了?可是,自己能夺别人之妻吗?随之而来的是一阵锥心的痛楚。
她不是小青,她不是小青,小青已经死了,永远不会再回到人间了。声音在他的心里大叫,泪水立即模糊了他的视线。
突地,他想起小青的舅舅路遥说过的一句话:“舅舅我一定要为你母女向‘凌云山庄’讨公道……”
讨什么公道?小青自小没娘,是由舅舅路遥当女儿带大的,到了成亲那一天,她一直认为是爹的舅舅才表明身份,可是又坚不说出原因,而小青是难产死的,母子同归于尽,为什么要向“凌云山庄”讨公道?这一定要查明……
“师妹!”方一平显然很痛苦:“没有你,我……”
“你一样可以活得很好!”司马茜似是铁石心肠。
“人生对我还有什么意义?”
“我不是你的人生!”
“师妹,我……究竟是什么地方使你讨厌?”“我说过我们只当不认识,谈不上讨厌二字。”“师妹,你一直说,我发誓会改?”
“我无话可说!”
“师妹,我会等,等你回心转意,即使到老死!”非常感人的话,山海之情,剖心之爱,但现在听在韦烈的耳朵里,丝毫也不受感动,从“花间狐”的话,证明方一平是个卑鄙小人,而与“花间狐”这类人物沆瀣一气的也绝对不会是正派人。
司马茜却不能不感动,毕竟他们是师兄妹,而且还凭父母之命订了亲,她低了低头,又抬起。
“师哥,我不值得你等,你等了也是空等!”“不管你怎么说,我的心唯天可表!”
“我要走了!”
“师妹……”
方一平叫出口,司马茜已飞掠而去。
韦烈心里在急转念头,该不该追下去跟她见面?
方一平口发一声冷笑,阴阴地道:“司马茜,你会后悔,我方一平会等你跪在地上求我,我只消一句话,你这辈子就别想再做人,你会哭不出眼泪!”
韦烈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冷战,他不明白方一平话里的真正意思,但却完全确定了方一平的心性为人。他很想现身出去理论一番,但想到自己根本没有立场,只好把那股无名之火压了下去,但心头又是一个大结。
方一平也离开了。
韦烈转身下了土丘,又站在桥头溪边。
月光下,他的身影得无比地孤独。
他在想许多心事……
不知站了多久,他忽然发觉不远处的溪边也有条冷寂的人影,仔细一辨认,一颗心狂跳起来,是司马茜,她没有远离。
现在,他反而觉得情怯,因为在土丘上的亭子边,她曾向方一平坦白她爱自己。
考虑了很久,他还是步了过云。
人已到了身边,但司马茜一无反应。
“紫娘!”韦烈低唤了一声。
“谁?”司马茜疾望着流水,连头都不转。
“是我,韦烈!”韦烈已感觉气氛有些怪异。
“哦!武林公子,幸会,踏月寻梦吗?”她转过身,神情木然,跟以前的司马茜相比判若两人。
韦烈连呼吸都窒住了,她怎会变成这样?
“紫娘,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也没有,一个梦碎了,又进入另一个梦,恶梦。”她古怪地说。
韦烈皱紧了眉头,看样子自己离开之后她一定受了很大的.刺激,不然不会性情大变,她替自己预付了房饭钱,又向方一平承认她喜欢自己,而现在见了面她却又如此,假使是故意装的,那又为什么?
“紫娘,我不明白……”
“韦公子不明白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她指了指鼻尖。“哈哈哈哈,我怎么样?”
“有什么事可以告诉我,不要憋在心里。”
“我没有事,就算有,为什么要告诉你?你是你,我是我对吗?女人的心事能告诉一个不相干的男人吗?”
“紫娘,你到底在说些什么?”韦烈真想伸手抓住她,但他忍住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你如此?快告诉我,别急坏人好不好?”
“怪了,我们之间算是什么关系,你一再逼问我?”
韦烈真的按捺不住了,双手捉住她的香肩连连摇晃。
“说,快说,天坍下来我会替你顶一半。”
司马茜双睛一红,泪水像断线珍珠般滚落,突地张开双臂,紧紧抱住韦烈,双肩抽动,她哭得很伤心;韦烈搂住她,潜意识里他把她当成小青,小青抱过他也这么伤心的哭过,他记得那是在新婚之后不久,两夫妻在房中喝酒,小青斟酒时壶把无缘无故断折,酒壶砸得粉碎,她认定这是不祥之兆。这时,远远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他俩,眼光很恶毒,是方一平,他在心里发了一百次誓,他要百倍报复。
两人丝毫未觉。
但第三者注意到了,是洪流,他和王道经常是在暗中尾随的,等于是韦烈的另一只眼睛,也是忠实的守护神。
久久,司马茜突然用力推开韦烈。
“我太不争气!”她掠了掠鬓边散发,顺手擦去眼泪。
“什么……不争气?”韦烈愣愕,他的感觉还停留在温馨的拥抱里,突然一分开,他像是失落了什么。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她仰起螓首:“夜夜心,此恨何消,此心何寄,月姐知否?”
韦烈满头雾水,他完全听不懂。
司马茜的心在滴血,自从韦烈走后的那晚,她中了算计而断送了清白,连是谁都不知道,要不是“恨”在支持她,她早已自己结束生命了。突地,她想到了“花间狐”龙生,他既在垣曲出现,能不做这种邪恶事吗?他装作初逢乍见,骨子里是什么?既然被称为“狐”,当然是狡诈万分。她咬咬牙,放平脸注视韦烈。
“韦公子……”
“你不是叫我韦烈的吗?怎么又改了称呼?”
“韦烈?不,那太没礼貌了,武林公子大名响当当,江湖上谁人不知何人不晓,还是称呼公子较为适当。”司马茜一本正经地说:“韦公子,你刚才说,即使天坍下来也愿意替我顶一半?”
“唔!”韦烈的情绪完全被司马茜的怪异言行搅乱了。
“我请你代我做件事。”
“你说?”
“请代我活捉‘花间狐’。”
“活捉‘花间狐’?”韦烈迷惑不解地望着司马茜。
“对,要活口,不要死人。”
“你跟他之间有什么过节?”
“现在还不知道,得由他口中找答案。”
韦烈如坠五里雾中,连东南西北都无法分辨了,他知道司马茜此举必有用意,但他却无从揣测起。
“怎么,你不愿意?”司马茜逼了一句。
“愿意,当然愿意,我会设法把他带来给你!”话锋顿了顿,换了话题道:“紫娘,你为什么要离开那家客栈,不是说好……”
“我有我的理由!”司马茜眸中恨意稍露即隐。
“回去吧!等着我替你找人。”
司马茜思索了片刻,终于点头。
万圣宫。
名虽为宫,实际上是一座破败的小庙,由于地处荒僻,加上年久失修,本来就不盛的香火早已断绝,庙祝耐不住清苦,也弃庙另觅枝栖了,所以等于是座废庙。
韦烈踏着晨曦来到,拨草而入,直达大殿。
神像塑泥已在蚀落,“有求必应”、“威灵显赫”之类的木匾布额也歪斜倒吊,炉冷无烟,蛛网尘封,说不出的凄凉。
韦烈不是来烧香的,他选这地方是图其隐秘。
“公子!”进来的是“梦中刀”洪流。
“什么事?”
“公子前晚在小桥边跟紫娘姑娘交谈时有人窥视。”
“哦!什么人?”
“梅花剑方一平。”
“嗯!这是意料中事,还有吗?”
“没有了,不过,据我观察,他是挟恨含毒。”
“好,我会注意,现在你出去庙外警戒,王道来了就叫他进来。”
“他已经来了,他让我先进来。”
洪流退了出去。
王道迅速地奔了进来。
“公子!”他行了一礼。
“打探的结果怎么样?”
“大刀会跟乌衣帮是兄弟门户,大刀会找上公子目的还是在于‘宝镜’,行动由总管‘鬼算盘’冷无忌全盘策划指挥,副总管宋世珍协助,姓宋的年纪不大,但很有几套,跟冷无忌搭档是红花绿叶,目前帮会已经联手,他们的眼线无孔不入,到处插桩。”
韦烈静静听完,盘算了一阵点点头。
“很好,继续注意对方的动静。”
“是!”
“还有样紧急的任务交代你……”
“嗨!交易热络,生意不断,公子请吩附。”
“赶快设法打探出‘花间狐’龙生的行踪。”
“花间狐……这只雄狐很难缠,好吧!”
“一有消息马上用老方法通知我。”
“遵命!”
“没事了,你去吧!”
王道施礼退出破庙。
韦烈一个人在静静分析眼前的状况——大刀会与乌衣帮联手图谋“宝镜”是不自量力。
“鬼算盘”冷无忌是相当邪刁的人物。但也不足虑。
自己已得到“藏珍之钥”,以后就看机缘了。
“梅花剑”方一平认定自己跟他的未婚妻司马茜发生了感情,采取报复手段是意料中事,只有好好应付一途。
目前最要紧的问题是司马茜性情突变,是什么原因?是否能从“花间狐”身上找出答案?
方一平伙同“花间狐”设计司马茜为的又是什么?自己已决定要插手,这决定是不是一个错误?最后,他又想到小青。
司马茜是小青的化身,而小青的舅舅路遥要向司马长啸讨公道,这情况相当诡谲,其中到底有什么蹊跷?
从而,他又想到天仙化人的白衣女子冷玉霜,那是个不可思议的奇特女子,想起来就让人心神不宁,她说过彼此一定会再见面,会有什么样的演变?
想了一阵,他也离开了。
入夜,旧梦重温。韦烈与司马茜的房中挑灯夜饮,但气氛与他赴中条山之前大不相同,司马茜的表现完全反常,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闹,澈底的放纵,完全不像个大家女子,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韦公子,今晚不醉不休!”
“好,我奉陪!”
“干杯!”
“干!”
韦烈在应付着,但应付得很痛苦。突地,他想起方一平在小桥头土丘凉亭自语时说过的一句话:“我只消一句话,你这辈子就别想再做人,我要你哭不出眼泪!”这句话暗示了什么?
莫不是司马茜做了见不得人的事。
他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寒噤,直勾勾地望着司马茜。
“为什么要这样望我?”司马茜醉眼迷离。
“没什么,我怕……你是醉了!”韦烈虚应着。
“酒醉……心明白,你……想要什么?”这句话极尽煽情,也明显地挑逗,她怎会说出这种近乎无耻的下流话。
韦烈呼吸一窒,接不上话。
他完全无动于衷吗?不,他是男人中的男人,怎会不动心,只是他理性极强,言行有一定的规范,他不会作出失礼败行的事。但控制理性是很痛苦的事,因为他已也当作小青的化身,情感的冲击是很大的。
“韦公子,随便说笑而已,不要……介意,我司马茜可不是低三下四的……”
“什么,你叫司马茜?”韦烈打蛇随棍上。
“我……说了吗?”司马茜惊觉已是不及。
“你说了,说得很清楚,不过……我仍然叫你紫娘,这比较顺口,不管你是什么来头,在我心目中你是紫娘。”
司马茜木然许久,泪水滚落,又一笑试去。
“为什么不叫,我小青?”
“叫你……小青?”
韦烈像是突然被人在心上扎了一针,全身起了痉挛。
“怎么样?”司马茜偏起脸。
“你……愿意做小青?”韦烈很费力的挤出这句话。
“当然愿意!”说完,突地神情一黯:“不,不愿意,我不配做你的小青,我……已经失去了资格。”泪水又涌了出来。“什么意思?”韦烈意识到快要接触到问题的重心。
房门突然被推开,一个威仪十足的老者站在门外,神光炯炯地双眼令人不敢逼视,脸是是怒极之色。
韦烈大吃一惊。
司马茜站起身来,娇躯微见发抖。
“爹!”她唤了一声。
“别叫我爹!”老者厉声吼叫。
韦烈一下子省悟过来,来的是名震武林的“凌云山庄”庄主司马长啸,他立即起身,在原位抱了抱拳道:“原来是司马庄主,失敬,幸会!”
“你就是‘武林公子’韦烈?”
“晚辈正是!”
“你是吃了天雷豹子胆,竟敢勾引老夫的女儿?”
“这……”韦烈的脸胀红了,两人在一起喝酒,而且是在店房中,这实在难以解释,也非三言两语所能解释,所以说不出话来。
“哼!这帐慢慢再算。”
“爹!”司马茜脸色连变之后开了口:“勾引二宇多难听。”
“丫头,你想气死爹娘?现在跟我走!”
“走?去哪里?”
“丫头,你……你……你……当然是回家。”“我不回家。”
“你敢再说一遍?”
“我不要回家!”
“好哇!丫头,你……反了!”司马长啸老脸已变青,连连抽搐:“我只当没生你这忤逆的不孝女,你不走,……很好,虎毒要食子,我带你的尸体回去。”说着,跨入房中。
父女已经决裂,情况非常严重。
韦烈不知如何是好?
司马长啸暴怒地瞪着司马茜,激越万状地道:“司马家宁可断后,也不能留你这败坏门风的东西。”
司马茜了无惧怯地道:“我哪里败坏门风?”
司马长啸怒吼道:“事实在眼前,你还要狡辩?”
司马茜扬着脸道:“交个朋友也不可以吗?”
马长啸猛一跺脚道:“气死我了,你这忤逆不孝的东西,是我宠坏了你,才会有今天的收场!”右掌扬了起来,但手在空中没有落下来。
“司马茜惨然一笑,噗地跪了下去,显得很平静地道:“爹,女儿的生命是你给的,你可以取回去。”
说完,闭上双眼,从容等死。
司马长啸浑身直抖,老脸阵阵扭曲,掌劈不下去。
韦烈再也忍不住了。
“司马庄主,能准许晚辈说一句话吗?”
“你……居然还敢开口,你比这丫头更该死!”
“晚辈只有一句话,晚辈与令嫒之间是清白的,并无儿女私情,纯粹是道义之交,请庄主明察。”
“韦烈,你……你说得冠冕堂皇,男女之间何来道义之交,城外溪边你跟她发生肌肤之亲,怎么说?”
韦烈心头一震,随即明白过来,洪流曾禀报当时方一平在暗中窥视,不用说,这问罪之师是他安排的。
司马茜张开眼上望。
“不能怪他,是女儿受了委曲情不自禁,虽然双方肌肤相接,但绝无邪念,女儿可以对灯火发誓……,”“住口!我不听你狡辩。”
“女儿只表明心迹,不是求饶,请下手吧,死在爹手中,心安理得。”她倔强得相当可以,丝毫也不屈服。如果她说几句忏悔的话,情况就会改观,但她没有,她自被无名的邪恶者强暴之后,心已死了,她活着是为了报仇,而现在她报仇的意念也消失了,不白之身虽然负屈而死,总比张扬开来有辱门楣更好。
韦烈当然不能袖手看这人伦悲剧上演。
“司马庄主,您不给令嫒辩白的机会吗?”
“还有什么好辩白的?”
“有,晚辈已觉出端倪,但不明事因。”
“你师出何门?”司马长啸似乎已经软化。
“家师‘枯木老人’!”韦烈目光如电芒般一闪。
司马长啸老脸大变,放下手,后退一步。
“你……是‘枯木’的传人?”声音有些颤抖。
“是的!”
司马长啸瞪视着韦烈,久久无言,最后自语了一声:“冤孽!”
韦烈一愣,对方的“冤孽”二字是什么意思?
“起来!”司马长啸显然气馁。
司马茜起身。
“跟我回去!”
“不!”
“你……还要强?”
“女儿会回去,一定会,但不是现在。”
“什么理由?”
“女儿目前有一桩比生死还要严重的大事必须了断,此事不了,死不瞑目,事完一定回家。”
“不让我替你作主?”
“不,除了女儿自己,谁也无法作主。”
司马长啸怔望着他这任性而倔强的女儿,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他完全猜不透女儿的心事,但他相信,因为这宝贝女儿任性归任性,却从来没说过半句假话,也从来没狡词掩饰过,什么事。
韦烈敏感地想到司马茜所谓的大事必与“花间狐”龙生有关,至于内情到底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他插不上嘴,也不想插嘴,该说的已经说了。
“我会查明!”司马长啸再次深深打量了韦烈几眼,转身出房而去,房门外传回来一声叹息,做父亲的屈服了。
沉默了一阵。
“紫娘,你应该随令尊回去的,这孝顺……”
“事不了,我不会踏进家门一步。”
“到底什么事?”
“还不到告诉你的时候!”
韦烈吐了一口气,他不想再追问下去。
“还继续喝酒吗?”
“要,说过不醉不休!”
任性就是任性,刚刚经过了这么大的风浪;她居然还有兴致喝酒。韦烈又坐回原位,心里得到了一个启示,自己昂藏七尺之躯,有些事却不如一个女子提得起放得下,的确,有的时候是需要这种坚强的。
“小烈!”一个手提拐杖的老人已来到门外。
“啊!舅舅。”韦烈大感意外,忙又站起。
“是你舅舅?”司马茜也很感意外。
“是的!”韦烈顺口回答。
来的是小青的舅舅路遥。
“舅舅怎么会找到垣曲来?”
“听到你在此地出现的风声,所以便赶了来。”
“有事吗?”
“有。”
“快请进!”韦烈上前扶进老人,然后关上房门。
路遥望向司马茜两眼登时发直,栗声叫道:“小青?”
“我……”司马茜错愕:“真的如此像小青?”
“舅舅!”韦烈引介:“她叫紫娘!”在真相未明之前,他不想说出司马茜的真实来路,怕节外生枝,因为路遥说过要向“凌云山庄”讨公道,同时,司马茜也没有对外公开自己的出身来历。
“她是小青……”路遥声如梦呓,老眼发红。
“舅舅,她不是小青,她叫紫娘,她,两个……是长得很像。”韦烈伤感地说:“我们不久前才到小青的坟上烧过纸,她已经整整走了一年。”
“她……走了一年。”老泪挂了下来。
司马茜忙挪椅子。
“舅舅,你请坐!”
“你……也叫我……?”路遥泪眼凝视,他似乎要从司马茜的身上,找回爱逾性命的小青。
“是的,我跟韦烈一样称呼您,可以吗?”
“那太好了,当然可以。”路遥坐下:“小烈,你跟紫姑娘……”
“我们是在洛阳认识的,起先我也把她误认为是小青。”实际上并非认识,他是把她当作小青的影子,对路遥他不能不这么说。要不是这层原因,两人不可能凑在一道,自小青不幸之后,他已经无法接纳任何女人。
“舅舅,我要店家重备酒菜……”司马茜突然对这舅舅感到兴趣,在礼数上便自然地表现得很好。
“好,好,有你陪着,我好像……”后半句没说出来,但听的人一听就明白,后半句应该是好像小青陪着我一样。
司马茜出房吩咐了小二,然后又回房。
“舅舅,你说……找我有事?”韦烈问。
“是有事,我想很严重。”
“嗅!舅舅请说。”
“最近一个月,我接连发现三次有一个神秘人物在小青坟前打转,不知目的何在?”一顿又道:“那鬼东西的身手太高,我竟然无法接近他,只要一踏入五丈之内,他便像幻影般消失,如果我信鬼,一定会把他当成鬼。”
“有这种事?”韦烈两眼瞪大。
“我觉得很奇怪,小青并非江湖人物,只是个无名的普通女子,说什么也不可能引起人注意,而且那只是一座随处可见的小坟,如果是一次,也许是巧合或误会,连来三次可就有蹊跷了。”
“更不解的是那神秘人不是普通高手,碑上明刻着‘爱妻小青之墓’,你不是普通人物,这当中可能牵涉到你,所以我说很严重。”
韦烈静静地思索了一阵。
“舅舅,我明天就去守候:一定要查明原因。”
“目前也只好如此。”路遥自我解嘲地笑笑:“说句丢人的话,我自忖对付不了对方,所以只好找你。”
“舅舅,这本来就是我的事,对方如此做说不定就是冲着我来的,必然有其特殊的目的,不过……对方选上小青的坟,这点实在令人想不透。”韦烈皱了皱眉,心头像压上了一块千钧巨石,小青死了,但仍是他的命。
司马茜口唇连动之后才找到机会开口:“你明天就去吗?”
“是的,这事不能耽延。”
“人不是每天在那里,你去一定能碰上?”
“对方的目的分明就是我,我去了他必现身。”
“我能陪你去吗?”
“紫娘!”韦烈温和地说:“你去了不方便,而且……你最好不要淌浑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那我……还是要在此地等你?”
“最好是这样。”
“那关于我拜托你找……”
“我已经另外着人打探,不过……要对付‘花间狐’那种邪恶人物,恐怕你一个人太危险,得等我回来。”“好吧!”司马茜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小二端来了酒菜杯箸,重新摆整。
一老二少入座畅饮。
另外一家客栈。
也是客房,一老一少也正在喝酒。
老的是“凌云山庄”庄主司马长啸,少的是他的爱徒兼准女婿“梅花剑客”方一平,但没有丝毫欢愉的气氛,两个的神色都很凝重。
“爹!你答应师妹留在外面?”方一平态度相当恭谨,师父改称爹,表示他的身份已完全肯定,超过了半子之分。
“暂时由她,她是宁折不弯的性子,逼急了……”
“爹说的是,不过……有句话一平不敢说……”
“你尽管说,为师的早已把你当成自己的儿子,有什么话不敢说的,就是说错了也没关系,你说!”
“说出来……爹定会生气。”
“一平,你是怎么啦?变成了婆婆妈妈!”
“爹,这个……”方一平又犹豫作态了一阵,才以很为难的样子道:“一平是斗胆妄测,也许是错,但目的是为了司马家的名声。师妹跟‘武林公子’从洛阳到垣曲,同出同入,已经很多时日……”
“你的意思是……”司马长啸的脸色变了。
“师妹的身体……可能已经属于韦烈。”方一平低下头,脸上现出非常痛苦的样子,为了尊重师父而尽量压抑下胸中的那股怨气:“一平蒙爹收容,视同已出,跟师妹一块长大成人,这桩婚姻是爹和师娘一起作的主,恩同山海,粉身难报,不过……人各有志,一平说什么也不敢怪师妹……”
“不要说了!”司马长啸按住酒杯的手缓缓降下与桌面齐平,一只酒杯已完全嵌进桌面:
“真有这种事?”
“一平只是据理推测!”
“这死丫头,如果真的……我不会饶她。”
“爹!”方一平抬起头:“师妹是不会承认的,也许……她会找很好的理由搪塞。”
“我还没昏聩。”
“是的……不过……”
“又什么不过?”
“要究明这种事,师娘出马比较方便。”
“唔!”司马长啸深深点头。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