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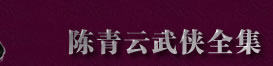 |
|
 |
|
 |
| |
|
第十二章
|
|
华锦芳被白石玉这一说,益发相信灰衣人的话不错,厉叫道:“‘冷面客’,你说是不说?”
白石玉立即帮腔助势道:“兄台还是坦白说出的好……”
武同春气极,算是有了发泄的对象,向白石玉迫近两步,寒声道:“该说出内情的是你呀,今天你休想再弄狡狯。”
白石玉口角一撇,道:“在下一向以和平处世为原则,任何事都可以和平解决,流血拼命,解决不了问题,也难有真正的是非……”
冷哼了一声,武同春道:“你在路上用鬼贼手段杀了‘天地会’左护法和六名武士,这也叫和平?”
白石玉面不改色地道:“天下事不能说绝无例外,得看对象而定。”
武同春不屑地道:“天下的理,都被你一个人占尽了?姓白的,在下不耐烦开口,今天你不交代清楚,可能又要破例了。”
白石玉道:“是威胁么?”
武同春道:“随你怎么说都可以!”
华锦芳喘了口气,道:“这位白少侠在现身时,说要少侠证明,说明什么?”
白石玉道:“武大嫂,事情太简单,既然这位见台声称是武大侠的生死之交,又受托办事,还接受了武大侠的兵刃,我们相信这位兄台先后所说的全无虚言,最直截了当的证明方法,便是带路找到武大哥,一切不就都迎刃而解了。”
华锦芳点头道:“不错‘冷面客’,你怎么说?”
武同春深深一叹,道:“好,小弟可以带大嫂去见武大哥!”
白石玉道:“你可要言而有信?”
武同春冷极地一笑,道:“没你姓白的份!”
白石玉挑眉道:“谁能保障武大嫂的安全?”
华锦芳心头一动,如果这“冷面客”心怀叵测,对自己不利的话,的确没有反抗的余地了,功力悬殊太大了。
武同春女口刃目苍在白石玉面上一绕,道:“凭你就能保障别人的安全么?”
白石玉分毫不让地道:“至低限度可以有个人证,不会变成无头案,是吗?”
武同春嗤之以鼻,道:“姓白的,别浪费心机,如果在下想杀人,随时都可以办到,不必费这多周折。”
白石玉针锋相对地道:“问题在于你兄台隐藏在内心的企图。”
武同春目中煞芒一闪,道:“可惜你没机会参与这件事……”
白石玉道:“为什么?”
武同春一字一句地道:“因为我要杀你,而且就是现在。”
白石玉下意识地向后挪了一步,依然很沉静地道:“兄台办得到么?”
“事实会告诉你。”
“如果在下不跟你打……”
“那是你自己放弃保命的权利!”
“在下不会放弃的。”
“很好,准备保命吧!”如霜白刃,扑了起来。
华锦芳冷厉地道:“你打算杀人灭口,以遂阴谋么?”
“这是小弟与姓白私事,与大嫂无关。”
“但事实上已有关了。”
“大嫂阻挡不了。”
“我会不计生死地一试。”
白石玉淡淡一笑,道:“武大嫂,你放心,他杀不了在下!”
武同春向前一迈步,道:“那就证明一下?”
话声中,正待出,只觉眼一花,白石玉已到了三丈之外,这种身法,简直与鬼魁无异,人似乎很难办到,武同春怔住了。
白石玉在三丈外沉声道:“在下全身而退,总可以办得到的吧?”
武同春愤火中烧,厉哼一声,闪电般扑去,白石玉掠上了屋面,武同春如影附形而上,一追,一逃,如两抹淡烟般消逝。
华锦芳也登上屋面,但已失去了两人的身影,她自忖绝对无法与这两个鬼魁般的人物角逐,只好站在屋面上发呆。
空地,身边多了一个人影,华锦芳心头剧震,本能地横闪数尺,一看,吐了口大气,激动地道:“原来是伯父!”
不速而至的,正是灰衣人,事实上他并未远离。
灰衣人沉声道:“锦芳,这件事很复杂!”
华锦芳道:“伯父,您跟‘冷面客’动过手,到底证实了没有?”
灰衣人道:“似是而非,还须要找旁证。……”
华锦芳脱口道:“难道伯父斗不过他?”
灰衣人笑笑道:“上焉者用智,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并非伯父我收拾不了他,而是临时改变了主意,他还有身后人,更加可怕,不能不谨慎从事。”
华锦芳粉腮一惨,凄声道:么说,同春他……八成是不幸了?”
灰衣人沉凝地道:“目前还说不定,我会尽力查明此事。锦芳,你回在房去.不要出来乱闯,一切有伯父我替你作主,你等我的消息。”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泪水在眶内打转,华锦芳点了点头,暗道:“我会失去丈夫么?我该怎么办?凭我这点能耐,能做什么?”……泪水滚落粉腮。
灰衣人一副长者之风,用手拍拍华锦芳的香肩,慈和地道:“锦芳,别难过,一切会很好的!”
武同春生死玄关已通,功力已达一个巅峰状态,白石玉身法虽然出奇地快,但他不虞追丢,能保持一定距离。
固然不会追丢,但在同等速度之下,要想缩短距离也很困难,像这种疾驰法,内力损耗非常可观,就要看谁的内元深厚,能坚持不坠了。
追逐了近十里,白石玉的身法已显迟滞,失去了轻灵。
距离逐渐缩短,武同春猛运内力,以凌风之势超到头里。
白石玉刹住身形,俊面一片苍白,喘息不止,如果再奔下去,他定会脱力。他本长得斯文瘦弱,眼前的神情,加上他腮旁的红藉,的确像个女人。
武同春气势还保持从容,似乎他的内元用之不竭,目芒一闪,道:“白石玉,你逃不了的!”口里说,心里仍一分震惊对方的超凡身法。
白石玉深深吸了几口气,调匀了一下呼吸,微喘着道:“兄台好像又增添了功力,大异往日?”
他居然有闲情说这话。
武同春森冷如敌地道:“我不跟你叙旧,事情非有个了断不可。”
“如何了断?”
“说出找武同春的真正原因。”
“说过是为了朋友正义。”
“鬼话。”
“兄台不信,在下有什么法子?”
“很简单,想办法让我相信!”
“否则呢?”
“手底下见真章。”
白石玉默然了片刻,目珠连转,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我都自认是武同春的至交好友,问题在于无法互相证实,所以才互相疑忌,兄台以为然否?”
武同春无情地道:“不然!”
“什么意思?”
“你居心叵测!”
“兄台是只知道有自己,没有别人,如果这句话由在下说……”
“你不配,因为在下与武同春是性命之交,如果有你这么一位知己朋友,他不会不告诉在下。”
“这仍然是一厢情愿的说法,在下也是如此想。”
“你的真正来路呢?”
“哈哈,在下有名有姓,而兄台只有个可能是杜撰的外表,说起来,到底是谁的来路不明呢?”
武同春为之语塞,但自己就是自己,自己不承认他是朋友,还有什么可以争辩的.难道真的要制造另一个武同春?当下把心一横,道:“在下没兴趣跟你泡蘑菇,干脆些吧!”
白石玉声调一变,道:“兄台放明白些,到底谁能杀谁还不能肯定,不过有一样可以肯定,兄合算能杀得了在下,兄台也绝对活不了。”
武同春心中一动,道:“危言耸听么?”
“这可以马上证明的。”
“好,就证明吧”
“在下之所以委曲求全,是怕铸成大错。”
“什么大错?”
“只怕造成亲者痛,仇者快的局面。”
这话有些莫测高深,武同春略略一怔,道:“谁是亲,谁是仇?”
“目前很难说。”
“废话!”
“这决非废话,也不是在了信口开河,有根据的。”
“由于白石玉行动鬼祟,而是不止一次言词反复无常,是以武同春并不为所动,冷冷一笑,显得很漠然地道:“什么根据?”
白石玉沉声道:“比如说,江姥姥之死,与兄台之遭受灾袭……”说了一半,便顿住了呀。
武同春闻言之下,不由心头剧震,这件事极可能与父系之死有关,因为江姥姥是在行将吐露实情之际被杀的,凶手的目的显系灭口,而自己在失神之际也遭碎袭……当下激动万状地道:“你知道谁是凶手?”
白石玉颔首道:“当晚在下也凑巧到场,还追了对方一程,当然知道。”
武同春一想,道:“当时你说没看清?”
白石玉道:“是没看清面目,但事后想起对方的身影和身法。”
武同春迫不及待地道:“是谁?”
白石玉略作沉吟,道:“兄台该说的不说,在下……有奉告的必要么?”
心火股股直冒,武同春大声道:“你是寻开心么?”
白石王挑眉道:“这并非寻开心的事。”
武同春气呼呼地道:“那你就说出来!”
“在下有这义务么?”
“是你自己提出来的!”
“不错,是在下提起的,不过……目前兄台身份不明,这件事关系重大,最妥当的办法是面告武大哥。”
绕了个大弯,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他用尽心机,想达到目的。武同春两眼发了蓝,冷哼了一声道:“说了半天,你还是想套出武同春的下落?”
白石玉期期地道:“在下……不敢冒这大的险告诉兄台。”
武同春不耐地道:“不说拉倒,反正你的话未必可信。”
口角一撇,白石玉道:“兄台这么一说,在下倒是要赌这口气,置上一次险了。江姥姥死后,身上并无显著伤痕,可以说是无痕,对么?”
心中一动,武同春道:“不错,是死后无痕。”
白石玉凝重地道:“即在下告诉兄台,凶手是灰衣人!”
如触了电似地全身一震,武同春连退三步,栗声道:“灰衣人?”
“不错!”
“这怎么可能?这……他为什么要杀江姥姥?”
“他也曾对兄台下手,又为什么?”
“我不信,你说谎,居心可怕,你的目的是想……”
“兄台不信?”
“不信,记得当晚灰衣人是跟武大嫂一路回家的。”
“那兄台错了!”
“什么意思?”
“灰衣人是在外与武大嫂会合的,以他的能耐,尽可在杀人??假装逃走,然后绕回来会合武大嫂。”
武同春猛打一个寒噤,颤栗地道:“难道武大嫂跟灰衣人是共谋?”
白石玉冷冷地道:“武大嫂是否共谋,就不得而知了。”顿了顿,又道:“可能么,这……不可能,太可怕了。”
武同春的心起了痉挛,这实在太可怕了,双眼一瞪,冷厉他道:“姓白的,如果你说了假话……”
白石玉不假思索地道:“这又不是死无对证的事,兄台可以马上回头去问武大嫂,不就结了么?”
武同春咬着牙道:“如果你是为了脱身而说谎,我会把你撕碎。”
冷冷一笑,白石玉道:“一句话,咱们之间的事,在武同春没现身之前不算完,兄台不找在下,在下也要找兄台。”
他的口风与态度显得很强硬。
情况诡谲万端,武同春已失去了主意,真不知如何是好,心头像一堆理不清的乱麻,找不出头绪。
白石玉拱手道:“后会有期了。”
一弹身,翩然而逝。
武同春没阻止,也没去追,他深深陷在丝乱的情绪里,努力地想,想从纷乱中找出头绪来,他回想那晚的经过——回到在房,见到江姥姥,获悉父亲是伤于“无影戮心手”而不治。
惨号声引去自己,江姥姥被害。
惊悟中计,回到原处,失神之际,猝遭突袭。
暴喝声起,人影追逐。
“天地会”巡监司马一夫率手下来,说是收尸。
灰衣人便与华锦芳一同回转,灰衣人击杀司马一夫……想到这里,突地一顿脚,厉声自语道:“华锦芳是有与灰衣人共谋的嫌疑,但这是为了什么?司马一夫怎会来收尸?如果说凶手是灰衣人,而灰衣人是‘天地会’的人,他为何杀自己人,司马一夫地位不低……”
心念之中,弹身反扑无双堡。
为了急于揭开谜底,武同春全速驰行,快如飘风。
行程过半,忽见远远一个女人身影,从前道缓缓行来,身影太熟,一眼就能判定是华锦芳。
她正走向赴在房的回程,武同春缓下势来,心急电转:“如果华锦芳真的与灰衣人有所勾结,她便不会承认,夫妻,难道要动武不成?还有,白石玉说的可靠么?这实在是个难题,极难处理……”
华锦芳身影接近,她似心事重重,走路低着头。
武同春现身道中。
华锦芳惊觉抬头,“啊”了一声,粉腮大变;厉声道:“是你?”
武同春强持镇定,沉声道:“是小弟。”
华锦芳咬咬牙,道:“你意欲何为?”
“有件事……想请问大嫂。”。
“你!准备玩什么花样?”
“没有,是真的有多请教,所以才回头。”
“什么事你说吧!”
整理了一下思绪,武同春徐缓地道:“贵府老管家江姥姥遇害那晚,大嫂是偕同灰衣人一起回家的……”
华锦芳眸光一闪,道:“不错,怎么样?”
武同春接捺住激越的情绪,放作平静地道:“请问大嫂,那晚大嫂与友衣人是远路同归的,还是在在门外才碰上?”
怔了怔,华锦芳道:“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武同春道:“当然有道理的,请大嫂据实相告?”
华锦芳惊疑地望着武同春,久久才道:“是在在门外碰上,才一道进门的。”
一句话,证明白石玉所说的并非凭空捏造,武同春狂激起来,连退了三个大步,眸中闪射骇人的光焰。
灰衣人杀人的目的何在?只有一个可能,灰衣人便是二十年前,伤害父亲的仇家,现在找上门,想根绝祸根,准此而论。
当也就是杀害“无我大师”的凶手,因为圣僧师徒知悉这桩陈年旧案。
华锦芳不安地道:“你什么意思?”
她既然说了实话,就证明没有共谋的嫌疑。
武同春定定神,道:“大嫂真的不知道灰衣人的来历?”
“你到底企图何在?”
“想证实一件事!”
“证实一件事……什么事外武同春口一张,又闭上,心里急忖:“这秘密暂时不能让她知道,如果露了风,说不定会发生意外,而自己却无法维护她。”
华锦芳有她的心思,她自忖绝不是眼前这诡秘的。冷面客”对手,灰衣人已答应管这件事,所以她绝口不提在堡内的那回事,只恨在心头。
默然了片刻,武同春含糊地道:“大嫂请便,没事了!”
华锦芳欲言又止,最后,疾步离去。
望着妻子的背影,武同春的心,又感到再一次剧烈的痛苦,有家归不得,夫妻相见如陌路,这的确是人间的大悲剧。
看着,看着,他的视线模糊了,两滴清泪,夺眶而出。
华锦芳的身影消失无踪,她,不幸成了这场悲剧中的无辜受害者。
白石玉的话,已经证实,灰衣人是凶手,可是动机呢?他杀了江姥姥,杀自己未遂,但仍没放过。为什么?白石玉也相当诡诈,这当中会有连带关系么?如果说,灰衣人旨在灭口,那他就是杀父仇人无疑。可是?江姥姥死了,二十年前的旧案,线索内断,从何查起呢?由于意识的作用,武同春又踅回无双堡,堡门已封,他照往常习惯越墙而入,不自觉地走向废墟。
凝碧已死了八年,幽冥异路,但凝碧生时的影子,仍很鲜明地闪现在他的脑海,他得承受这无尽期的精神折磨。
突地,他发现一条人影,兀立在凝碧墓前的空地上,负手仰头,像一尊石像,白衫佩剑,长的一分英武,看上去年纪在二十七八之间。
奇怪,这陌生武士到此何为?武同春缓缓迫近前去,直到对方身前不足一丈之处。
白衫人冷冷扫了武同春一眼,又转头望着空处,那份冷做,令人受不了。
武同春惊诧地望着对方,也不开口。
白衫人喃喃自语道:“迟了,我来迟了,无双堡已成废墟,人大概死绝了。”
武同春一听对方话中有话,大为震惊,冷沉地开口道:“朋友何来?”
白衫人道:“你是谁?”连头都不转,一副目中无人之态。
武同春冷傲之性突发,反问道:“你是谁?”
白衫人徐徐转过身,面对武同春,冷电似的目芒在武同春面上一绕,道:“你不会是无双堡的人吧?”
心中一动,武同春道:“朋友先表明身份来意,在下自会相告。”
“如果你不是堡中人,就不必说了!”
“看样子……朋友是来讨债的?”
“听口气,你是堡中人?”
“纵使不是,也有相当渊源。”
“好,你说说看,是什么渊源?”
“朋友还没表明身份?”
“天南一剑童光武!”
人陌生,名号也陌生,武同春心念一转,道:“在下‘冷面客’。”
一顿,又道:“朋友来自南方?”
“不错!”
“来此何为?”
“对笔旧帐!”
“讨帐……什么帐?”
“你是‘无敌剑’之后,还是门人?”
提到父亲昔年名号,武同春不由激动起来,对方既然称是来讨帐,当然是陈年老帐,因为父亲已经过世二十年,对方年纪不大,显系上一代的恩怨,父债子还,这件事非接下不可了,但以什么身份呢?深深一想,道:“都可以!”
童光武剑眉一挑,道:“什么叫都可以?”
武同春道:“在下也姓武,份属武氏同宗,而且也承受了艺业。”
童光武目芒大盛,寒声道:“听说少堡主叫武同春,是个美男子,他人呢?”
心弦一震,武同春道:“他目前不在此地……”
“你带我找他。”
“可以,但请说明来意?”
“区区要当面对他说。”
“那就无法从命了。”
“你……”
“在下可以作大半主。”
童光武默然了半晌,才冷极地开口道:“好,告诉你无妨,二十年前,先师与‘无敌剑’在洞君山论剑,本属砌磋,武进竟然下了狠手,以‘无敌剑法”断了先师一臂,先师因此含恨而殁,因此区区特别来到中原,领教‘无敌剑法’,进人中原后,才知道武堡主已经作古,只好退而求其次,找他的后人了这笔帐。”
武同春为之一震,他根本不知道父亲生前有这一门过节,咬咬牙,道:“请问令先师名讳?”
“这不必告诉你!”
“在下说过可以作一半主。”
“一半,那表示不能完全作主……”
“也许能!”
“区区找的是武氏之后,并非是你。”
“在下已经表明过身份,有资格接下这过节。”
“区区说你没资格。”
武同春想了想,道:“朋友的目的是寻仇报复;还是想证明什么?”
童光武道:“证明一下‘无敌剑法’是否真的无敌!”
因为父亲过世早,武同春事实上并没得‘无敌剑法’的全部精髓,不过招式倒是没遗漏的,以他目前的内力修为,还可以一试的,心念之中,道:“证明了又为何?”
童光武气势迫人地道:“如果证明武氏所创剑法并非无敌,区区只要带走一只手臂,不想杀人。”
武同春激声道:“带走一条手臂?”
“不错,这是公道。”
“朋友办得到么?”
“你不配问这句话!”
“在下接受这挑战。”
“愿意牺牲一条手臂?”
“不错,这算不了什么。”
“可惜区区的对象不是你。”
想了想,武同春冷然道:“在下是武氏一脉,也承受了家业,一样以‘无敌剑法’应战,如果不敌,奉上手臂,再由少堡主出面,如果幸胜一招半式,少堡主便没出面的必要,朋友就请回转天南,这公道吧?”
童光武冷笑了一声道:“你想白搭上一条手臂作利息?”
武同春目甚一闪,道:“这还得有待事实证明。”
童光武道:“如果区区不接受呢?”
武同春断然地道:“不过这一关,朋友就休想见到武少堡主。”
冷极地一哼,童光武道:“这可是你自找的?”
武同春道:“就算是吧!”
葛在此刻,一条人影从残垣中一歪一斜地走了出来,赫然是“鬼叫化”,武同春精神大振。
“鬼叫化”直迫两人身前。
童光武目芒一扫,皱眉道:“阁下何方高人?”
“鬼叫化”嘻嘻一笑道:“不是摆明着是要饭的么,还用问!”
武同春抱拳道:“您老,久违了!”
“鬼叫化”道:“可不是,一晃就两个月了,你们……怎么回事?”
童光武冷声道:“请阁下离开如何?”
“鬼叫化”偏头道:“为什么?”
童光武道:“照江湖规矩,解决私人争端,不欢迎第三者插脚。”
“鬼叫化”咧嘴一笑道:“碰上了,老要饭的作个见证人,如何?”
童光武道:“不必,阁下还是自便的好!”
一翻眼,“鬼叫化”道:“要走,你们走,老要饭的可不走!”
童光武脸色一沉,怒声道:“什么意思?”
“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老要饭的先到,你们后到,要走你们走!”
“阁下要硬插一手?”
“谈不上,老要饭的绝不会动手。”
“阁下是存心……”
“老要饭的在此地已经睡了一大觉,你们来还只片刻,总不能后到的赶走先来的,这不像话。”
童光武气呼呼地道:“阁下讲理么?”
“鬼叫化”道:“老要饭的不正在讲理吗?”
武同春淡淡地道:“这并非见不得人的事,有个见证又何妨?”
“鬼叫化”一拍大腿,道:“这才像话。”
童光武无奈何地狠瞪了“鬼叫化”一眼,道:“丐帮帮规极严,一向不许帮中弟子干预江湖是非,以阁下的年龄看来,在帮中多少有点地位,为何干冒帮规之所不许?”
“鬼叫化”怪叫道:“好哇!小子,范天豪对我要饭的也不敢如此放肆,你竟然教训起老叫化来了,哼!”
童光武神色大变,后退了一个大步,栗声道:“阁下认识先师?”
“鬼叫化”大刺刺地道:“岂止认识,多少还有那么点香火情。小子,你听着,范天豪什么都好,就是坏在太于好名!”
童光武又退了一步,怔望着“鬼叫化”,期期地道:“阁下想来便是丐帮首座长老‘鬼叫化’?”
“鬼叫化”摸了摸下巴,道:“什么想来,本来的就是!”
童光武沉声道:“很好,阁下就见证一下吧!”说完,转注武同春道:“话可是你说的,输了自断手臂,同时要武进的儿子出面?”
武同春慨然道:“当然,大丈夫一言九鼎!”
“鬼叫化”斜着眼道:“老弟,你真的要跟他斗?”
武同春将头微点,道:“这是无法避免的事!”
“鬼叫化”道:“老要饭的不以为然,人家找的是武氏后人,你何必越俎代庖?”
武同春有苦说不出,这本来就是他的事。
童光武冷冷地道:“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武同春傲然道:“在下从不出尔反尔,准备了?”
双方拔剑,各取位置,凝神对峙。
“鬼叫化”摇摇头,感慨地道:“武林中仇连怨结,多半为了虚名之出,说穿来何苦,事实上又能证明什么呢?证明了、又得到什么呢?”
这大道理谁都懂,但要勘破却很难,劝别人容易,一旦自己成了当事人,便无法克服这人性上的弱点。
武同春与童光武又何尝不懂,但有所为与不为之间,本就没严格的分野,端看各自的想法与做法,孜孜求名不可取,完全否定了名之一字,也属不可能。
双方的气势都无懈可击,同属绝顶剑手,鹿死谁手,尚难预卜。
夕阳,把两人的身影拉得很长。
紧张的气氛,令人窒息。
童光武的额头鼻尖沁出了汁珠,而武同春的情况稍为好些。
这种对峙,是内力和定力的比拼,较之挥剑搏杀还要凶险,只要一方稍弱,致命的打击立至。
足足盏茶时光,人僵化了,投射在地上的影子也僵化了。
“鬼叫化”在一旁也随着凝住。
一声暴喝,打破了凝冻的空气。
震耳的金铁交鸣,随青白两道剑芒的绞缠而传起,一触而分,很短暂。
武同春霜刃横斜,人没移动。
童光武退了数尺,手中剑虚虚下垂,脸如紫血。
“鬼叫化”不由自主地“啊”出了声。
震世骇俗的一个照面。
童光武的身躯在颤抖,脸上的肌肉开始抽动,久久片言不发,弹身飞逝。他败了,败得很修,因为在他心目中一对手不是他要找的正主。
“鬼叫化”略显激动地道:“这小子是名杰出的剑手,可惜碰上的是老弟。”
武同春徐徐收了剑,心里有一种怅然之感,胜利并没有使他高兴,他想象得到失败者的心情。
“鬼叫化”像发现了什么似地栗声道:“不对……”
武同春吐了口气,道:“什么不对?”
“鬼叫化”道:“老弟的功力似乎……比两月前突然高了许多。”
武同春心中一动,他还不能说出西门尧转交“无我大师”遗丹的事,那样将暴露身份,但一时又无法自圆其说,空了片刻,才含糊地应道:“是吗?在下……却没这感觉,大概是全神专注的关系。”
顿了顿,故意岔开主题道:“在下……有件事请教您老。”
“鬼叫化”心中疑念未解,但没再追问,轩眉道:“什么事?”
武同春道:“当今江湖上有什么人物以古制钱作标记?”
“古钱?”
“是的!”
“这倒没听说过。老弟!怎会有此一问?”
“证明一个人的来历。”
“谁?”
“灰衣人!”
“灰衣人?他……用古钱作标记么?”
武同春掠起身形,在废虚内绕了一圈,确定没人潜伏,才又回到原地,把灰衣人赠古钱与华锦芳吊挂在门,以及证实杀害江姥姥与一再追杀自己的经过说了一遍,然后沉声道:
“您老有何高见?”
“鬼叫化”惊震不已地道:“有这等事?灰衣人……什么来路?”
武同春道:“以您老江湖阅历之深,想不出古钱来历么?”
“鬼叫化”期期地道:“阅历深,只是见闻比一般人多些,仍有其限度,一个人岂能尽知天下事,尤其武林诡谲万端,不知道的东西多着呢!说到信物标志一类,有的是公开使用,代表某人,有的只能说是对某些特定的人所用的一种暗号,局外人无从知道。”
武同春皱眉道:“这么说……还须从他本人身上追查?”
“差不多!”
“这可难了,灰衣人的行动令人莫测……”
“从他杀害武家老管家江姥姥这一点上追查,看是什么动机。”
武同春心思又呈紊乱,如果说,灰衣人就是二十年前伤害父亲的凶手,杀江姥姥是为了灭口,可是他为什么又以古钱作记,维护华锦芳,华锦芳是武家的媳妇呀,只有一个很勉强的解释,他的确是妻子华锦芳的父执,可是亮出古钱,岂非自暴其短,予人以追查的线索?
“鬼叫化”悠悠地道:“你说灰衣人自承是武家媳妇的父执之辈?”
“是的!”
“可是他没抖露过来历?”
“是的!”
“嗯!这当中有问题,放长线钓大鱼,伪造身份,有所图谋。”
武同春连连点头,道:“极有可能,除此别无解释。”
“老弟见到武同春了么?”
“这……见到了!”
“要饭的口讯带到了么?”
“带到了!”
“他怎么说?”
“目前尚未竟功,还无法来见您老,但他表示绝对照‘无我大师’的遗愿去做。”
“很好!”
“天地会主究竟是何许人物?”
“鬼叫化”摇头道:“这实在妙,堂堂一个江湖大帮派的首脑,竟能隐秘住身份而长时期不泄,武林中还很少听闻,老要饭的舍全力查探,非揭开他的真面目不可!”
突地,武同春想起了丑女“魔音”与紫衣少女素心,她俩是异母姊妹,都是天地会主的女儿。
紫衣少女曾把一面“彩玉牌”借自己挡过“天地会”高手的追杀,两姊妹久已不见现身。
记得数月前“魁星娘娘”与丑女设计,以自己作工具,想陷害紫衣少女失身,是“鬼叫化”解的围。
如找到紫衣少女,就可套出她父亲的来历。
心念之中,武同春眸光一闪,道:“您老记得送子庵中,紫衣少女那回事么?”
“鬼叫化”约略一想,道:“记得,怎么样?”
“紫衣少女自称素心而无姓,她是天地会主前妻的女儿……”
“噢!”
“这是条好线索。”
“好,老要饭的马上着手去办!”
他可是说走便走,声落,人已疾风而去。
夜幕已垂了下来,废墟内顿呈一片阴森。
望着凝碧的墓,武同春心想:“世间根本没有鬼,鬼魂之说是因缘附会而来的,凝碧显魂,当然是人扮的,自己在此地待了四十九天,为什么扮鬼的女人不再出现?遗珠的失踪,必与那装鬼的有关,她是谁?”
呆立了一阵,他突然想起今天是父亲的忌辰,记得厅地上曾散了祭品香纸,那当是华锦芳来尽人妇之道。
于是,他弹身奔向前堡旧屋,迳上后楼。
祖宗龛前,有烧残的素烛和纸箔,看来妻子已拜祭过了,面对父母灵位,他伏跪下去,用泪水来尽哀思。
就在此刻,一条幽灵似的人影,无声无息地来到了楼廊窗边,向里窥视,武同春懵然未觉。
尽哀之后,武同春站起身来,望着父母灵位,喃喃地道:“爹,您在天有灵,保佑孩儿找到当年伤害您的凶手。”
江姥姥临死遗言,又响在耳边:“灵牌……灵座……”
一线灵光,像闪电般划过脑海,武同春双目放光,若有所悟,立即跪下叩了个头,然后恭谨地捧下灵牌,启开灵座。
他的心跟手一样在颤抖。
灵座内,赫然藏有一个小纸卷。
武同春的心几乎跳出口腔,手抖得更厉害,打开纸卷,是数行蝇头小字,屋里太黑,看不清。
想了想、把灵位复原,然后移步窗边。
窗外的人影隐去。
就着窗户透入的微光,武同春以其超人的目力,辨认纸卷上的字。
上面写的是:“字遗示吾儿同春,汝见此柬之时,当已艺业有成,香烟有续,余南下川湘,遇‘至上剑客’华容,无理挑战。以无敌与至上不能并存武林……”武同春眼前一黑,打了个踉跄。
“至上剑客”华容,锦芳的父亲,这太可怕了。
武同春痛苦地厉哼出声,振起精神往下看:“双方比剑,约定败者必须退出江湖,永远除名,华容在剑斗中,突使‘无影戮心手’,余重伤而退,自知不治,特留此柬,意非报仇的,乃为维护武道,使屑小丧德之徒有所戒。父武进遗谕。”
像灵魂被聚然撕离躯壳,武同春紧倚窗框,支持将倒的身体。
太残酷了,仇家竟然是自己的泰山大人。
江姥姥定然不知道凶手会是“至上剑客”华容,不然她会阻止自己娶华锦芳进门,同时临死时,不会只说灵座,定会抖出凶手之名。
华容二十年前客死南荒,华锦芳没见过生父之面。
灰衣人自称是华容生前至友,这一点没错,他杀人旨在灭口,想使这件公案,永远的湮灭。
凶手已死,血债讨不回,父亲将永远含恨九泉。
武同春像突然得了重病般,口里发出了呻吟,这是痛苦的极度表现。
父仇无由报!
妻罪无从赎!
他歇斯底里地狂叫出声:“我是人么?我不是人!”
一口鲜血,呛了出来。
无比的怨毒攻心,使他迹近发狂。
一个冷酷的女人声音隐隐传来:“武同春,你没有人性,根本就不是人!”
麻木中心头剧震,他昏乱地冲出楼廊,不见人,他停住了,此刻,他甚至无暇去研判女人声音的来源,痛苦与恨,已经填塞了他的心胸。
冷酷的声音又告传来:“武同春,你还是自己暴露了身份,掩饰的功夫还不到家!”声音似远又近,像来自虚无的空中。
武同春狂吼道:“你是谁?是鬼么?”
冷酷的声音应道:“不错,我是鬼,鬼!哈哈哈……”厉笑声远去。
武同春发了狂,跃下楼廊,冲到前厅,奔出,冲向后堡废墟,像一头疯了的野兽,到了凝碧墓前,他栽了下去,又爬起,扶着墓碑狂喘。
气氛死寂而阴森,仅有的,是武同春的喘息声。
可怖的声音又告传来:“武同春,你偿付代价的时候到了,凝碧不能白死!”
猛打了一个震颤,武同春清醒了些,他听出声音了,粟声道:“‘黑纱女’!”
“不错,是我!”
“你……要替凝碧报仇?”
“不,她会自己来报!”
“她……她……自己来报?”
“你等着吧,怨气可以使精灵不散,不报仇她不能投生。”
恐怖的厉语,使人不寒而栗,但武同春没有怕的感觉,赎罪的心理,使他产生了一种求解脱的意念,咬着牙道:“你……是凝碧的什么人?”
“代言人!”
“什么样的关系?”
“你不必知道。”
“好,你说,要我……付什么样的代价?”
“你后悔了么?”
“后……悔!不,这两个字不足以代表我对凝碧的亏欠。”
“你怕了,是么?”
“怕?”
“如果你不是怕,不会说出亏欠这两个字,她是淫妇,她不守妇道,她辱没了武家的门楣,她该死,她……”
武同春掩耳狂叫道:“不要再说了,求你,不要……”
“黑纱女”的声音道:“你不想听?你怕听?武同春,这是八年前你口里吐出来的,我只不过是加以复述而已。”
武同春坐了下去,狂乱地道:“说吧,你准备如何折磨我?”
“那是凝碧自己的事。”
“为什么……还要假托鬼魂?”
“不信么,转头向后看……”
武同春回转头,全身的血液一下子冻结了,五丈之外,一个披头散发的白衣人影,身体的确像凝碧。
鬼?世间真的有鬼?擦擦眼睛再看,白色身影消失了,像突然化去。
“黑纱女”的声音道:“你看到了,她随时在你左右,她不会放过你。”
武同春厉叫道:“没有鬼,世间根本没有鬼,‘黑纱女’,你说好了,要怎样报复我?
要我付什么代价,我……完全照办,只要你说出来。”
一阵冷极的笑声,“黑纱女”道:“信不信由你,我只是代言人。”
难道凝碧没有死?不可能,是自己拣的骨,而且在七年之后才出现。不错,是“黑纱女”故弄玄虚,目的代凝碧报仇。
武同春站起身来,努力一咬牙道:“好,算凝碧英灵不散,她要我如何做?”
“要你活下去!”
“活下去?”
“不错,好好地活下去,慢慢地的品尝你一手造成的恶果。”
惨酷的报复手段,比杀人还残忍。武同春凄厉地道:“再重的罪,再严厉的惩罚,没有大过死的,我在墓前用死赎……”
“你不能死!”
“我已经打定主意了。”
“武同春,死不够代价……”
“我只能付出这么多了!”
说完,举掌拍向天灵。
“经渠穴”一麻,武同春拍向天灵的手垂了下来。
不见人影,对方是如何打的穴?夜暗之中,认穴如此之准,的确骇人。
“黑纱女”的声音道:“武同春,你想死么?堂堂无双堡的继承人,未免太丢人了吧?
死并不能解决问题,你不见得毫无牵挂,死了,留下的未了之事,由谁负责?”
居心恶毒,但说的却不无道理,武同春窒住了。女儿遗珠下落不明,江姥姥的血债未讨呀,“无我大师”的遗愿未竟……的确是还不能死。
“黑纱女”又道:“对了,你是被谁毁了容的?”
戮中了武同春的痛处,也激发了他生的意志,寒声道:“这不干芳驾的事!”
“黑纱女”无情地道:“当然不干我的事,随口问问而已,毁容也好,残肢也好,与旁人无涉。”
武同春心念一转,道:“芳驾凭什么带走遗珠?”
这一问是单刀直人,而且出其不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问的心理上没有准备,很容易露出马脚。
果然不出武同春所料,“黑纱女”没有立即传回答话,半晌才道:“你似乎很笃定?”
一阵激动,武同春紧迫不放地道:“芳驾想否认也不成,事实非常明显!”
“我不想否认,不错,有这回事。”
“请把她交还在下。”,“办不到!”
“什么,办不到?”
“是办不到。”
心火骤发,武同春厉声道:“芳驾凭什么要虐害一个无知幼女?”
“虐害,谁说的?”
“在下只问芳驾,拆散人家骨肉,居心何为?”
“骨肉?”
继之是一阵刺耳的厉笑。
武同春狂声道:“这有什么可笑的?”
“黑纱女”敛了笑声,冷酷地道:“骨肉?武同春,你们心自问,你把她当作骨肉么?
你妻子对她有过怜悯么?她是孽种,自小就被遗弃,你只差没除掉她……”
像无数把利刃,插在武同春的心上,脱口大喝道:“住口!”
“黑纱女”分毫不让地道:“你敢否认?”
武同春像斗败了的公鸡,咬着牙,垂头道:“我不否认;当着凝碧的墓说,我是亏待了遗珠,但那已经过去了……”
“什么,过去了?”
“是的,那是个可怕的误会,误会已经澄清了。”
“什么误会?”
“八年前用恶毒阴谋陷害凝碧的,是本堡被逐的师爷段秀峰……”
“谁说的?”
“在下结拜兄弟许中和,他也是被害人,是他调查出来,并手刃了段秀峰,在下……亏负了凝碧,要在遗珠身上补偿。”
空气突趋死寂。
久久之后,才又响起“黑纱女”的声音道:“武同春,就凭你几句轻松的话,能安抚屈死之魂么?”
武同春沉痛地道:“在下愿接受任何酷烈的惩罚,只请把遗珠交还在下。”
“我说过办不到!”
“你……”
“凝碧不愿再离开她的骨肉。”
“你……别太残忍,为什么假托鬼魂……”
“凝碧刚才已经显魂,你看到了,我只是代言人。”
“那是假的,假的!”
“信不信由你,交人办不到。”
武同春双手握拳,挥动着狂叫道:“我求你,‘黑纱女’……我求你把遗珠还给我,我……你要什么?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才称心,你说吧?”
“黑纱女”道:“我没资格说,那要看凝碧的意思。”
情绪有如鼎沸,武同春咬牙切齿地道:“为什么尽说鬼话,你代凝碧报复我,我接受,我罪有应得,请把女儿还给我,别的我全认了。”
“黑纱女”道:“对不起,我办不到!”
武同春的理智崩溃了,狂喊一声:“还我女儿来!”
身形弹起,在废墟中盲目奔撞,他要逼出“黑纱女”,他要把这件事彻底解决,他又回复不久前的意念,愿以死作代价。
一圈又一圈,他发狂地游奔,但什么也没发现。
如果他没带面具,如果他脸没被毁,此刻,他的神情不知有多凄厉可怕。
“黑纱女”再没声息,她是走了,还是蓄意折磨他不得而知。
最后,武同春又回到墓前,颓然木立,是狂激之后的消沉,此刻,恨也没有了,怨也没有了,脑海呈现一片空白。
突地,一个声音道:“注意!”
是“黑纱女”的声音,是用传音之术发出的。
本能上的反应,武同春闪电般斜里弹开八尺,一看,骇然大震,但随之的是浓炽着杀机了。
眼前站着两条人影,不知何时来的,一个是不久前铩羽而去的童光武,另一个赫然是他誓要得之而甘心的灰衣人。
目中杀芒一闪,道:“来得好!”
灰衣人嘿嘿一笑道:“能一找便找到你,的确是很好!”
童光武接着道:“该叫你‘冷面客’还是‘鬼脸客’?”
灰衣人会与童光武走在一道,的确是意想不到的事。
两对目芒,如冷电交辉,武同春在狂激中还保持了三分冷静,心念疾转:“两人的功力,比自己差不了多少,单打独斗,绝无问题,如果对方合手,情况便两样了,两人武功之和,当然是超过自己……”
心念未已,灰衣人开口又道:“冷面客’,老夫查实你是武家仇人之后,坦白说一句,武氏遗孤武同春是不是已经遭了你的毒手?”
武同春猛一挫牙,道:“灰衣人,用不着鬼话欺人了,你杀害武氏管家江姥姥,又一再追杀本人,是为了灭口,想掩盖二十年前华容以卑鄙手段,暗算武堡主的公案,对不对?”
灰衣人向后退了一步,厉声道:“老夫不懂你在胡诌些什么,华容暗算武堡主,这倒是稀罕事?”
“你不敢承认?”
“笑话,老夫与华容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他赴南荒之前……”
“那你杀人的目的何在?”
“维护武家!”
“放屁,江姥姥是武氏三代管家,你……”
“‘冷面客’,别狡辩了,那老虔婆是你一路的,老夫干脆点明,老虔婆是‘九指剑客’的师姐,你是‘九指剑客’的传人,而‘九指剑客’的一个手指头,是堡主‘无敌剑’武进所削落的,你受备索仇,对不对?”
说的凿凿可凭,武同春愕住了,他根本不知道“九指剑客”的事。
童光武似已不耐,冷声道:“他已经默认了,动手吧!”
武同春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是好,照对方的说词,江姥姥是被误杀,这笔帐该如何算呢?灰衣人沉声道:“冷面客’,你拔剑保命吧!”
“呛!呛”两声,灰衣人与童光武齐齐亮剑,站成犄角之势,不可言喻,他俩个准备联手合击。
武同春骑虎难下,不应战,便得抖出真面目,不抖出真面目,便得应战。
灰衣人又道:“你真是鬼话连篇;华容的女儿,是武同春的妻子,你说华容二十年前暗算武堡主,根本就不像话。”
童光武大声道:“拔剑!”
武同春目注童光武道:“姓童的,你不是专程找武同春寻仇么,现在跟着起哄,为什么呢?”
童光武阴声道:“我的事你少管,武同春死在你手下,我现在杀你,天公地道。”
有理说不清,武同春无可奈何地拔出剑来。
二对一,三剑相峙。
武同春突发豪性,他要试一试玄黄剑法在全力施展下的威力,于是,他摒除杂念,凝神抑志,把功力运至极限。
可怕的沉默,但为时短暂,因为灰衣人与童光武自认稳操胜算。
暴喝声起,二青一白三道剑光碰击,绞扭,分开,剑气四溢,裂空有声,泣鬼惊神的一瞬,像一块巨石,投人熊熊的火堆,星火怒迸,又趋于沉寂,但那厉人的瞬间印象,却留在脑际不去。
童光武退到三尺之外,胸衣见红,他已挂了彩。
灰衣人也后移了数尺。
武同春凝立如天神,剑仍扬着。
他已接下了两个盖世剑手合攻的一击,表面上看是如此,但他自己内心明白,这一个回合,无与伦比的压力使他几乎吐血。
童光武目爆厉芒,迫进到原来位置。
灰衣人也跟着挪步取势。
如果缠斗下去,后果十分难料。
蓦在此刻,“黑纱女”的声音倏告传来:“住手!”
灰衣人目芒一闪,沉声喝问道:“什么人?”
“‘黑纱女’!”
“什么?‘黑……纱女’?”
“不错!”
童光武惊声道:“‘黑纱女’?”
灰衣人大声道:“你意欲何为?”
“黑纱女”的声音道:“没什么,二对一不公平,我们一对一试试看。”
灰衣人厉声道:“你凭什么横岔一枝?”
“黑纱女”道:“看不惯!”
童光武怒声道:“很好,现身吧,区区倒要见识一下中原道上令人丧胆的‘黑纱女’,到底是什么样的脚色?”
冷哼一声,“黑纱女”道:“我一现身你就没命了,你还没见识我的眼福。”
董光武手中剑一抖,道:“区区不信这个邪!”
“黑纱女”道:“你最好是相信!”
灰衣人目芒连闪,道:“‘黑纱女’,老夫今夜买你一个面子,下不为例!”说完、目光扫向童光武道:“我们走!”
童光武竟似不愿地道:“走?”
灰衣人道:“听老夫的话准没错!”
说完,当先弹身离开。
童光武当然有自知之明,沉声道:“‘冷面客’,后会有期!”
声落,跟着弹逝。
深泽透口气,武同春收了剑,心头又回复昏乱。
“黑纱女”的声音道:“我代你保持了身份的秘密,再见了!”
武同春脱口大叫道:“你不能走!”
“我为什么不能走?”
“遗珠……”
“遗珠怎么样?”
“求你还给我!”
“这不是废话么?”
“你……可以把任何残酷的手段加在我身上,我绝不逃避,可是……孩子无辜,你不能……”
一连串的冷笑,“黑纱女”道:“我对她很好,她愿意跟随我,她已经懂事了,她记得她所受的待遇,她不需要那个使她痛苦的家。”
武同春狂叫道:“你……你真的这一残忍?”
“黑纱女”悠悠地道:“完全相反,这是仁慈,你别忘了,你的脸,她还认得你么?”
无情的一击,击碎了武同春的心,的确,遗珠还认识这面目全非的父亲么?这面目能见她么?后果会如何?以往,由于误会,父女之间没有建立半分感情,现在如何向她解说?伤心痛泪流了下来。
久久,才哀声道:“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凝碧的代言人,遗珠的保护人!”
“身份,我问你真实的身份?”
“你定要知道,好,我是凝碧的同胞共乳人。”
武同春身形晃了两晃,激颤地道:“没听说过凝碧有什么姊妹……”
“当初我反对你们的结合,她何必告诉你。”
“是……真的?”
“你想会是假的么?”
吴同春颓然挪步,扶着墓碑,怆声道:“请……让我……看遗珠一眼:只看一眼,求你……”
“唔!可以,你不许出声。”
“我……不出声!”__目光凝注处,只见远远一堵残垣上,出现一个小小身影,不错,是遗珠,骨肉之情,武同春凄哼了一声,飞身掠去。
到了残墙边,什么影子也没见到,像根本没这回事!
“遗珠!遗珠!……”武同春声声凄唤,什么反应也没有。
死寂的废墟,在武同春的心目中,是一座炼狱,在熬炼他的灵魂。
夜的帏幕撤去了。
初升的旭日,扫尽了废墟的阴霾,但武同春的心,仍是一片灰暗,没有一丝丝的亮光,他觉得似乎天底下的不幸,全集中在自己身上——睑孔因坠谷而毁,变成了一个见不得人的怪物。
元配妻子吴凝碧,因为一场可怕的误会而惨死。现在她的同胞姊妹“黑纱女”出面讨债,还带走了爱女遗珠,骨肉活生生被拆离。
“父亲死于“至上剑客”华容的卑鄙暗算,华容已客死南荒,父仇欲报无由。
偏偏续继弦的妻子华锦芳是仇人的女儿,即使脸孔不毁,这辈子夫妻如何相对?……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