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新生代长篇小说评介
作者:吴义勤

吴义勤,著名文学评论家,本刊顾问,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师范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国家级重点学科带头人和山东省文化建设重点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山东省首批“泰山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山东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入选者。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长篇小说与艺术问题》等著作8部,主编各类著作10余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等国内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有数十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权威刊物转载。2004年其长篇论文《难度·长度·速度·限度》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新生代长篇小说是90年代崛起的新生代作家成长的标记,是他们艺术上走向成熟、强大的一个标志。出于对一种文学事实的尊重,我无法不在这里开出一份长长的书单: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曾维浩的《弑父》、李洱的《花腔》、艾伟的《爱人同志》《越野赛跑》、麦加的《解密》、东西的《耳光响亮》、红柯的《西去的骑手》、刁斗的《证词》《游戏法》《回家》、迟子建的《穿过云层的晴朗》、叶弥的《美哉少年》、刘建东的《全家福》、朱文颖的《高跟鞋》、王彪的《越跑越远》、朱文的《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韩东的《扎根》、荆歌《民间故事》、戴来的《我们都是有病的人》、毕飞宇的《那个夏天,那个秋天》、马枋的《生为女人》、徐坤的《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须兰的《千里走单骑》、王芫的《什么都有代价》、何大草的《刀子和刀子》、魏微的《一个人的微湖闸》、丁丽英的《时钟里的女人》、宋潇凌的《个别女人》、邱华栋的《正午的供词》、刘志钊的《物质生活》、李冯的《碎爸爸》、祁智的《呼吸》、周洁茹的《小妖的网》、丁天的《玩偶青春》、张懿翎《把绵羊和山羊分开》、姝娟的《摇曳的教堂》、罗望子的《在腼腆的桥上求爱》……
在我看来,新生代长篇小说整体上主要呈现为四种形态:一是以曾维浩的《弑父》、须兰的《千里走单骑》、艾伟的《越野赛跑》、麦加的《解密》等为代表的具有强烈的寓言色彩和超现实意味的小说;一是以李洱的《花腔》、红柯的《西去的骑手》、艾伟的《爱人同志》、韩东的《扎根》等为代表的把“现实”与“历史”进行“互文”处理,具有某种新历史小说特征的文本;一是以刘志钊的《物质生活》、王芫的《什么都有代价》、朱文的《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戴来的《我们都是有病的人》、徐坤的《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等为代表的近距离书写欲望化的生存现实,渲泄生存之痛和世纪末情绪的小说;一是以叶弥的《美哉少年》、何大草的《刀子和刀子》、魏微的《一个人的微湖闸》、王彪的《越跑越远》等为代表的反应“成长”主题的小说。四种形态的小说虽然题材有异,故事涵蕴不同,叙述风格迥异,但是在对“世界在崩溃”这一主题的表达上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因此,新生代长篇小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图像”就成了一种“崩溃的图像”。当然,这种“崩溃”在新生代长篇小说中也有着不同的层次:
首先,“世界”和“生活”本身的崩溃。这是新生代小说展开的一个大背景,也是新生代作家关于当下时代和现实世界整体感受的传达。在新生代长篇小说中,主人公的生活世界总是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总是在突然之间偏离原有的轨道和方向,总是把主人公拖入陌生而迷茫的生活泥潭,总是使他们陷在生存困境中不能自拔,因此,沉沦与挣扎、堕落与逃亡、恐惧与焦虑就成了“生活”和“世界”的“底色”。无论是《弑父》里的洪水、旱灾以及介的逃亡之路,还是《我们都是有病的人》中的刘末失踪,亦或《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中陈米松的离家出走,都让我们直观地看到了生活和世界走向破碎、走向崩溃的感性图景。而刘志钊的《物质生活》和罗望子的《暧昧》无疑是言说“崩溃”主题的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文本。《物质生活》通过对一个诗人从精神的“诗”的王国堕入物质的“欲”的王国的人生历程的刻划,准确地勾划了中国社会从80年代向90年代演变的精神轨迹,也完成了对时代本质的准确概括。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人性的扭曲、爱情的殒落和伦理亲情的流失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暧昧》则对当下时代的“暧昧”的精神情绪进行了独特的阐释。这确实是一部“暧昧”不清的小说。暧昧的主题、暧昧的人物、暧昧的情节、暧昧的情绪、暧昧的氛围、暧昧的叙述在小说中交相辉映,呈现给读者的是一种混沌而迷茫的阅读感受。作者赋予小说主体一个看门人“手记”的形式,这个“手记”,混乱、矛盾、头绪繁多、杂乱无章且毫无逻辑性可言,它把新闻事件、消息、道听途说、哲学沉思、家庭生活场景、个人传说、情史、写实与梦想等等全都“杂糅”、“拼贴”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典型的“后现代”文本景观。作家努力完成的似乎只是对日常生活丰富性和混沌性的还原,小说消泯了感性与抽象、形而上与形而下、诗性与世俗、此岸与彼岸的彼此界限,并让它们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混合“发酵”成了一个独特而费解的艺术世界。尽管在这些小说中,作家对崩毁的生存图像的描写具有某种显而易见的寓言色性和荒诞性,作家力图以某种夸张和抽象的手法挖掘这种崩溃图像的普遍性与形而上内涵,进而完成对时代和世界的阐释以及对主人公普遍性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境遇的象征化表达,但是,在新生代作家这里中国经验和私人经验的强调,还是保证了其笔下“世界图像”的感性质地。这也是新生代小说的寓言化风格与新潮小说的寓言化风格的区别所在,如果说新潮小说在寓言化和象征性地阐释世界时总是以对“生活”和“世界”本身的架空与扭曲为代价的话,那么新生代长篇小说则首先维护的是“生活”和“世界”的原生态和日常性,因此,“世界的崩溃”就不再是生活之外、个体之外某种“寓言之物”和“象征之物”的崩溃,而切切实实就是在主人公经验范围内的可触可感的“生活”本身的一种崩溃。在这方面,应该说,新生代作家对时代和现实的诠释与理解、对新的生活景观和新的世界图式的建构都是相当准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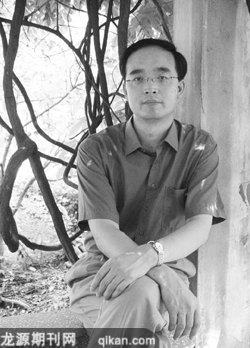
其次,“父亲”的消失。与对世界和生活本身的困惑与不信任相一致,“父亲”作为权威和秩序的象征,某种程度上其实也就是世界的象征。在新生代作家的小说中,“父亲”开始成为一种缺席的对象,一种被审判的对象。“父亲”神圣、坚强、伟岸、崇高的形象一一被瓦解,由“父亲”所支撑和主宰的生活也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崩溃与破碎。可以说,“父亲”的消失既是世界走向崩溃的表征,又是这种崩溃之所以发生的内在根源。《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中“父亲”成了一个可笑的对象,他的“说教”和他肥胖的“裸体”一样令儿子生厌,《耳光响亮》中“父亲”则在一夜之间消失,成了一个“不在”,一个不负责任的逃亡者,一个失去记忆的偷渡者,一个“杀人犯”。《美哉少年》中的落难“父亲”既不能拯救自己,也无法保护老婆和孩子,只能以自欺欺人的方式寻求内心的平衡。《爱人同志》中“父亲”则成了主人公不幸生活中的一丝遥远的记忆,他是那样的无奈和渺小,既无法影响和改变女儿的人生选择,也无法解救女儿出苦海。偷偷摸摸来参加女儿的婚礼,但也只是一个“偷窥者”。《弑父》则更是直接展开了对“父亲”的追杀。介通过对“父亲”的解剖来认识自我与世界,他的弑父行动直接导致他被所居住的城市判死刑。他逃亡到肯寨之后,又与枇杷娘和所有的女人交媾,成了肯寨的“父亲”。最终,在一场洪水之后,他在肯寨所创造的一切(文明、科学、秩序等)被颠覆和否定,他再次成为一个逃亡者,受到了他的儿子东方玉如的追杀,并在寓言化的想像中被“杀死”。在解构“父亲”主题的诠释上,刘建东的《全家福》也很有特色。作为新生代作家中的一员,本质上刘建东并不缺乏放肆、撒野的能力,但是在他的长篇小说《全家福》中,我们感受到的却是另一种理性而温情的力量,其对个体精神存在和内在疼痛的抚摸与触碰感人至深。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对艺术的唯美和纯粹性的追求,看到了一种舒缓、抒情、温暖的叙事风格,看到了新生代作家“粗暴”的外衣下温柔甚至脆弱的一面。90年代以来,新生代作家对启蒙叙事传统和启蒙价值观的背弃是坚决而果断的。对新生代作家来说,“反启蒙”是建筑在两个基本支点上的,一是反伦理、反道德的解构主义立场;二是欲望合法性的证明。作为新生代作家中的一员,刘建东在《全家福》中所体现的基本叙事倾向可以说与新生代作家的“反启蒙”原则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艺术的展开过程中,启蒙价值观和反启蒙价值观的冲突、欲望和精神情感的冲突、伦理和反伦理的冲突却一直贯穿小说的始终,正是它们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内在紧张和内在张力。在这个问题上,刘建东所表现出的审慎、犹疑和矛盾,既是对新生代作家简单粗暴世界观的警惕,又使小说的思想内涵和人性内涵更浑厚、更有魅力了。小说中“父亲”的瘫痪、叹息算得上是反启蒙“弑父”传统的继续,他的权威的丧失正是启蒙者命运的一种写照。但是,在小说中,“父亲”其实又并没有失去力量,他的“飘来飘去的身影”、他的叹息都有着超现实的力量。而小说通过母亲与人的偷情,既肯定了情欲的合法性,又解构了传统的“圣母”形象。但是,在对母亲的反道德、反伦理的解构中,小说又对“母亲”形象内含的道德价值和伦理情感持认同的态度。即使“全家福”本身,在小说中也是一个矛盾的意象,作为一种反讽,作家对其的情感和态度是复杂的,对其的解构也毫无疑问只是一种“温柔的解构”。与“父亲”的消失相呼应,“英雄”的“去魅”、还原和日常化也是新生代长篇小说的主题目标。《花腔》中“英雄”葛任在三种不同视角的“叙述”中不仅面孔暧昧,而且死得也是不明不白。《解密》中的容金珍是一个“隐秘”的天才和英雄,但在历史、国家、政治、科学、思维、人性等重重“密码”的“压迫”下,他也只能无奈地走向“崩溃”和疯狂。他的结局可以说是“英雄”命运的一个普遍性隐喻。《西去的骑手》对马仲英“英雄”形象的塑造,与其说是在追怀一个“英雄”的时代、张扬一种野性的有血气的生命,不如说是在借“英雄”的毁灭来批判政治、历史和人性的黑暗,而“英雄”和“土匪”的潜在置换,则更是秘密地完成了对于由意识形态所建构的英雄话语本身的解构。此外,荆歌的《民间故事》对孟姜女神话传说的“解构”也同样有着显而易见的弑父意味。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