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文学经典与文学教育
作者:樊 星

樊星,著名文学评论家,本刊顾问。1957年生于武汉,祖籍河北邢台。当过知青、中学教师。曾就读于荆州师专、华中师大。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世纪末文化思潮史》、《别了,20世纪》等书,并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文艺评论》等刊发表论文百余篇。曾获湖北省文联“文艺明星奖”、“屈原文艺创作奖”、“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湖北省师德先进个人”称号及“中国文联2000年度优秀文艺论文奖”。
近年来,经典问题引起了教育界和文学界的普遍关注。这显然是因为大众流行文化已经猛烈冲击了传统经典文化,而这样的冲击也已经使得当代大学生、甚至研究生明显疏离了那些被历史证明是人文精神核心的经典著作。经常有同学问我:为什么按照老师的指点,去读经典,可就是找不到感觉?应该说,这是当代人文教育面临的严峻挑战。因为很难想象,远离了那些凝聚了一个民族乃至人类的丰富智慧的经典,而在通俗读物、流行读物的泡沫中随波逐流,我们会找到建构新的文化的正确起跑线。我也常常问那些同学,天天跟在阅读新潮的后面跑,今天流行韩寒就都谈韩寒,明天流行郭敬明就都谈郭敬明。几年过后,蓦然回首,结果发现大家曾经读过的流行书竟然惊人的一致。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你的个性在哪里呢?所以我常常说,这是一个个性解放的时代;同时这也是一个个性很容易被形形色色的潮流淹没的时代。当然不是说为了打造与众不同的个性,就有意去逆潮流而行。而是应该在了解潮流的同时努力去超越潮流。因为在今天这个“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时代,在这个文化精品与文化垃圾常常一起涌现,而文化垃圾显然常常多于文化精品的年代,在出版物已经达到应接不暇的年代,老是跟着潮流跑,是难免会进入书籍的迷宫,一不小心就迷失了自我的。因此,就需要了解:那些穿越了漫长历史的烟云,影响了无数代知识分子乃至整个民族和全人类的经典,为什么能成为经典?那些经典对于指导我们做人、处世、择业、成功,对于我们了解什么是传统、什么是人文精神、什么是最优秀的书籍具有怎样的指导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年来,教育界提倡青年学生多读文史经典,文学界也展开了关于文学经典的讨论(从“经典的意义是什么?”到关于“红色经典”的讨论到“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的探讨),都显示了重返经典的必要。
那么,什么是经典呢?《辞海》(1979年版)上的定义是:“①一定的时代、一定的阶级认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②古代儒家的典籍。也泛指宗教的经书。”
如此说来,首先,经典是有时代性的,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和《毛主席语录》、《创业史》、《红岩》等等就是共产主义运动时期的政治、文学经典。那些经典曾经鼓舞了许多热血青年走上了革命之路。有人也许会说,时代已经变了,那些革命经典应该也过时了吧。其实未必。在美国,《共产党宣言》就是高中生必读的课外书之一。在西方思想界,左派知识分子的力量仍然不可低估。读当代小说,张炜的长篇小说《古船》中的主人公就一直想从反复读《共产党宣言》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我甚至觉得,有那么多的政治教科书,有哪一本在思想的凝炼、文风的简洁方面能够与《共产党宣言》媲美?像《共产党宣言》的开头那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就很有文采,值得学习。还有《红岩》的故事,在今天读来仍然有着强烈的感染力。那些为了革命的信仰连生命都可以牺牲的人们,充分显示了信仰的力量,显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传统气节。由此可见,共产主义气节与儒家传统的士大夫气节之间还是有着深刻的联系的。
那么,有没有永恒的人文经典?显然也有。像《圣经》、《古兰经》、《论语》、《道德经》,像希腊神话、莎士比亚、《战争与和平》、《堂·吉诃德》、《红楼梦》。不读《圣经》、希腊神话,就不可能了解西方文化的精神,因为西方文化的许多思想和典故都来自《圣经》和希腊神话。同样,不读《论语》、《道德经》,也不可能了解中国的文化精神。这两年,重读《论语》的热潮持续高涨,就显示了经典回归的魅力。为什么这些经典能够超越时代?为什么像《论语》这样的经典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猛烈冲击和“文革”中“批林批孔”运动的猛烈批判,仍然能够在现代化加速发展的年代里重新焕发出不可思议的影响力?值得研究。一方面,中国社会的人伦关系尽管已经受到西方伦理观念(像民主、尊重个性、女士优先等等)的冲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有些基本的东西其实没有变。而那些东西就在《论语》中。海外对于“亚洲的崛起”也有一说,叫“儒教资本主义”,说的也是东方儒家文化的精神(例如崇尚集体主义、讲究和为贵,讲“温良恭俭让”等)可以与资本主义精神(像崇尚个性、竞争)结合在一起(其实西方也讲公平竞争、fair play的,这与中国的“温良恭俭让”有相通之处)。“亚洲道路”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走的这一条道路。
还有,经典有没有阶级性?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阶级性的。像《共产党宣言》就是无产阶级的经典(但也有许多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研究它);而希特勒的著作《我的奋斗》则是法西斯主义的经典(法西斯主义的幽灵,代表着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在今天的欧洲仍然不散)。像张爱玲的小说,这些年许多青年学生爱得不得了,好象也成了“小资”的经典。不过,具有严格的“阶级性”的经典,好象不那么普遍。更多的,人们在更经常的意义上谈论的,还是超阶级的经典。永恒的人文经典显然就具有超阶级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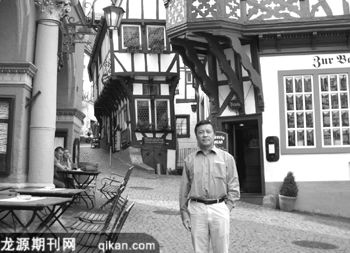
除了时代性、阶级性、人类性,经典常常还具有个人性。托尔斯泰就不喜欢莎士比亚,在他看来,莎剧中充满了阴谋与凶杀,而这是与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大相径庭的。他十分推崇的,是《圣经》,还有雨果充满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是大名鼎鼎的文豪。但王蒙就不喜欢他的《战争与和平》,觉得太拖沓。王蒙还不喜欢《红与黑》,但路遥就十分喜欢《红与黑》。他的《人生》就被称为“中国的《红与黑》”。由此可见,经典是有一定的个人性的。人性千差万别,读书的眼光当然不可能一样。还有,鲁迅就曾经十分偏激地主张“不读中国书”(尽管他其实读了许多中国书)。他欣赏的,是尼采的哲学和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他受果戈理、契诃夫、安特莱夫的影响很深。可见在不同的人的心中,有不同的经典尺度。
每一位作家、学者的心目中都有几部对于自己的创作和研究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经典作品。而那些作品当然是他们在自己读书的过程中通过比较才找到的。这样就产生出这样的问题:怎样找到对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具有长久指导意义的人文经典?经常有同学问我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不好回答。因为我喜欢的经典你不一定喜欢。对于我,影响最大的外国经典有: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因为我从其中学会了以超越唯物论和唯心论之争的眼光去了解哲学史,也学会了将文学与哲学结合在一起研究的眼光。我非常喜欢的小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这本厚厚的小说使我知道了人性的深不可测。还有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其中充沛的理想主义激情和精辟的人生哲理也深深感染过我。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中国当代学术经典有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和钱钟书的《管锥编》。它们共同的特色是:视野开阔、气势恢弘、思想独到、文风灵动,都令我神往。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