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第三十章 非童话的尾声
窗外下着雨,雨水拍打着我身后的玻璃窗。艾略特没有穿雨衣,他被雨水淋透了,他的外套“滴答滴答”地向下滴着水。 他走了过来,坐到我的对面,说道:“这糟糕的天气,这雨说下就下了起来。”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很高兴看到你,我还以为你把老朋友给忘了呢。” “你好像一直在忙。” “生意刚刚起步嘛,我总得做出个样子来。”我故作轻松地答道。 艾略特笑了,说:“单单是世界博览会的那一项缉窃任务,就能使你赚得一个开门红。” 我点点头,放下了手中的钢笔,“的确如此,你打算明天就走吗?” “明天上午,我,贝蒂还有那辆装满行李的福特车。” “你到辛辛那提法院去做些什么呢?” 艾略特耸耸肩,满不在乎地说:“禁酒法令已经被取消了,人们还能把我这样一个禁酒专员送到哪儿去呢?我猜那些家伙想派我去铲平‘月光山’,不知道我猜得对不对?” 我半是调侃,半是担心地说:“山地人的猎枪和机关枪一样凶狠,他们会杀了你的。” “我是这么想的,要知道我可从来没有把自己想象成一名‘勇士’。” “你说得没错。” 这使得艾略特脸上略微浮现出一丝笑容,不过是一丝忧伤的笑容,我很理解他此时的感受。 他说道:“内森,别忘了去辛辛那提看我们。” 我郑重其事地点点头,“我会的。你的老朋友都在这里,我想你也一定会时常回来看看大家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突如其来地说了一句:“难道这不是很值得的吗,艾略特?” “什么?” “你打了相当精彩的一仗,把卡朋给扳倒了,还有其他的一切。” 艾略特有些伤感地说:“是的,能够铲除卡朋,这的确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可是问题是,现在没有人去理会奈蒂,所有的人都忙着追捕那些在逃的银行抢劫犯,因为公众们只关注流血事件。” “在你离开之后,梅尔汉·班维斯会继续整理芝加哥的治安。” “那个饭桶,”艾略特不屑一顾地说道,“不过是一个酒囊饭袋。” 说到这里,艾略特意识到我是在故意套他的口风,我们二人互相看着对方,禁不住大声笑了起来。 之后,艾略特又说道:“我刚才在楼下停留了一会儿,邦尼不在那里。” 我说:“他现在正在卡茨科尔斯训练呢,几个星期以后,他将和坎佐内拉再度交手。” 艾略特若有所思地说道:“说到再度交手,我真希望自己能够亲眼目睹对兰格的正式审判。” 对兰格的正式审判也是在几个星期以后的事。 我耸耸肩,评论道:“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兰格和米勒一定会被革除警察职务的。” 现在,兰格和米勒已经被暂时停止了在警察局里的工作。 “是的,一定会有这样的结果,不过,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亲眼目睹这两个败类的下场。”说到这里,艾略特关切地看了我一眼,“最近收到玛丽·安的信了吗?” “上个星期她给我寄来了一张卡片,告诉我说她在一部片子中扮演了一个不太重要的角色。” 艾略特不加思索地说:“好莱坞一定很适合她。” 我点了点头,附和道:“是的,那是为她准备的地方。” 艾略特有些迟疑地说道:“我想……你对她是认真的。” “是的。” “你现在还好吧,内特?”艾略特的脸上充满了关切之情。 我勉强向他笑了一下,“你知道现在我想去哪儿吗?” “你想休息一下?那些报告可以暂时放一放,不是吗?” “你总是能猜对我的心思。”我向艾略特说道。 艾略特已经站了起来,“是的。现在咱们到楼下去吧,我请你喝上一杯。” 打那以后,我就很少再见到艾略特,不过,我不时地能够得到他的消息和其他人的一些情况。 在离开了芝加哥以后,艾略特在肯塔基州、田纳西州、俄亥俄州等地继续追捕残余的私酒贩卖商,大约干了两年左右。后来,他又当上了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的安全署长。克利夫兰市是美国最年轻的一座城市,当时只有三十二年的历史。在二战期间,艾略特又担任了联邦安全局的局长,这是一个很多人都垂涎的头衔,艾略特的工作主要是负责美国军队内部对性病的斗争。 在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期间,艾略特始终在从事着抵抗性病的斗争。与此同时,他的一位“老朋友”艾尔·卡朋也在和性病做着斗争。在艾尔·卡朋从亚特兰大监狱中被释放出来以后,他并没有如他所愿地“重振雄风”,他患上了“顽症”——梅毒,这种病一向被认为是一种“危险的、难以对付的罪犯的最终归宿”。他的病症十分严重,梅毒已经蚕食了他的大脑细胞。在一九三九年时,他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不过他已经成为一个不能行动,不能自由思考的废物了。在一九四七年,艾尔·卡朋告别了这个世界,当时他只有四十八岁。在他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性病已经将他折磨得骨瘦如柴了。 至于艾略特呢,他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并成为宾西法尼亚州一家报社的社长。他的一些老明友,包括我在内,劝他把与卡朋帮之间的斗争记述下来。在我看来,他的影响力不减当年,因为后来他的那部自传《隐形人》拍成了电视系列剧,观众收视率一直居高不下。从此,艾略特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卡朋的名字也经常被人们挂在了嘴边。 可惜的是,艾略特本人并没有看到这一切,他刚刚修改完自己的自传,就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了。那一年是一九五七年,当时他五十四岁。 在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二日,邦尼在纽约举行的复赛中彻底把坎佐内拉赶回了老家。在此之后,他的非法酒店的生意也日益兴隆,最后发展成为邦尼·罗斯鸡尾酒店。在一九三八年,亨利·阿姆斯特朗打败了邦尼,从他的手中夺走了冠军的荣誉。在那以后,邦尼把全部精力投注于俱乐部和赌博业里,可惜不太成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邦尼参加了海军,并被派往瓜达尔卡纳尔作战。他在那里的表现十分英勇,并由此获得了总统亲自颁发的嘉奖今,不过也染上了疟疾。医生像对其他的许多美国兵一样,给他使用了吗啡镇痛,结果邦尼也成为了一名深陷其中的瘾君子。我不想把邦尼和那些皮包骨的吸毒者联系在一起,可是,邦尼确实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不过邦尼毕竟是邦尼,凭借着自己坚强的毅力,他后来戒掉了毒瘾。当邦尼成功地戒掉毒瘾的消息传开以后,他又一次成为公众交口称赞的对象,就如同他第二次获得世界冠军一样荣耀。在一九六七年,癌症最终击倒了这名顽强不屈的轻量级拳击冠军。 弗兰克·奈蒂又在这世上辉煌地生活了十个年头。在舍迈克被他暗杀以后,他在黑社会的帮派首领、政客和警察们的心目中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一言一行都能左右着他们的命运。而且,弗兰克·奈蒂也不是卡朋那样嗜杀成性的凶残匪徒,他对于使用暴力手段击败对手,制造流血新闻一类老式做法毫无任何兴趣。奈蒂更像是一名商人,一名拥有至高权威的总经理级人物,他一手创立了现代意义上的黑社会共同体。 和其他许许多多总经理一样,奈蒂也有着行政管理人员们的常见病——胃病。兰格的枪击引发了他的隐性胃溃疡,虽然那些皮外伤早就已经痊愈了,可是伤病的疼痛一直伴随着他,特别是背部的伤口。在一九四三年,他指使肯帕戈纳和其他一些手下从一家电影企业敲诈了一大笔钱,这件事引发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各界的压力向奈蒂席卷而至,面对着巨额的敲诈罚金和坐牢的危险,奈蒂只身离开了他在郊区的房子,在雨中狐独地沿着铁轨走着。当时,他心爱的妻子安娜在十八个月以前已经离开了他,他也已经五十八岁了,又饱尝了胃病的折磨。事后,有人推测说弗兰克·奈蒂只是不愿意再次忍受长期监禁的折磨。在当时,有三名目击者看到他开枪自杀了。那一天正好是三月十九日,恰好是乔·扎戈那说:“按按钮吧。”这句话十周年的前一天。 在弗兰克·奈蒂的墓碑上写着:“失去了生活,只有死亡。” 在一九五一年,道维斯将军在书房里看书时死去了。在他去世前不久,他曾经接受过一次记者采访。他告诉记者,他对于那些懂得如何利用传媒来展现自己聪明才智的人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他的那句结论,也可以视为他的遗言:“愿上帝赐予我们普通的见识吧!” 珍妮同一位来自郊区的共和党的乡村官员结婚了。她的丈夫先是被选为州议员,后又被选为众议员,在多年以后的一次连任选举中被对手击败了。不过尼克松政府为他在政府部门中安排了一个职位,后来他在水门事件中扮演了一个不太光彩的小角色,被关到一个监狱农场里服了十八个月的劳役。在他服刑期间,珍妮与他协议离婚了。现在珍妮一个人住在埃文斯顿,他们的三个孩子早已长大成人,各奔东西了。我知道珍妮又看上了一个商人,他是埃文斯顿的前一任市长,生活得很阔绰,拥有自己的乡间别墅。 我的那位路易叔叔在一九四八年死于中风,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势同水火,没有得到一点儿改善。 在沃尔特·温切尔担任了《隐形人》电视系列剧的旁白解说员之后,他的事业又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峰。 乔治·拉弗特在一九三四年出演了一部名为《巴列罗舞》的影片,在这部影片中,他跳舞的镜头要远远多于他对白的镜头,他在此片中的舞蹈搭档之一就是那次在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中出尽风头的萨利·兰特。直到萨利·兰特前几年去世,她都一直在跳着脱衣舞。在一九五○年左右,拉弗特的表演事业发生了大滑坡,部分原因是他只肯出演“好男人”的角色,而当时,汉弗莱·博加特因出演拉弗特拒绝出演的“冷血杀手”一角而迅速走红。同时,拉弗特与艾尔·卡朋的兄弟约翰一类的黑社会人物来往甚密,这也使他的公众形象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在他演艺事业下滑的那个阶段,拉弗特频繁出没于哈瓦那和伦敦的各类黑社会赌场中,充当勾引赌客的不光彩角色。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拉弗特扮演最为成功的一个角色是一个电视广告片中的罪犯。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着他的逃税指控,他的表演也同样的出色,这使得他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达茨·里根后来也走上了从事演艺事业的道路。 肯帕戈纳在一九五五年死于心脏病,当时佛罗里达警方正因一起诈骗案在悬赏缉拿他。他终年五十七岁。 我失去了米勒的消息。我只知道他在被逐出警察局以后离开了芝加哥,但不知所终。兰格在对他的开庭审判中被宣判有罪,不过他又立即提出了上诉,要求重新审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大肆地宣扬如果判他坐牢的话,那么他就会“揭开民主党的老底”。几年以后,兰格一案被法院撤销了。又等了几年,直到这桩丑闻差不多完全被公众遗忘之后,兰格又一次向芝加哥市政府提出了申请,并恢复了他警官的职务,居然还被补发了在离职期间的全部薪金。我有的时候还能在路上遇见他,不过我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人,在退休之后还能干些什么。 玛丽·安去了好莱坞,她后改的名字比玛丽·安·比姆更受欢迎。在同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签约以前,她拍过不少小成本的通俗影片。也许我应该去好莱坞,那样的话我们就会结婚了。玛丽·安曾经数次结婚,可其中没有一次是由我做新郎。她在去年死于肺癌,《国家调查报》上披露道,玛丽·安抽烟过量。 当我在报纸上读到玛丽·安的死讯时,那些尘封的往事又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一直住在佛罗里达,在几年前退休了。我和一名我在本书中没有提到过的一名出色的女人结了婚,婚后,我们住在博卡-罗顿,有时也去迈阿密住上一阵。 在二月份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和妻子携手在贝朗佛特公园里散步。当我看到纪念碑上写着“我很高兴是我,而不是你”的时候,我朗声大笑起来。我的妻子问我,究竟是什么让我觉得这样有趣,于是我告诉了她,然后她就建议我把这些写下来。 于是,我就写了这样一本书。 至于那场世纪盛会的宏伟场景也只维持了短短的一年,当他们最终关闭世界博览会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涌到泻湖前面去观看“梦幻之城”的毁灭,现在人们能去的地方只剩下了“空中飞行”的东塔了。 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一日,那是一个星期六,从华尔街涌来了大约两万人,前来观看最大规模的爆破。工程师们在“空中飞行”北面的支柱上绑上了重达七百五十磅的炸药箱,在卢福斯·道维斯自杀的枪声响起的时候,这座“伟大的高塔”也轰然倒塌了。 它引起了一场喧哗与骚动。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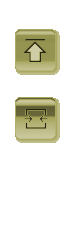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