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鲁智深 第十四章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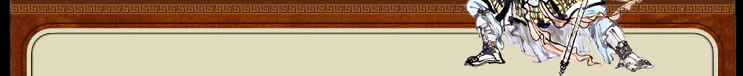 |
|
人生就是这样,你最终到达的地方,往往并非你最初的目的地。
但这并不是人们常说的“事与愿违”。
这是造化的戏剧天才,它让所有人永远走在奇妙的抛物线上,每走一步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情节,让你错愕、让你茫然、让你如在梦中。
人生在世唯一的魅力也可能就在于此。
就像野菊花院,40年前,它的出发点是妓院,不过起了一个具有山野气息的名字而已;到8年前,辣婆的个人总资产已经已经达到了300两黄金;之后,阿潮来了,野菊花院开始歇业调整经营模式、改造品牌形象;8年后,野菊花院除了固定房产、满院的野菊花、辣婆个人的寿材外,已经没有了一两流动资金,而它也名副其实地变成了一家专营野菊花的花坊。
但是,无论如何,辣婆认为自己是对得起自己的信念和努力的。
尽管自从猪头灾难后,8年来,野菊花院横祸不断:13个教师跳楼自尽(其中有4个未遂,长期在院中养老)、2次火灾、难以记述的自残及械斗事件、野菊花院甚至一度成为老鼠养殖基地……
尽管阿潮到现在为止还不会媚笑、不会弹琴、不会跳舞,甚至不会沏茶。
但是,阿潮的笑声愈发清脆、阿潮的笑脸愈发甜蜜、阿潮的身形愈发轻盈!
见到她的人都会立刻联想到山坡上、微风里、自由自在生长的一朵小野菊。
谁能比她更适合做野菊花院的形象代言人?
不羞婆婆在遗作中不也说:他奶奶的孤拐腿,老娘现在才明白——最标致的妓女是——根本不是妓女的妓女。
人生能有这样的成就,这难道还不够吗?
所以,辣婆在死的时候是瞑目的,是安详的,许多年后,在墓地流浪的老鼠能看到她的骷髅依然含着欣慰的微笑。
至于阿潮,这8年来,她想说就说,想笑就笑,有那么多漂亮的衣服任她穿,满院的鲜花任她采、任她戴。
就算这样的生活再继续8万年,她也依然是那个爱说爱笑的阿潮。
当然,只除了八月十五那一天。
这一天是阿潮的生日,可是惟独这一天,阿潮总是忍不住要发呆,有时候还会流眼泪。
而且,她从来不吃枣。
没有人知道在14年前的八月十五这天,还有两个孩子和阿潮一起出生在同一个地方。
更没有人知道,枣是这三个孩子当年唯一可以尽情吃的东西。
人人都说阿潮的心是透明的,因为他们看不到埋在阿潮心底的两个名字:阿风、阿达。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人都有他宿命的水土。
“不是黑店”里那小小的土炕就是阿达、阿潮、阿风宿命的水土。
土房低矮、土炕窄小、除了黄昏的光线和薄薄的脏棉被,这里见不到可以称之为温暖的东西。命运给他们的生命底色是一片昏黑。
这土炕是这三个孤儿的母亲,从出生起,他们三个就并肩躺在这阴郁潮湿冰冷昏黑沉默的母体上,在这方黑土中生长的梦和记忆是没办法区分彼此的。
尽管后来,这三个名字渐渐有了自己的颜色。但只要转回头,它们会立刻重新融合成当初的那一片昏黑。
蓝的天、黄的月、红的枣,阿潮、阿风和阿达——这并不是什么美丽的梦想,而是命定的起点和归宿。
就算天空陷落、月亮粉碎、红枣干枯,从哪里来,你就必须回到哪里去。
灵魂的落叶,必然归记忆的根。
所以,阿潮从没有太为分离伤心,总是要重聚的,这信心根本不需要理由。
所以,即便流泪,也不因为悲伤,只是命运吹来的风有些凉。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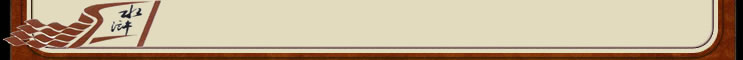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