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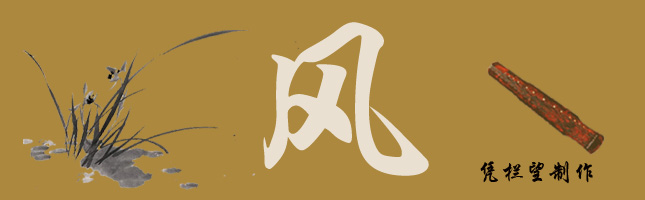
10.2 国风·唐风.山有枢
山有枢
题解:嘲讽守财奴。
【原文】
山有枢①,隰有榆②。子有衣裳,弗曳弗娄③。
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④,他人是愉。
山有栲⑤,隰有杻(6)。子有廷内(7),弗洒弗扫。
子有钟鼓,弗鼓弗考(8)。宛其死矣,他人是保(9)。
山有漆(10),隰有栗(11)。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
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注释】
①枢:树名,即刺榆树。
②隰(Xi):潮湿的低地。榆:树名。
③曳:拖。娄:牵。曳、拖在这里是指穿着。
④宛:死去的样子。
⑤栲(kǎo 考):树名,即山樗。
(6)杻(nǐu 纽):树名,即镱树。
(7)廷内:庭院和房屋。
(8)考:敲击。
(9)保:占有,据为己有。
(10)漆:漆树。
(11)栗:栗子树。
[译文]
山上长着刺榆树,榆树长在洼地中。你又有衣又有裳,为何不穿在身上?
你又有车又有马,为何不乘又不坐?到你死去那一天,别人占有尽享乐。
拷树生长在山上,镱树长在洼地中。你有庭院和房屋,为何不洒又不扫?
你又有钟又有鼓,为何不击又不敲?到你死去那一天,别人占有乐陶陶。
漆树生长在山上,栗树长在洼地中。你又有酒又有食,何不弹琴又鼓瑟?
姑且用它寻欢乐,姑且用它遣时光。到你死去那一天,别人占有进室中。
【赏析】
关于这首诗的主题,《毛诗序》认为是讽刺晋昭公,说晋昭公“不能修道以正其国,有财不能用,有钟鼓不能以自乐,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将以危亡,四邻谋取其国家而不知,国人作诗以刺之也”。这一说法毫无史实根据,不足为信。我们从诗歌本身来考察,认为它该是嘲讽一个守财奴式的贵族统治者的作品,郝懿行《诗问》云:“《山有枢》,风(讽)吝啬也。”可谓一语破的。也有人以为这首诗是“刺俭而不中礼”之作(如季本《诗说解颐》、方玉润《诗经原始》),这与“讽吝啬”说相去不远,但似较拘牵,不及前一说那么圆通无碍。至于朱熹《诗集传》认为此诗为答前篇《蟋蟀》之作,“盖以答前篇之意而解其忧”,“盖言不可不及时为乐,然其忧愈深而意愈蹙矣”。也可聊备一说。
全诗分三章,每章起首两句都用“山有×,隰有×”起兴,以引起后面所咏之词。有些诗的起兴与所咏之词有一定的关联,但本诗的起兴与所咏的对象则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这与现代许多即兴式的民歌相似。《诗经》本是音乐文学,往往随意借物起兴,取其易于顺口吟唱而已。
三章诗句文字基本相近,只改换个别词汇。一章的衣裳、车马,二章的廷内、钟鼓,三章的酒食、乐器,概括了贵族的生活起居、吃喝玩乐。诗歌讽刺的对象热衷于聚敛财富,却舍不得耗费使用,可能是个悭吝成性-的守财奴,一心想将家产留传给子孙后代。所以诗人予以辛辣的讽刺。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诗中为什么没有提到田地?难道田地在贵族死后不也是被他人(包括子孙)所占有的吗?这可能田地只是贵族吃用享受的资金来源,而不是可供玩乐的直接对象;也可能分封的土地只享有租税权而无所有权,贵族死后土地便将被王室收回。更主要的是文学作品只须提出若干典型性的事物以概括一般,而不必面面俱到、巨细无遗地罗列一切。这是欣赏文学作品必须注意的地方。
清陈继揆《读诗臆补》评此诗为“危言苦语,骨竦神惊”,直接从诗的语言看,似乎并不怎么危苦,但四“有”字、八“弗”字的“互相激宕”(陈震《读诗识小录》),后人读来确也有“愈旷达,愈沉痛”(吴闿生《诗义会通》)的感觉。陈继揆以为《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等篇,“是祖述此意(指劝人及时行乐)者”,虽然对《山有枢》的诗旨理解不在“讽吝啬”而在“劝行乐”,与笔者的观点有异,但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说,他的意见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读解】
钱财皆为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我们是赤条条来到这世上,也是赤条条离开这世上,既无什么可以羁绊,也无什么可以留恋。然而,偏偏有人想不开这个极其明显的理儿,一头钻进钱眼儿里,一头扎进财货中,做钱物的奴仆,变作挣钱聚财的机器。
或许有人会辩解说,挣钱聚财是一种个人爱好,一种寄托和追求。想来也是。挣钱聚财不也像收藏古董、收集邮票之类的爱好一样吗?纯粹的爱好和实用态度大不相同。
买用态度的着眼点是钱物的使用价值。按照这种态度,便要使钱、物充分发挥其使用效益。它们的使用效益,说穿了就是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仅此而已。对钱、物的要求取决于人的需要,可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人的需要和欲望难以有止境,吃饱了窝窝头。就想吃白面馒头,有了白面馒头吃就想白面包,有了白面包就想奶油面包,如此等等,钱、物就永远也填不满人的欲望的无底洞。纯粹爱好的着眼点是精神价值。这种价值满足的是精神上的需要和满足,甚至可以成为精神上的支柱。难道我们能说葛朗台、严监生一类的守财奴看重的不是这一点?难道他们对钱财的痛惜不像痛惜古董宝贝?
人各有志,不能勉强,守财奴有守财奴的活法,若痛恨他们,不相来往就行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贪得无厌也是一种活法,我们无法剥夺贪得无厌者的生存权,顶多在舆论上加以谴责,在道义上加以抨击。当然也有像诗仙李白那样的活法: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
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更多E书“应天故事汇——天天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