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第12章
|

|
|
|
饭厅里,三个人围着桌子喝茶:容貌酷似伊芙雷太太的老妇,一头红发肌肤苍白的女孩,还有黎凡特人。当主人为他开路,准备将他带到他们眼前的时候,格兰特隐身在壮硕的牧师身后,趁机留意他们每一个人,他甚感得意的是:他要抓的人认出了他。拉蒙双眼瞪视着他两秒钟,血液上冲涨红他的脸又迅速退去,一脸惨白。格兰特以旁观者的心态想着丹尼·米勒不知会怎么奚落这番景象——丹尼这家伙一向不留口德。黎凡特人无疑是这种游戏的大外行——过失杀人的可能性大于蓄意谋害。
“我带了一位访客,”牧师说。“这位是格兰特先生。
我看到他在钓鱼,但是什么都没钓到,所以邀他进来喝杯茶。这位是我的姐姐,迪摩太太。外甥女,迪摩小姐。还有我们的朋友,拉尔先生。现在,你要坐在哪儿? “
格兰特被安排坐在迪摩小姐旁边的位子,正对着拉蒙。牧师介绍的时候,拉蒙向格兰特微微点头示意,并无失态的表现。他纹丝不动地坐着,然后安静地起身去拿东西。他坐下时,格兰特注意到一件事,让他心里突地为之一震。拉蒙放在盘中的杯子方向错了。这个人是左撇子。
“我很高兴你们没有等我,爱格尼丝,”罗更先生打开清朗的嗓音说,“我本来以为你们会等我。我走过了那座摇晃的桥,绕道河的对岸回来。今天的黄昏真美。”
他的外甥女说:“我们很高兴你带格兰特先生回来,这样刚好凑成奇数,我们就可以进行投票了。我们曾经争执混血儿究竟是好是坏。我指的不是黑人和白人,而是不同语系的白人。我母亲说血统纯正的人种最优秀,当然,她这么说是因为她是如假包换的高地人,渊源直可追溯至创世纪的洪水时期。罗更家是麦坎南族人,从来就没有一个麦坎南男人没有自己的船。我的父亲生长于苏格兰和英格兰交界地带,祖母算是英国人,拉尔先生的祖母是意大利人,大家都各持己见。现在,罗勃舅舅无疑是站在我母亲那一边,身为一个血统纯正的高地人,他拥有这个纯正所有的冥顽不灵和这族人讨厌的自豪。所以我们找你加入我们的讨论,你的祖先该不会也是穿格子纹呢的吧。”
格兰特坦白说,他认为混血儿比血统纯正的人更受重视。所以说,混血儿到今天还能存在。混血使人类变得更多元化,不再仅限于几项单一的特质,这是件好事。混血儿多半聪明机伶多才多艺,甚至心胸宽阔,对人体贴关怀。总之,他认同迪摩小姐及——拉尔——先生的观点。
原本只是轻松的闲聊,格兰特大感讶异罗更先生竟激烈又认真地反驳他的话。高地人的血液蛊惑着他,他以此和西欧大多数的国家做比较,证明其他国家受到的遗害。
直到茶喝完时,格兰特才发现一件很可笑的事,罗更先生这辈子居然没有走出过高地一步。到低地去还只是因为三十年前的神职人员训练,他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其他的国家。善解人意的迪摩小姐适时接话,打断他的高论,缓和了这段争议。格兰特担纲罗更希腊合唱团中的一角( 宗教庆典或戏剧表演中的合唱团,在古希腊的悲剧中,他们扮演兴高采烈的观隶,借以说明戏剧的过程和诠释戏剧的主题,与演员产生共鸣。) ,他让自己的思绪专心针对拉蒙。
黎凡特人开始表现得比较自然一点。他出于个人的敌意正眼迎视格兰特的目光,旁的事全无法引起他的注意。
他无意掩饰他大拇指上的伤疤,尽管他已经知道格兰特看出他泄露秘密的杯子,该死的证据。他显然在盘算着这出正在上演的好戏。走着瞧吧,等时机到了,他就会乖乖就范。格兰特终于看到他眼里闪动敌意的凶光。逮捕个胆小鬼不是什么好差事。办案人员一刀砍了他的脚胫都比用刑具紧夹他膝盖来得干净利落。此时此刻,根本就不须动用到膝盖夹。
面对着这个男人,有一件事教格兰特不得不狠下心:在他留宿的短短三天时间里,似乎就已经赢得了迪摩小姐的青睐。他用飞快的浅笑回应她,他眼光停留在迪摩小姐身上的时间多过席间其他人。迪摩小姐看起来是个很会照顾自己的女孩——她像所有的红发女孩一样机伶聪慧——所以不嫌弃缺乏男子气概的拉蒙。拉蒙是否是想找一个盟友? 一个正在亡命天涯的杀人凶手通常没什么兴趣和人谈情说爱——尤其他对犯罪根本不在行。这就是机会主义者的卑鄙与无情。好吧,他不可能有机会达到目的的。格兰特静观其变。他重新加入谈话,品尝牧师宅五点半午茶中的主食炸鱿鱼,黎凡特人也吃了,格兰特好奇地想拉蒙怎么吞咽得下每一口食物? 他在意吗,还是他觉得一切都过去了? 他难道真的无耻到认为“你难道不这么想吗,格兰特先生? ”他是虚张声势还是胸有成竹? 他的手很稳——杀了他好友的那只细长黝黑的手——他在这席谈话中并未刻意回避他应该扮演的角色。对其他的人而言,现在坐在这里的男子和午餐时坐在同一个位置的男子并没有两样。
黎凡特人这一点做得太高明了。
茶喝完后,他们准备抽烟,格兰特向迪摩小姐奉上一根烟。她故作害怕地扬起她的眉毛。
“亲爱的先生,”她说,“这里是牧师会馆。如果你想出去走走,到河边的石头上坐坐,我可以奉陪,但在这屋顶下可不成。”
“在这屋顶下”这话显然别具深意,她的舅舅假装没听到。
“这真的是让我受宠若惊,”格兰特说,“只是,现在时间已经晚了,我还得走回葛宁村。我想我现在最好动身了。很感激各位让我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也许,拉尔先生愿意陪我走一小段路? 反正还早,天气又很好。”
“没问题,”黎凡特人说,比他早一步走向门厅。格兰特怕拉蒙一走了之,匆匆向主人道别。然后他看到拉蒙静静地在门厅穿他早上穿的旧军用外套。迪摩小姐跟着她的舅舅出来,在宅院前目送他们离去。格兰特一度担心她会追上来要与他们同行。也许是拉蒙转身背对着她的坚持让她却步。她若无其事地对他说:“你也不想自己一个人回来吧? ”他不答腔,明知她还站在那里,头也不回。这只意味着一点:他不要她同行,她最好识相地闭上自己的嘴。格兰特默不作声,要是能够避免的话,他不愿让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蹦这浑水。走出大门,两名男子转身向站在门口的两人致意。格兰特戴上他的旧软呢帽时,看到拉蒙致意,于是也脱下无边帽,跟着他回礼。除此之外,格兰特还真不知道有哪些其他的姿势可以表示道别的诚挚。
他们一语不发地朝前段的上坡小路走,直到远离房子所能看见的距离,驻足在通往山上的公路路段和沿着河通往田地那条小径的岔口,格兰特说:“我想,你该知道我要你做什么,拉蒙? ”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拉蒙说,迎面看着他。
“我是从苏格兰场来的格兰特探长,我有搜捕令可以逮捕13日晚上在沃芬顿队伍里杀了索瑞尔的凶手,就是你。我得警告你,任何你说的话,都会是法庭上的呈堂证供。我要确定你没有携带武器。能否麻烦你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一下,让我搜身? ”
“你弄错了,探长。”男人说,“我说我愿意陪你走一段路,不过我可没说走多远,恕我只送到这里。”他抽出插在口袋里的左手,格兰特惟恐是支左轮,在他出手的霎那,格兰特急忙举起双手。虽然他本能地闭上眼,还是看到拉蒙拿出的是牧师会馆下午茶桌上蓝色的茶杯纸垫。尴尬之余,他半睁半闭着眼睛,假装咳嗽打喷嚏,却只听到田埂上飞快离去的脚步声,他马上集中注意,辨识声音的方位,待他分辨清楚要追上去,已经过了两分钟。史翠德那晚的记忆向他袭来,他决定急起直追。没有人——即便是像黎凡特人这般身手矫捷的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跑得了多远。他的活动范围受限于精力耗尽的临界。他一定是沿着某条路逃,黎凡特人虽然顺利逃脱,但等他最后筋疲力尽时,终究还是被困在乡间里。没错,他够狡猾,对这点一定心知肚明。因此,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故伎重施,重耍在史翠德那晚的诡计;躲起来,等到天色全暗,能够安全的行动时,再来个名符其实的大逃亡。
格兰特想,这么一来,黎凡特人应该会站在较高的地势以方便掌握情况。远处几英里的地方,一条细窄的涓流从山上流下来。溪谷不足以挡住他直立的身躯,但是,如果他弯下身,它绝对可以遮蔽他沿着荒地爬上山头的行动。他锐利的双眼迅速朝眼力所及的四周环顾。他就着小峡谷,弯下身子,往上攀爬,每爬行几码就停下来,确定视野内没有任何动静,自己尚未暴露行迹。继续爬行,峡谷被桦树阻隔,更远处,峡谷贯入稀疏地散布着几株桦树的一片小台地。在黄昏绿晕的暮霭中,桦树尚未被黑暗吞噬,从台地放眼望去一览无遗,格兰特决定放手一搏。他小心翼翼地从溪边的沙岸起身,朝台地那片稀疏的草坪走去。越过草坪走到山腹前仅几码的茂密的扫帚树边缘。地理位置的优势让他得以侦查眼下整座山谷,只除了他右侧的那块石板被一堆乡间四处可见的柴薪遮住。看到这堆柴薪让他安心不少。柴薪对拉蒙来说,就如同贝德福街对街的店门,他毫不怀疑地确定拉蒙现在就藏在那里,等着格兰特从马路某处叫唤他。让他好生不解的是:拉蒙究竟是打算搭巴士还是计程车。除了等待黑夜来临之外,他迫切需要的是什么? 他一定很清楚,如果他等到天黑,格兰特将会发布警报。天色就要暗了下来。他该不该放弃自己的藏身之处,向拉蒙发出警告? 拉蒙就是想要他这么做吗? 他若是放弃继续监视,回去寻求救兵,这么做是否正中拉蒙的下怀? 他希望自己能够设身处地——以识破拉蒙的诡计。他越想越相信拉蒙算好他会折返寻求援助。显然他没别的路可走。他已经给了拉蒙一次开溜的机会,是他自己没有好好把握机会,从现在的处境看来,他是在做无谓的挣扎。无疑的,接下来,他料想探长已经吓得手忙脚乱,无暇念及他或其他人的感受,决定回去找救兵继续他的逮捕行动。一定是这样子,格兰特决定停留在原处,继续监视乡间的动静。
他藏身在充满湿气、萧瑟的桦树丛间好一阵子,眺望部分被树叶覆盖的溪谷。车子的煞车一度从他的左侧下山的公路尖声擦过,不久他看到车子经过村前那座桥,像只黑色的小蜘蛛一路爬到卡耳尼许旅馆后方,消失在北上的滨海公路。遥远的山头传来山羊的叫声,晚归的云雀在太阳还垂挂在山腰的天空中引吭高歌。除了潺潺水流,溪谷里没有任何动静。慢慢的,北方的天光逐渐开始隐没。有动静了,在河流的下方。不消说,那是河流水面上忽隐忽现的粼粼波光在流连。然而,那并非河水,是别的东西正在移动。他屏住呼息伺机行动,心脏压在草坪上,耳朵里听到自己脉搏跳动的频率。他必须稍安勿躁,但瞬间他清楚看到他想见的。他的猎物从河边一块十二英尺的巨石后溜了出来,消失在河的对岸底下。格兰特依然耐心守候。
他是想到平地上来吗? 还是他正盘算要到哪里去? 心情焦虑不安的格兰特,意识到自己正很可笑地耽溺于观看无自我意识的野生动物忙自己的事——大多数人在窥探时心里都会有那种痒痒的感觉。此时他朝河的下游缓缓前进,为了要确定拉蒙并非按兵不动。拉蒙成功地伪装成一名村民人,朝某处前进。他曾上过战场——格兰特差点忘了,拉蒙这个年纪多半曾经服过兵役。他或许熟知所有该知道的掩护技能。第二次,格兰特什么也没看到——那纯粹是自己蠢动的意识。如果拉蒙从岩石闪到河对岸隐蔽处的身手比直接现身在空地上更利落,之前他可能眼花没看清楚。
没有更进一步的行动,格兰特想起,河的左岸几乎可以说是最佳的藏身之处。该是他弃守高台上的席位,走下竞技场搏斗的时候了。拉蒙打算怎么做呢? 从他现在的位置来看,他可以在十五分钟之内重回牧师会馆。那里是他预定的目的地吗?他打算藉此激起眼光甚高的迪摩小姐的侧隐之心吗? 这个主意倒不坏。不过,换成格兰特,要是他是拉蒙,勘查情势后要回去找救兵,牧师会馆无论如何都是最后的选择。
格兰特相信自己想得没错,再度尽可能快速地爬下溪谷,保持隐蔽不被发现。他不假思索重返荒芜的小径,暗自期许这么做是对的。河流和他之间有一段延展开的荒地,遍地鹅卵石,但都不足以挡住比兔子大的东西,远处的柴薪堆掩护拉蒙,在趁他不注意时逃到河里去了。这么一来,现在干脆回去准备发布警报吧? 他要逮捕的犯人是否已经被牧师的外甥女窝藏起来了呢? 向第三者求救,有何不可? 他愤然反问自己:如果她真的窝藏他,她就要自行承担所有的后果。但是目前仍不须打草惊蛇,他克制着自己。他得弄清楚,拉蒙是不是真要回牧师会馆,再跟踪他,当场逮他个正着。
这样似乎比较明智,格兰特为了不让其他在河的下游、和拉蒙距离一样远的人看见他,快步穿过那一小段荒地。他想涉水渡河,跟着拉蒙到河床上继续监视他。他不想让他的犯人跑了,他要等他回到牧师会馆,他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轻取囊中之物。他若趁机冒险过河,可以就近监视拉蒙到了对面岸上的活动,必要时才能同步行动。
他若真追得上他,拉蒙绝对不会察觉到有人在跟踪他。他看着湍急的水流。时间宝贵,这个节骨眼上,就算全身弄湿了又怎么样。他咬紧牙关心一横,纵身潜人冰凉的水里,以舍命追逐的狂热栽进洪流之中。在河水被两块巨石分成三道水流处格兰特选择了一个定点,假如他能够顺利地接近第一块巨石,就能够攀住第二块巨石,跳到岸上去。就算跳不上岸也不要紧,只要他的手能够到河岸就行了。他要强行渡河。他往后退了一两步,目测他与第一块巨石间的距离。第一块巨石比第二块来得平坦,可以当成渡口,第二块形状较尖,用来做掩护。口中喃喃祷念着,他开始朝目标跋涉,感觉踩在石头上的靴子趾端有点打滑,他稳住脚步,却发觉脚下的石头斜向黑色的水坑,他只得往前一跳。明知从滑溜的石头跳跃会缺乏抓地力,但他还是顺利跳到了第二块石头的边缘,他感觉到自己拽在河岸的手离腰部很远。感谢上帝,他上气不接下气地爬上岸,匆忙拧干湿重的斜纹呢裤,以免水的重量妨碍他在高地上的行动。荒原里看不见一样诡异的事物。草坪上的枯草在他脚下变成一摊泥泞,干枯的黑莓固执地粘附在他被浸湿的呢裤上,等他挨近河岸的边缘时,已经被遮蔽着他的桦树树枝打得浑身红肿,还一脚踏进石楠窟窿踩个空。
他没好气地想着,这哪里是擒拿罪犯的行动,简直就是在演一出音乐舞台剧。气喘吁吁地他走到河流改道的位置,跳入水中继续侦查。他发现了他的猎物在离牧师会馆五码远的地方,小心缓慢地移动。格兰特脑中萌生一个念头,追捕者经过精心计划终于在户外攫取到猎物的那一刹那快感就要来临了。要不了太久的。瞬时,拉蒙转进清朗晨间有说有笑地穿过的那道矮小后门。他,格兰特,从桦木丛后现身,尽可能以两倍快的速度从河边的小径往下窜。他口袋里有一把自动手枪和两副手铐,现在终于要派上用场了——如果有必要的话,全都用得上。他的犯人未持枪械,从茶几上顺手牵羊的纸制杯垫也扔掉了,他不再具有威胁性。此时此刻,他也顾不了任何人的感受——只除了他自己的。就算会把这条街所有的女人都吓得歇斯底里——他也在所不惜。
格兰特仍然气得横眉竖眼,暗许着一等拉蒙走进了那道门就要他好看。我真想看看格兰特当时脸上的表情——一脸怨怼和忿恨的男人优雅地准备开始行动,想借着他高贵的行止掩饰住小男孩手拿着他第一支焰火时眼中不敢置信的惊喜。他费力的眨眼,眼前的画面还是没变。他真的没看错。拉蒙经过了那道门,走到牧师会馆围墙的尽头,准备过桥。这个笨蛋想做什么? 没错,格兰特觉得他是个大笨蛋。他已经帮他想好一条无懈可击的逃亡路线——回去求迪摩小姐,让他窝藏在牧师会馆里——这个笨蛋竟然辜负了他的良苦用心。他慢慢接近桥墩,这家伙在做什么? 他的脑袋在想什么? 他的一举一动都必有其目的,绝不是随随便便或是故弄玄虚的把戏。意识到自己太专注于脑中悬念的问题而忽略了留意自己现在的位置,他突然朝后方的河床瞥了一眼。一切看起来都正常,山谷附近没有什么异样。即使是在这个煞风景的时间,人人都正在大啖美味的晚餐而足不出户;但再过一个钟头,他们就会走出来,站在桥底的泥地上抽烟斗。来来往往的行人会愈来愈多,届时他躲藏的行踪就即将败露。拉蒙爬到桥边的路上,既不往北朝右边村子走,也没往左边的村子去。他穿越马路,再度消失在河堤。他准备去那里做什么? 他要从那里绕到位于河海交接点的旅馆,还是打算偷走福特? 但他显然在等格兰特发出警告。在他故意要引起格兰特的注意而等候了一段时间之后,并没有冒险沿着河岸走到车库。河岸? 河岸! 感谢上帝,他弄清楚了! 这个家伙想搭船一走了之。有许多船停泊在无人的河岸边,远离村子的视线范围内。现在河水退去——正好在退潮——神不知鬼不觉,没有半个人会看到他从河岸离开。格兰特奋力冲下山,心不甘情不愿地赞赏这个家伙的机灵。格兰特对西海岸十分熟悉,他十分清楚这些船只的使用率有多频繁。如果你住在西海岸的村子里,你会发现最供不应求的生活必需品竟是新鲜的鱼。如果麦肯锡人的船不见了,他们会先假设船是别人借走的,他们不会大声嚷嚷——免得万一借船的人把船还回去,还得费力气解释。脚踩着凹凸不平的小路,格兰特猜想着,拉蒙坐在牧师会馆里喝茶的时候,心里打的就是这个算盘? 还是他突然灵机一动决定这么做? 如果从马路跑到桥上这么远的路程是他事前计划好的,那么,队伍命案就可能是他一手筹划的。回过头来想,就算拉蒙的祖母是意大利人,他也不会没事带着派不上用场的匕首在身上。尽管这家伙两次逃跑都表现得欠缺克制力,但他本质比他的作为更恶劣。
在格兰特飞快地奔往下山的小路的这段时间里,他已经决定好下个步骤该怎么进行。今天上午,他在卡耳尼许旅馆向德莱斯戴尔暴露他的身份时,注意到房子另一侧突出、以沿海一道小小的防波堤为屏障的船库。格兰特记得很清楚,他看到一艘汽艇的船尾。如果他猜得没错的话,德莱斯戴尔现在应该在家,他的灯亮着,拉蒙正在动他的歪脑筋。
此时他已经跑到桥头,上气不接下气。他是从山谷的另一头,脚踩沉重的钓鱼专用靴,拖着一身湿重的斜纹呢裤跑下山。手脚敏捷的他,得凭恃坚强的意志才能以两倍的速度从马路北端最后几百码一鼓作气冲到卡耳尼许旅馆的大门。一到达那里,最糟糕的都过去了。旅馆坐落在离大门仅几码的介于海和马路之间的一条狭长的小路上,德莱斯戴尔的仆人惊讶地看到一个气急败坏、喘不过气来的人站在门边,马上跳起来妄下断语。
“主人发生了什么事? ”他说,“出了什么事? 他溺水了? ”
“他还没回来吗? ”格兰特说,“该死! 那是艘汽艇吗? 我能不能借用一下? ”他随手指了指前面的船库,仆人似乎被他弄得一头雾水。格兰特今天早晨出现的时候,这里没有半个佣仆。
“抱歉,先生,我们不能借给你。”仆人说,“你赶紧离开这里,这样会对你比较好。我先警告你,要是等德莱斯戴尔先生回来看到,他会让你很难看。”
“他就快回来了吗? 什么时候? ”
“他随时都会回来。”
“那就已经太迟了! ”
“出去! ”仆人说,“不然我就找人来撵你出去。”
“你给我听着,”格兰特说,伸出手臂紧抓住仆人,“别做傻事。我跟你一样,头脑清楚得很。过来,站在看得到海的地方。”
格兰特说话的语气攫住了这个人的注意,人为的胁迫让仆人吓得不得不慢慢走近海边,旁边还跟着一名女侍。
湖边一艘划艇,趁着退潮,快速从狭窄的出海口朝海里划去。
“你看到了吧? ”格兰特问,“我得赶上那艘船,用一般的船来不及。”
“不行,你别想借这艘汽艇,”男人说,“这里退潮退得很慢。”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借汽艇的缘故。平常是谁在开这艘汽艇? 德莱斯戴尔先生吗? ”
“不。他不在的时候通常是我在开。”
“来吧,你现在就来开。德莱斯戴尔先生非常清楚我的来历。我已经在河边钓了一整天的鱼。那个人偷了船,正要逃跑。我们还有其他的理由非得追上他不可,劳驾你开船。”
“如果我照做,你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 ”
“哦,那当然。正义会站在你这边。我答应承担责任。”
“好吧,我得先去交代一声。”他急忙想冲进屋里。
格兰特伸手拦住他,但迟了一步。有一瞬间他担心仆人不值得信赖,这么做只是借故脱身。但是没一会儿工夫他就回来了,他们穿过窄长的草地跑到船库,“罗勃船长”
号正浮在那里。德莱斯戴尔显然是用他的马从全国锦标赛赢来的奖金买了这艘船,领班抽拉引擎,发出短暂的空转声,德莱斯戴尔扛着他的枪走到屋子旁侧,看来是傍晚才从山里回来,格兰特高兴地跟他打声招呼,匆忙向他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德莱斯戴尔一语不发,和他一起从船库走回来说,“没事,皮金,我都知道了,我来载格兰特先生出海。待会儿准备一顿丰盛晚餐等着我们两个——不,三个——我们什么时候回得来? ”
不用再胆战心惊的皮金轻松地从船上下来。他推了罗勃船长一把,德莱斯戴尔发动引擎。一阵轰隆震响,他们驶离码头航向泻湖。格兰特的双眼锁定住衬着西天昏黄余晖的黑点。拉蒙此刻在做什么? 他们就快接近了吗? 那个黑点开始改变了它的航程。它似乎要划向南边的陆地,远离微亮的地平线,背后是南边山丘,小船几不可见。
“你看得见他吗? ”格兰特忧心地问,“我看不到了。”
“我还看得见,他现在正往南岸划。别紧张,我们会在他抵达前赶到。”
他们全速前进,南边山丘以看似不可思议的方式升起来与他们会合。短短一两秒间,格兰特想再确认一次那艘船。男人没命地划向岸边,对格兰待来说,他难以从水上的距离估算那人离岸边有多远或是他们离他有多远,罗勃船长的速度突然减缓,他掌握了所有之前悬念在心的事。
德莱斯戴尔减低速度。有一瞬间他们几乎追上他了。当两艘船距离五码远的时候,拉蒙突然停止划行。格兰特想,他准备束手就擒了。他看到拉蒙在船里弯下身。他是不是以为我们会对他开枪? 格兰特对此举感到困惑。接着,德莱斯戴尔关掉引擎,他们从容地滑近拉蒙的船。拉蒙脱了他的外套和帽子,站在船边弹腿,仿佛准备要跳水。他光裸的脚从湿答答的船缘滑开,整个人头上脚下落入水中。
他们清楚地听见一声可怕的撞击声,他的后脑勺撞到船,身影消失在水面。
趁着汽艇靠近拉蒙的这段时间里,格兰特已经脱下他的外衣和靴子。
“你会游泳吗? ”德莱斯戴尔冷静地问道。“如果你不会的话,我们干脆等他浮上来。”
“我没问题,”格兰特说,“我游得很好,能撑到船过来救我。如果我真的要逮他,我必须现在就游过去。他那下子撞得似乎不轻。”他从船缘纵身一跳,六七秒光景后,头从水面破水而出,格兰特把已经失去意识的人拖回船边,德莱斯戴尔帮着把他拉上船。
“逮着他了! ”他说,推滚着甲板上一团松垮垮的庞然大物。
德莱斯戴尔将划船绑在罗勃船长号的船尾,重新发动引擎。他好奇地看着格兰特一边马马虎虎地拧扭他的湿衣服,一边替他的猎物搜身。那个家伙被撞得完全不省人事,脑后一道伤口还淌着血。
“不好意思,把你的甲板弄脏了。”格兰特为地上的一汪血迹表示歉意。
“没有关系,”德莱斯戴尔说,“擦掉就没事了。这就是你要逮捕的人吗? ”
“是的。”
他看了一下那张黝黑、没有表情的脸。
“恕我冒昧地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抓他? ”
“他杀了人。”
“真的? ”德莱斯戴尔说,一副格兰特说的是“他偷了羊”的表情。“他是外国人? ”
“不,伦敦人。”
“他看起来似乎终于可以被处以绞刑了,不是吗? ”
格兰特突然朝他逮到的人瞥了一眼。他真坏到罪不可赦吗? 肯定没有。
直到卡耳尼许旅馆出现在他们的眼前,格兰特说,“他和牧师会馆的罗更住在一起,我不能把他带回那里。
我想,旅馆是最恰当的地方。政府将负担一切所需的费用。“
当他们迅速浮在码头栈桥上,大老远就看到他们回来的皮金赶紧下来迎接他们。德莱斯戴尔说:“我们追到的这个人撞到头了。哪一问生了火的房间能让格兰特先生休息? ”
“先生,你房间隔壁。”
“很好,我们把这个人抬上去。叫马特森到葛宁村找安德森医生来,顺便告诉葛宁的人,格兰特先生今晚住在这里,把他的东西全都带回来。”
格兰特婉拒他这种没有必要的慷慨。“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家伙可是从背后捅了他的朋友一刀! ”他说。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他,”德莱斯戴尔笑着说,“也无意要对付我旅馆的最大竞争对手。但你既然已经逮到你的人犯,总不能再让他逃了吧。想想看你的状况,你必须时刻看守着他,而他们这时才要开始替你冷冰冰的房间生火——”他指着河的另一边的旅馆,“把他带到床上,你的人犯现在半死不活的,你最好趁现在在房里洗个澡,把身体弄暖和。把他留在这里会方便得多。还有,皮金! ”他转过身,“管牢你的嘴,不准透露任何风声。就说这位先生划船的时候意外落水。我们看到了,就过去帮他一把。”
“是的,先生。”皮金说。
格兰特和德莱斯戴尔两个人扛着一团松软的庞然大物上楼梯,不假他人之手亲自将他搬进一间燃着壁炉火的卧房。接着,趁德莱斯戴尔写封短笺向迪摩太太解释,她的客人因一点小意外当晚必须留宿在旅馆里的当儿,皮金和格兰特把拉蒙搬上床。他有点轻微的脑震荡,他们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格兰特换上了主人的衣物,坐在床边等候,直到有人敲门通知他吃晚餐,他应了一声“请进”,迪摩小姐走进房里。她没戴帽子,手腕上拎着一个小包包,神情看来十分平静。
“我带了点儿他的东西来,”她说。走到床前,面无表情地看着拉蒙。为了得说点儿话交代一下,格兰特说他们已经去找医生来,而他——格兰特——的看法,拉蒙只有点轻微的脑震荡,他后脑勺受了一点伤。
“是怎么发生的? ”她问。格兰特面对他已经将自己的湿衣服换下,难以自圆其说。
“我们遇到德莱斯戴尔先生,是他对我们伸出援手。
拉尔先生站在防波堤边缘,一个不小心失足滑到水里,他跌倒的时候,后脑撞到地上。“
她点点头。似乎还是有些疑虑,但却又无法清楚表达出来。“那么,我今晚留在这里看护他吧,真多亏了德莱斯戴尔,及时救他一命。”她解开装杂物布袋上的结,“你知道吗,今天早上我们沿着河朝上游走的时候,我就有不祥的预感,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似的。很高兴发生的是这件事,没有太大的损害。我还以为会有人死掉,或是得了不治之症。”停了一会儿,手还是没闲下来,她把头别到肩后说,“你今晚也会留在德莱斯戴尔先生这儿吗? ”
格兰特回答“是”,话音一落门正好打开,德莱斯戴尔走了进来。
“准备好了没,探长,一定饿坏了。”他话刚出口,才发现迪摩小姐在场。在那一瞬间,格兰特觉得德莱斯戴尔不愧是个聪明人。他的眼睛眨都没眨。“哦,迪摩小姐,你在担心你逃课的学生吗? 依我看是没这个必要。他只是一点轻微的脑震荡,安德森医生待会儿就会过来看他。”
尽管这个女人跟着打马虎眼,在与迪摩小姐机灵的眼神交会时,格兰特的心仍不免往下沉。“谢谢你把他带回这里,”她对德莱斯戴尔说,“在医生来之前,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今晚想留在这里照顾他。”说罢她转身面向格兰特,故意问,“你刚刚叫什么探长? ”
“学校的督学,”( 也有督察者、督学之意。) 格兰特马上脱口而出,说完立刻后悔。
德莱斯戴尔也察觉到这个失误,硬着头皮帮他圆谎。
“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对吧? 调查工作一向是笨拙的最后手段。我们去用餐前,你还需要点儿什么东西吗,迪摩小姐? ”
“不用了,谢谢你。如果我需要任何东西,可以摇铃找服务生来吗? ”
“我希望你这么做。如果你要找我们,我们就在楼下的房间里。”他出了房门,沿着走廊走,而正当格兰特尾随着他出去时,迪摩小姐跟着他一起走出房间,顺手掩上身后的门。“探长,”她说,“你当我是傻瓜吗? 你难道不知道我在伦敦的医院工作了七年。你不能心存侥幸地把我当成这里最无知的人来要。能不能请你好心告诉我,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
德莱斯戴尔已经走到楼下,走廊上只剩他们两个。他觉得此时若再捏造另一个谎言是对她莫大的侮辱。“事到如今,迪摩小姐,我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你吧。我之前不愿让你知道真相,是因为我以为这样可以保护你,让你免于——免于对某些事感到遗憾。不过,这么做也无济于事。
我从伦敦来,是为了要逮捕这个现在和你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人。从我加人你们的下午茶,他就知道我的来意了,因为他曾见过我一面。他送我走了一段路之后,趁机逃脱。后来,他偷了一艘船潜逃,我们追到他时,他正准备从船上跳水,才会撞到自己的头。“
“你为什么要逮捕他? ”‘最后还是无法避免。“他在伦敦杀了一个人。”
“谋杀! ”这句话似乎是宣判,而非质疑。她似乎已经了解,在其他情况下,探长会说他是过失杀人,“所以说,他的本名并非拉尔。”
“他原名姓拉蒙——乔瓦得·拉蒙。”
他等着她像一般女人做出强烈的反应,嘶吼着“我不信! 他不可能做出这种事”这类的话,但是他错了。
“你要逮捕他只是因为他有嫌疑,还是他真的杀了人? ”
“恐怕这件事已经没有转圜的余地了。”格兰特委婉地说。
“但是我阿姨——怎么会叫他到这里来? ”
“我想可能是伊芙雷太太对他有所亏欠吧,她认识他有一段时间了。”
“在伦敦的时候,我只跟阿姨碰过一次面——我们对彼此都没什么好感——但她绝不会以为我能轻易同情做错事的人。我相信她这么做自有她的道理。这么说,他并不是新闻记者喽? ”
“不是,”格兰特说,“他替赛马赌注登记人工作。”
“哦,谢谢你终于告诉我真相,”她说,“我现在得帮安德森医生做些准备。”
“你还是愿意照顾他? ”格兰特不由自主地问。不相信事实竟然如此的狂喊现在才要爆发了吗? “没错,”这名让人刮目相看的女孩说,“他是个杀人凶手,但我们不能改变他脑震荡的事实,不是吗? 就算他滥用了我们的仁慈,我是名专业护士是不容改变的事实。
你可能知道过去的高地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即使客人用他的箭杀了主人的兄弟,他还是能受到最热诚最神圣的款待。我从来不以高地人为荣的,“她说,”但这次例外。“
不知道是因为想笑还是哽咽,她轻轻地倒抽一口气。说完,她回房间里去看护那名不小心利用了她和她家人的男人。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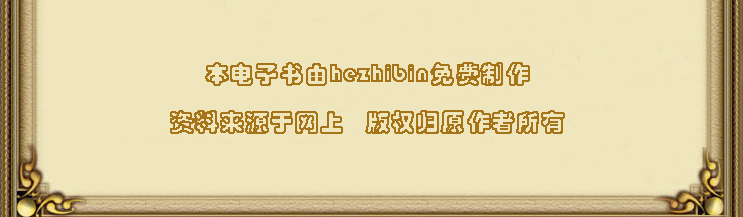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