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维尔停住了,狼狈不堪。“你们没有更多的要说?你们不感到惊奇?你们不感到震惊?你们没有受到刺激?”
奥维尔等着回答。这帮人互相看看,耸耸肩膀,终于头一个中年妇女代表他们说话了。
“太普通了,”她说。
“你是说对你们来说太熟悉了?”奥维尔追问。
“熟悉,”她说,其他人都点头表示同意。
奥维尔犯了难,试图继续往下进行。如果得不到某种真正的反应,他就无法调查他们的刺激反应样式。“你们有人想讨论这幅画吗?能猜出在此之前发生过什么,这期间会发生什么,能想象出下面会发生什么?”
这伙人默默地交换着眼色,眉毛弓起,肩头抬起,似乎一致认为他们的访问者是个疯子。一个人举起了手,是一个瘦瘦的20来岁的小伙子。“我想讨论,”他宣布说。“他需要爱,她需要爱,他们便做爱。一会儿,他快乐了,她快乐了,他们就休息。然后,如果他们不睡觉,就会再爱。他们很壮,他们会爱很多次,我想是这样。”
“对,对,”奥维尔不耐烦地说。“但没有别的你想说的东西了,这没有什么使你想到你自己——或烦扰你——或使你产生愿望——我是说——”
“没有什么可想的,”这个年轻人顽固地说。“太普通了,我们都这样干,我们都愿意这样干,没有更多要说的。”
奥维尔用询问的目光环视了其他5位。他们一致点头表示同意。
奥维尔泄了气,将这幅无用的厌贝壁画放在膝盖上,低头看着它。图画立刻引起了他的反应。一是,他从来没有同一个女人处于这么个难看的位置,他怀疑这种位置的可能性。另外,他除了一种位置外从没有用过别的位置,而且仅同少数几个女人,这真让他后悔。还有,他从来没有像画面上所明白表现出来的那样感到快乐,这让他伤心。还有,他的思想已飞向贝弗利·穆尔,这使他感到孤独。
这些念头,加上他那不可战胜的“彭图应询”在影响这6个对象上的失败,将他置于此刻的极度失望中。
他顽强地决定坚持下去,直到他的对象们投降。他把庞贝壁画扔到一旁,抓起了画堆上的第二幅。是琼·弗兰科斯·米勒的作品《情人》。它所描绘的现代内容同庞贝壁画所描绘的古代内容完全相同。奥维尔始终将米勒的作品当作一种发现,因为它使他的朋友们感到惊奇。大多数人只知道米勒传统的《拾穗女》,不相信同一个艺术家会将自己同惹人注目的性搅在一起。奥维尔将这幅画的复制品传了一遍。这些石头面孔仍然无动于衷,当询问他们的反应时,他们再一次无言以对,表现同上次差不多。
第三幅和第四幅是伦勃朗的《床》和毕加索的《拥抱》,都真实地揭示了男女面对面相交的情景。对此,反应是彻底的厌烦,6个对象一言不发。奥维尔不顾这些,又从画堆下面抽出帕辛的《女友》。对这幅画着一对裸体的法国女性恋者的肉感的画作,反应是迅速的,大声的,一致的,6个土人毫不掩饰地齐声大笑。奥维尔马上希望倍增。
“什么东西这么有意思?”奥维尔想知道。
那个20来岁的瘦小伙子说,“我们笑是因为我们都说——多么浪费时间!”
“这儿不干这种事吗?”
“从不。”
“你们感觉如何?”
“除了感到白费时间外别的什么也没有。”
奥维尔继续推进,想再弄出点什么,他再也没得到什么,帕辛画了一张白纸。
带着不断增长的沮丧,奥维尔传出了十六世纪吉乌里奥·罗马诺的一幅版画。画面上一对没穿衣服的男女,女的在上面。这伙人头一次表现出兴趣,他们挤到一起看这幅画,用波利尼西亚语交谈着。
奥维尔又来了情绪。“你们熟悉这个吗?”
坐在头上的中年妇女点头承认。“熟悉。”
“在海妖岛很流行?”
“是的。”
“真有意思,”奥维尔说。“你们瞧,在我的家乡,我们的人中,较少使用,比——”
“你们的人经常使用,”中年女人说。她直截了当地作出了声明。
“不全对,”奥维尔说。“据统计我有……”
“瓦塔说你们的女人在这方面很棒。”
“谁是瓦塔?”
“死去的那个。”
“啊,是的,”奥维尔说。“我为他感到伤心,但怀着对他的尊敬,我以为他不可能知道我们如何——”
瘦小伙子打断了他的话。“他知道,他已经爱过你们中的一个。”
奥维尔迟疑了,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肯定是语言交流上的问题。“瓦塔怎么会认识我们的人呢?”
“你们不是来到我们中间了吗?”
“你是说——我们中的一位——我们的女人?”
“当然。”
奥维尔试图控制自己。他不能反应过头,免得吓着他们,又缩回去不开口。小心,小心,他告诫自己,他得认真对待。
“有意思,有意思,”他开始说。“你们对我很有帮助,你们还能做得更好,我对瓦塔很好奇,想知道的详细些,以及我们的那个成员——”
用了5分钟,他得到了全部细节,全部可怕的细节,在第6分钟时他解散了他们,只想要求开会研究,他什么时间可以恢复使用主题知觉试验。
草房无人以后,奥维尔还在摇晃,实际上是发现自己在为他们最薄弱环节上的背信弃义、有失国格和无耻的行为而颤抖。只有一种事情要做,去向莫德·海登博士揭露这件丑闻,把罪犯从岛子上撵走。
奥维尔冲出他的住处,一口气越过他们的赫斯特·普林的住所,越过马克·海登的住所,激动得连门都没有敲,推门直奔莫德·海登的办公室。
她坐在桌子旁边写东西,他来到她面前,面红耳赤,领带歪斜。
“奥维尔,什么事?你看上去很失常。”
“是的,我是这样,”他说,努力屏住呼吸。“莫德,我不愿带给这个——太可怕了。”
莫德放下手中的笔。“请吧,奥维尔,什么事?”
“通过我的一项试验,我刚刚从土人那儿得知,你队中的一员,一个女的,已经——已经——已——,”他无法将这个字说出口。
“私通?”莫德轻声说。“对,我估计你说的是哈里特·布丽丝卡。”
“你知道了?”
“当然,奥维尔,我早已知道,了解真情是我的本行。不管怎么说,这种事情在这种封闭的社会传得很快。”
奥维尔向前迈了迈,弯着身子,活像正在生气的葛西摩多的样子,盯着莫德的脸。“你看来是赞成这种有失身份。”
“我不是不赞成,”莫德明确地说。“我既不是哈里特的母亲,也不是她的监护人,她正在度过她的21岁生日。”
“莫德,你对礼节的判断力哪儿去了?这可用来对付我们所有人,在他们眼中看低我们。另外——”
“恰恰相反,奥维尔。哈里特的表现是那么超群,在这么一个崇尚性技能的地方,她简直被看作王族,我们也是这样。他将得到更多的合作,我们也会。一句话,奥维尔,在他们眼中,我们不再是一伙装得一本正经的奇怪家伙。”
奥维尔在这番出乎意料的鸨母护妓的言论中直起了身,几乎气得要跳起来。“不,不,莫德,你全错了——你只讲科学没有人味,太客观——你看不出这会成什么样子。为了我们大家的利益,你得干涉,限制这位护士的下流行径,打发她回去,你应该这么做,打发她回去。你会对她说吗?”
“不。”
“你不?”
“不。”
“好吧,那么,好吧,”他结结巴巴地说。“如果你不,我来干,为了她自己的利益。”
他从肩上将领带结拉下来,带着受到伤害的尊严,昂首走出去了。
莫德长叹了一声,她原以为戴维森牧师很早以前就在帕果帕果沙滩上用刮脸刀片自聀身亡了,她错了。她不知道奥维尔会干什么,是否能干什么,她要自己注意他。艾德莱经常说,一个传教师可以在1分钟内破坏掉10个人类学家10年的工作。值得欣慰的是艾德莱在这个问题上站在她的一边,她拿起钢笔,重新开始记笔记。
雷切尔·德京10分钟前开门让莫尔图利的妻子爱特图进到她那简陋的问询治疗室时,还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么一个小村庄,女人们仅在有限的范围里活动,在她见过和碰到过这么多女人的时间里,她竟然从来没有见过莫尔图利的妻子。在约见前她还没意识到这一点。只是在等待爱特图,并想记起有关她的什么事情时,雷切尔·德京才觉察到这个问题。于是,她思忖着,没有见过莫尔图利的妻子是否是个偶然现象,或者是存心躲避,有爱特图的原因,也有她自己的原因。
现在,喝着卡普维茨送过来的洋铁杯盛着的凉甜茶,雷切尔能够肯定一点是,她等来了莫尔图利的妻子。尽管以前没有见过她本人,但在莫尔图利那个被大加渲染的自由协会里天听到。她料想——什么样子?当然是一个年龄比莫尔图利大的女人,很少魅力。她预料的是一个泼妇,一个丑婆,是长在外向好色的莫尔图利身上的一块溃疡。她预料的是一位赞瑟皮。旧日在学校里学《驯悍记》中的一段话浮现脑际:“她像弗洛伦蒂斯的情人一样凶恶像西比尔一样苍老、暴戾像苏格拉底的赞瑟皮,甚至更糟,她怎能让我动心。”
然而,在这儿的第一次见面,根本没有发现上述的一点证据,尽管雷切尔怀疑在深处肯定存在某种证据。从一开始握手,爱特图就镇静自若,平等待人。她内心极不情愿前来赴约——莫尔图利已明明白白地说写了——她的到来没有违背这一约定。雷切尔估计,她不到30岁;娇小的身材很匀称,太匀称了;脖颈挺拔;小小的乳峰高耸着。她有一种超越对话人向前看的异常习惯,你难以肯定她是真在对你说话或听你说话。她的声音细弱,必须向前探着身子来听她说什么,这就使人感到费力和不便。
“请喝茶,”雷切尔将冷茶放到她面前。“我希望你会感到它很提神。以前喝过茶吗?”
“喝过几次,是拉斯马森船长带来的。”
爱特图端起洋铁杯无声地喝起来,雷切尔在她对面草垫上坐下,喝自己的茶。雷切尔隐隐感觉到来访者的敌意。莫尔图利已经承认他告诉了妻子关于他的精神分析的详细情况。爱特图自然会怨恨一个局外人的干预,会将局外人视为丈夫反对自己的同盟。爱特图来此只不过是要证明,她不是像她丈夫对局外人所宣称的那样是她不般配。
如果她们之间出现诚心诚意的交流,雷切尔明白,也得先从自己开始。爱特图是不会带头的,这是可以理解的。要想让她讲出所有事情,雷切尔不得不用莫尔图利对家庭状况的不满来刺激她。雷切尔不愿用这个战术,但它又必需用。没有能让爱特图躺到病床上的希望,就是说让她进入病人的角色的希望。爱特图连一秒钟也不会允许,她来这儿是作为一位夫人拜访另一位夫人,作为一位被中伤的邻居准备纠正一个人听到的不正确传闻。她来这儿是为了喝茶和仔细地交谈。
对雷切尔来说,在过去的几天里已经证明莫尔图利是个比较好合作的精神分析对象,一旦他们之间的隔阂消除,他就尽力合作。他把疗程当作游戏。他双手抱头,仰面躺着,训斥他的“博士小姐”,粗言粗语,随随便便。他喜欢用他的爱情经验来扰乱雷切尔,他喜欢添油加醋地讲述他的梦,他从制造惊奇中获得乐趣。雷切尔立刻完完全全看透了他,他对他的未意识动机不十分感兴趣。当他的家庭危机爆发时,总是由传统的主事会来照料他。他的唯一的兴趣,他的游戏,据雷切尔观察,就是让他的精神分析医生谈论女性。他并非没有教养,但对教养不感兴趣。调查自己的思想,在自己脑海里的原始丛林中反省,对他根本没有什么吸引力,他所关心的,同他已故的朋友瓦塔一样,是肉体的感觉,彻头彻尾的享乐主义者:吃、喝、运动、舞蹈、交媾。对一个自由的灵魂,天生的单身,妻子尽职是一种负担。他并不急需要同爱特图离异,但急需要脱离婚姻的违背天理的牢笼。
雷切尔在过去的一周中想过,或许爱特图不像莫尔图利所说的那样冷漠,或许,在莫尔图利这样的人眼中,任何妻子都会是冷漠的。雷切尔断定,她总是无意识地在为爱特图辩护,因为这是为她们这一性别的辩护。像莫尔图利这样的男人对在一夫一妻制下依附于他们的女人是一种威胁。与此同时,尽管雷切尔还没有很深刻地研究自己内心的这一矛盾心理,但她在偷偷地同莫尔图利一道对付他的妻子。反正,爱特图站在了雷切尔和她的病人之问。在分析医生和分析对象之间没有了直线,因为爱特图使之成了三角形。雷切尔总感到有一种负罪感在限制着她,每当被莫尔图利的疯话吸引住的时候,是爱特图那看守人的眼睛制止了进一步的交流。
但是雷切尔知道她是在自欺欺人。爱特图根本没有站在莫尔图利和她自己之问。主要阻力是雷切尔执意要通过心理分析同莫尔图利沟通。越往下进行,证明困难越大。她对他讲年轻女子的阳物羡慕或青年男子的去雄恐惧,莫尔图利会放声大笑。她对他讲恋母情结罪和不可接受欲望的转移时,莫尔图利就嘲笑她,直到她眼看要流下泪来。
渐渐地,雷切尔得出一个结论:上世纪末在崇尚狡辩的维也纳由一个了不起的大胡子犹太人创始的一种心理治疗体系,效果不怎么好,即便在一种文明中产生点效果,也不是针对西方那种紧张社情的。对雷切尔来说,将她的那些关于在一个有高度学问、精心妆扮、压抑、物质化和竞争的社会产生出的神经病人和心理病患者的知识,同一人相对懒散、不很顽固、享乐主义、隔绝的,并且许多价值观都相反的半波利尼西亚社会联系起来,的确很费劲。是的,雷切尔能够看出,如果弗洛伊德、荣格、爱德乐在三海妖上接管主事会,他们一定会被绝望驱使互相进行分析。
但是,雷切尔接着看出,这是又一个借口。在她和成功治疗莫尔图利之间的障碍,不是爱特图,不是西方精神分析,说来说去,是她自己。她的病人的安然、缺乏规矩、男子气,使她害怕,放不开手脚。她无法追问他有关的问题,没有追问途径,因为他强大而她虚弱,而且还不敢让他明白这一点。优越的知识倒是挺好,它使你可以控制在贝弗利山上的一间带空调的办公室,它使你可以控制一个被有秩序的社会判定有病的人。另一方面,它作为你的唯一武装,在原始丛林中都不会给你力量。碰上了一头巨大动物,一头自由逛荡、靠本能和欲望生存的动物,用上述智慧、自我、超自我之类是治不了他的。你该做的是避开近距离接触,拼命跑开。
现在,兽中之王的配偶就在她的面前,这个配偶代表着雷切尔已经着手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的一半。必须做点什么。雷切尔看到来访者已经放下杯子在等待,一只手的手指不安地在草裙的腰带上摸索。雷切尔喝完自己的茶,将杯子放到一边,努力显出她的职业风采来。
“我再重复一遍,爱特图,你来了我真高兴,”雷切尔说。“你对我的工作有所了解吗?”
“我丈夫和婆母已经告诉我了。”
“好,我是说你同意我来帮助你和你的丈夫解决你们的问题。”
“我没有问题。”
雷切尔预料到她会不为所动,因此不感到惊奇。“就算没有,可你丈夫上诉主事会,基于你们存在婚姻麻烦而要求离婚,这件事交到我这儿了,我只不过是想在主事会的位置上提供服务。”
“我没有问题,”她重复说。“他有问题,是他上诉的。”
“我是事实,”雷切尔承认这一点,想起了莫尔图利第一次来访时也做了类似的否认和指责。“然而,如果一桩婚姻的一方不幸福,也就表示另一方也可能不幸福。”接着她补充说,“在某些情况下是这样。”
“我没说我幸福,我可以幸福,问题是他。”
“好了,你愿意让你们之间的事情继续下去吗?”
“我不知道……有可能。”
雷切尔不能让这种情形继续下去,她得让爱特图敞开。
“你知道我天天见你的丈夫,对吧?”
“是的。”
“你知道他讲的是他自己的生活以及他和你在一起的生活?”
“是的。”
“你知道他讲了什么?”
“是的。”
“爱特图,我已听了他的一面之词,为了对你们俩公平,我要听你的。他日复一日地告诉我,你不友好,不爱交际,行事不像个妻子,我只好相信她该离婚——就是说,如果我只听他的就会如此。但只听他的是不正确的,我必须听听你的,兼听则明。”
爱特图的脸第一次出现了变化,她的镇静瓦解了。“他撒谎,”她说。
“你肯定?他怎么撒谎?”
“他说我行事不像个妻子,我行事比村子里的任何一位妻子都不差。他说我不友好、不爱交际,根本不是一个妻子,其实说的只是一件事。他的感情不比一个孩子多。他不懂得一个妻子不只意味着一件事,而是许多事情。我为他做饭,我收拾他的屋子,我对他很好,我照顾他,这些对他都是白搭,只有一件事起作用。”
雷切尔等着她往下说,可她没有。“你说只有一件事管用。是什么?”
“肌肤之爱,那就是妻子,别的什么也没有。”
“你反对肌肤之爱——我们称作性交——你拒绝吗?”
爱特图的脸第一次显出愤怒。“反对,我没有。拒绝,我非这样不可。婚姻就没有更多的内容了吗?一周3、4次,我是接受的,我感觉正合适,我投入。但是从早到晚,天天如此,行吗?那是发疯。一个妻子无法满足他,100个妻子也不能,这不叫婚姻。”
雷切尔不禁打了个冷颤,爱特图的说法与她丈夫的说法竟然如此不同令她大感为难。“你说的同莫尔图利说的不一样,”雷切尔说。
“他告诉你的不真实。”
“他告诉我,除了对他最重要的那事,你完全是个出色的妻子。他说你冷漠,总是回绝他。他说他要求的在这儿很正常,但你一个月只跟他睡一、二次觉。”
“这是撒谎。”
“他说他不断地到‘共济社’大棚去得到满足,是吗?”
“当然。一个什么样的女人能满足他呢?”
“让我问点别的,爱特图,当你同他睡的时候,你愉快吗?”
“有时候,我愉快。”
“大部分时间你不这样。”
“在他的爱中痛苦太多。”
“能说明白点吗?”
“他爱的时候像换了一个人,他发疯,使人受到伤害。我们弄不到一块去,他伤人。”
“老是这样吗?”
“也许是的,但我不在乎,愉快胜过痛苦。现在更糟了,没有愉快,只有痛苦。他想甩掉我。”
“为什么不甩掉他?何必忍受呢?”
“他是我的丈夫。”
雷切尔闪出一个念头。“并且他是头人之子。”
爱特图立刻做出反应,她的措辞充满怒气,“你为什么这么说?什么意思?”
“我想找出是否有别的你不理解的动机影响。”
“我怎么这么对我讲话!”她跳了起来,怒气冲冲,站在雷切尔面前。“你和他串通一气,我一直尽力对你耐心些。也许你公平,但他战胜了你,像赢得所有女人一样。你以为他没有撒谎,你认为我撒谎,你认为我冷漠,你认为我不讨人喜欢,你认为我只是为了权威才试图控制他,你希望他休了我。”
雷切尔赶快站起来。“爱特图,不,我为啥要那么干?理智些。”
“我很理智,我看透了你,你要他离婚,这样他就为你而自由了,这是事实,你为你自己着想,不是为我,并且你反对我。”
“噢,爱特图,不——不——”
“我看到你的脸就明白了真象,你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但别烦我。”
雷切尔连忙追到门口,拉住她的胳膊想留住她。爱特图甩掉了她的手,打开门,一溜烟走了。
雷尔尔打算追出去喊住她,但没有这么做。关门时,她想起了在主事会也出现过这种情形。她曾想剔出莫尔图利的名字,但没有这么做。接着他明白了为什么,打了个冷颤。凭着直觉的某种感受,爱特图已经窥视到了雷切尔的潜意识,已经看出了雷切尔视而不见的东西——雷切尔在同她竞争她的丈夫——雷切尔是在治疗她自己,而不是他们俩的任何一个。
雷切尔站在门边,陷于自责的痛苦中。
过了好大一会,她的心神方定,理智占了上风,可以作决定了。她必须永远不管他们俩的事了,她得到胡蒂娅和主事会的其他人那里将这个案子交回去。
作为一个实地考察者,她可能是失败者。作为一个女人,她不会成为一个傻瓜。
后半晌,汤姆·考特尼带着莫德和克莱尔在公共托儿所呆了半个多小时。
托儿所有4间屋子——实际上是一间70英尺长的大厅用三堵隔墙间开来——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一些竹杆、木块、人和独木舟的小雕像,拉斯马森船长从塔希提买来的廉价玩具,成碗的新鲜水果,全是用来哄孩子的。
几个2到7岁的孩子蹦蹦跳跳地进出房间,追逐嬉闹。两个年轻妇女(志愿每次服务一周的母亲们)在照料他们。据考特尼讲,照料不是强迫性的。孩童来这儿全凭自愿或母亲的意愿,没有严格的时间表。有时,孩童们在指导下分组游戏,唱歌或跳舞,但大多数时间他们爱干什就干什么。青少年自由放任。
考特尼解释说,老赖特起初想引进一种源于柏拉图的极端体制,新生儿要从父母身旁拿走,放到一起喂养。因为分不出谁是谁,父母们就按要求把所有孩子都看作自己的孩子去爱。然而,这一梦想为海妖岛严禁乱伦的律条所粉碎。如果赖特的计划付诸实施,以后就会出现兄妹互婚,因为不知道他们的血缘关系。波利尼西亚人对这一想法深恶痛绝,考特尼引用布里福特的话说,不是道德观念使土人不接受乱伦,确切地讲,这条禁忌的存在是因为古老的神秘原因,因为,母亲潜意识地爱她们的儿子,想避开她们的女儿的竞争。
后来,老赖特向波利尼西亚人让了步,并且从未反悔,因为他们的体制用一种不那么激烈的方式吸收了他自己的主意。赖特对海妖岛上养育的孩子的唯一重要贡献就是公共托儿所,一直保留到现在。
当他们3个在最后一个房间观察孩子们玩耍时,莫德和考特尼讨论起斯波克和格塞尔戒律的优点,并同海妖岛上的相比较。克莱尔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他俩谈话,一边观察着房间里的娱乐活动,不觉联想到自己,心中又涌起近来对马克不让她生孩子产生的不满。
她觉察到考特尼细长的身影朝门口走出。“我们到外面看看,”他说。“外面太热或下雨时孩子们就在里面玩,大部分时间他们在后面像小野人一样厮闹。”
克莱尔和莫德跟着他从开着的门走进野草丛生的院子,周围既无墙也无篱笆,开放的三面只有稀稀拉拉的树和灌木丛为界,除了少数几个在跳跃、扔石头,外面的大多数孩子聚集在就要成为他们的游戏室的工地周围,个个都在为这座矮小的草房搬运竹杆和树叶子。克莱尔看了一会,发现只剩她一个了。考特尼已经带莫德到一株古树伞盖般的荫凉下去了。莫德慢慢地在草地上坐下,活像一只飞艇着地,考特尼则在她旁边一屁股坐下。不一会,克莱尔也同他们坐到了一起,舒适地伸开双腿。
克莱尔知道,考特尼在留意着她,而不是孩子们,但她佯装没注意。然而,由于感觉到这一点,她努力使自己尽量优雅些,像在博士尔吉斯镇卡诺瓦倚到波里纳·波那帕特身上那样。同这位自逐的芝加哥律师不断地接触,并没有使克莱尔对他失去兴趣。尽管12天前他向她揭示了他自己的过去,在克莱尔眼中他仍然是个谜。那次以后,他又多次谈到自己,但都没有新东西。偶尔,他像一个玩斯塔德牌戏的人,一次只翻开一张牌,让她获得一星半点他生平的事实,根据这个线索只能对他增加一点点了解。他已经确立了向导和指导二合一的角色,当他的听众离得太近时,就用玩笑或讥讽让他们离开些。
她突然决定要让他知道,她已觉察到被人观察。她敛住笑容,坦白地迎着他的视线,但他却笑了。“我刚才一直在看你,”他说。他越过莫德对她说话,好像莫德不在那儿。莫德也确实像不在一样,完全沉浸到孩童们的游戏中去了。“你同外面这些小女孩一样,活像只弓腰的猫。”
克莱尔感到失望。她想扮演的是卡诺瓦,代表的却仅仅是玛丽·劳伦辛。“是这儿的气氛,”她说,“游戏的气氛,对小女孩大有好处。”她瞥了一眼正在盖草房的孩童们,然后转向考特尼。“你喜欢孩子吗,汤姆?”
“当然,喜欢。”他又补充说,“更喜欢自己的。”
她吃了一惊。“你自己的?我不知道?”
“我是要让你相信,”他说。“我的意思是,我会喜欢自己的,许许多多自己的孩子,许许多多小家伙在我身边。”
“我明白了,”她说着,大笑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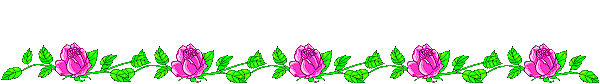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