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罗庆柯是个谨慎的人,他认为最好尽量不去利用留给他的秘密接头地点,其中也包括伏罗希洛夫格勒方面的接头地点。但是在最重要的地区书记雅柯温柯遇难之后,普罗庆柯到伏罗希洛夫格勒去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了。他是个勇敢的人,他冒着危险去利用老关系,——去找他妻子的女友,一个性情温和、个人生活不幸的单身妇女。她名叫玛莎·舒宾娜。她原来在机车制造厂里当制图员,在工厂第一批和第二批疏散的时候,她纯粹是出于热爱故乡而没有从伏罗希洛夫格勒撤退。不管怎样,她坚信故乡决不会沦陷,有一天她会有用的。
普罗庆柯听了妻子的劝告,决定去找玛莎,这是他们夫妇坐在玛尔法的地窖里那一夜决定的。
普罗庆柯不能带妻子走:他们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工作多年,两人在一起太引人注意。而且从工作考虑,卡佳也是留在这里更为相宜——可以跟区里的游击队小组和地下组织联系。所以他们当时在地窖里就决定,卡佳还是装做亲戚留在玛尔法家里,等住熟之后,如果有可能,就在附近村里找个教书的工作。
可是当他们作出这样决定的时候,他们不由地想到,自从他们共同生活以来,他们还是第一次要分别,而且是在他们可能永远不能再相见的这种时候分别。
他们沉默起来,久久拥抱着坐在那里。突然他们感到,他们这样拥抱着坐在这个黑暗潮湿的地窖里是美好而幸福的。
正像在许多结合已久的,由于观点的一致,而且不仅由于丈夫的、也由于妻子的劳动生活,还由于有了子女而牢牢结合起来的家庭里一样,他们的关系已经不需要经常的外表的感情流露。他们的感情深藏在内心里,好像灰烬里的热炭,遇到生活考验、社会动荡、痛苦和欢乐的日子,它就会突然发出熊熊的火焰。啊,那时在记忆中就多么鲜明地浮现出他们在鲁干斯克公园的最初几次相会、荡漾在城市上空的这种浓郁的槐花的香味、展开在他们青春岁月之上的繁星密布的夜空、青年时代的海阔天空的梦想、第一次肉体接触的欢乐、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感到的幸福、以及由于性格不同而产生的最初的酸涩的果实!不过这仍然是多么美妙的果实啊!吃了这种果实,只有脆弱的灵魂才会分离,坚强的灵魂是会永世结合在一起的。
对爱情来说,严峻的生活考验和对初恋的生动的回忆,都是同样不可缺少的。前者把人联系在一起,后者令人永葆青春。共同的道路把人联系在一起的力量是伟大的,假如可以用“你可记得?……”这寥寥几个字来表达的感情永远能使你们激动。这甚至不是回忆。这是水恒的青春的光辉,是更向前进、走向未来的召唤。把它保存在自己心坎里的人是幸福的……
普罗庆柯和卡佳坐在玛尔法的漆黑的地窖里所体验到的正是这样的幸福之感。
他们坐在那里默默无言,但是他们心里却鸣响着:“你可记得?你记得吗?……”
他们特别难以忘怀的是他们最后表白爱情的那一天。他们已经有好几个月经常会面,实际上,根据他的可以为她赴汤蹈火的言谈和举动,她已经一切都明白了。但是她总不让他倾吐心底里的话,自己也没有向他许下任何诺言。
头天晚上他说服她第二天到他宿舍的院子里来找
他,——他在州委党校里学习。她同意来,这就是他的一大胜利:就是说,她在他的同学面前已经不感到怕羞,因为下课后这几个钟点里,院子里总是挤满了学员们。
她来的时候宿舍的院子里都是人。学员们正在院子当中玩打棒游戏,他也在玩。他穿着乌克兰式衬衫,没有束带子,敞着领口,兴高采烈。他跑到她面前问了好,说:“你等一下,我们马上就完……”这时院子里所有的学员都望着他们,后来大家闪开一点,让个地方给她,于是她也来看游戏,但是她只望着他。
她一向总因为他的个子不高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可是现在她仿佛是第一次看见他的全身,看到他是多么强壮、敏捷和顽皮。最复杂难打的棒子他只要一棍就能把它们打出去。
她觉得,这一切他都是为她做的。他不断地在耍弄对手。
那时列宁大街初次浇上柏油,天气炎热,他们在发软的柏油路上走着,非常幸福。他穿着那件乌克兰式衬衫,但是腰里已经束上带子,披散下来的亚麻色头发是波浪形的。他在她身边走着,不停地说着。走过一个摊子的时候,他买了些干枣,放在纸袋里拿着。枣子是热的,很甜,可是只有她一个人吃,因为他老在说话。她记得最清楚的是在这样美妙的柏油路上竟没有垃圾箱,连枣核都没有地方吐,她只好把枣核含在嘴里,希望等拐到一条较差的街上再吐掉。
突然他住了嘴,用那样的眼光望了望她,把她看得不好意思起来。接着他说:
“我现在就要在大街上当着人家的面吻你!”
那时她身上的那股犟劲发作了,她含着愠意瞟了他一眼,说:
“你敢试一试,我就把枣核都吐到你脸上!”
“多吗?”他非常正经地问。
“有十一二颗!”
“我们跑到公园里去吧?跑步走!……”他喊了一声,不容她思索,一把就抓住她的手。他们就一路上嘻嘻哈哈,旁若无人地朝公园跑去。
“你可记得?……你记得吗,那一夜公园里多么美?……”
现在,在这黑洞洞的地窖里,就像当年在星空下的鲁干斯克公园里一样,卡佳信任地把她的发烫的脸藏在丈夫的有力的令人感到舒服的肩膀、脖子和长满柔须的面颊中间。他们就这样坐到破晓,没有一丝睡意。后来普罗庆柯把妻子紧紧搂了一下,接着把脸移开一点,放松了手。
“该走了,是时候了,我的小燕子,我亲爱的小鸽子!”他说。
但是她仍然不肯把脸从他肩上移开,他们又这样一直坐到外面通明大亮。
普罗庆柯派柯尔聂·季霍诺维奇祖孙俩到米佳金根据地去打听队伍的情况。他花了很多时间向老头说明,应该怎样采取小组行动,怎样由农民、哥萨克和定居在各个村里的复员军人组成新的游击小组。
玛尔法招待他们吃饭的时候,一个老大爷,玛尔法的远亲,终于突破孩子们的警戒线闯进来,正好赶上吃饭。对什么事都感兴趣的普罗庆柯就抓住老大爷问长问短,想了解了解一个普通乡下老头对目前局势的估计。这个老大爷就是给柯舍沃伊和他的亲属赶车的那个饱经沧桑的老头,他的黄骠马到底还是被过路的德国军需官们抢去了,因此他只好回乡去投靠亲戚。老大爷一听就明白,跟他说话的不是个普通人,他就七拉八扯地谈起来:
“你瞧,是这么回事……三个多星期以来一直有他们的军队开过去。开过去的兵力可真大呀!红军现在是不会回来了,不会回来了……战事已经在伏尔加对岸,在古比雪夫附近进行,莫斯科被包围了,列宁格勒被占领了,还有啥好说的呀!
希特勒说,他要用围困法拿下莫斯科。”
“我相信你已经把这些谎话信以为真了!”普罗庆柯眼睛里带着魔鬼般的火星说,“你瞧,老朋友,咱俩个子差不多,你们你的衣服给我一身,我把我的留给你。”
“哦,原来如此!”老大爷一下子全都明白了,用俄语说道,“衣服我马上给你拿来。”
个子矮小的普罗庆柯自己虽然并不老,但是胡子已经留得相当长,他就穿着这个老大爷的衣服,背着背包进了石滩城,闯到玛莎家里。
他乔装打扮在故乡的街道上行走,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
普罗庆柯在这里出生,又在这里工作过多年。许多企业、机关、俱乐部的房屋和住宅都是他亲眼看着——并且大部分是由于他的努力——兴建起来的。比方说,他记得怎样在市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订出兴建这个小公园的计划,他怎样亲自监督布置和栽种灌木。他本人在故乡的市政建设上不知花了多少心血,可是在市委还总是有人责怪,说院子和街道不够清洁,这倒也是事实。
现在一部分房屋被炸毁了。在保卫战最激烈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种破坏使城市变得多么难看。但是问题甚至不在这里:相隔不过几个星期,这个城市已经变得满目荒凉,仿佛新的主人连自己也不相信他们是搬来久居的。街道不洒水,不打扫,小公园里的鲜花都枯萎了,草坪上杂草丛生,纸片和烟蒂旋风似的在浓密的红色尘土里盘旋。
这里是煤都之一。以前运到这儿来的货物比运到国内其他许多地区的要多。街上的人群都衣冠整齐,色彩华丽。可以感到,这是南方的城市:总是有许多水果、鲜花、鸽子。现在却是人群稀少,色调灰暗,不引人注目了。人们都穿得马虎、单调,仿佛是故意不修边幅似的。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似乎连脸也不洗。给街道增添表面色彩的是敌人官兵的制服、肩章和证章,最多的是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但也有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只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只有他们的汽车乱揿着喇叭满街飞跑,卷起阵阵的尘土。普罗庆柯有生以来还没有感到过对这个城市和它的居民怀着这样深切的爱怜之情。
他有这样的感觉:他有过一个家,但是他被赶出这个家,现在他偷偷地回到老家,眼看着新的主人们在盗窃他的财产,用脏手掠夺他所珍惜的一切,作践他的亲人,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毫无办法。
在妻子的女友身上也打着这种普遍的抑郁和邋遢的烙印:她穿的是破旧的深色衣服;亚麻色的头发胡乱挽了一个髻;好久不洗的脚上穿着便鞋,显然,她就是这样脚也不洗就上床睡觉的。
“玛莎,怎么可以这样消沉!”普罗庆柯憋不住了。
她无动于衷地望望自己身上,说:
“是吗?我倒没有注意。大家都是这样生活,而且这样也比较好:省得他们来纠缠不清……再说,城里也没有水……”
她不作声了。普罗庆柯这才注意到,她是多么消瘦,她的房间里空空荡荡,不像个家的样子。他猜想她大概经常忍饥挨饿,早把东西变卖一空了。
“啊,我们来吃点东西吧……这都是一个好心的妇女给我预备的,真是个聪明的女人!”他在他的背包旁边忙起来,不好意思地说。
“我的天,问题难道是在这里吗?”她用双手捂住脸。“请您带我走吧!”她突然感情激动地说,“带我到卡佳那里去,我情愿尽我的力量服侍你们!……我情愿做你们的仆人,只要不天天受这种窝囊气,只要不这样慢腾腾地等死,没有工作,生活又没有任何目的!……”
她像平时一样对他称“您”,虽然她跟卡佳从小就是朋友,从他跟卡佳结婚起就认识他。他以前也猜到,她所以不肯对他称“你”,是因为不能排除她这个普通制图员和他这个重要干部之间的悬殊之感。
普罗庆柯的宽阔的前额上出现了一条深深的皱纹,他的灵活的蓝眼睛里露出严峻的、关切的神色。
“我要直截了当地跟你谈一谈,也许很不客气,”他说,并不望着她。“玛莎!要是问题只关系到你和我,我就可以带你到卡佳那儿去,把你们俩藏起来,我自己也躲起来。”他带着严厉的苦笑说。“但是我是国家的公仆,我希望你也能尽最大的力量为我们的国家服务:我不但不带你离开这里,我还要让你去赴汤蹈火。你要对我直说:你同意不同意?你有没有这样的力量?”
“干什么我都同意,只要不过我现在过的这种生活!”她说。
“不,这不是答复!”普罗庆柯严厉地说,“我给你指的出路并不是为了拯救你的灵魂,我是问你:你同意不同意为人民和国家服务?”
“我同意。”她轻轻地说。
他迅速地隔着桌角向她弯过身去,抓住了她的手。
“我要跟这儿城里的自己人建立联系,可是这儿出过事。哪一个接头地点可靠,我没有把握……你应当拿出勇气和魔鬼那样的狡猾,去检查我给你的那些接头地点。你肯不肯去干?”
“我去。”她说。
“你要是出了事,他们会慢慢地折磨你,让你不死不活。
你不会泄露吧?”
她沉默了一会,仿佛在检查自己的灵魂。
“我不会泄露。”她说。
“那么你听着……”
在昏暗的灯光下,他把身子向她弯得更近(近到使她看见他的秃鬓上的一个新伤痕),给了她一个就在石滩城的秘密接头地点,他认为这一个比其他的可靠些。他特别需要这个接头地点,因为通过它,他可以跟乌克兰游击队司令部联系,并且不仅可以了解一个州里的情况,而且还可以了解苏联各地的情况。
玛莎表示愿意立刻就去。这种缺乏经验的表现和天真的牺牲精神的结合,使普罗庆柯心里深受感动。狡黠的火星顽皮地从他的一只眼睛里跳进了另一只眼睛里。
“这怎么行!”他带着高兴的、亲切的谴责口吻说。“这需要做细致的工作,就像在时装公司里工作一样。你要大摇大摆地大天白日去,我会教你怎么做和做些什么……我还要保证我的后方不出问题呢!你住的是谁的房子?”
玛莎在机车制造厂的一个老工人的小房子里租了一间屋子。这座小房子是石头砌的,当中有一条过道,过道的一头通大街,一头通到用石砌矮墙围着的院子。小房子的一半有一间屋子和一个厨房,另一半是两个小房间,玛莎就租了其中的一间。老头的子女很多,但是他们早已跟他分开:儿子有的在军队里,有的疏散了,女儿们结婚后都住在别的城市里。据玛莎说,房东为人谨慎仔细,爱读书,虽然有点孤僻,但是为人正直。
“我就说您是我的舅舅,从乡下来的,我母亲也是乌克兰人。我就说是我自己写信叫您来的,要不然我的日子不好过。”
“你把你舅舅带去见见房东:我们来看看,他这个人怎么孤僻法!”普罗庆柯干笑着说。
“那算是什么干活,拿什么来干活啊?”那个“孤僻人”阴郁地嘟囔着,偶尔抬起鼓出的大眼睛望望普罗庆柯的胡子和他右边秃鬓上的伤痕。“我们两次亲手把设备从厂里搬出来,德国人也轰炸过我们好几次……我们造过机车,造过坦克和大炮,可是如今我们反而修理起煤油炉和打火机来了……当然,车间里还有一些零件留下来,要是去收罗收罗,厂里这儿那儿还有好多设备,不过要知道,这需要所谓真正的主人。可是如今……”他挥了挥捏成拳头的干枯、粗糙的小手。“这些人都不是认真办事的人!……目光短浅,而且——都是些贼。你信不信,一个厂里一下子来了三个主人:一个是克虏伯①派来的,从前这个厂是哈特曼的,克虏伯收买了他的股票;还有两个主人是铁路管理局和电力公司——电力公司把我们的热电站抢到手里,虽然我们的人在撤退前把发电站炸了……他们在厂里东晃西晃,结果把厂分成三份。真叫人哭笑不得:一个被破坏了的工厂,他们居然还要给它竖起界标,就像沙皇时代农民给自己的一小块土地竖桩子那样。连厂里的那些路上,也像被猪拱过那样挖了好多坑,截成一段一段。他们分了赃,竖起界标,就各自把残存的设备运回德国去。至于比较小比较次的东西,他们就拿去到处兜售,像旧货市场的投机商人一样。我们的工人讥笑说:‘上帝赐给我们的老板真不赖!’弟兄们这些年来,你自己知道,已经习惯了什么样的规模,可是给这批家伙干活,弟兄们不但不愿意干,连瞅着他们都别扭。总之是叫人哭笑不得……”
--------
①克虏伯是德国最大的军火康采恩的老板之一。
他们——留着长胡子的普罗庆柯、默不作声的玛莎、驼背的老太婆和“孤僻人”——坐在油灯光下,好像是一群穴居人。他们的怪诞的影子时聚时散,在墙上和天花板上显得非常高大。“孤僻人”快上七十了,他身材矮小瘦弱,脑袋很大,使他支持着这个脑袋很费劲。他说话声调阴沉而单调,只听到一种“布—布—布”的声音。但是普罗庆柯乐意听他讲话,不单是因为这老头说得有理,说的是实话,还因为他喜欢听到一个工人能这样认真而详细地向一个偶然遇到的农民介绍德国人统治下的工业情况。
普罗庆柯终于憋不住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在乡下都这么想:他们压根儿不打算在我们乌克兰发展工业,他们的工业都在德国,他们只要我们的粮食和煤。乌克兰好像是他们的殖民地,我们就像是他们的黑奴……”普罗庆柯觉得“孤僻人”在惊奇地望着他,就干笑了一声,说:“我们乡下人这样议论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人民大大地成长了。”
“哦,不错……”“孤僻人”对普罗庆柯的议论已经毫不感到奇怪,说道,“好吧——就算是殖民地。那么,他们把农业推进一步了吗?”
普罗庆柯轻轻地笑起来:
“冬小麦我们插种得稀稀拉拉,有的播在残留着冬麦茬和春麦茬的地里,翻地用的是斫柴刀。你自己明白,我们能播得了多少种!”
“就是那么回事!”“孤僻人”对这事也不表示惊奇,说道。
“他们不会经营。他们搞惯了敲榨勒索,像骗子那样夺取别人的东西,他们就靠这个生活,上帝宽恕,他们还打算带着这种文化去征服全世界呢,真是一批愚蠢的畜生。”他不带恶意地说。
“唉,老头,比起像我这样的庄稼人,你可强得太多啦!”
普罗庆柯高兴地想道。
“您来看您外甥女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人看见您?”“孤僻人”声调不变地问。
“看倒是没有人看见,可是我怕什么?我证件都齐全。”
“这我明白。”“孤僻人”回避地说,“不过这里有规矩,我应该给您向‘警察局’报一下,假如您待不久,就不如免了。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因为我一眼就认出了您,所以照直告诉您,要知道,您到我们厂里不知来过多少次,万一坏人也认出了您……”
不,妻子说得不错,她一直对他说他的运气好。
第二天一清早,玛莎到一个接头地点去过之后,带了一个陌生人来见普罗庆柯,那人跟“孤僻人”招呼,好像他们昨天还见过面,这使普罗庆柯和玛莎非常惊讶。普罗庆柯从此人嘴里知道,“孤僻人”是留下做地下工作的自己人。
普罗庆柯也是从这个人嘴里初次听到,德国人已经深入国土:这是伟大的斯大林格勒大战开始的日子。
以后几天,普罗庆柯一直忙于检查和部分地恢复城里同全州的联系。
在活动最紧张的这个时候,给普罗庆柯跟本城组织接上关系的那个人带了“女演员刘勃卡”来见他。
普罗庆柯听完刘勃卡所能讲的关于被关在克拉斯诺顿监狱里的人们死难的详情之后,闷闷地坐着,半晌说不出话来。他为舒尔迦和瓦尔柯惋惜,深深惋惜。“两个多么好的哥萨克!”他心里想。突然他想起了妻子:“她一个人在那边不知怎么样了?……”
“是啊……”他说,“艰苦的地下工作!这样艰苦的地下工作世界上还从来不曾有过……”他在房里来回地踱着,一面仿佛是自言自语似的跟刘勃卡谈话。“有人把我们的地下工作比做那一次武装干涉时期在白党下面的地下工作,可是这哪儿能比呢?这批刽子手的恐怖手段毒辣透顶,白党跟他们一比简直像孩子,这批魔王杀的人要用百万来计算……可是我们也有当时所没有的优越性:我们的地下工作者和游击队,有我们党和国家的全部威力、有我们红军的力量做后盾……我们游击队的自觉性比较高,组织比较严密,技术——武器和通讯工具等等也比较强。这些情况应该向老百姓说明……我们的敌人有着任何人都没有的弱点:他们笨拙得要命,什么事都按照指示去做,按照时刻表去做,他们在我们的老百姓中间生活和行动完全是两眼漆黑,什么都不懂……这是应该利用的一点!”他在刘勃卡对面站住,说,接着又从一个角落踱到另一个角落。“这一切都应该向老百姓说明,让老百姓不要怕他们,让老百姓学会骗他们。应该把老百姓组织起来,——他们本身就会产生力量:到处都要建立可以在矿井、在农村活动的地下小组。人们不应该躲到树林里去,——我们,去他妈的,偏要待在顿巴斯!应该到矿井去,到农村去,甚至到德国机关里去——到职业介绍所、市参议会、办事处、农业指挥部、‘警察局’、甚至到秘密警察机关里去。用破坏、怠工、无情的恐怖行动从内部来瓦解他们的一切!……把当地的居民——工人、农民、青年——组织成小组,五个人一组,但是到处都要有,不要有死角……他们全是吹牛!敌人在我们这儿吓得牙齿打战!”他说时怀着满腔仇恨,这种情绪也感染了刘勃卡,使她开始呼吸困难起来。这时普罗庆柯记起了刘勃卡“受上级委托”转告他的话,“就是说,你们的工作很得手?在别处也是这样。不过,做这种工作要没有牺牲是不可能的……你叫什么名字?”他又在她对面停下来,问道。
“哦,这不像话:这么好的姑娘不可能是刘勃卡,应该是刘巴①!”快乐的火星在他的一只眼睛里跳了一跳。“啊,你再说说你要些什么?”
--------
①刘巴是刘波芙的爱称,刘勃卡是昵称。
刘勃卡有一霎时觉得,她眼前非常鲜明地呈现出他们七个人排列在一起站在室内的情景。低低的乌云在窗外奔跑。每一个走到队列前面的人都脸色苍白,宣读誓词的声音都提得很高,达到响铃似的调子,遮盖了那虔敬的颤抖。由奥列格和万尼亚起草、经他们全体通过的誓词,这时突然离开了他们,高升到他们头上,比法律更为森严,更为不可动摇。刘勃卡回忆起这幅情景,她的脸色由于重又感到激动而发白,脸上那双稚气的、射出冷酷刚强的光芒的蓝眼睛也显得异常富于表情。
“我们需要指导和帮助。”她说。
“你们是谁?”
“‘青年近卫军’……我们的指挥员是伊凡·杜尔根尼奇,他本来是一个红军中尉,因为受伤曾陷入过包围。政委是奥列格·柯舍沃伊,他是高尔基学校的学生。现在我们有三十来人宣过誓表示忠诚……我们是五个人一组,正像您所说的,是奥列格建议这样做的……”
“大概是上级的同志告诉他这样做的。”普罗庆柯恍然大悟地说。“不过反正一样,你们的奥列格是好样的!……”
普罗庆柯非常兴奋地坐到桌旁,叫刘勃卡坐在他对面,要她报出全体总部委员的名字,并且把每个人都描述一下。
刘勃卡说到斯塔霍维奇的时候,普罗庆柯垂下了眉角。
“等一下。”他说,一面碰碰她的手,“他叫什么名字?”
“叶夫盖尼。”
“他是一直和你们在一起的呢,还是从别处来的?”
刘勃卡叙说了斯塔霍维奇怎样在克拉斯诺顿出现,关于他自己他是怎么说的。
“你们对这个小伙子要小心,要审查他。”普罗庆柯就把斯塔霍维奇从游击队里失踪的怪事告诉了刘勃卡,“希望他没有落到过德国人手里。”他沉思着说。
刘勃卡的脸上表现出的不安由于她不喜欢斯塔霍维奇而更加强烈。有一会工夫她一声不吭地望着普罗庆柯,后来她脸上的线条舒展了,眼睛亮了起来,她平静地说:
“不,这是不可能的。大概,他只是因为胆怯,所以就溜了。”
“你为什么这样想?”
“小伙子们很早就知道他是个团员,他虽然自高自大,可是干这种事还不至于。他的家庭非常好,父亲是个老矿工,几个哥哥都是共产党员,都在部队里……不,那是不可能的!”
她的异常清晰的推断使普罗庆柯感到惊讶。
“聪明的姑娘!”他眼睛里带着她所不了解的忧虑说,“有过一个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想的。是的,你看见吗,事情是这样的。”他像对小孩说话似的对她非常简单明了地说,“世上还有不少堕落的人,在他们看起来,思想就像是暂时穿一下的衣服,或是像一个面具,——法西斯分子在全世界培养着千千万万这样的人,——可是也有些人只不过是意志薄弱,经不起打击……”
“不,不可能的。”刘勃卡说,她是指斯塔霍维奇。
“但愿如此!不过他既然胆怯过,也可能还会胆怯。”
“我告诉奥列格。”刘勃卡简短地说。
“我说的话,你全明白吗?”
刘勃卡点点头。
“那么就这样干吧……在这儿城里,你不是跟带你来的那个人联系吗?就跟他保持联系吧。”
“谢谢您。”刘勃卡的眼神变得高兴起来,她抬起眼睛望着他,说。
他们俩都站起身来。
“你向‘青年近卫军’的同志们转致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战斗的敬礼。”他用他的动作准确的小手小心地捧住她的头,先吻了吻她的一只眼睛,又吻了吻她另一只眼睛,然后轻轻地推开了她。“去吧。”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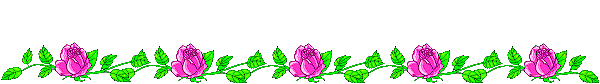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