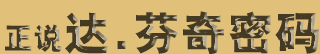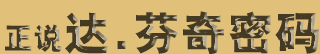|
圣杯的圣地
漫步巴黎之前,我们必须先绕道英国,去一下苏格兰,因为《达·芬奇密码》的女主人公索菲·奈芙在那儿得到了启示:她出身于墨洛温王族,算是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后代。她的祖先是普朗塔尔(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姓后面的那个真人是谁了)和圣克莱尔(我们将很快知道为什么)。在得知这难以置信的消息时,这位法国女警察正在这座距爱丁堡市中心十一公里的罗斯林礼拜堂里。丹·布朗描述说,它是“圣杯的圣地”,一个秘术的殿堂,各种传统的交汇点。奇怪的符号,古怪的星形,花饰……读着丹·布朗的描述,新教徒不禁会想,罗斯林礼拜堂是不是一个异教的祭拜场所、撒旦的、星相学的、共济会的、圣殿骑士团的、埃及人的、犹太人的、基督徒的,用于“崇拜女神”或者“性”的场所。罗斯林礼拜堂是从丹·布朗小说中掠过的所有象征符号和所有神秘事物的集合。它是一出压轴戏。一个为他的所有论点提供诚信的合情合理的延长音符。
根据历史学家的观点,礼拜堂是1446年由威廉·圣克莱尔爵士建造的。请注意,这是索菲·奈芙的“祖先”的姓氏!也是创建郇山隐修会时,我们的老皮埃尔·普朗塔尔兼并过来的姓氏!威廉·圣克莱尔,即罗斯林伯爵,为感谢上帝,决心在有生之年为他修建一座“最豪华,最荣耀”的教堂。这是理查德·奥古斯丁·雷神父告诉我们的,他是苏格兰家族编年史学家,在1700年为此写了三卷专著。苏格兰贵族从国内外找来最好的工匠:瓦匠、木匠、铁匠、金银匠……礼拜堂最终建得壮丽辉煌。但是,自1571年起,罗斯林礼拜堂便遭到了宗教改革势力的冲击。信奉英国国教的当局认为,天主教礼拜堂是一处“罗马天主教徒偶像崇拜的建筑”。当局禁止洛德·圣克莱尔(威廉的后代)在此安葬他的妻子,限令他拆掉祭坛,并威胁说要把他逐出教会。洛德·圣克莱尔不从,继续信奉天主教。但是,罗斯林礼拜堂在随后的世纪就被废弃了。
因此,就像爱丁堡大学的历史学家加里·迪斯克森所指出的,看到一个“非常纯粹”的天主教教堂如今转变为所有异端派的总部真的可以说很滑稽!因为罗斯林礼拜堂很久以来(比《达·芬奇密码》早多了)就已经是新时代(NewAge)的或者秘密社团的信徒聚会之地。来访者带着护身符、神圣的地形图或数学公式纷纷来到这里。他们把星宿的位置和地上的一块石板的位置联系起来。他们相信地下室藏着圣杯或者圣殿骑士团的宝藏(如果相信丹·布朗,这一场面就会重新出现)。应该说有大量的文学作品促使他们来到这里。《达·芬奇密码》的作者则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使用了这个文学主题。
错误的圣殿骑士标签
丹·布朗毫不犹豫地说,罗斯林礼拜堂是“圣殿骑士团于1446年建造的”(P?郾410)。无论是威廉·圣克莱尔从未参加过圣殿骑士团,还是在建造罗斯林礼拜堂的时候骑士团已经灭亡了两个世纪,对丹·布朗而言都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已经知道,随着他们的领导人雅克·德·莫莱在巴黎被处以火刑,圣殿骑士团于1314年就灭亡了。骑士团的所有财产——土地、房产、农田——都被没收。美男子腓力指望插上一手,而教皇克雷芒五世答应将这些财物给圣殿骑士团的对手医院骑士团。
对历史学家们来说,“圣殿骑士团宝藏”是一个神话(甚至法国国王都对它抱有幻想)。历史学家们还确信,骑士团没有人幸存下来。当然,法国镇压得最厉害。但是在西班牙、葡萄牙,骑士团的财产也被没收并转给了两个新的骑士团:西班牙的蒙特萨骑士团和葡萄牙的基督骑士团。不同意圣殿骑士团已经消失的人说,这些团体是“乔装打扮的”圣殿骑士团!除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外,这些“骑士迷们”还将目光转向苏格兰,因为“骑士们在那儿建了一个他们主要的避难处”,林恩·皮克内特和克莱夫·普林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写道。在有关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两位作者。关于骑士团后代问题的争论并不是新鲜事。自18世纪以来,它就让人们大费笔墨,当时,古代骑士热被重新燃起,对共济会而言更是如此。一部分共济会成员,自该组织成立起——准确说是从1723年,当它的创立章程《安德森宪章》公布的时候——就打着骑士传统,打着应用在骑士团,或者建造教堂、骑士府邸的手工业行会中的一些价值观或原则的招牌(行会、共济)。可是,大部分共济会会员自己都认为,这种演变关系并不是历史,只是纯粹的传说。
所有这些与罗斯林礼拜堂有什么关系呢?答案是:圣克莱尔家族与苏格兰共济会的历史紧密相连!事实上,在1736年,威廉·圣克莱尔,罗斯林伯爵(是建造礼拜堂的那个威廉的后代,但同名同姓)当选为苏格兰共济会总会的大师。这是苏格兰现代共济会正式诞生的一幕(与欧洲的其他共济会差不了几年)。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的各个共济会分部都在规范礼仪制度。它们经常相互竞争,每家都声称自己比别人资格更老。因此,一些象征性的符号(例如希兰的传统永存的象征符合,所罗门圣殿的建筑)就直接被搬过来了。苏格兰共济会希望有别于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兄弟,让人家把自己看作是耶路撒冷骑士的后代。根据这个事实,我们就明白了,18世纪的圣克莱尔家族,苏格兰共济会分部的负责人认为,让别人相信他们的祖先威廉伯爵——罗斯林礼拜堂的建造者,是一位圣殿骑士,肯定是大有好处的!另外,1736年,圣克莱尔家族开始修复礼拜堂。1861年,礼拜堂经爱丁堡主教的再次祝圣,恢复了做弥撒。
罗斯林礼拜堂的果酱和共济会成员袖口的扣子
如今,礼拜堂一直在翻修。工程耗资数百万。罗斯林礼拜堂的传奇有助于它获得资金:进门要买票,纪念品商店出售罗斯林礼拜堂果酱、圣殿骑士团的装备等等。还有共济会的饰物:大师的银质证章(99英镑)、袖口的三角形扣子(36英镑)、带三个点的戒指(200英镑)……望族的一位后人尼文·辛克莱尔(他的姓随着岁月的流逝似乎也发生了某种变化)忙于向世人普及礼拜堂的神秘事件。例如,他对《圣殿骑士团的显形》的两位作者解释说:“要了解圣彼得大教堂的秘密,仅仅去一两次是不够的。相反,我去了无数次罗斯林礼拜堂,次次都有新发现。这地方的东西实在太丰富了。”两位“调查者”就在他们的书中热情地解释说:“尼文为我们提供的大量证据表明,圣克莱尔家族不但是圣殿骑士,而且也是异教徒(原文如此)。他宣称,有关他们的知识以密码的形式被写入礼拜堂里,以便传给后人。”尼文还说,罗斯林礼拜堂是圣殿骑士和共济会会员镌刻的一部“石头书”。
这也就是丹·布朗在他的小说中所描述的:“教堂各处都雕刻了各种各样的符号,其中有基督教的十字、犹太人的星状物、共济会的印章、圣殿骑士团的十字架、丰饶角、金字塔、占星学符号星座、各种植物、蔬菜瓜果、五芒星以及玫瑰等,这些能工巧匠精雕细刻,不放过任何一块石头。”(P?郾412)罗斯林礼拜堂的大量浅浮雕和雕塑毫无疑问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它那非常漂亮的拱顶,精细地装饰了星形、玫瑰、花朵、鸽子和橄榄枝,丹·布朗对我们说的异教的象征性符号。兰登教授在走进礼拜堂时还高声地说:“它们是玫瑰,是女神子宫的象征!”(P?郾412)也许是吧。但所有这些象征性符号十分常见啊!在中世纪建造的教堂中,常常见到这样的东西。它们是永恒的,全球性的,在耶稣之前很久,犹太人、希腊人、埃及人中就有。后来被基督教吸纳了。
鸽子和五瓣玫瑰
例如:在希腊,鸽子是阿佛洛狄忒的鸟。在犹太基督教的象征符号中,它是“纯洁、朴素的象征,而当鸽子给挪亚方舟送去橄榄枝的时候,它还是和平的象征”(让·舍瓦利耶、阿兰·吉尔布朗《象征符号辞典》)。后来,随着《新约》的出现,它最终成为圣灵的象征。无论如何,在各种传统中,它都与心灵有关。至于说玫瑰(丹·布朗在他的书中经常提到的玫瑰),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是再生或者神秘复活的象征(人们当时把玫瑰摆在坟墓上)。在基督教的符号体系中,它表示基督的伤口,或者接盛基督鲜血的杯子(圣杯)。百合花,在作为法国王朝的象征之前,在中世纪的教会中,象征童贞(或许因为是白色的),因此也象征圣母。至于五角星,我们已经知道了,在教堂的装饰中经常使用……
总之,《达·芬奇密码》在象征性符号中看到了“加密的启示”,这些符号,在它们被雕刻的时代,应该被所有人理解为简单的装饰性元素,或者某种图形化的教理。尽管其中一些象征符号只能被一位精英读解,但它们也被纳入到它们与异端毫无关系的一个传统中。
瓦匠和共济会
另外,丹·布朗把瓦匠师傅和共济会会员搞混了。瓦匠师傅们建造了中世纪的教堂。他们是建筑工人。共济会的出现则晚得多,是在18世纪。这是一个传授奥义的宗教组织。共济会多多少少与瓦匠有直接的关系,确切地说是与他们的行会有关(尽管几乎没有确凿的历史证据证明这种传承),它们是从11世纪起,围绕着大型王家的建筑,因此也围绕着圣殿骑士兴建的骑士封地、教堂而创立的(这可能是我们在骑士和共济会之间可以建立的惟一的联系)。这些建造者们(瓦匠们)形成行会,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它们有自己的规章,自己的道德观念,自己的宗教理解和自己的知识体系。当他们来到一个工地时,他们就建起自己的“工棚”①,即生活和聚会的地方。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操作型共济会”②,拥有非常复杂的知识的行业团体(例如建筑业)。
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工棚逐渐落伍了。于是,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时候,一些瓦匠就想出个主意,让教士、有产者、学者、“知识分子”进入他们的工棚。大家把这些新入棚的人称为“被接纳的瓦匠”。工棚变成了某种俱乐部,行业中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在此聚会,交流思想。在英格兰,萌发这种演变主要与皇家协会(类似于科学院)有关,而艾萨克·牛顿就是皇家协会的成员。共济会保留了等级(伙计、师傅),也保留了行业协会的工具,但只是以象征符号的形式出现。因此木槌和凿子(用来对石头做粗加工)表示自己要从事的工作,角尺是公平的图形,圆规表示真实(如今在共济会中仍然使用)。这就是“纯理性”的共济会的起源。其第一个地区总会于1717年在英格兰建立,相应的总会也在爱尔兰、苏格兰、法国建立。但是,从“操作型共济会”到“现代的纯理性共济会”的演变仍是一个棘手的历史问题,专家们对此还在争论。
多说这些话是为了解释罗斯林礼拜堂出现的“瓦匠们的印鉴”并不让人吃惊(也是因为丹·布朗没有明确说)。这并不表明我们是在一个异教的宗教场所里。一些土木工程的符号(角尺、圆规)过去有时也被“施工的瓦匠”刻在石头上。我们并不确切知道这些标记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宗教的象征符号,还是仅作为一个行会或者个人的签名,这些泥瓦匠的符号后来被纯理性的泥瓦匠们搬了过去,有时被安放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某些建筑物上。例如,在巴黎的国民议会大厦内,我们就能看见嵌在天平上的“上帝的眼睛”。在三角楣上,两个女人环绕在寓意宪法的图案边上,一个拿着三角尺,另一个拿着圆规,就像弗朗克·马松在《巴黎共济会之旅》一书中所记载的。为了得到七十七个包含“可能是”共济会的符号的建筑立面,他在四年中考察了四万个建筑立面!其实,就像他本人也在思考的那样,这真是共济会的符号呢,还仅仅是一些19世纪常用的科学与艺术的符号——特别是建筑艺术的符号(参见《金字塔的诅咒》一章)。
共济会会员还收回了他们的瓦匠“兄弟”建造的教堂里的一些象征符号,但这次是为了用在他们自己的殿堂和总会的仪式中。我们如今已经很难想象这样的事情了,尤其是在常常把共济会和反教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法国。这里包含着带偏见的历史观点。我们就拿里昂做个例子,因为它被看作“共济会的大本营”。在如今仍被遵从的七个宗教仪式里,就有两个被加密。如1778年,由让-巴蒂斯特·维莱尔默兹(Jean-BaptisteWillermoz)传播的改良的苏格兰教规(在这儿,不但有苏格兰的影响,而且还有“苏格兰主义”的影响,受圣殿骑士团影响的宗教仪式)。还有埃及的共济会,这是1784年由著名的占星家卡廖斯特罗①(Cagliostro)提议创立的。让-雅克·伽布在《术士的和神圣的里昂》一书中写道:“在18世纪的里昂,共济会和教会之间几乎没有区别,许多的神职人员都进了共济会的俱乐部。”
法国大革命之后,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在19世纪,特别是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教会与共济会的关系变得糟透了。教会反对共和派的价值取向,而许多共济会会员却要求成为自由派思想家。(在里昂也一样,属于社会主义-共济会的市长打算关闭Fourvière教堂!)后来,两者关系有所改善。在历史上,教会和共济会冲突最激烈的国家就是法国。
总之,在一段时期,教会与共济会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原则上的激烈对抗,原来教堂中瓦匠们的象征性符号也就自然而然地在后来成为共济会的符号。
我们在《达·芬奇密码》中读到兰登教授的解释,在罗斯林礼拜堂祭坛的背部,“这两根柱子,就是所罗门圣殿前两根柱子的翻版……(左边)那根柱子被称作波阿斯——又叫石匠之柱。另外一根柱子,被称作亚钦——或称作学徒之柱。实际上,世界各地所有由共济会建造的神殿都有两根这样的柱子”(P?郾414)。这就是兰登教授想证明罗斯林礼拜堂是一座“共济会的殿堂”的证据。事实上,这是一钱不值的证据!也是弄错了年代的典型的例子。兰登教授所说的两根柱子是《列王记》中提到的(那里有对所罗门圣殿的惟一描述)。波阿斯真正的含义是“力量”,而亚钦的意思是“他将建立”(从两个词生发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一种解释就是“雅赫维将建立他的永久的统治”)。
中世纪的瓦匠和建筑工人们非常了解经文。他们受神学家的指挥,神学家一丝不苟地监督他的工程,他们同时也受自己信仰的指引。对他们来说,建筑是一门神圣的手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略知一些几何学、毕达哥拉斯定理,以及后来的炼金术的学说。因此,在中世纪的,包括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教堂里,人们都看到了所罗门圣殿的这两根柱子。如今在共济会的殿堂里,在一个柱子前安置学徒们(刚刚入会的那些人),在另一根柱子前则是伙计①(不是兰登所说的师傅)。
总之,罗斯林礼拜堂并非《达·芬奇密码》所描述是象征符号的大集市,或者其他的什么“历史轮回”的建筑物。这没什么了不起的——自《达·芬奇密码》出版后,成群的游客到这里寻找丹·布朗所说的大卫之星。它是一条想象的线,据说以看不见的形式(只能如此!)穿行在礼拜堂的六根柱子之间。没关系。但是一些游客坚信这颗星的存在,并且不厌其烦地到罗斯林礼拜堂的各个角落搜寻。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