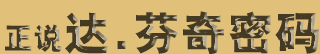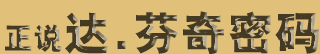|
一位天才的阴影部分
法国最著名的达·芬奇专家之一,达尼埃尔·阿拉斯(DanielArasse)在《列奥纳多·达·芬奇》一书中指出:“除了上帝,人们写得最多的恐怕就是艺术家了。”阿拉斯还说:每个时代都创造出自己的列奥纳多,“他从最合情理的幻想中,从最荒唐的演绎中汲取灵感”。《达·芬奇密码》的主人公兰登教授提出了最新的荒唐的演绎:“列奥纳多是一位伟大的女权主义者!”(P?郾110)
画家或许对此已经不在乎了!马塞尔·杜尚难道没有给《蒙娜丽莎》加上过胡子吗?作家们难道没有把他当作魔术师或者魔鬼吗?广告代理人在各处叫卖他的面孔。弗洛伊德论述过他的性生活。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绘画引起过异常的反应吗?与其他画家相比,他的作品挨过更多的石头、刀子、子弹(例如国家艺术馆的《圣安娜》)。或者这些画作会让人产生控制不住的感情?一位卢浮宫的守卫爱《蒙娜丽莎》爱到心生忌妒、不允许参观者接近这幅画的地步!博物馆只得让他提前退休。
为了理解“达·芬奇热”(这与丹·布朗的小说的成功并非无关),必须试着理清哪些事是传奇,哪些事是真事。这是困难的工作。因为自童年起,在这位艺术家身上发生的事情似乎都是例外。他的父亲,一位公证人,把十二岁的他送进佛罗伦萨著名的画家和雕塑家韦罗基奥(Verrichio)的画室。一天,老师让学生在老师的一幅画中画一个天使。天使画得非常美,完满和纯洁,以至韦罗基奥吃惊,继而绝望地看着这个超越了自己的学生,再也不碰那幅画了!然后,列奥纳多为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Médicis)家族画画,又为统治米兰的斯福尔扎(Sforza)家族画画。最后,他作为弗朗索瓦一世的宫廷画家死于法国。
他的同代人回忆他的古怪穿着(“齐膝的玫瑰色袍子”,当时流行穿长袍),垂胸的大胡子,素食,左撇子的书写,喜欢漂亮的男孩。他不是一个多产的画家:他的一生只完成十五幅左右的作品,其中有几幅还不是出自他一人之手。有几张未完成的作品。这种永不衰竭的狂热是他人格的一个突出特点。例如他的难以满足的科学的好奇心,他的令人吃惊的直觉。地形测量、地图、研究眼睛、光、生殖器官、“隐形眼镜”的想象,针孔镜(暗箱)的使用,画“战车”的草图,在CorneD′Or上建造连接欧亚大陆的大桥的计划,制造机器人,机械玩具或者乐器,为戏剧设计特效,制作超高效的纺织机或者“搓麻绳机”,超前地发明(至少在图纸上)自行车和飞行器!列奥纳多生前就已经是个传奇。从1550年起,他刚死去三十年时,他的传记作者吉奥尔吉奥·瓦萨里(GiorgioVasari)谱写了一曲受到蛊惑的颂歌,颂扬他的“挑战任何赞美的形体美”,他的“无尽的优雅”,他的“过人的体力”。瓦萨里还说:“在才华横溢的这同一个人的身上有一些超自然的东西。”
与上帝还是与魔鬼签下的约定
瓦萨里还说,列奥纳多“如此全面和巨大的才能”让人印象深刻。尽管如今,我们知道他并不是一个完全孤立的天才,例如,某些他的同代人与他同时试验“潜水艇”;人们经常认为是出自他的想像力的潜水服和手蹼,公元前2世纪的阿基米德(Archimède)就已经想过了。安德烈·沙泰尔(AndréChastel)在《列奥纳多或绘画的才能》一书中肯定地说:“我们夸大了他的创造力的范围,他的计算的可靠性。”这不是理由,列奥纳多耍弄着那么多的天赋以至于他像是超人,一个神。他是从诸神那里窃来这些秘方吗?或者,反过来说,他是不是与魔鬼订下了契约?瓦萨里的一句话使人困惑。他写道:列奥纳多“在他的精神中形成了一种非常异端的,以至于不属于任何宗教的学说,或许把科学知识放在基督教信仰之上”。瓦萨里在定稿中把这句话删掉了。太晚了。因为这种异端指责,列奥纳多感受到了痛苦。而对丹·布朗而言,这就是圣体。可是在艺术家用左撇子书写涂抹的数不胜数的文章中(在其中有时难以区分哪些出自他自己,哪些是抄录别人的),我们找不到“渎圣”的痕迹。
丹·布朗反驳说:“他从梵蒂冈接受了数百项赢利性的工作。在画基督教题材的画时,他并不是要表达自己对它的信仰,而是将其视为商业行为——一种可以支付他奢侈生活的手段。”(P?郾39)当然,列奥纳多在记述中揭露了高级神职人员的腐败,买卖宗教物品和恕罪,“我又一次看见被出卖、被钉上十字架的基督和他的那些殉教的圣人”。他像宗教改革席卷欧洲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教会十分挑剔。但不能根据这一点把他说成怀疑基督基本教诲的人。的确,达·芬奇在笔记本中写过“太阳不动”的话,就像一个世纪后,于1633年被教会处死,且不得不收回前言的伽利略。但是画家绝没有从这里演绎出一个新体系。列奥纳多不是一个思想家,而更多地是一个天才的“喜欢修修补补的人”。他没有留下任何革命性的理论。
但是他勇于试验,他天不怕,地不怕,“异端”的情调熏人。就像是伊卡洛斯(Icare),达·芬奇甚至尝试从一座塔上飞翔,就像他要挑战自然法则和上帝。“与其说异端,更应该针对的是骄傲的罪孽的主题”,一本出色的达·芬奇传记的作者塞尔日·布朗利(SergeBramly)肯定地说。因为列奥纳多把他的艺术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他在论文中说:画家是“任何个体和任何事物”的“主子和神”。他还说:“绘画的神的特点使得画家的思想转化为上帝的思想的一幅图!”列奥纳多亵渎神明的观点就是从这儿产生的。可是,他像米开朗琪罗一样,公开主张当时的秘传学说的理论:在十五、十六世纪,佛罗伦萨把绘画当作艺术的最高等级。但是列奥纳多不仅是一个“自命不凡的”画家,他还是一个自高自大的科学家。他梦想找到万能法则。他在尸体上,在波浪和水流的运动中,在昆虫和鸟类的飞行中,在空气对物体的颜色产生的作用中,在植物的生长中,在声音的和谐中寻找这种万能的法则。这是当时几乎所有的人文主义者的共同态度:例如,阿拉伯语言文化和《旧约全书》的专家以及投影图的发明者、与弗朗索瓦一世关系密切的吉约姆·波斯特尔(GuillaumePostel,1510—1581)就为了找到再现宇宙结构的象征性的形式而解剖母鸡……
可是丹·布朗肯定地说:“他是一位绘画天才,但他也是一位非常惹眼的同性恋者和自然的神圣秩序的崇拜者,这两点使他永远背上冒犯上帝和作奸犯科的罪名。”(P?郾39)结论下得有些仓促,因为列奥纳多的态度并不违背基督教的教理。画家“只是”希望发现主宰创作的完美的几何学。像他当时的所有人一样,他一只脚踩着中世纪,另一只脚踩着现代性。他既是形而上学的又是理性的。在所有与宗教有关的事情常常都被打上非理性,甚至是蒙昧主义印记的今天,我们常常难以想象这样的事情。列奥纳多既不反对持批评思想的人(一个世纪后,我们称他们为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也不反对相信启示的人。他希望科学地理解上帝的作品。
神圣的比例和不吉利的五角星符号①
列奥纳多·达·芬奇相信“神圣的比例”。画家甚至在1509年为一位方济各会数学家卢卡·帕西奥里(LucaPacioli)探讨这个问题的作品《神圣的比例》画了插图。丹·布朗在他的小说中多次提到这个长久以来一直让人们遐想不已的命题。因为神圣的比例是以黄金数②为基础的。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个黄金数隐藏着知识的关键——黄金数等于■,“约等于1?郾618,符合一个被认为是特别美的比例”(《小拉鲁斯辞典》)。它确定了一种理想的关系,适合于眼睛运算的一种尺寸,也被称作“恰当的位置”或者“黄金段”(这是列奥纳多·达·芬奇使用的术语)。它使图形展开和精细的数学和几何学规则成为可能。为了加快速度,不陷入细节,我们简单地说它也被称作PHI,其作用之一就是用于画十等分的圆,即十角形,或者五等分的圆,即五角星,也被叫做星形五角形,总之,是有五个角的星,按照丹·布朗的说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个符号,公元前四千年以前使用的……一种异教的符号……显然也和恶魔有关”(P?郾31—P?郾32)。
马里于斯·克莱耶-米肖(MariusCleyet-Michaud)在他的《黄金数》一书中断定:黄金数的经验主义的发现可以“上溯到远古,或者是史前时代”。人们推测,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应该知道画圆并对其进行分割。如果说他们喜欢将圆十等分,或五等分,那是因为——我们的每只手有五根手指头。“一目了然的”数自然而然地引导人们去计算某些比例。所以古埃及的一些纪念性建筑(例如胡夫金字塔)就是(有意或无意地)根据黄金数的几何学规律建造的。但却是希腊人,特别是欧几里德(Euclide),将这些聪明的计算上升为理论。在欧几里德之前,毕达哥拉斯①(Pythagore),或者至少是他的弟子们也在寻求揭示这个数字的秘密。
在他们的最绝密的宗派中,黄金数与神圣的事物联系到一起。特别是与五角星,生命、美、爱的符号联系起来。人们认为五角星符号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符号。但是因为常常被认为是健康的护身符,它就流传下来(直至承袭了这个五角星符号的共济会):我们在古钱币上见到这个符号,在许多的天主教大教堂里(特别是亚眠大教堂)或者哥特式教堂里也常常看到。柏拉图也把黄金数放在解释宇宙一个重要的地位。在12世纪,被称为比萨的列奥纳多(LéonarddePise)的斐波那契(Fibonacci),数学家,商人和大旅行家,在中东初步学会了这门科学。丹·布朗在他的小说中用来想象密码的著名的“斐波那契数列”就出自他。在中世纪,五角星符号,对于艺术家和建筑师们而言,就变成了“以太”,即第五元素的符号,因此是绝对的完美,无可挑剔的美。在众多的绘画作品中,人们都见到隐蔽的这个造型:人物根据五角星符号的各条线分布,夏尔·布洛(CharleBouleau)在他的《画家的神秘几何学》一书中解释说。这些精确地画出来的五角星和圆,曾经是行会们小心翼翼地保守的秘密。所以,列奥纳多·达·芬奇画了插图的书引起了轩然大波,他把口耳相传的一个真谛落到纸上。他揭发了一个秘密。
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如今,我们知道神圣的比例被用在建筑艺术(柯比西埃经常使用)、绘画、音乐和某些诗歌的结构上,也表现在动物界和植物界(有些花有五个瓣,有些叶子在茎上的分布符合PHI,海星或海胆也符合PHI)。神圣的比例似乎也支配着人体。所以,肚脐根据黄金数分割人体(更确切地说,人体的高度与肚脐高度的比率等于黄金数。第一个手指节与第二个手指节的比,或第二个手指节与第三个手指节的比也等于黄金数,等等)。在列奥纳多·达·芬奇最著名的素描,一个正方形中,有两副胳膊和两副腿的裸体男人(布朗的小说从这儿展开),就证明了这个原理。这幅画被称作《维特鲁威人》,以纪念古罗马的建筑师,研究人体、建筑、城市规划神圣比例的著作《论建筑》的作者玛库斯·维特鲁威。这部在文艺复兴时期被重新发现的著作深刻地影响了列奥纳多·达·芬奇。
赫耳默斯主义和埃及的神
画家和他的同时代人一样恢复了与古代文化的联系。在列奥纳多时代的意大利,柏拉图和他的弟子,公元前四、五世纪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很流行。另外,在著名壁画《雅典学派》里,据说拉斐尔按照列奥纳多的特征表现了柏拉图。这是个有争论的问题,但它仍将维系着对艺术家的误解。大家会错误地先把列奥纳多·达·芬奇推断为自由思想家,既而是无神论的哲学家。但是在当时,柏拉图的思想和基督教的思想并不是相悖的。相反,人们把“神圣的柏拉图”看作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耶稣的先驱者。拉斐尔的画还让人认为列奥纳多加入了佛罗伦萨著名的柏拉图学园。这又强化了这位画家的危险形象。可是,他不但不是学园的成员(列奥纳多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人,他没有上过学,直到四十岁才学拉丁文,这点长期地妨碍他接触基础文献),而且,柏拉图学园也根本不是异端者的标签。
学园是美第奇家族的卡西摩(CosmedeMédicis,它是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保护人)于1450年创建的,由神学家、后来成为一名议事司铎的马尔西里奥·菲西诺(MarsileFicin)主持。菲西诺翻译了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的作品,也研究其他来自亚历山大的作品,例如《赫耳默斯奥义书》(Corpushermeticum),这是一本研究星相学、炼金术和医学的神秘著作,它的“作者”据说是赫耳默斯·特里斯美吉斯托斯(HermèsTrismégiste,“最最最伟大的赫耳默斯”)。这是个传奇性人物,是埃及神透特(Thot)和希腊神赫耳默斯(Hermès)的综合体,他用摩西时代的秘术启发他人。马尔西里奥·菲西诺认为从这里找到了贯穿该书的三大宗教的“教义”。他认为,赫耳默斯·特里斯美吉斯托斯和柏拉图一样,预言了基督教的产生。同时,比萨的列奥纳多,文艺复兴时代的大思想家之一,发现了卡巴尔学说对《旧约全书》的解释(由被驱逐出西班牙的犹太人引入意大利),并发展出他自己的基督教的变体。在列奥纳多的时代,这些思潮的发展得到了教会的认可,教皇希望借此促进东西方的融合并让众多的希腊智者来托斯卡纳。可是,赫耳默斯主义是人们后来称之为“秘传学”的核心,了解新柏拉图主义的列奥纳多也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
《蒙娜丽莎》和同性恋者
作为出色的小说家,丹·布朗把这些事实扩大化了。我们以有关《蒙娜丽莎》这幅画的名字的好玩的理论为例。MonaLisa可能是AmonI′Isa的缩写,Amon是埃及的男性的丰饶之神,而Isa是Isis①的古代象形符号,是与Amon相对称的女神。因此,按照《达·芬奇密码》的说法,MonaLisa象征着“男人和女人的神圣的结合”。更有甚者,《蒙娜丽莎》是“一个两性畸形人的肖像”,兰登教授解释说,“正因为如此,它的模特显露出这种狡黠和古怪的微笑”。只是,列奥纳多从没有给自己的任何一件作品起过名字,也没有把这幅画称作《蒙娜丽莎》。是瓦萨里在1550年称呼油画中表现的人物时这样叫的:“蒙娜丽莎,弗朗西斯科·德·吉奥康多的妻子。”“Mona”是“Madonna”的简写,表示“夫人”——“Amon和Isis”,这可太荒谬了!
丹·布朗或许深受15世纪佛罗伦萨的赫耳默斯·特里斯美吉斯托斯的影响,放出这条埃及的长线。此处,他可谓一箭双雕。两性畸形人的神话——赫耳阿芙罗狄蒂,赫尔墨斯和阿芙罗狄蒂的儿子,既是男人,又是女人①——是柏拉图理论的核心,同时也构成了秘传学文学的传统主题。丹·布朗在他的小说中通过提及由被谋杀的卢浮宫博物馆的馆长雅克·索尼埃组织的“圣婚”②仪式,不断印证这个主题。
确切说他是一箭三雕。因为,同样按照丹·布朗的说法,列奥纳多·达·芬奇是一位“非常惹眼的同性恋者”(P?郾39)。“惹眼的”也许并不是一个贴切的词,因为列奥纳多从未吹嘘过他是一个“性倒错的人”,这是当时人们对同性恋的叫法。但几乎可以肯定他没有结过婚,也从未有过孩子。此外,在1476年列奥纳多二十四岁的时候,他与他的三个同窗被指控共同鸡奸了在韦罗基奥的画室里做模特的一个男孩。从法律上讲,他面临着被处以火刑的惩处。但是,同性恋当时在佛罗伦萨很普遍,以至于这样的惩处从未实施过。由于缺少证据,他被无罪释放。但是诉讼引起很大的轰动,并给他造成终身的烙印。当然,对他的同性恋身份的假定在今天更增加了他的几分神秘。但已不再停留在可能是同性恋的问题上。这点在他的某些画像的两性同体中隐约可见,也在他的文章中显露出来。此外,在他的某些表明完全不懂女性性器官的素描中,在精确地表现出男性泌尿生殖器官的素描中都表现出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列奥纳多的病例产生了兴趣,把他的艺术创作抑制(许多作品的未完成)和“性欲抑制”(与同性恋相当的性无能)联系起来。他在出版于1910年的《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一段童年回忆》中分析了艺术家记在笔记本上的一个梦:“当我在摇篮里的时候,一只秃鹫飞来用它的尾巴打开了我的嘴。”可是,在古埃及,秃鹫的图像曾是象征母亲的象形文字。(我们看到布朗并不是惟一玩弄象征符号的人!)弗洛伊德分析了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私生子的身份如何影响艺术家的性生活(也影响了他的作品)。事实上,画家的母亲是一个农妇,只抚养了孩子几年。正如这位精神分析学之父所说,列奥纳多从来没有消除这次分离对他的影响。只是,弗洛伊德研究的列奥纳多的梦出自一个翻译错了的版本。(不能看作是“秃鹫”,而应该是“鸢”,是在任何神话都没有出现过的一种猛禽。)可是,弗洛伊德有关列奥纳多的同性恋的结论并不是毫无根据。再加上1490年画家在近四十岁时,还接纳了年轻的科莫作为他的画室仆人。他们的关系引来不少闲言碎语。小男孩常偷东西,不听话,但美得像神。很快列奥纳多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萨拉伊(Sala?觙),塞尔日·布朗利写道:“这是个源于阿拉伯语的词,用托斯卡纳方言讲就是机灵鬼,恶神。”
炼金术士和圣杯卫士
列奥纳多于是有了他的小鬼。另外,萨拉伊这个名字更像是由安拉(Allah)演变过来的。艺术家显然不是十足的天主教徒!丹·布朗写道:“达·芬奇偷盗尸体来做人体解剖学研究;他神秘的笔记是用别人看不懂的颠倒的字母记下的;他相信自己拥有一种点石成金的本领,可以把铅变成黄金,甚至可以靠研制出一种灵丹妙药推迟死亡而欺骗上帝。”(P?郾39)对天发誓,列奥纳多没有偷过尸体!他只是去医学院解剖犯人的尸体(这已经足以引起他的某些好友的愤慨)。但是,列奥纳多的确经常从右到左地书写,使用反向的文字,以至需要一面镜子去阅读。这是左撇子的一个怪癖。也许是一种游戏——画家喜欢自娱自乐。也许是渴望保守自己的某些秘密。谁知道呢?
我们回到炼金术的问题。列奥纳多从未找到长生不老液,也没有炼过黄金。但在他的手稿里,他使用过炼金术士的隐喻。他提到朱庇特或墨丘利①,把为了熔化而放进火里的金属说成是回到“它们的母亲胸膛中”的金属。他有时以“烧焦、晒干的人的排泄物”为主要成分进行古怪的混合。其实,这是一些制造颜料的配方。他也许为了更好地保守配方的秘密而使用一种加密的语言。或者更简单,因为炼金术在佛罗伦萨很时髦,因为重新发现的赫耳默斯·特里斯美吉斯托斯的作品,它们给这种活动带来了好处。与偏见相反,炼金术不仅仅属于巫师和想入非非的人。直到17世纪,许多思想家和艺术家经常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教会并不禁止。炼金术并不仅限于企图把“不值钱的金属变成金子”,它也关注把物质或者生命转化为“神秘的能量”,转化为磁气。因此它与化学、医学、天文学有关。它不仅吸引了列奥纳多,也吸引了艾萨克·牛顿,还有后来的法国神经科医生夏尔科①(Charcot)和他的学生弗洛伊德。由此看来,应该把炼金术看作一条启蒙之路,带人穿越象征符号的丛林,看作从不完美走向完美的一种探索。研究自我的工作,超前的心理分析治疗。
但是,如丹·布朗所说,列奥纳多总是拖着他的“魔鬼光环”。尤其是在19世纪,浪漫派作者把他塑造成一位创世神②(démiurge)。米什莱③(Michelet)把他定义为“浮士德的意大利兄弟”。到了20世纪初,传奇就更离谱了。1900年,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DimitriMerejkovski),一个如今有些被淡忘了的俄国作家,发表了《诸神的复活》,其副标题是“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传奇”。这本书在全球取得极大成功,影响了整整几代人(弗洛伊德后来说,这是他最喜欢的十本书之一)。几乎是同时,秘传学的各个团体也把列奥纳多·达·芬奇据为己有。1906年,保罗·维利奥(PaulVulliaud)在《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秘传学思想》一书中专门论述了列奥纳多·达·芬奇在《酒神巴科克斯》(Bacchus)这幅作品中的卡巴尔倾向(这是画家的最后一幅作品,它表现了崇高的施洗者约翰)。他分析说:“伟人在全身心投入设计图和经过艰深的试验之后,把艺术作为表达他的神秘学思想的手段。”
但是,最霸道地占有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是天主教玫瑰十字会的创始人约瑟芬·佩拉当(JoséphinPéladan),他在本书前边的章节已经出现过。深爱意大利的神秘小说作家和艺术批评家佩拉当甚至把这位佛罗伦萨人塑造成“玫瑰十字画展”的招牌。在1892年和1897年之间,他围绕着“神秘的唯心主义艺术”主题组织了几届画展:一份海报描绘了具有圣杯卫士特征的列奥纳多·达·芬奇(“秘密教义的守卫者”)。这张海报后来对所有把画家看作“秘密社团成员”的人都起到重要的作用。约瑟芬·佩拉当在1904年发行的题名为《达·芬奇在米兰学园的最后一课》的小册子也强调了这些观念。无论是米兰还是佛罗伦萨,列奥纳多从未领导过学园。可是,人们在他的笔记本中看到了一系列花叶边饰和涡形装饰的草图。有些还带有铭文“列奥纳多·达·芬奇学园”。以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园为模式的“列奥纳多学派”的幻想就从这里产生了。更有甚者,画家领导着一个秘密组织。请跟着我们继续往下看!(顺便说一下,我们不知道列奥纳多画这些纹章作什么用。)
耶稣裹尸布的捏造者!
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皮埃尔·普朗塔尔要把这位佛罗伦萨的艺术家打造为郇山隐修会的大师了。达·芬奇长期以来就是秘传学说组织中的一位神。丹·布朗并没有追溯到约瑟芬·佩拉当。显然,他是从一本时间近得多,与《圣血,圣杯》同类的书中汲取的思想。这本书就是写于1997年的《圣殿骑士团的显形:耶稣的真实身份的秘密捍卫者》,作者是两位盎格鲁-撒克逊人:林恩·皮克内特(LynnPicknett)和克莱夫·普林斯(ClivePrince)。丹·布朗谨慎地向他的先行者致谢:他让这本书出现在小说中的英国学者雷·提彬的书架上。这个“调查”建立在与《圣血,圣杯》相同的“基础”上(皮埃尔·普朗塔尔、郇山隐修会、雷恩城堡等等),但是,它的推理方式更加离谱。按照作者的观点,列奥纳多·达·芬奇知道抹大拉的马利亚和耶稣(他是埃及咒术的一位信徒)的结合。他还知道施洗者约翰在精神上高于耶稣。这就是佛罗伦萨艺术家试图在他的作品中表达的内容。
同往常一样,这类的推理以一个事实为基础。我们清楚地看到,作者是如何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利用列奥纳多·达·芬奇时代佛罗伦萨所经历的各种思潮的。特别是赫耳默斯主义,在作者这里被转化为名副其实的异教。显而易见,作者避免提及教会在列奥纳多时代并不反对赫耳默斯主义,而且教皇们还很迷恋这些东西。正是因为这种迷恋,特里斯美吉斯托斯才于1488年出现在锡耶纳大教堂,梵蒂冈的博尔吉亚建筑才被装饰上五角星的象征标志。当然,赫耳默斯哲学家吉奥尔达诺·布吕诺因为其他的原因,被圣职部(Saint-Office)处以火刑,但那是在1600年,是列奥纳多去世八十年之后的事。(参见弗朗西斯·雅特:《吉奥尔达诺·布吕诺与赫耳默斯教义》)
无论如何,皮克内特和普林斯从未怀疑过他们的观点的可靠性。他们写道:当然,“不存在任何列奥纳多·达·芬奇本人入会的证据”。但是有佩拉当的海报!尤其是,他们“发现”列奥纳多·达·芬奇曾经制造了都灵的裹尸布!让我们试着概括一下他们的论证。
1.1988年的碳十四检测表明,这块被认为带有基督受刑的身体印迹的圣布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末期。
2.我们的作者写道:“只有一个天才可以创造这件令人着迷的圣物。”
3.因此,造假的人是——列奥纳多·达·芬奇!
为了使他们的诡辩生效,皮克内特和普林斯用一个“暗箱,一块用十五世纪可以随意使用的化学材料浸泡的布和大量的光线”,还原了(他们)认为的“制造这个骗局的原始技术”。他们得到了与裹尸布上完全一样的图形。结论是:列奥纳多·达·芬奇(因此他也发明了摄影)为了制造耶稣裹尸布给自己照了相。圣物是画家的一张照片!作者继续说,一个信徒永远不会做出这样的亵渎行为。这就意味着列奥纳多·达·芬奇是一个炼金术异端者。
最后,有一个发现,印在圣裹尸布上的脸有一个“与脖子颈根部位不吻合的印迹”。“列奥纳多·达·芬奇希望以此暗示砍头。”谁被砍了头?施洗者约翰!画家因此属于将先驱施洗者约翰放在高于耶稣地位的教派,作者借助多张绘画作品的“解码”猛击一掌。我们在《达·芬奇密码》的一些主人公的口中听到了完全一样的分析(至少是圣裹尸布的故事)。让我们一个一个地分析。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