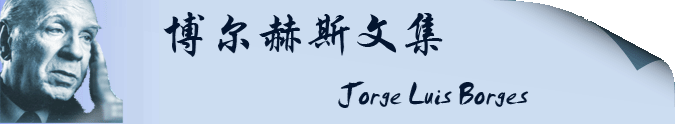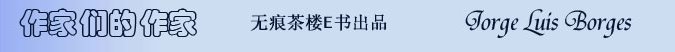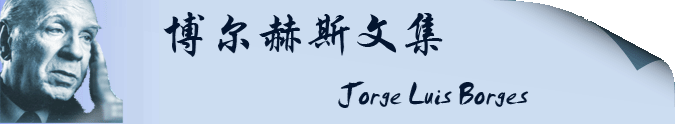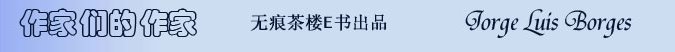|
作者:莫非
世界通过博尔赫斯成为一本书。这样“一本书”需要读者的思索与洞见,好像是王尔德说过,不是艺术模仿了生活,而是生活模仿了艺术。多么不讲“道理”啊!不讲“道理”也就意味着艺术在讲它自己的道理。在常识遇到麻烦的地方,小说家获得了自由。在语言的迷宫里,博尔赫斯一边寻找出口,一边小心地把“出口”盖好,有时连他自己好像也忘了哪一个“出口”才是应该停留下来的。博尔赫斯的读者由他自己小说去创造。为此他必然经受不是他的叙述方式培养起来的读者的反应。博尔赫斯的自信和耐心最终得到厚报。他活到了可以享用自己荣耀的年龄。他热爱的作家爱伦坡和卡夫卡没有他走运。在博尔赫斯之前之后形成博尔赫斯谱系,随着时光的推移,以及其他后继者的加入,博尔赫斯的小说将会有越来越多虚掩的迷宫之门被打开。如今,博尔赫斯已是“小说中人”。一个小说家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中渐渐化为自己笔下的故事的重要环节。没有这个“环节”,世界就不会像一本书那样静静地合上,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
博尔赫斯的世界,也是个寓言的世界。死亡在那里是生活的倒影。如果说看起来不那么清晰是因为动荡不安的生命深处扰乱了它的平静。博尔赫斯的出现使短篇小说这一考验作家叙述技巧与天赋的文学形式有了更好开放的边界。他的小说所达到的艺术巅峰并不妨碍“别人的小说”。这同卡夫卡的作品不一样:卡夫卡“妨碍”别人的写作,这就是两种经典写作的命运。尽管他们同属广义上“小说谱系”。晚年的博尔赫斯以他的“盲目”深入体验了人类命运的无常。失明后的博尔赫斯观察得反而更仔细了。他看见了《沙之书》,一部永远没有最后一页的书,如果不是“世界”还会是什么?谁也不敢担保博尔赫斯以此隐喻形而上的世界抑或讽嘲人类固有的傲慢与偏见。“我想把它付之一炬,但怕一本无限的书烧起来也无休无止,让世界乌烟瘴气。”博尔赫斯在失明之际却被委任为国立图书馆馆长,这样的人事安排简直就是对小说家笔下情节的戏仿,一幅逼真的博尔赫斯风格的漫画,这实在耐人寻味。
博尔赫斯一身永远地刻在了镜子的背后。博尔赫斯看你你看这个虚实不明的世界。如果这面镜子碰巧镶在大门上,那么,一扇门打开时,“世界”将随之移位,转换,变化。仿佛只有镜像才是真的,不动的景象反而显得呆头呆脑的。具体可触的东西在博尔赫斯大的小说精神里被挽留。因为博尔赫斯,读者很难进入“下一个安眠之夜”。他总是喜欢以“查有实据”的叙述风格杜撰自己的故事。甚至看得出他陶醉其中,在字里行间流露的那种智力上的优越感和一本正经的谦卑的混合物摊在读者面前。当你沉浸于他的故事迷宫寻找出路之际他已经抽身而去。甚至让人觉得,此时此地,他还在写着另一个故事的开篇。那样的开篇仿佛世上已有的故事都不曾采用过。他那样写着并非是让读者感到突然。只是想提醒昏昏欲睡的读者抖一抖精神。这世界并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地方。假如我们不曾忘掉过去,同时又不能回忆未来的话。在博尔赫斯编就的地毯上,表面的图案眼光缭乱,实则秩序井然。他趁人不备穿插进去的一条金线,哪怕对于眼力极佳的读者也只是偶尔闪光稍纵即逝。博尔赫斯无意制造迷宫,只不过他的叙述过于机智。正如他在《两个博尔赫斯的故事》所说的那样:“虚假的回忆、双重的象征游戏、长长的列举、熟练运用的平铺直叙、批评家的兴高彩烈发现的不完美的对称、不总是假冒的引证”,这些都深深地迷惑了读者又使读者着迷。博尔赫斯以“传奇作家”的方式,进入迷宫并一路沿着语言的线索摸索着走来,从而成就了博尔赫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街上,博尔赫斯拐进了他的小说迷宫,他碰壁、曲折、迷失、窃喜如数记下。在某个玫瑰色的街角上,这位失明的老人还在那里推想着《曲径交岔的花园》里新的发现。甚至极有可能遇见他熟悉的中国《聊斋》中的鬼男魔女。盲诗人荷马的歌唱和瞎子阿炳两根琴弦上的泉与月他感到了他也看见了。如果说卡夫卡是作家们的挥之不去的“幽灵”的话,那么,博尔赫斯留给作家的只是“化身”。因此,他“活”得很自在,很安全。试想这样一个出入迷宫的“化身博士”上帝找到他也不是件特别容易的事。即使“叫走”一个,又怎么能断定是作家博尔赫斯本人还是他的化身呢?
博尔赫斯渴望成为伊索。读者也有理由相信博尔赫斯相信自己才是《一千零一夜》的真正讲述者。最后的夜晚被永远地推迟了,真实的恐怖之夜被提前到达回忆之中。奇迹在杜撰中出现,就像侦探把无头案最终讲出作案细节一般。“你将触摸那些没有文字的书。”博尔赫斯警告过我的。这样的书需要用我们身体去阅读,从而体验我们身陷其中的世界。可以说,博尔赫斯的小说是我们时代的心灵的慰藉。博尔赫斯说过“所有的作家最终都会成为自己的不聪明的学生。”与此相反,“所有的读者最终将是别人故事的聪明的听众”,而这就不是博尔赫斯想说了的。
(1999-1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