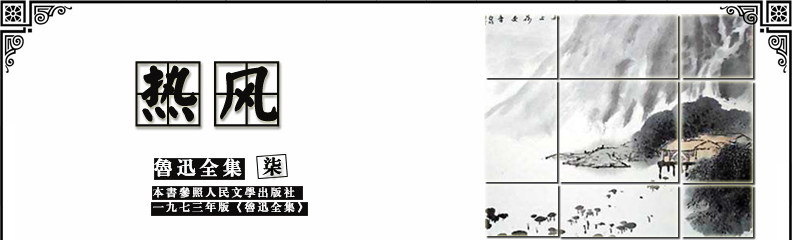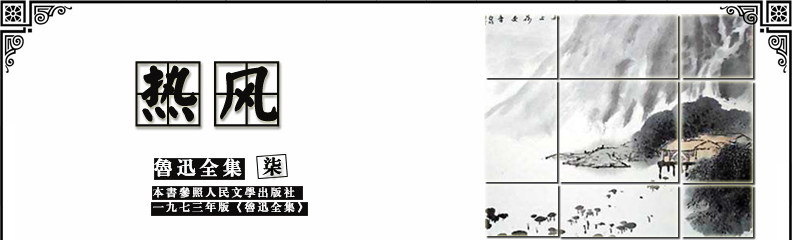|
随感录三十九至四十三>>
|
三十九〔1〕
《新青年》的五卷四号,隐然是一本戏剧改良号,我是门外汉,开口不得;但见《再论戏剧改良》〔2〕这一篇中,有“中国人说到理想,便含着轻薄的意味,觉得理想即是妄想,理想家即是妄人”一段话,却令我发生了追忆,不免又要说几句空谈。
据我的经验,这理想价值的跌落,只是近五年以来的事。民国以前,还未如此,许多国民,也肯认理想家是引路的人。到了民国元年前后,理论上的事情,著著实现,于是理想派——深浅真伪现在姑且弗论——也格外举起头来。一方面却有旧官僚的攘夺政权,以及遗老受冷不过,豫备下山,〔3〕都痛恨这一类理想派,说什么闻所未闻的学理法理,横亘在前,不能大踏步摇摆。于是沉思三日三夜,意想出了一种兵器,有了这利器,才将“理”字排行的元恶大憝,一律肃清。这利器的大名,便叫“经验”。现在又添上一个雅号,便是高雅之至的“事实”。
经验从那里得来,便是从清朝得来的。经验提高了他的喉咙含含糊糊说,“狗有狗道理,鬼有鬼道理,中国与众不同,也自有中国道理。道理各各不同,一味理想,殊堪痛恨。”这时候,正是上下一心理财强种的时候,而且带着理字的,又大半是洋货,爱国之士,义当排斥。所以一转眼便跌了价值;一转眼便遭了嘲骂;又一转眼,便连他的影子,也同拳民时代的教民〔4〕一般,竟犯了与众共弃的大罪了。
但我们应该明白,人格的平等,也是一种外来的旧理想;现在“经验”既已登坛,自然株连着化为妄想,理合不分首从,全踏在朝靴底下,以符列祖列宗的成规。这一踏不觉过了四五年,经验家虽然也增加了四五岁,与素未经验的生物学学理——死——渐渐接近,但这与众不同的中国,却依然不是理想的住家。一大批踏在朝靴底下的学习诸公,早经竭力大叫,说他也得了经验了。
但我们应该明白,从前的经验,是从皇帝脚底下学得;现在与将来的经验,是从皇帝的奴才的脚底下学得。奴才的数目多,心传〔5〕的经验家也愈多。待到经验家二世的全盛时代,那便是理想单被轻薄,理想家单当妄人,还要算是幸福侥幸了。
现在的社会,分不清理想与妄想的区别。再过几时,还要分不清“做不到”与“不肯做到”的区别,要将扫除庭园与劈开地球混作一谈。理想家说,这花园有秽气,须得扫除,——到那时候,说这宗话的人,也要算在理想党里,——他却说道,他们从来在此小便,如何扫除?万万不能,也断乎不可!
那时候,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 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那些理想学理法理,既是洋货,自然完全不在话下了。
但最奇怪的,是七年十月下半,忽有许多经验家,理想经验双全家,经验理想未定家,都说公理战胜了强权〔6〕;还向公理颂扬了一番,客气了一顿。这事不但溢出了经验的范围,而且又添上一个理字排行的厌物。将来如何收场,我是毫无经验,不敢妄谈。经验诸公,想也未曾经验,开口不得。
没有法,只好在此提出,请教受人轻薄的理想家了。
注释: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署名唐俟。
按从本篇起到“六十六”止,都是一九一九年的作品,作者误编入一九一八年,现已加以更正。
〔2〕 《再论戏剧改良》 作者傅斯年,当时是《新潮》杂志的主编。这里所引的一段话的原文是:“中国人不懂得‘理想论’和‘理想家’的真义。说到‘理想’,便含着些轻薄的意味,觉得‘理想’即是‘妄想’,‘理想家’即是‘妄人’。”
〔3〕 辛亥革命后,清朝反动官僚、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胁迫孙中山辞职,窃取了国家政权,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为了镇压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势力,曾宣称他“政治军事经验不下于人”,要用武力征伐反对者,并指令熊希龄组织所谓“第一流的经验内阁”。后来袁世凯又阴谋复辟帝制,清朝遗老如劳乃宣、宋育仁、刘廷琛等也不甘寂寞,同时在北京等地进行复辟活动。以后又有张勋、康有为等人于一九一七年扶植清废帝溥仪复辟的事件。
〔4〕 拳民时代的教民 拳民时代,指义和团运动时期。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加紧利用宗教作为侵略的工具,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国各地设立的教堂,广收信徒。这种信徒被称为教民。其中有一部分是恶霸、地痞、流氓,他们在帝国主义者的庇护下,横行霸道,欺压平民,引起群众的愤恨;在义和团运动中,一般教民也受到打击。
〔5〕 心传 佛教禅宗用语。指不立文字,不依经卷,只凭师徒心心相印,递相授受。
〔6〕 公理战胜强权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等“协约国” 宣扬它们战胜德、奥等“同盟国”是“公理战胜了强权”。当时中国也有一些人随声附和,大肆颂扬。
四十〔1〕
终日在家里坐,至多也不过看见窗外四角形惨黄色的天,还有什么感?只有几封信,说道,“久违芝宇,时切葭思;”〔2〕有几个客,说道,“今天天气很好”:都是祖传老店的文字语言。写的说的,既然有口无心,看的听的,也便毫无所感了。
有一首诗,从一位不相识的少年寄来,却对于我有意义。——
爱情
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我有父母,教我育我,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我有兄弟姊妹,幼时共我玩耍,长来同我切磋,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但是没有人曾经“爱”过我,我也不曾“爱”过他。
我年十九,父母给我讨老婆。于今数年,我们两个,也还和睦。可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
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诗的好歹,意思的深浅,姑且勿论;但我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
但从前没有听刻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
然而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形式上的夫妇,既然都全不相关,少的另去姘人宿娼,老的再来买妾:麻痹了良心,各有妙法。所以直到现在,不成问题。但也曾造出一个“妒”字,略表他们曾经苦心经营的痕迹。
可是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我们所有的是单是人之子,是儿媳妇与儿媳之夫,不能献出于人类之前。
可是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恶;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这叫声。
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
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鸮便鸱鸮般叫。我们不必学那才从私窝子〔3〕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第一”的人的声音。
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我们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
旧账如何勾消?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
注释: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署名唐俟。
〔2〕 “久违芝宇,时切葭思” 这是旧时书信中常用的客套语,意思是久不见面,时刻想念。芝宇,即眉宇。《新唐书·元德秀传》载,唐代房琯每见元紫芝,常感叹说:“见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尽。”后来就以“芝宇”作为他人容貌的美称。“ 葭思”,对友人的思念。语出《诗经·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3〕 私窝子 私娼住的地方。
四十一〔1〕
从一封匿名信里看见一句话,是“数麻石片”(原注江苏方言),大约是没有本领便不必提倡改革,不如去数石片的好的意思。因此又记起了本志通信栏内所载四川方言的“洗煤炭”〔2〕。想来别省方言中,相类的话还多;守着这专劝人自暴自弃的格言的人,也怕并不少。
凡中国人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倘与传来的积习有若干抵触,须一个斤斗便告成功,才有立足的处所;而且被恭维得烙铁一般热。否则免不了标新立异的罪名,不许说话;或者竟成了大逆不道,为天地所不容。这一种人,从前本可以夷到九族〔3〕,连累邻居;现在却不过是几封匿名信罢了。但意志略略薄弱的人便不免因此萎缩,不知不觉的也入了“数麻石片”党。
所以现在的中国,社会上毫无改革,学术上没有发明,美术上也没有创作;至于多人继续的研究,前仆后继的探险,那更不必提了。国人的事业,大抵是专谋时式的成功的经营,以及对于一切的冷笑。
但冷笑的人,虽然反对改革,却又未必有保守的能力:即如文字一面,白话固然看不上眼,古文也不甚提得起笔。照他的学说,本该去“数麻石片”了;他却又不然,只是莫名其妙的冷笑。
中国的人,大抵在如此空气里成功,在如此空气里萎缩腐败,以至老死。
我想,人猿同源的学说,大约可以毫无疑义了。但我不懂,何以从前的古猴子,不都努力变人,却到现在还留着子孙,变把戏给人看。还是那时竟没有一匹想站起来学说人话呢?还是虽然有了几匹,却终被猴子社会攻击他标新立异,都咬死了;所以终于不能进化呢?
尼采〔4〕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现。到那时候,类人猿上面,怕要添出“类猿人” 这一个名词。
所以我时常害怕,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5〕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我又愿中国青年都只是向上走,不必理会这冷笑和暗箭。尼采说:
“真的,人是一个浊流。应该是海了,能容这浊流使他干净。
“咄,我教你们超人:这便是海,在他这里,能容下你们的大侮蔑。”(《札拉图如是说》的《序言》第三节)
纵令不过一洼浅水,也可以学学大海;横竖都是水,可以相通。几粒石子,任他们暗地里掷来;几滴秽水,任他们从背后泼来就是了。
这还算不到“大侮蔑”——因为大侮蔑也须有胆力。
注释: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署名唐俟。
〔2〕 “洗煤炭” 见《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通信》栏载任鸿隽给胡适的信:“《新青年》一面讲改良文学,一面讲废灭汉文,是否自相矛盾?既要废灭不用,又用力去改良不用的物件。我们四川有句俗语说:“你要没有事做,不如洗煤炭去罢。”
〔3〕 九族 指自身及自身以上的父、祖、曾祖、高祖和以下的子、孙、曾孙、玄孙。另一种说法是以父族四代、母族三代、妻族二代为九族。
〔4〕 尼采(F.Nietzsche) 参看本卷第59页注〔26〕。下文所说的《札拉图如是说》,即《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他的一部主要哲学著作。
〔5〕 随喜 佛家语,《修忏要旨》说:“随他修善,喜他得成。”意思是随着别人做善事,为别人获得善果而高兴。
四十二〔1〕
听得朋友说,杭州英国教会里的一个医生,在一本医书上做一篇序,称中国人为土人;我当初颇不舒服,子细再想,现在也只好忍受了。土人一字,本来只说生在本地的人,没有什么恶意。后来因其所指,多系野蛮民族,所以加添了一种新意义,仿佛成了野蛮人的代名词。他们以此称中国人,原不免有侮辱的意思;但我们现在,却除承受这个名号以外,实是别无方法。因为这类是非,都凭事实,并非单用口舌可以争得的。试看中国的社会里,吃人,劫掠,残杀,人身卖买,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凡有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拖大辫,吸鸦片,也正与土人的奇形怪状的编发及吃印度麻〔2〕一样。至于缠足,更要算在土人的装饰法中,第一等的新发明了。他们也喜欢在肉体上做出种种装饰:剜空了耳朵嵌上木塞;下唇剜开一个大孔,插上一支兽骨,像鸟嘴一般;面上雕出兰花;背上刺出燕子;女人胸前做成许多圆的长的疙瘩。可是他们还能走路,还能做事;他们终是未达一间〔5〕,想不到缠足这好法子。……世上有如此不知肉体上的苦痛的女人,以及如此以残酷为乐,丑恶为美的男子,真是奇事怪事。
自大与好古,也是土人的一个特性。英国人乔治葛来〔4〕任纽西兰总督的时候,做了一部《多岛海神话》,序里说他著书的目的,并非全为学术,大半是政治上的手段。他说,纽西兰土人是不能同他说理的。只要从他们的神话的历史里,抽出一条相类的事来做一个例,讲给酋长祭师们听,一说便成了。譬如要造一条铁路,倘若对他们说这事如何有益,他们决不肯听;我们如果根据神话,说从前某某大仙,曾推着独轮车在虹霓上走,现在要仿他造一条路,那便无所不可了。(原文已经忘却,以上所说只是大意)中国十三经二十五史,正是酋长祭师们一心崇奉的治国平天下的谱,此后凡与土人有交涉的“西哲”,倘能人手一编,便助成了我们的“东学西渐”〔5〕,很使土人高兴;但不知那译本的序上写些什么呢?
注释: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
〔2〕 印度麻 亦名菽麻,豆科,一年生草本,可作麻织品原料和牲畜饲料。在印度和一些其他国家,又用作麻醉品。
〔3〕 未达一间 还有一点差距的意思。汉代扬雄《法言·问神》:“颜渊亦潜心于仲尼矣,未达一间耳。”
〔4〕 乔治葛来(George Grey,1812—1892) 英国人。曾任英国驻澳大利亚、新西兰(即本文中所说的纽西兰)和南非的殖民地总督。所著《多岛海神话》一书,一八五五年出版。“多岛海”(Polynesia),通译波利尼西亚。
〔5〕 “东学西渐” 一九○九年日本汉学家槐南陈人著《东学西渐》篇,在日本东京《日日新闻》上发表,当时上海《神州日报》曾译载过这篇文章。其中说:“伦敦二三书肆发售之书目……有《十三经注疏》,有《史记》,有《前后汉书》……凡考索中国文物礼制之书,殆皆具。……庸讵知东学西渐已有如斯之盛,宛似半夜荒鸡,足使闻者起舞耶。”《神州日报》编者又在按语中加以称颂。
四十三〔1〕
进步的美术家,——这是我对于中国美术界的要求。
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周彡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令我们看了,不但欢喜赏玩,尤能发生感动,造成精神上的影响。
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家,是能引路的先觉,不是“公民团”〔2〕的首领。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品,是表记中国民族知能最高点的标本,不是水平线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数。近来看见上海什么报的增刊《泼克》〔3〕上,有几张讽刺画。他的画法,倒也模仿西洋;可是我很疑惑,何以思想如此顽固,人格如此卑劣,竟同没有教育的孩子只会在好好的白粉墙上写几个“某某是我而子”一样。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美术也是其一:学了体格还未匀称的裸体画,便画猥亵画;学了明暗还未分明的静物画,只能画招牌。皮毛改新,心思仍旧,结果便是如此。至于讽刺画之变为人身攻击的器具,更是无足深怪了。
说起讽刺画,不禁想到美国画家勃拉特来(L.D.Brad-lev 1853 —1917)了。他专画讽刺画,关于欧战的画,尤为有名;只可惜前年死掉了。我见过他一张《秋收时之月》(《The Harvest Moon》)的画。上面是一个形如骷髅的月亮,照着荒田;田里一排一排的都是兵的死尸。唉唉,这才算得真的进步的美术家的讽刺画。我希望将来中国也能有一日,出这样一个进步的讽刺画家。
注释: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
〔2〕 “公民团” 指袁世凯雇用的流氓打手,他们在一九一三年十月六日自称 “公民团”,包围当时的国会,强迫议员选他为总统。后来的北洋军阀段祺瑞、曹锟也都使用过这类手段。这里是比喻反动统治者的御用工具。
〔3〕 指上海《时事新报》的星期图画增刊《泼克》。关于这个画刊的内容和倾向,可参看本书《随感录四十六》。“泼克”,英语Pucd的音译,是英国民间传说中喜欢恶作剧的小妖精的名字。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