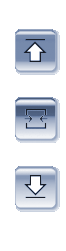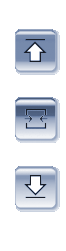| |
| |
|
认识化学结构
|
|
在19世纪,西欧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炼铁技术得到飞速发展,他们把煤经过干馏制成焦炭用于炼铁,但对在炼铁过程中同时产生的煤焦油和煤气等,这些乌黑、气味难闻而又容易着火的东西要找个出路,曾经大伤脑筋,并为此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但在当时,化学家们却对它们很感兴趣。化学家把这些煤焦油和煤气拿来,经过仔细的分离提炼后,得到了无数种有机化合物。原来,有机化合物中,它们是非常特殊的大家族,有机化学家们把它们称为芳香族化合物。
起初,人们从香树脂、香料油等天然物质中得到一些有特殊香味的纯物质,现在又从煤焦油等物中,得到了其组成、化学特性与前者相类似的东西,尽管其气味并不芳香,但品种却更多,在科学研究上的意义更大,作为有机化合物的一族,也更具有代表性,只是它的含义已不再是表面上有香味而已。
芳香族的有机物中,最主要的化合物便是苯。
最早发现苯的人是英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法拉第。他是偶然从贮运煤气的桶里所凝集的油状物中,经过分离后得到了一种无色的液体。他用当时原子量H=1、C=6的标准测出它的实验式是CH,并测出它的蒸汽比重是氢气的
239倍。但他并没有推出它的分子式。如照现在原子量标准H=1、C=12、苯的实验式则应该是CH,根据蒸汽比重就能算出它的分于量是78,便很容易知道苯的真正分子式是CH。在约9年之后的1834年,又有人把安息香酸和石灰
66放到一起干馏之后,也得到一种碳氢化合物,才给这个化合物取名叫“苯”
(benzene),接着又有人测定出它的分子式是CH。
66
19世纪中叶,有一位德国有机化学家凯库勒(1829~1896),在研究芳香族有机化合物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发现所有芳香性 (族)有机化合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们进行非彻底破坏 (不燃烧)的激烈反应后,经常失去了一部分碳,但主要产物总是至少含有6个碳原子。这种包含有6个碳原子的化合物,就是以苯为主体的化合物。于是1865年凯库勒提出了以苯为基团的芳香族化合物的设想,并曾用多种图式来表示苯的分子结构,最后确定为正六边形图式,也就是我们现在学化学时常用的苯的结构式。
早些时候,凯库勒在研究有机化合物的分子组成过程中,于1857年提出了“原子数”的概念,指出:氢、氯、溴、钾为“一原子的”,氧和硫是“二原子的”,氮、磷、砷是“三原子的”,而碳是“四原子的’”。这是化合价的早期说法,也就是说,这些元素分别是一价、二价、三价和四价。在这一基础上,凯库勒认为有机化合物中,碳原子之间可以连成链状,这就能很好的说明。例如碳氢化合物中,由甲烷(CH)开始,随着碳原子数目的增多,
4就分别能有组成不同的乙烷 (CH)、丙烷(CH)、丁烷(CH)等一系
26 38 410列化合物存在的道理了。
几乎是同时,英国的有机化学家库帕,于 1858年也独立的提出了碳是四价及碳原子间可以相连成链的学说。
凯库勒和库帕所提出的这些学说,为有机化学结构理论的建立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化学结构”这个概念,在19世纪上半叶就已为化学家们所采用,“化合价”概念,特别是碳为四价的共识,更为探索有机化合物分子结构铺平了道路。但是苯 (CH)分子的出现,让凯库勒等一直认为碳原子能够连成链
66条的人,为难了好久,实验的事实证明,苯分子中六个碳原子、六个氢原了的性质分别完全相同,即它们分别以相同的关系,处在相同的位置上,如果这6个碳连成一个有头有尾的链条,而且又性质完全相同,若用碳四价的理论,是根本解释不通的。
凯库勒经过冥思苦想,终于认为可能这六个碳原子是连成一个环,经过现代的结构理论研究确认了这个六碳环是真实存在的。
对于凯库勒的设想,有人传说是他一次睡梦中见了一条蛇,咬着自己的尾巴直打转而受到启发的。不知是否确有其事,而他提出的苯的环状结构学说,在有机化学发展史上的确起到了巨大的作用。1890年,在纪念苯的结构学说发表25周年时,伦敦的化学学会指出:“苯作为一个封闭链式结构的巧妙构想,对于化学理论发展的影响,对于研究这一类及其相似化合物衍生物的异构现象的内在问题所给予的动力,以及对于像煤焦油染料这样巨大规模的工业的前导,都已为举世公认。”
前面说到的芳香族有机物,人们自从认识了苯环之后,它的真实含义便是具有苯环的化合物的简称了。这其中包括了很多种染料、医药、香料和炸药。
自然界的煤,开始对被人们当成黑色的石头,在后来却发现它能燃烧,因而在很长的时间内只被当作燃料。随着炼铁工业的发展,大量的煤堆着闷烧成焦碳时,便产生了浓烟而被排放到大气中,污染环境,损人健康。后来改为干馏炼焦,一方面提高了焦碳的产量和质量,同时所产生的煤气和煤焦油,也被当作气体燃料和化工原料,都有其各自的用途,这样又降低了炼焦生产的成本。
化学家们研究了苯结构后,发展了以煤焦油为基础的焦化工业。芳香烃有机物的提取和合成,更极大地丰富了有机化学的内容,并且也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
几代人辩论的定律
纯净的化合物,必然各有其固定的组成,也就是定组成定律,又称为定比定律。在初中化学里,虽然不提这一定律的名称,然而在讲化合价和分子式时,学生却必须掌握有关的概念,并认识到纯净的化合物,之所以性质固定,是由于它的组成固定,而且原子间排列的关系也是固定的。
就是这样一个现在看来似乎简单的定比定律,在科学史上却由1781年争论到1860年才被确定下来。这一事实,充分说明科学家们的态度是十分严谨的。
从17世纪末起,西欧的一些药剂师和化学家们,在进行一系列的科学实验中,就已对各种类型的化学反应进行了定量的研究,有些人已经从研究碳酸钙,水及氧化汞的过程中,明确的发现了它们的组成是固定的。如 1755年,英国化学家布拉克在他研究石灰石的论文中提到:石灰石经过煅烧后,重量会减轻44%。1781年,英国化学家凯文第旭研究水的合成时,发现所消耗氢氧气体的体积比总是 1∶2,由此而认识到水是化合物而不是一种元素,曾提出科学的燃烧理论的法国化学家拉瓦锡,从1772年到1777年用了五年多的时间,做了大量的燃烧实验,进行了精确的定量分析研究。例如他在进行氧化汞的合成与分解实验时,将45份重的氧化汞加热分解,恰好得到41.5份重和汞和3.5份重的氧气。这也就是说,拉瓦锡的实验,不仅说明化合物有其固定组成,并且用具体数据,证明了化学反应中的质量不灭定律。
明确的用文字描述定组成定律的是法国的一位药剂师普罗斯,他在1799年明确地写道:“两种或两种以上元素相化合变成某一化合物时,其重量之比例是天然一定的,人力不能增减。”这是早于化合价形成共识之前50多年提出的,这显然是普罗斯根据自己大量的实验数据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自信。
但普罗斯的关于定比定律的理论,却遭到了当时法国化学界的权威贝托雷的激烈反对。原来是在此之前,贝托雷正好发表了他的《化学亲合力之定律》,其中说道:“一物质可与有相互亲合力的另一物质以一切比例相化合。”一个是以一定的比例,一个却以一切的比例,两者针锋相对而互不相容。那么到底是谁正确呢?看一下他们两人的实验内容就明白了。贝托雷以溶液、合金或玻璃类物质,可以形成多种组成的铅的氧化物和铜的碱式盐等物质为例子,这些都是混合物或是不同的化合物。表面看来它们是以“亲合力”而形成,然而它们都不是真正的或单一的化学反应,当然“化合”的比例,就不会存在“一定”的问题了。
既然贝托雷用的是错误的实验例证,为什么又能长时间的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呢?这还得再来看看普罗斯的说法和做法才能得到解答。
普罗斯确切的发现了贝托雷的实验对象并不是纯净物和单一化合物,于是先后从1802年到1818年,写了许多文章,发表在法国《物理杂志》上,用来答复贝托雷的错误的批评。
按贝托雷的说法,他认为化合物的组成会随着生成该物质的物理条件不同而不同。普罗斯则指出,一种化合物无论是天然的还是人工合成的,无论是产生在地球深处,还是产生在人们的实验室里,也无论是取自什么地方,其组成都是相同的。普罗斯还指出,即使是铅和氧化合,铅跟氧的量之间,也只有几个固定的比例 (即PbO、PbO、PbO和PbO),而绝不会是任意的
2 2 34比例,显然它们是组成各不相同的铅的氧化物,而根本不能混为一谈。
普罗斯还用铜、锡、锑、钴等多种金属和硫化合,用在各种条件下所得硫化物,其组成都相同的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然而在普罗斯的时代,化学界还没有足够精确的定量分析的技术手段和方法。普罗斯的实验结果,对同一物质的分析往往也存在很大的误差,这就使他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遗憾终身。“定组成定律”就只能暂时作为假说,停留在当时人们的心中。
到了19世纪的中叶,定量的化学分析,已得到完善,人们已能在实验时得出相当精确的结果,但极小的偏差仍是难免存在。就因为这些,因此依然有人认为“这个定律(指定组成定律)或者也有些偏差,……”而仍然不愿十分肯定的承认它。
后来,比利时的分析化学家斯达 (1813~1891)曾经用多种不同的方法制取金属银,又用多种不同的方法把银制成氯化银,所有实验偏差都在千分之三左右。在斯达1860年发表了他许多精确的分析实验结果之后,这场围绕着定比定律是否实在可信的辩论,前后经历了大约80多年才算结束。
而一个叫“倍比定律”的,却在1804年就被确认下来,在时间上比“定比定律”的确定要早50多年。
倍比定律的内容是:“当相同的两元素可生成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化合物时,若其中一元素之重量恒定,则其余一元素在各化合物中之相对重量有简单倍数之比。”
倍比定律是英国化学家道尔顿提出来的,当时道尔顿正在构思他的原子论,首先提出了原子量这一概念,认为:“同一元素的原子,其形状、质量及各种性质都是相同的”,他还认为:“不同元素的原子以简单数目的比例相结合,因而形成化学中的化合现象”,等等。道尔顿根据其原子论的设想,用推理的方法而得出了倍比定律,并还测定了碳的氧化物(CO、CO)氢化物
2
(CH、CH)中碳氧之比和碳氢之比,确实在碳的量一定时,两种氧化物中
4 24氧的重量比是1∶2,两种氢化物中氢的重量比为2∶1。
后来精于化学分析的瑞典化学家贝采利乌斯,分析了铅的两种氧化物和铜的两种氧化物以及铁的氧化物和硫的氧化物,也都取得了精确的结果。而斯达也做了碳酸气(CO)和一氧化碳之间转变关系的实验,发现两种氧化物
2中碳的重量一定时,氧的重量比确为2∶1。这些事实都比确认定比定律要早十多年。
从现在的原子、分子观点和化合价的概念来看,定比定律和倍比定律实际都是定组成定律的内容在形式上的不同表现。因为历史的原因,它们的发生和被确认的过程,却是那样的不同,这实在是一件令人回味的事。
质量守恒定律
一场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工业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人们对生产原料产生更深刻的认识。而纺织工业的发展又促使人们去研究染料,研究酸碱,因而向化学领域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在这方面领头的,却是一个法国人,他叫拉瓦锡 (1743~1794年)。
1743年8月26日,拉瓦锡生于巴黎。父亲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律师,拉瓦锡从小就不愁吃穿,上了中学又上大学,从法律系毕业后很顺利地也当上了律师。然而不知是什么缘由让拉瓦锡对矿物特别感兴趣。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常常放着一些石头、硫磺、石膏等等,就连卷宗里也时常可抖出一些红绿颜色的矿粉来。出乎意外地他的一篇论文在一次竞赛中竟获得法国科学院一枚金质奖章,这便让他下决心辞掉了律师职务,而献身于自己酷爱的化学事业。
然而个人研究化学,需要建实验室,买仪器,是需要一笔不小的资金的,那么钱从何来?拉瓦锡凭借他律师的阅历,用特有的眼光在财政界一扫,便发现了一个生财之道。原来18世纪中叶,法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已聚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但封建王朝却不甘退位,更加紧了对人民钱财的搜刮。其中的一个妙法就是收重税。但政府并不出面,而是承包给“包税人”。包税人预先向国家交一笔巨款,然后再去收税。包税人只要保证向国家缴钱,至于再向老百姓收多少,国家便不管了。为了研究化学,拉瓦锡便从父亲那里借来钱作抵押金,违心地当上了一名包税人。这样,很快拉瓦锡便拥有了自己的化学实验室,而且还认识了一位金发碧眼的姑娘玛丽,玛丽是包税公司经理的女儿,才14岁。但他们感情笃深,很快结为夫妻。玛丽性情温柔,又写得一手好字,并擅长绘画,为丈夫抄论文,绘图表,天赐一个贤内助。一年后,拉瓦锡当选为科学院院士。在这以后,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实验室里渡过的。
1789年一个冬夜,寒气笼罩着巴黎,拉瓦锡和娇妻玛丽正围炉闲聊,玛丽手中拿着一篇刚收到的文章正在朗读,拉瓦锡听完以后便再也坐不住了。他一把抢过文章连续看了两遍。文章中说到将一块金刚石用高温灼烧以后,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东西烧完后总要留下一点灰烬。拉瓦锡立即钻进实验室,照着做了一次实验,果然如文章所说,金刚石不翼而飞了。整整一夜,拉瓦锡无法入眠。天刚亮时,他翻身坐起:“玛丽,我们赶快进实验室去,办法有了,也许问题就出在这里。”
拉瓦锡只穿一件睡衣坐在实验台旁,他用不怕火的石墨软膏厚厚地将一块金刚石裹起来,然后放在火上进行高温灼烧。他考虑过去人们研究燃烧都是在空气里进行的,谁敢保证这种看不见的空气里会不会有什么物质在燃烧时参加进去,或是带走什么呢?现在将这金刚石裹得严严实实不与空气接触,看它会出现什么现象。他就这样睡衣托鞋、蓬头黑手地在实验台旁忙着。这时在高温火焰下,那裹着厚厚一层石墨的金刚石已被烧得通红,就像炉子里的红煤球一样。拉瓦锡小心地熄灭火,等它慢慢冷却后再剥开一看,发现金刚石竟完好无损!
“看来燃烧和空气有很大的关系。”他一边洗脸,一边说。
“燃烧不是物质内的燃素在起作用吗?”玛丽一边收拾仪器,一边问道。
“大家都这么说,我看未必就是这样。”
拉瓦锡早就对燃素说产生了怀疑。今天这个实验更加明确地证明了,燃烧现象根本不在燃素,而在于空气。
然而在燃烧过程中空气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检测一下它的重量。拉瓦锡立即又设计出新的实验方案。
他在密闭的容器里烧炼金属,在燃烧前后他都仔细地用天平称过重量,发现重量没有一点变化,他再称金属灰的重量,增加了,又称烧过后的空气的重量,却减少了,而减少的空气和增加了的金属灰正好重量相等。于是拉瓦锡便推断出化学上一条极重要的定律即:重量(质量)定恒定律。物质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化学反应只不过是物质由这种形式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的形式转换。
当拉瓦锡由燃烧金属发现燃素说并不可靠后,他便放下了其他研究课题而专攻各种燃烧现象。他又投资添置了一些设备,带了几个助手,将自己的实验室重新布置一番,实验室真成了一个燃烧展览馆。他这个豪华的实验室曾接待过许多科学名人,瓦特、富兰克林都曾到这里作客。一天英国学者普里斯特利又来这里访问,拉瓦锡陪他在实验室边漫步边讨论问题。当来到几个玻璃罩前时,普里斯特利问:“这是在干什么?”
“我将磷用软木漂在水面上罩着燃烧,烧后水面就上升,占去罩内空间的五分之一,你再看这个罩内是烧硫磺的,水面也是上升了五分之一。这个现象说明燃烧时总有五分之一的空气参加了反应。”
“对。我也曾发现空气中有一种 ‘活空气’,蜡烛遇见它时会更亮,而小老鼠没有它很快就会死亡。拉瓦锡先生,你知道舍勒在1772年就曾找见过这种空气,他叫它为 ‘火焰空气’,我想,这和你找到的那五分之一的空气很可能是一回事。但是,我觉得物质燃烧是因为有燃素,恐怕和这种空气没有关系。”
“不,有没有它大不一样。你看这玻璃罩里剩下的五分之四的‘死空气’,你若再放进什么含有‘燃素’的东西,无论磷块还是硫磺,它也不会燃烧了。尊敬的普里斯特利先生,你的发现对我太有启发了,看来空气里一定包含有两种以上的元素,起码这 ‘活空气’就是一种,空气并不是一种元素。”
“这么说,水也不应该是一种元素了。因为我已经发现在水里也包含有这种活空气,而且用一种活空气和另外一种空气(氢气)在密封容器里加热,就又能生成水。”
“真的吗?”拉瓦锡突然停下脚步,眼睛直盯着普里斯特利。
“真的。你这里的实验条件太好了,让我们重新做一次。”
普里斯特利熟练地制成了两种气体,然后将它们混合到一个密封容器里,便开始加热,一会儿容器壁上果然出现了一层小水珠。拉瓦锡等实验一完就拉着普里斯特利到客厅里,连叫玛丽。
“玛丽,你知道吗,我们今天不但进一步发现了燃烧的秘密,还找到了新的元素,它既存在于水中,又存在于空气中,这可就打破了水和空气是一种元素的说法,说明了它们都是可分的。这种东西能和非金属结合生成酸,又能使生命活下去,就叫元氧吧。”
“拉瓦锡先生,你真是一个很大胆的科学家,我曾经做过不知多少次实验,你就是不敢放弃燃素说,总也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今天这个发现真是我们化学界的一件大喜事。”
氧气本是舍勒和普里斯特利最先发现的,然而他们为什么看不到它与物质燃烧之间的关系呢?原来是受了旧燃素说的束缚,使他们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本来做学问首先靠观察积累,第二要靠思考比较。观察积累基本上还是在旧理论指导下的收集、整理,需要非常细心且能吃苦;而思考比较却是在新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归纳与突破,要的是大胆与勇敢。一个旧理论的推翻也就是一个新理论的建立。只有少数既聪明又勇敢的人才会去不断的观察新问题,收集新材料,不断的打破旧的理论框框,摈弃旧假设,胜利便是属于他们这些人的。
段时间后,拉瓦锡的处境便开始困难起来,不久他正式被控贪污,又过了不久他的实验室也被查封了。拉瓦锡并不觉得会有什么大事发生。他想,作为一个科学家,总要为社会办一点事,于是他便加紧编书。过去他曾出过一本《化学教程》,这本书总结了他多年来所做的实验,并提出了氧化学说,将统治化学界近百年的燃素说完全推翻。书刚一出版即被抢购一空。现在拉瓦锡又将这本书补充修订准备再版。并且他又将这几年新发现的元素整理成一张表,共33种,分作四类:
1.气体单质:光、热、氧、氢、氮。
2.非金属单质:硫、磷、碳、盐酸根、硫酸根、硼酸根。
3.金属单质:锑、银、砷、铋、钴、铜、锡、铁、锰、汞、钼、镍、金、铂、铅、钨、锌。
4.土类单质:石灰、镁土、钡土、铝土、硅土。
这是化学史上的第一份科学的元素表。那些世界由水、土、气、火构成的四元素说到此也就彻底破产了。化学在拉瓦锡面前是彻底敞开了大门。许多新奇的现象,有趣的问题,接踵而至。但是他有一种预感,感觉有什么祸事就要临头了,手头的工作可能干不完了。这种莫名的念头又不敢对妻子说,因此他整天埋头写作,妻子也加紧帮他画插图。
果然,一天上午,拉瓦锡刚在桌旁坐定就有两人进来,说法庭传他去一趟。他知道那个预感今天可能要变成现实了。他冷静地站起来说:“幸好我的书已经全部完成了。”返身取了一顶帽子便随来人而去。在法庭上,审判也极为草率,他本是律师出身,但也未能够张口为自己辩护几句。一位好心的律师提醒法官说:“拉瓦锡先生可是一位全欧洲闻名的科学家啊!”法官却说:“革命不需要科学家,只需要正义。”当即判了他的死刑。
1794年5月8日,拉锡被反绑着双手,押向广场中心的断头台。这时广场上已人山人海,将要断头的几个人一字排开的站在台上。拉瓦锡被判死刑的消息,惊动了巴黎的许多科学家,真是太荒唐了,什么时候听说过一个科学院的院士被抓来砍头呢?曾与他一起研究过化学命名法的柏托雷连忙赶来。妻子玛丽也来了,她一夜之间衰老了许多,这时正抱住拉瓦锡的头失声痛哭。拉瓦锡多么想用手为她拭去泪水,去拥抱一下这个从14岁起就开始追随他的妻子,可是由于手被反绑着而无能为力。他让玛丽抬起头来,说要再仔细的看看她。拉瓦锡平静地说:“玛丽,你不要为我悲伤,感谢上帝,我已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我今年51岁,可以说已经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生,而且可以免去一个将会有诸多不便的晚年。我能够为后人留下了一点知识,可能还留下了一点荣誉,应该说我是幸运的。”玛丽瞪着两只泪眼,只是呆呆地望着他,喉咙里像被什么东西噎住发不出一点声音来。
这时,只听身后那面大铡刀由空而降,嗖地落下,卷起一阵凉风,扫得人心里发慌,接着就听“嚓”的一声,一颗人头像被菜刀剁下的一节黄瓜液在台上。刚杀掉的是一个僧侣。接着,那面铡刀又嘎吱吱地升了起来,就听监斩官吼道:“下一下,拉瓦锡!”玛丽听到这吼声,便昏倒在拉瓦锡的脚下,柏托雷还抱着一线希望,冲到监斩官面前,高声喊道:“不能杀他啊,法国不能杀掉自己的儿子。你们一瞬间就砍下他的头,可再过100年也不会长出一颗这样的头了啊!”但是,这位现代化学的创始者倾刻间便人头落地了。
钾与钠的发现
由于伏打发明了电池组,从而开辟了电化学这一领域。这一领域刚拓开便有人大踏步走来。这人就是戴维 (1778~1829)。
戴维出生在英国一个沿海小城的一个木匠家庭,小时候便是一个有名的浪荡子。父母很希望他能成才,好改换门庭,于是送他到学校去读书。然而小戴维虽头脑十分灵活,却不肯用在书本上,他每天左边口袋装着鱼钩鱼线,右边口袋装着一只禅弓,早晨上学前也经常要跑到海边去打几只鸟,钓几条鱼,因此经常迟到。有时正在上课,他也悄悄将口袋里的鸟放出来,学生们便一窝蜂地去捉鸟,老师知道是戴维这个罪魁,所以他一迟到就气得先提住他的耳杂厉声训斥几句,又追问去干了什么坏事,并没收了他口袋里的弹弓、鱼钩、小鸟等物。这天戴维又迟到了,两个口袋鼓鼓囊囊,疯了似的冲进教室正要向自己的座位上奔去。老师厉声喊道:“戴维!又到哪里闯祸去了!”说着上来用一只手扯制着他的耳朵。谁知戴维向他鼓了鼓小眼睛,一句话也不答。老师便更提高嗓门吼道:“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
“就不给你!”戴维说着还故意用手将口袋护住。
“给我!”当着全体学生,老师丢了面子,因此他一只手掐紧戴维的耳朵,另一只手便向他口袋里掏去。谁知他的手刚伸进口袋便“啊”的一声尖叫着抽了出来,连扯着戴维耳朵的那只手也早已松开。随着老师抽出的那只手,一条绿色的菜花小蛇落在老师的脚下。教室里一下炸了窝,学生们有的惊叫,有的哄笑。而戴维却不说也不笑,一本正经地拾起小蛇,装进口袋里,又慢慢的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就像刚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他越是这样一本正经,学生们就越是笑得前仰后合,而老师更是气得脸红脖子粗一句话说不出来,最后挟起讲义,摔门而去。
老师离开教室后便径直向戴维家走去。戴维的父亲正在干活,老师气呼呼地推门而入,如此这般地学说一遍,把老木匠气得两手发抖、五脏乱颤。戴维放学回来了,一进门就劈头挨了一巴掌,母亲闻声过来拖住父亲,一边心疼地喊:“你下手那么重,真要打死孩子吗!”
“这样的孽子不要也可以!”
一个要打,一个要拉,两位老人也扯缠在一起,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你呀……”老木匠气得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我这辈子算是对你没有指望了。”
发生这件事后不久,戴维的父亲便一病不起,过了一阵子便作古而去。戴维的母亲拖着五个孩子,日子实在无法维持下去,只得将他送到一家药店里当学徒,也好省一张吃饭的嘴。就这样戴维每天给人抹桌子扫地、端脸盆倒尿壶,到了月底别人都领了工资,他却分文没有。他伸手问老板去要,老板当众将他那只小手狠狠地打了一巴掌说:“让你抓药不识药方,让你送药认不得门牌,你这双没用的手怎好意思伸出来要钱!”店里的师徒也哄堂大笑,戴维满面羞愧转身就向自己房里奔去,一进门就扑在床上,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他从前可没受过这种羞辱,可是现在不能跟学校和家里相比。现在是吃人家的,喝人家的,再说如果跑回家去吧,不也是让母亲为难吗?戴维在学校时功课学得不怎么好,却爱写几句歪诗,他一翻身揪起自己的衬衣,撕下一块来,随即又咬破中指在上面写了几句话,便冲出门去。外面店员们正闹哄哄地向老板敬酒,不提防有人啪地一声将一块白布放在桌子中央,只见上面写着:“莫笑我无知,还有男儿气,现在从头学,三年见高低。”大伙再一细看,竟然是鲜血写成的,大家非常吃惊,只见戴维挺身站在桌旁,眼里含着泪水,脸面绷紧,显出十二分的倔强来。他们这才明白,这少年刚才自尊心受到伤害,忙好言相劝拉他入席。然而戴维却说:“等到我有资格时再来入席。”返身便走。
就这样戴维开始发愤读书了,他给自己制订了自学计划,光语言一项就有7种。他还利用药房的条件开始研究化学。果然不到3年,药铺里的伙计谁也不敢小看戴维了。我们常说的才学、才学,世上有许多人是苦学的,然而缺才;但也有很多人非常有才,却就是不肯用在学问上,所以成为歪才、废才。而戴维本是有才之人,一朝浪子回头,把才能用在治学上,其能量是不可估的。当时,恰好贝多斯教授在布里斯托尔成立了一个气体疗养院,专用新发现的气体为人治病,而戴维也被邀请去那里工作。在这里戴维发现了一种“笑气”(一氧化二氮),人一吸入这种气体便会不自觉地兴奋发笑,因此更是名声大振,第二年升为教授。第三年,他还不满25岁便又当选为皇家学会的会员。
戴维本是一个钓鱼打鸟的顽童,浪子回头,发奋读书,十年工夫便取得了如此成就是难得的。他更知时间的可贵,条件难得,因此也就更加刻苦研究新的课题。在许多研究题目中他对伏打电池的电解作用非常感兴趣。他想用电解能将水分成氢、氧,那么其他物质也一定能分解出什么新元素来。当时化学实验最常用的物质就是苛性碱,不妨拿它试一试。戴维现在搞起科研来也还保留着少年时胆大豪爽的作风,他刚有这个想法便立即和他的助手、堂兄埃德蒙得把皇家学院里所有的电池都统统集中起来,其中包括24个大电池,光是那锌、铜制的正负电极板就有35厘米宽;还有100个中等电池,其电极板都有18厘米宽;另外还有150个小电池。这真是一支电池的大军,戴维决心要让那苛性碱在他的手下分出个清清楚楚。
这天戴维和他的堂兄起了个大早,开始了这场计划已久的试验。他们先将一块白色的苛性碱溶解成水溶液,然后再将那庞大电池组的两根导线插入溶液中,这时溶液立即沸腾发热。两条导线附近马上出现了气泡,冲出水面。开始他们还为这热闹的场面而高兴,但一会儿就发现上当了,发出的气泡是氢气和氧气,刚才被分解的只不过是水,而苛性碱却还是原封不动!这苛性碱真的就是一种元素而不能再分了吗?戴维的倔劲又上来了,他不信邪。水溶解不成,改用火攻。接着他将一块苛性碱放在白金勺里用高温酒精灯将它熔化,然后便立即用一根导线接在白金勺上,再将另一根导线插入熔化物中,果然电流通过了,在导线与苛性碱接触的地方出现了小小的火焰,颜色是淡淡的紫色,并且是从未见过的美丽颜色。戴维大叫:“埃德蒙得,快看,它出来了!”
“它在哪里?”
“就是这火,这淡紫色的火焰。”埃德蒙得也兴奋极了,他把鼻子凑近白金勺,仔细看着说:“但我们总不能把这火苗储存在瓶子里啊!”
那么,怎么收集这种物质呢?戴维又犯了愁,看来这是因为熔融物的温度太高,这东西又易燃,一分解出来就着火了。水溶不行,火熔也不是个好办法。
1807年11月19日,是英国皇家学会一年一度举行贝开尔报告会的日子,戴维满怀希望这次能拿一样新发现的元素去轰动一番。但是时间只剩个星期了,这奇性碱却软硬不吃,水火不成,他设计了很多种方案都不奏效。这些日子戴维就像只拧紧发条的钟,一刻也不停地摆动,他一会儿冲到楼上摆弄一下电池,一会儿冲到实验桌上,墨水飞溅地在记录簿上随便涂几行字。他到底不是书香门第出身,身上还留有那海边小镇上的野风与儿时的顽皮习气。实验再紧张也忘不了享乐,就像当年上学不误打鸟一样。每晚只要有舞会宴席,每场必到,只是忙得顾不上换衣服,从实验室里出来,在外面冉套一件干净外衣就去赴宴,回来后也不脱衣倒头就睡,第二天晚上去舞会时再套上一件。过几天猛然醒悟再一起脱掉。因此人们常说戴维教授常常胖几天,瘦几天,很叫人无法捉摸。他情绪极易冲动,冷静的时候不多,头脑极聪明,但又缺乏耐心,怕寂寞孤单,也爱慕虚荣,最顽强,又非常自信。对他这种风风火火的工作作风,助手们早已熟悉,而大家却极信任他的才气,因此总是每呼必应,实验室上下团结一致,倒也配合得非常默契。
戴维眼看报告会的日期就到,电解苛性碱还是水火攻不进。他焦虑地苦思苦干了十几天,比较了十几个方案。这天他忽然想出一个办法:何不把苛性碱稍稍打湿,令其刚好能导电却又不含剩余水份呢?这个点子一冒出来,他高兴地一拍大腿高喊一声:“成了!”倒把埃德蒙得吓了一跳,忙问:“什么成了。”
“不要多问,赶快拿碱块来。”
一个碱块儿放在一只大盘里端了上来。要让这东西轻轻打湿并不必动手加水。只须将它在空气中稍放片刻,它就会自动吸潮,表面成了湿糊糊的一层。这时戴维和他的一群助手围着这块白碱,下面垫上一块通电的白金片,等表面刚刚发暗变湿,就一声令下:“插上去!”不等话音落地,另一根导线便“咝”地一声穿入碱块。然后啪的一声,像炸了一个小爆竹一样,那导线附近的苛性碱便开始熔融,并且熔得越来越快。你想那小小碱块哪能经得起这数百个电池的电流的通过,一会便渗出滴滴眼泪,亮晶晶像水银珠,一滴一滴往下淌。有的刚一流出就啪的一声裂开,爆发出一阵美丽的淡紫色火焰,随即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有的“珠子”侥幸保存下来,却又很快失去了光泽,表面蒙上了一层白膜。
戴维看到这里突然离开了实验台,就地转了一个漂亮的舞步,如醉如狂地大跳起来,他边跳边拍着巴掌,嘴里念道:“真好,好极了!戴维,你胜利了,戴维,你真行啊。”他这样疯疯颠颠地在实验室里转了几个圈子,带倒了三角架,打落了烧杯、试管等,大约有五六分钟他才勉强使自己镇静下来,忙喊道:“拔掉,拔掉导线,埃德蒙得,不必要了,我们找到了,成功了!”
戴维确实成功了,他电解出来的那亮晶晶的珠子就是金属钾,接着他又用同样的方法电解出了金属钠。
作报告的日期到了。这些天来戴维已经疲劳到了极点,而且身上还时冷时热。但他怀着极兴奋的心情支撑着走上了讲台。讲演前,皇家学院的报告厅里早已水泄不通。那些上流社会的爵士、贵妇们其实根本不懂什么是科学,然而化学表演,就像魔术一般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这天,戴维不负众望,将自己这些日子辛苦制得的一小块金属钾泡在一个煤油瓶里,向人们介绍说:“这是三天前世界上刚发现的新元素。我给它起名叫锅灰素(英国人叫苛性钾是锅灰)。它是金属,然而性格却真怪,既柔软又暴烈,身体还特别轻,入水不沉,见火就着。”
戴维说着就用小刀伸进煤油瓶里轻轻一划就割下一块钾来,然后把它挑出来放进一个盛满水的玻璃盆里。这时钾块立即带着咝咝的呼啸声在水面上像着了魔似的乱窜,接着一声爆响,发出一团淡紫色的火焰,接着声音越来越小,体积越来越小,慢慢消失在水里,无影无踪……
世上哪有这样的金属?台下的人简直看呆了,大家都凝神屏息看着这种奇特的新元素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也许那玻璃盆里一会儿还会出现什么新东西,他们看到戴维伏首在桌上也不说话,头都抵住盆沿了,全场一片肃静。然而等了一会儿,盆里什么也没有,主讲人也不说话。突然有谁喊了一句:
“戴维先生怎么了?”
这下提醒了人们,前排几个人立即跳上台去,将戴维扶起。一碰他的双手,早冷得像冰一般,人们狂呼着:“快送医院!快送戴维去医院!”
送到医院以后,经过尽力抢救,才保住了生命,然而已元气大伤。因而没过几年,他就因身体欠佳被迫离开了皇家研究院。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