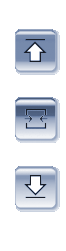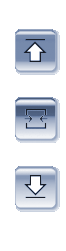| |
| |
|
发现青霉素
|
|
1928年夏季的一天,在伦敦大学圣玛丽医学院的实验室里,弗莱明像往常一样,从事着他的课题研究——机体中防御园子(特别是白细胞)抵抗葡萄球菌导致病因子的作用机理。为了研究葡萄球菌,他全身心地扑在实验室,常常工作到深夜,仔细观察这些细菌在培养过程中的变化,研究影响这些变化的条件。每次,当他打开培养皿的盖子,取出里面的细菌,放在玻璃片上,准备拿到显微镜下观察时,空气中飘浮的微生物——细菌或霉菌,常常“乘机”飘落到培养皿里。这些外来的微生物在培皿中繁殖,经常妨碍正常的实验,弗莱明很是讨厌这些“不速之客”。
这天,弗莱明正准备用显微镜观察从培养皿中取出的葡萄球菌时,突然发现了一个特殊现象:在原来长了很多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的培养皿里,长出了一种来自空气中的青绿色的霉菌菌落,并已开始繁殖。更令他惊奇的是,在这个青绿色霉菌菌落周围,原来培植的葡萄球菌菌落全被溶解了,而离得较远的葡萄球菌则完好无损。弗莱明立即意识到这个青绿色的霉菌可能分泌了一种能够裂解葡萄球茵的物质,而这种物质可能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自然抗菌物质。
弗莱明对这种青绿色的霉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对这个偶然发现的奇特现象作了详尽的记录,小心翼翼地把这些“不速之客”从培养皿中分离出来,培养在液体培养基中,让它们迅速繁殖。
弗莱明把这种青绿色的霉茵称作青霉菌,他从青霉菌“吞食”顽固的葡萄球菌这一事实出发,推断青霉菌分泌了一种极强的杀菌物质,正是这种可以扩散的物质,消灭了周围的葡萄球菌。通过实验,他作了值得注意的观察:当培养皿整个平面被葡萄球菌布满时,青霉菌周围仍旧没有任何细菌。这就说明:青霉菌阻止了细菌的蔓延,并且把它们加以消灭。
弗莱明想:如果能把青霉菌的分泌物提取出来,该多好啊!他马上动手进行实验。首先他把青霉菌接种到肉汤培养液中,让它旺盛地繁殖,然后,把长满青霉菌的液体小心谨慎地过滤出来,得到一小瓶澄清的滤液。弗莱明将这种滤液滴进长满葡萄球菌的培养皿里。几个小时以后,原来长势繁茂的葡萄球菌统统被杀死了。
弗莱明的发现和实验使实验室的同事们都很兴奋。弗莱明进一步进行实验研究,他利用了以前在研究溶菌酶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测定技术,将这种滤液用水稀释,重新做实验,鉴定了这种培养液对各种致病菌的抑制性状。结果表明:1∶1000浓度的培养液仍可抑制葡萄球菌的生长,而当时著名的消毒剂石炭酸在1∶30O的浓度时就失去了抑菌作用。弗莱明又取来凶恶异常的链球菌进行测试,结果1∶100的培养液就致它们于死地。弗莱明将这种抗菌物质命名为“青霉素”,因为产生这种物质的是青霉菌(后来经过鉴定,这个产生菌是特异青霉)。这就是青霉素的发现。
弗莱明是英国细菌学家,1881年8月6日出生于苏格兰基马尔诺克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他父亲经营一个小农场,但经营收入微薄,只够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7岁时,他父亲故世,从此弗莱明便跟同父异母的大哥一起生活。大哥非常喜爱天生伶俐,好学上进的弟弟。弗莱明每天徒步到4英里外的镇上乡村小学读书,后来考上了离家12英里的基马尔诺克的一所中学。
弗莱明自幼好学,酷爱大自然,注意观察种种自然现象,喜欢思索那些新鲜事物,常常向大人们提出五花八门的问题,弄得大人们也难以回答。有一次,他跟着母亲去探望一个住院的亲戚。看着病人那痛苦的情形,他问:
“您得的是什么病?怎么会得病?……”病人一问三不知。喜欢刨根问底的弗莱明,又去向医生打听,医生也无法明确答出病因,只得对好问的弗莱明说:“孩子,没有详细研究的病症还多着呢,哪能样样病都知道啊!”医生的话使弗莱明产生了学习医学,为人治病,解除病人痛苦的愿望。
13岁时,弗莱明的一个哥哥到伦敦当了开业医生,弗莱明和姐弟们一起都迁居到了伦敦。弗莱明进入伦敦综合技术学校,由于家境窘迫,只学习了很短一段时间,便被迫退学,到造船厂当学徒,1900年应征入伍,在伦敦苏格兰军团里服役。
服役结束后,弗莱明考取了伦敦大学圣玛丽医学院,并获得奖学金,他决心学医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牢记着少年时代与那位医生的对话,矢志于探究细菌致病的秘密。他以惊人的毅力,忘我的精神,刻苦钻研,深受导师赞赏,1908年获得医学士和理学士学位,同时获得伦敦大学的金质奖章。1909年,通过国家考试,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学会会员。
大学毕业后,弗莱明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并在该学院校长、著名细菌学家赖特领导下,致力于广泛的细菌学研究。虽然他和赖特的性格不同,但弗莱明总是谦虚地向导师学习,他们密切合作了40年之久。
弗莱明跟随赖特从事痘苗治疗和预防传染病的研究,他坚持实践赖特关于通过接种疫苗防止细菌传染的免疫学说。弗莱明在其早年的医学科学生涯中就十分注意血液的天然抑菌作用,并对防腐剂也进行了研究。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弗莱明以中尉军衔参加了英国皇家军医部队,在赖特上校的领导下,在布洛涅创伤研究实验室工作。当时,那些用于避免伤口感染的药物都不符合他的要求,虽然这些药物外用时能够使伤口消毒,但是当它一旦进入血管,很快就会破坏血细胞。因此,他希望能找到一种既能帮助身体产生防御作用,但又不会使身体受到损害的物质。他发表了《化学和生理抗菌剂在脓毒性创伤中的作用》等文。由于他成绩显著,到战争快结束时,已晋升为上校。
战后,弗莱明回到圣玛丽医学院,继续从事他的医学科学研究,放弃了到苏格兰行医的优厚待遇,全心致力于研究能杀死使伤口感染发生危险的病菌的药物。1922年,他在动物组织和分泌物中发现了一种能够溶菌的物质,他把这种淡黄色的、可溶解菌落的粘液命名为“溶菌酶”,写了题为《关于在组织和分泌液中发现一种值得注意的溶解成分》的论文。后来,在实验室里,他得到了这种溶菌酶的结晶体。因为溶菌酶在对某些革兰氏阳性菌的细胞壁具有特异性破坏作用,所以它在细菌细胞学的研究中,很有价值。然而,由于溶菌酶来源有限,而且对致病病菌没有抑制作用,所以尽管弗莱明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始终未能成为实际应用的药物。于是,弗莱明就暂时停止了这个研究课题。但是,在长期研究溶菌酶的过程中,弗莱明建立了一系列测定抑菌特性的技术。
接着,弗莱明开始全神贯注地研究另一种溶菌剂,这就是前面所描述的青霉素的发现。弗莱明终于找到了他长期以来寻找的物质。然而,这种具有强大杀菌能力的物质,会不会损伤人体和动物体呢?
弗莱明用小白兔做试验,当青霉素注射到小白兔的血管里时,小白兔不但没有死,也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症状。这说明青霉素对动物体没有损害,证明它具有医用价值。他在1929年发表的论文中说:“青霉素不干扰白血球的功能,对试验动物无毒,可能是一种适用于注射的杀菌剂。”
弗莱明脑海中又涌现出孩提时随母亲去看病人的情景,既然青霉素可以成功地杀死许多人体以外的病菌,能否用青霉素去治愈那些久病不愈,等待死亡的传染病人呢?如果能用它医治人类的顽疾,那该多好呀!
然而,提炼医用青霉素的过程很复杂,要经过青霉菌的培养、滤液的浓缩、提炼和烘干等一系列过程,靠弗莱明个人的力量是很难解决的。弗莱明邀请了一些生物化学家合作,打算把培养液中的青霉素提取出来供临床试用。但是这种化学物质极不稳定,在一般的溶媒中很快遭到破坏,所以他始终没有获得过青霉素的提取物,所有提取青霉素的试验都失败了。
不过,弗莱明具有科学预见和坚韧不拔的勇气、稳重的耐性,他深信总有一天会有人来继续研究青霉素。于是,他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耐心地、默默地将这个菌球一代一代的繁殖下去,一直进行了10多年。
1939年,弗莱明关于青毒素的论文引起了澳大利亚病理学家弗洛里的注意,他向弗莱明索取该菌作进一步的研究。弗洛里和当时侨居在英国的德国生物化学家钱恩,在另外几位科学家协同努力下,克服了在研制过程中的种种困难,终于在1941年,从青霉菌滤液中提炼出了青霉素的棕黄色粉末。经试验,把它稀释到二百万分之一,也足以杀死病菌,这种青霉素粉末的杀伤力是史无前例的。
1941年,青霉素第一次使用在被葡萄球菌传染的病人身上,获得成功。青霉素的显著疗效得到了医药界的承认。但是还有一个难题,就是青霉素的制造太麻烦,而且费用昂贵,为了治愈一个病人,必须制造和加工1000升霉菌溶液。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大批的受伤者急需治疗,在美国和英国,有38个研究小组加紧改进青霉素的制造方法,至战争后期,工业制药已获得成功,并首先在战场上发挥了巨大效用。
1942年,伦敦来电话向在牛津的弗洛里请求出让10克青霉素,弗洛里接到电话,不加思索就同意了,请求者就是弗莱明,他为了给一位重病的朋友治病需要这种昂贵的青霉素。接到青霉素后,弗莱明说:这一天是他生活中最幸福的一天。英国报纸《利刀》上曾写道:“青霉素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得不到它。”
1945年,弗莱明同弗洛里、钱恩一起荣获诺贝尔医学及生理学奖。弗莱明成为许多科学协会的名誉成员,18所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他以前工作的地方,现今叫赖特一弗莱明微生物研究所。
1955年3月11日亡故的弗莱明,生前最高兴的是亲眼看到了他发现的青霉素的工业制药所获得的成功。青霉素的发现及临床应用成功,开创了医疗科学的新纪元,被誉为“奇迹药物”,被看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堪与原子弹和雷达并驾齐驱的“武器”。
根治“瘴气”
1857年,罗纳德·罗斯出生在尼泊尔西北部的桠木兰,父亲曾是英国的将军,母亲是印度人。父母共生了10个孩子,罗斯是最大的一个。
当时,疟疾正在全世界肆意横行。全世界每年患疟疾的至少有3亿多人,而死于疟疾的就达300万人。在印度的情况尤为严重:在印度医院里的病人三分之一是疟疾患者,每年直接间接死于疟疾的达100万人以上。罗斯小时候居住的桠木兰,情况也不是很好。这儿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海拔5500米的群山中。每年一到夏季,便蚊蝇孳生,疟疾就流行开来。罗斯的母亲很怕他传染上疟疾,总是把他关在家里,不允许他上街去玩,但好动的小罗斯哪里肯听劝告,还是偷偷地到街上去玩。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吓唬地说:“街上瘴气正闹得凶,不听妈妈的话,你就会得病。”
小罗斯惊异地睁大眼睛,好奇地问:“妈妈,瘴气是什么东西?”母亲望着孩子说:“瘴气能使人得一种热症。早在公元5世纪,东方人就发现了这种病,叫它 ‘打摆子’,而欧洲人则叫它‘琴娇夫人症’。直到现在,医生还没有想出什么办法对付它。”
“那为什么叫琴娇夫人症?”小罗斯又问。
“琴娇是西班牙殖民地秘鲁总督的夫人。她跟着丈夫到秘鲁去,在那里染上了这种热症。眼看着就要死了,当地的土人便采来一种树皮,煎成汤让她喝下去。说也奇怪,她的病却一天一天地好起来。这种树皮就是我们常说的金鸡纳树的皮,是这种树皮救了她的命。从此以后,欧洲人就把这种热症叫作 ‘琴娇夫人症’。”
听了妈妈讲的故事,小罗斯的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妈妈,先给我吃点金鸡纳吧!这样,我就可以出去玩了。不然我会在家里闷坏的。”
“不行!好孩子,金鸡纳也管不了那么多的。”母亲连哄带骗地对孩子说,“我们这条街几乎家家都有人得了疟疾症,你要是染上了那可怎么办呢?”
没等母亲说完,罗斯小脑袋里又蹦出了几个问题:“难道疟疾是疟疾病人传染的吗?”
母亲被他问得张口结舌,答不上来。那么这种病到底是怎样传染开的呢?从此这些问题便总是在罗斯的脑海里索回着。
1861年,罗斯有8岁了,父母便把他送回英国读书。他在学校当住宿生,由于聪明勤奋,数学、物理和文学都学得很好。他总是念念不忘幼年时就产生的消灭疟疾的愿望,所以1874年从中学毕业后,他就进了圣巴塞罗缨医学院学医。大学毕业,他得到了皇家外科学会会员的执照,在轮船上当了一名外科医生,并经常在伦敦与纽约之间航行。几年以后参加了印度马德拉斯医疗服务团,来到了疟疾流行的印度。
早在1880年,法国医生拉夫伦就发现了疟疾微生物。罗斯很想通过自己的实验来验证拉夫伦的发现。他用各种办法弄来了身患疟疾的印度人的鲜血,并放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结果却没有找到什么东西。
“拉夫伦一定弄错了。可能根本没有什么疟疾菌!”罗斯得出了这种错误的结论。于是,他接连写了四篇论文,力图证明疟疾是由于肠功能紊乱而引起的。这就是罗斯研究疟疾的开端。应该说,这个开端并不“好”,但幸亏在后来,他很快就摸索到了正确的道路,终于取得了成功。
1894年,罗斯回英国度假,在伦敦,他遇见了热带医学的老前辈——一位相当有名的英国医生帕·曼森爵士。
罗斯原来并不相信有什么疟疾微生物,但曼森及时纠正了他的错误。曼森把罗斯带到他的诊所,拿出拉夫伦发现的疟疾微生物给他看。罗斯看见这种苍白的疟疾微生物身上存在着一种发黑的色素。他们把这些疟疾微生物放进人的血液里。他俩看到这些微生物在红血细胞里变成一队球状体,然后从血细胞里跑出来。
“如果在人的血管里,这时候人就要发冷了。”曼森向他说明。
罗斯对于疟疾原虫在血里具有如此神秘的活动感到极为惊异。他目不转睛地继续观察着:这些小球离开红血细胞之后,突然变成了新月形,然后又长出二条、三条、四条、……有时甚至是六条鞭子;这些鞭子抽打着、蜷曲着,就像章鱼的触角一样。
“罗斯,这就是疟疾微生物,在没有患疾病的人身上,你是决不会找到它的。让我伤脑筋的是:它是怎样从一个人身上传到另一个人身上去的呢?”
罗斯即将离开英国回印度去了。有一天,他和曼森在牛津路上散步。曼森向罗斯谈起了他的关于疟疾传播途径的设想,他说:“罗斯,你可知道我有一个理论,我认为蚊子会传播疟疾……”罗斯既没有表示赞同,也没有表示反对。那么蚊子到底是怎样传播疾病的呢?这位老医生,畅谈起他想入非非的设想:“蚊子吸疟疾病人的血,……血里含有的那些新月形的东西……它们因而进入蚊子的胃,并且长出那些鞭子……鞭子摆动,脱离新月形物体,进入蚊子身体……鞭子变得坚硬,像炭疽菌的芽胞……蚊子死子……它们落到水里……人又喝着死蚊子做的汤,于是就得了疟疾……”
曼森的想法是非常离奇的,但罗斯听得津津有味。他想:“如果能够证明蚊子真是传播疟疾的罪魁,那多好啊!找到罪魁祸首,疟疾就完全可以扫除掉了。”曼森接着说:“我老了,你还年轻。疟疾由蚊子传播,照这条思路研究下去,是完全可行的,你继续努力吧!”罗斯决心沿着曼森所发现的路线走下去。
1895年3月,罗斯离妻别子,乘船前往印度,来到锡康德拉巴德。这个地方非常的荒凉贫穷,夹在炎热的小湖之间。罗斯便在这里开始了研究蚊子的工作。
他像猫捉老鼠一样,到处去捕捉蚊虫。有一次,他在医院墙壁上看到有一个奇怪的蚊子。
这个蚊子与过去见到的都不一样。他蹑手蹑脚,一巴掌刚拍过去,蚊子飞了。他紧紧尾随追捕。蚊子却像跟他开玩笑似的,越飞越高,他跳起来拍,跳呀跳呀,累得他浑身是汗,终于捉住了这只蚊子。
“这个人真的疯了!”
别人的嘲笑,他好像根本没听见,他专心一意地捂着这只蚊子,兴高采烈地走进实验室里。划开它的肚子,在里面找到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寄生物,他看来看去,却发现与疟疾毫无关系。
“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不断实验和抛弃。”他正准备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研究工作的时候,却被调到班加罗尔去试图遏止霍乱的蔓延。直到1897年6月,他才回到锡康德拉巴德,到了贝贡佩特医院。他决心重新开始进行研究工作。他捉到了三只褐色的蚊子,让他们在蚊帐里吸疟疾病人的血,然后再去观察蚊子的胃。他切开了一只蚊子的胃,不存希望地开始观察蚊子的胃壁。胃壁那整齐的细胞,好像铺在路上的石块。他机械地俯视着显微镜筒,忽然间,有一种非常怪的东西直逼眼前,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是什么?在平铺的胃壁细胞间,出现了一个奇妙的环状体,直径约二千五百分之一英寸。又有一个!真是要命!天气太炎热,他观察不下去了……
第二天,他又继续解剖蚊子的胃。最后两只蚊子中的一只,四天前吸过疟疾病人的血,现在它的胃壁也存在同样的环状体,清晰得比胃细胞的轮廓更为明显,而在每一环状体上,都有一个小颗粒,其黑如墨。
这里又有一个这种奇形怪状的东西,咦,还有一个……”
他数了数,共有12个。天气太热了,他打了个呵欠。这环状体上的黑色素,很像他见过的人体血液中的疟疾微生物身上的黑色素。天气真热,罗斯直打呵欠。于是回家去睡了一会儿。
当他一觉醒来,忽然有所醒悟:“蚊子胃壁里的环状体——这些带黑色素的环状体,一定就是在生长中的疟疾寄生物。蚊子吸过病人的血液之后,我如果多等一段时间,再杀死它,那么时间越长,这些圆状体就应该长的越大……如果它们是活的,它们一定会长大!”
罗斯坐立不安起来,好容易等到第二天黎明。他切开最后一只蚊子,又看见胃里有许多曾看见过的环状体。
“一点不错!它们又在这里,一二三四……六……20个……它们满身是漆黑的点子,确凿无疑!唷,它们比昨天那只蚊子的环状体要大一些。它们真的在生长!它们一定是生长中的疟疾微生物!”他兴奋地自语着。
他即兴吟诗,满以为他的研究工作会赢得印度医疗服务团的支持和赞赏。但就在这关键时刻,他却接到印度医疗服务团的一封信,拆开一看,竟是一份调任书。上司叫他打起行李到印度北方去。那里蚊子数量不多,好容易捉到了几只,但又不肯叮人,天气冷得很,蚊子根本不活动。他无事可做,只能钓钓鳟鱼,治治生癣的病人。他在绝望中写信恳求远在英国的曼森帮忙。
曼森没有让他失望。不久罗斯就离开北方,南下到加尔各答,并到了一个条件很好的实验室里工作。
他登广告招请帮手。来了一群各式各样皮肤发黑的人,他挑选了两个。第一个名叫穆罕默德·布克斯。第二个叫浦尔布纳,这个人在第一次拿到工资以后,就溜之大吉了。
就这样,罗斯就和穆罕默德·布克斯开始着手工作了。他想在蚊子胃里再重新发现有黑点的环状体。穆罕默德·布克斯到处侦察,在加尔各答的阴沟、水管和散发着臭气的储水池中捉蚊子。他捉到的蚊子很多,有灰色的、褐色的、绿色而翅膀有圆形斑点的,各式各样。穆罕默德真是顶呱呱的能人,蚊子好像很喜欢他。罗斯丝毫没有办法让蚊子叮人,但是只要穆罕默德对他的蚊子低声念念有词,它们就肯为他叮人。他真是一位难得的助手。
有一天,罗斯忽然发现鸟也会生疟病,并且鸟的疟疾微生物很像人的疟疾微生物。他想:“为什么不能拿鸟来试试呢?”
于是他让穆罕默德·布克斯再去捕捉麻雀、云雀和乌鸦。他们把这些鸟关进笼子,放在床上,拉上蚊帐。穆罕默德睡在几张床铺之间的地板上,看守着这些鸟,以防止猫进来吃掉它们。
1898年的一天,罗斯来到实验室,把10只灰色蚊子放进关着3只云雀的笼子里,这些云雀正患疟疾,血里充满了疟疾微生物。这十只蚊子叮了云雀吸饱了血。3天之后,罗斯解剖了这些灰色蚊子的胃壁,发现鸟的疟疾病原,在蚊子的胃壁里生长着。
接着,罗斯又做了一次实验。他向穆罕默德要来3只麻雀,其中一只是完全健康的,血里没有疟疾微生物;第二只里也很少有疟疾微生物;第三只却病得厉害,它的血液里挤满了黑点的微生物。罗斯把这三只麻雀分放在三个笼子里,在每一只麻雀笼子里都放进一小群蚊子。
妙极了,蚊子纷纷飞向麻雀,吮吸麻雀的血,吸得饱饱的都飞不动了。这时,罗斯便将这些蚊子的胃解剖后,用显微镜进行观察,结果发现:那些吸过无病麻雀血液的蚊子,胃里没有那些带黑点子的环状体;叮过患病较轻的麻雀的蚊子,胃里有少量的环状体;而叮过重病麻雀的蚊子,胃里、食管里布满了带有漆黑的黑色素的环状体。
罗斯从早到晚都泡在实验室里。当他切开最后一组蚊子的胃时,他发现这些环状体在胃里膨胀,在生长,它们开始像戳出胃壁的疣突。
“这些疟疾微生物从蚊子的胃里又到哪里去呢?它们是怎样进到另一只未患疟疾的鸟的体内的呢?”罗斯又开始思考着这一问题。这一问题,在他脑海中萦绕,使他寝食难安。吃饭时想着这个问题,睡梦中还想着这个问题。
“还是到实验室去吧!让实验来回答。”他想。
六月的气温,使实验室里的温度达到摄氏37.7度以上。罗斯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一边老在想:“疟疾微生物,在蚊子胃壁里长成大疣的环状体到哪里去了呢?”
罗斯搬过显微镜,观察一只雌蚊的胃壁。这只蚊子吸过一只生疟疾的鸟的血已经7天了,他看见那个疣裂开了。从疣里跑出一大队古怪的纺锤形的线,向蚊子“螯针”的管子里进军。
“呀!疟疾微生物到了这里,是不是都这样呢?”汗滴在显微镜周围的桌面上,把桌面都打湿了一片。罗斯没有功夫去擦一擦汗,接着又解剖了许多个叮过生疟疾的鸟的雌蚊,想探明真相。结果,观察到的现象都一样;疟疾微生物由环状体长成疣,成熟破裂后,射出这些纺锤来,充满蚊子的全身,然后再进入蚊子的螯针。
“那么,疟疾的传播是由蚊子的叮咬引起的了!”罗斯低声说。他终于发现了传播疟疾病原的罪魁,弄清了蚊子传播疟疾的途径。
1898年6月25日。为了证实他的这一发现,他又做了一次实验。他让穆罕默德·布克斯拿来三只没有生病的麻雀。当天夜里,罗斯亲眼看着穆罕默德把叮过有病麻雀的一群雌蚊,关进了无病麻雀的笼子里……一夜又一夜,罗斯守在旁边,就像等待头胎孩子出生消息的父亲那样,坐立不安。他咬着嘴唇,流着汗。他看着这些“魔鬼”叮着健康的麻雀,嘴里还不停地咒骂着。由于咒骂太用力,汗便出得更多了。
几天以后,三只本来无病的麻雀得了病,全身充满了疟疾病原。
罗斯兴奋极了。他写信把这件事告诉了曼森,告诉了在巴黎的疟疾微生物的发现者拉夫伦。他写了论文寄给一家科学杂志社和两家医学期刊。他在加尔各答逢人就谈起这个发现。这时候,他好像是一个孩子第一次扎了一只风筝,并且看见这只风筝已经起飞了,兴奋得不能自抑。
由于高度兴奋加上长期的劳累,他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而病倒了。
盛大的医学大会正在爱丁堡举行。曼森赶到爱丁堡,向到会的医生讲述了罗斯的发现,医生们听得个个目瞪口呆。于是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以大会的名义祝贺罗斯的这一伟大的划时代的发现。大会相信:这个研究结果对鸟是肯定的,那么对人也决不会例外。
不久,英国利物浦大学给罗斯颁发了聘书,聘请罗斯去当教授。罗斯接受了聘请,离开了印度医疗服务团,乘船西行。当航船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靠岸时,他听说西非疟疾猖撅,便改变了主意,率领一个探险队深入西非,继续研究蚊子传播疟疾的问题。他们在那里爬山涉水,风餐露宿,奔波了三个月,终于在按蚊 (又称疟蚊)的肠胃道中发现了人类疟疾原虫的卵囊,证实了人类的疟疾是由疟蚊传播的。并且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就是:只要扑灭疟蚊,就可预防疟疾的传播。
他的成就得到了世人的赞誉。他被封为巴斯勋位的上等爵士、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勋位的上等爵士。他的著作《疟疾预防》被翻译成许多国的文字。终于在1902年冬,他荣获诺贝尔奖金。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