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怀念的清纯
作者:关 峰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初恋》是周作人《夏夜梦》中的一篇,最初面世于“副刊的开山祖师”①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镌》(1922年9月1日)上。五四时期,周作人曾自述有三个恋人,除乾荣子外,杨三姑娘、郦姊(《娱园》)都有专文记述。
《初恋》可分两部分来理解,即杭州和家里。杭州部分约占全文的五分之四,与“家里”相比,充斥着争斗、专制和憎恨。祖父周福清(介孚公)因科场案,其时正关押在杭州府的司狱司里。作为文明社会的惩罚方式,监狱“首先是由于它采用了‘剥夺自由’的简单形式”②,而每隔三四天须去牢狱陪侍祖父的周作人不自觉地形成了对于监禁与专制进行反抗的心理。平素容易发怒和咒骂的祖父此时却出人意料地表现些和悦气象,一定程度上使周作人坚定了同情和维护祖父的决心,直到南京求学时期,周作人仍然显现出对于专制的强烈愤恨和谴责。不过,祖父既是专制制度的牺牲品,却也成了旧道德的共谋者,其妾宋姨太太(即潘姨太太、大凤)就是受害者。她比祖父小32岁,与祖父的小女儿同龄,不正常的婚姻养成了她乖戾、狠毒的性格,及至介孚公死去,也便同了本地的“破脚骨”姜阿九远走他乡,不知所终。
宋姨太太与姚宅老妇、石家媳妇的关系揭示了市井邻里间的龃龉与碎屑。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她们或协作,或敌视,把社会加于自身的重压从新分配。本来社会的不公应该激起更猛烈的反抗,大家联合起来,共同面对与筹画,而现实却异常残酷,宋姨太太和姚宅老妇“感情很坏,彼此都不交口”。姚家夫妇老来无儿无女,很是不幸,难免多疑,自然面对社会流俗多有敏感,不过,他们认杨三姑娘为干女儿,又显见防老的隐忧,不得不向社会敷衍和靠拢,与同是旧制度产物的妾媵似乎容易走近,却也难免维护脆弱的心,以嘲笑、挑剔、苛刻相向,而后者也许更占上风。此外,姚家老妇与宋姨太太毕竟年龄悬殊,加上宋姨太太妾的身份所形成的性格特征,即使是间壁,难保不被刺探了隐私去。不难理解,与姚家老妇关系实在不易处好。对羊肉店石家媳妇来说,她的年龄与宋姨太太相当,虽是远邻,又是再醮而其夫尚在的“活切头”,难得的是,他们做了羊肉生意,有着官能享受的天然优越性,足以赢得宋姨太太的好感。仆人阮升(即阮标、阮元甫或元夫)系宋姨太太所用,不过与周作人共用板桌,倒也能够想见其间关系的融洽,如同鲁迅悼念女仆长妈妈时的深情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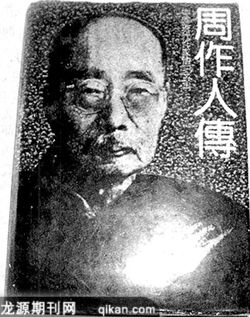
《初恋》的写作借鉴了希腊作家蔼夫达利阿谛思的小说《初恋》。辛亥归国后,周作人即在家乡译介了蔼氏《老泰诺思》《秘密之爱》《同命》等三篇小说,《初恋》沿袭了蔼氏小说一贯的“爱”的主题,写了少年男女无言的“秋波之恋”,小说在男女主人公的离散中结束。周作人《初恋》的结构也与蔼氏的基本相同,只是突出了“性”在少男少女内心中的体验。对此,周作人颇有感触,南京读书时的日记中已流露出对郦姊的思念。北京应试期间,丫鬟淫邪的戏台表演产生了挥之不去的激刺和教训,初至东瀛看见女孩子(即乾荣子)赤脚在地上来回走动的情形甚至成为他终生难忘的震撼。五四时期,周作人大胆地翻译了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替女人说话,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广泛的讨论。《初恋》里的杨三姑娘外貌算不得美丽,“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却能够调动起正处于青春期的“我”的全部情感:纯洁的情意和心灵的感动。三姑娘脱凡超俗,可以不顾及大人们的是非恩怨,搭讪宋姨太太后随即走来,看“我”映写陆润庠的字帖。与大人们的势利、刻薄、浮华的“毡裘气”相反,三姑娘的行为更显出人间真情,尤其是她怀抱着猫的样子更使人怜爱。与鲁迅不同,猫很为周作人所青睐。《初恋》发表后十年,周作人仍累日念念不忘以猫为题的文章,最终于1937年初写就,副题为“猫与巫术”,实际上赓续了此前周作人“古野蛮”思想的批判,其实,杨三姑娘就是“野蛮”祭坛上的牺牲,甚于宋姨太太。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女人与猫一样有九条命,生命力非常强盛,面对重荷,杨三姑娘俨然微拂的春风,融出条条雪道,如仙女般立于凡尘,温馨而优雅,烤暖了处于困苦与冷眼中的人心,难怪周作人不惜使用了两个“第一”热烈地剖陈衷肠:“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的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了。”
没有一见钟情的轰轰烈烈,也没有父母之命的心绪不宁,彼此多是心与心的贴近,“始终没有想到男女夫妇的问题”,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功利贪图,却多了无穷的力量和辽远的回响。性的生活可以是两性生理的渴求与震颤,也可以是别无旁逸的情感的专一与迷悦,传达着彼此的真性,唤出彼此心底的快乐。同时,自我充溢了倔强的力量与痴绝的情愫,甚至挣扎和疯癫,“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并不问她是否爱我,或者也还不知道自己是爱着她,总之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这样神秘而圣洁的个人情感与体验,毫不顾虑得失,也不希图所谓回报,纯粹一片名副其实的托尔斯泰似的“无我爱”。
第二部分与第一部分在时间、空间上都有了间断。空间上从杭州转到了绍兴,一洗杭州时的争斗、专制和憎恨,幸福、平等的空气弥漫开来。母亲的病由我在杭州而起,一旦回到家里,她的病也就祛除了,查1898年5月17日的日记,“下午至西郭门育婴堂门口上岸,唤小舟至大云桥上岸。至家,祖母、母亲均各安健,三四弟亦安,不禁欢然。”③然而,由于“我”的离去,杭州越发成为了“人间地狱”,杨三姑娘终因霍乱死去。周作人曾写有《霉菌与疯子》一文,指出中国人并不惧怕霉菌,甚至还可生出友谊,切实奉行优待疯子主义,“他随时可以杀人,也随时可以与叭儿狗对坐谈心。”杨三姑娘即使侥幸长大成人,那种情感的力量也总会被丑恶的社会加以利用,如宋姨太太所说,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
蔼夫达利阿谛思的《初恋》把时间编进了主人公哀伤的初恋之中。周作人同样注意到了时间间断的力量,文本构设的一月的间隔,幻化出沧海桑田的境界,杭州重又回复到了争斗、专制和憎恨的境地。多年后,周作人还将杭州与南京并列,表示“总没有什么感情”,恐怕与此大有关系罢。
文章最后一段来得较为奇特。“不快”是可以理解的,但“安静”如何解释呢?首先,此时传来杨三姑娘的死讯,原来心中搭救的负担终于卸却,未尝不会感到轻松。其次,周作人五四落潮期的作品总有一种冷隽、内敛的格调,仿佛情感淡漠的旁观者,如《前门遇马队记》《西山小品》《碰伤》等,冷反衬着热,源于自然主义的描写背后矗立起跳动的心的写实,如鲁迅对于五十自寿诗的评价所言。
《初恋》以“现在的我”为视角,时间的阻隔加深了对于往昔真情的眷顾与怅然,死者长已,而生者不能不有所挣扎,忆念本身即表明现在生活和情感的困惫。初恋是美好的,美在纯洁而至情,但初恋又是悲哀的,哀在一旦失去,不可复得。
五四后思想解放潮流蔚成大观,不过却很多为情而情的单薄之作,而《初恋》却是用心之作,甚至成为一种范式,废名等作家就曾有同题《初恋》呈现出相近的旨趣。
作者系复旦大学博士后,现任教于长安大学
(责任编辑:赵红玉)
①周作人:《〈晨报〉副刊与孙伏园》,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八十心情》,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552页。
②[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第2版,第260页。
① 周作人:《周作人日记》(上),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