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2007年女作家长篇小说新作短评
作者:白 烨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怀旧是表象 寻根是内里
2007年上半年间,两位著名女作家分别拿出了自己的长篇新作,这就是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和池莉的《所以》。两部作品虽然故事与人物迥不相同,但却有一个相似相近之处,那就是在重温过往历史的大背景中,回溯个人的成长史。个体与个人,在这些年是越来越凸显出来了,这使人们常常遗忘了与此相关的一些勾连,比如家境、出身、遗传、社会、时代,等等;两位女作家好像是在向人们证明个人并非是孤立的和自在的“个人”一样,由她们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的不顺遂的成长,不适意的经历,推本溯源地书写并揭示个人命运背后的历史隐秘。
王安忆《启蒙时代》中的上海中学生南昌,虽然出身于军人家庭,本人又积极向上,但遇到“文革”这样的政治旋涡,仍然找不到应有的出路;率先“造反”当了红卫兵,信服“血统论”,却因为父亲的历史错误,无辜受到牵连,从“中心”退居“边缘”;他又试图通过到北京找关系,重振旗鼓,却又被打成了“联动”分子。种种努力无望又无果之后,他便只好与同病相怜的年轻伙伴一起,在圈子化的交往中打发时光,至多通过阅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来在理论的想像之中接近“革命”,认识“革命”。大时代中的小圈子,大革命中的边缘人,使得这部作品以独特的视角切入了“文革”历史,并写出了这个时代所孕育出的革命激情加小资情调的一群男女青年的苦闷青春。《启蒙时代》究竟得到了什么样的启蒙?这其实很难一言以蔽之。但可以肯定的是,《启蒙时代》不仅精雕细刻地写出了“老三届”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史,而且大含细入地描画出了上海在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混合型的都市气质。
池莉的《所以》中的女孩叶紫“我”,也正如一片风中的叶子一样,飘浮在理想与现实不断错位的矛盾纠葛构成的风浪之中。因为从小并不驯顺,常常受到母亲的无情呵斥,耳朵更是“常遭涂炭”;好不容易长大了,考上了武汉大学,孰料又被分到县城文化馆;爱上了从事导演职业的华林,却因他已婚和风流弄得声名狼藉,终于如愿以偿地与离婚后的华林结婚并先后有了两个孩子,却发现华林暗中经由网恋,早已与别的年轻女人勾搭在一起。“我”以为是“好”的,却一直得不到;“我”以为是“对”的,结果却错了。这使“我”不但对自己困惑了,也对所面对的世界疑惑了,从而在心里不断自问:“是这世界变得奇怪了,还是自己一直都是一个小孩?”因为错误,所以成熟;因为困惑,所以诘问。有意味的是,池莉笔下的叶紫虽为一位普通女性,但却在坎坷与困惑之中,始终努力维护着自己应有的尊严与个性,在与社会、家庭,与亲情、爱情,与亲人、男人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不停地寻找和肯定自己的存在价值。“我”错故“我”思,“我”思故“我”在,这使人们不能不对叶紫这个寻常女性肃然起敬。
怀旧是表象,寻根是内里。两位女作家通过各自主人公成长过程的细节追溯,揭示了个人命运的非个人因素,也撕扯出从家庭到环境、从时代到社会的根根须须。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妨把他们的两部作品《启蒙时代》和《所以》,看作是个人角度和传记写法的社会生活史。
关注底层民众直面底层生存
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通过歇马山庄一个名叫吉宽的农民进城之后的遭际与困惑,描写了当下的农民工实在的生活情景与精神状态。吉宽在城市里,一改在歇马山庄乡下时的懒汉的秉性与旧习,到处打工,自食其力,但都始终没有能够走出生存的困境来。而因为身份的改变,空间的转换,先前的许多人际关系重又受到了检验、考验,乃至拷问。比如,他早年与许妹娜始于月夜马车的浪漫情爱,是否属于彼此倾心的真爱?他与几个兄嫂之间的亲情总在不断变化,个中是否越来越多地混入了生意与交易的成分?作品经由吉宽这样一个独特人物的独特故事,实际上既实现了“公审”,又实现了“自审”。这“公审”,便是就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审问社会,审视现实,审议公理;这“自审”,便是在城乡交叉地带构成的尴尬境地,自省自己得到了什么,又丢失了什么;自问自己置身何处,又去往何方?作为现代都市森林里的“一片落叶”,吉宽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做了“时代的垃圾”,这种自审与自省的精神,相当的难能可贵,这也使得吉宽这个农民工人物形象,不仅卓有了个性,而且富有了灵魂。
强劲登场精彩亮相
70年代女作家无论是看取生活的着重点,还是叙说故事的表现力,与前几代作家都有明显的不同,她们普遍摈弃宏大叙事,更为注重由情态到心态的细枝末节,在心灵的丰富性与艺术的可能性上。2007年间,映入人们眼帘并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即有盛可以的《道德颂》、戴来的《鱼说》、鲁敏的《逝者的恩泽》等。
从“道德颂”的书名望文生义,人们会以为盛可以的《道德颂》是颂扬道德的,其实这是个反讽的修辞手法。从作品女主人公旨邑“婚外恋如何被婚姻所腐蚀”的感喟里,人们能够觉出这部作品的不同寻常。事实上,这部在传统眼光看来是写女主人公旨邑陷入不怎么道德的婚外恋泥淖的小说,通过女主人公旨邑的始终如一的追求和推心置腹的省思,反而向当下的婚恋现状发出了严肃的诘问:到底谁更道德?我们的道德到底怎么了?故事卓具张力,人物颇见内力,使得这部作品成为当下长篇写作中,切入现状有力度,揣摩人性见深度的情爱力作。《道德颂》的叙事口吻带着作者一贯的言近旨远和意在言外,机警的比喻与莞尔的自嘲搀杂在一起,以浑然一体的方式顺流而下。一个没有多少悬念的故事,就这样被作者经营得有声有色,细腻的心理描写与跌宕的情节设计将它扩撑得血肉饱满,令人由动容到动情,跟着一起反思和反省。
值得关注的“80后”之作
在这一年里,她们中的不少人都以自己全新的力作,表现出了一定的转型或相当的进步。如充满感恩意识的七堇年的《大地之灯》,状写飞扬的青春何以平添苦闷又彼此不同的鲍尔金娜的《紫茗红菱》,都以题材与题旨等方面的厚度扩伸与力度增强,大大地超越了青春文学的已有范式,显示着“80后”一代伴随着人生成长的艺术上的成长。
《大地之灯》的作者七堇年,是个只有19岁的在校女生,但这个少女作者却显示出了超乎她的年龄与阅历的成熟与老到。作品在一个名叫简生的男孩的成长故事中,涵盖了相当丰厚的人生内容,个中既涉及父辈的上山下乡经历,父母在特殊境况下的爱恋及其无奈弃子;又涉及破碎家庭的孩子的孤独无助及其与单亲母亲的矛盾与恩怨,还涉及一个无助的学生、孤独的男生对可亲又可信的女老师的忘年依恋。而作品的动人之处,还在于一直遭遇不幸的简生,在历经了种种磨难长大成人之后,满含着一颗爱心和善心,即原宥了出事遭罪的母亲,又收养了无奈逃婚的藏族少女,还在自己挚爱的女老师的弥留之际毅然舍弃一切陪她度过了最后的余生。感恩的精神在这里放射出了奇异的光彩,也给人一种意外的感动。
《紫茗红菱》的作者鲍尔金娜,是北京服装学院的在校学生,作品通过紫茗和红菱这一对校园姐妹花彼此有别的个性与遭际,书写了从青少年时代就岔开了的迥不相同的人生故事。作品在直面学校与家庭存在的问题中,揭示了学生生活的生态现状,批判了羁绊着学生健康成长的诸种社会性因素。作者的语言,有一些鲜活,又有一些不屑,读来硬朗、犀利、痛快,这种少有学生腔和文学腔的文字,在青春文学中委实并不多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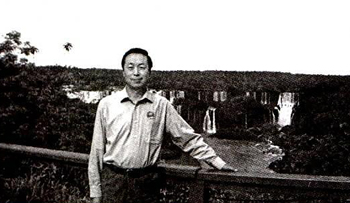
白烨,陕西黄陵人。毕业于陕西师大中文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室主任、总编辑助理;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学术专长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当代文学的理论批评和作家作品评论方面,撰著了300多万字的理论批评文章,出版了7部文学理论评论著作;另主持或主编有“文坛纪事”、“文论选”、“文情报告”等多种文学选本和文学现状概观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