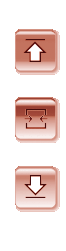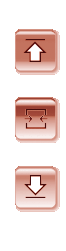|
|
|
|
58
|
冯永祥在徐公馆教林宛芝京剧的辰光,潘信诚带他的爱子潘宏福已经巡视完在浦东的各个企业,踽踽地来到了黄浦江的东岸,有一只小汽艇在岸边等着。
码头上两边的树木的叶子早已落尽,光秃秃露着枝枒,在寒冷的北风中抖嗦,像是赤身裸体的老人,浑身的筋骨看得清清楚楚。潘信诚望着那些树木,感慨万端地对儿子说:
“你瞧,这些树木长大了,老了,完了!”
潘宏福会意地叹息了一声。
父子两人跳上小汽艇,马达嘟嘟地响了,汽艇离岸了。潘信诚站在操作台上,眯起老花的眼睛,不舍地望着冬天的原野。潘家在浦东的企业,大半靠近码头,汽艇一离岸,那一排排锯齿形的厂房,那一座座红色的高大的仓库,那一团团从高耸云际的烟囱里冒出的浓烟,都一一呈现在他的眼前。浦东,他来过不知道多少次了。这些企业,他看过不知道多少回了。但都没有今天这么可爱,简直比冬天的阳光还可爱啊!
黄浊浊的江水给汽艇划开,卷起两股浪花,在两边船舷飞驶而去,那雪白的浪花仿佛是千万粒珍珠突然从水里跳出来,一眨眼的工夫,便消逝在奔腾的黄浊浊的江流去了。
潘信诚望站滚滚的江流,往事像澎湃的江涛一样,涌到心头。他二十七岁那年从英国留学回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帝国主义还来不及向中国市场伸手,中国民族工业有了发展机会。他跟父亲办厂,从三万多纱锭发展到十万五千锭子,接着又扩展了印染部分,成立了印染厂。事业一天天发达,觉得添制锭子老是仰仗外国,发展起来总有限制。自己动手创办了通达纺织机械厂。先是专门给通达制造锭子,后来也接外边的定货。通达的纱锭发展到十七万光景,父亲就死了。潘信诚的兴趣转到毛纺。他认为英国毛纺在世界上占第一把交椅,他在英国,参观过两个厂,也学了点毛纺的知识。他想到中国西北部的羊毛并不推板,发展起来,中国的呢制业在国际上也可以有个地位。厂办起来了,销路并不好,弄得高不成低不就,有钱的人要穿外国的毛织品,不要通达的;没钱的人买不起,想要,也穿不上。他想到麻织品比较大众化一点,用途也广。就在杭州开了一爿通达麻织厂。一九四八年上半年,本想在杭州再开一爿丝织厂,用他的话来讲,就是棉毛丝绸样样都有,不管你是穷人富人,只要穿衣服,总要照顾通达。另外,他对面粉业和粮食业也有兴趣。上海有名的庆丰面粉厂就是他一手创办的。他还创办了永丰碾米厂,规模不十分大。他对粮食加工方面兴趣不大,有兴趣是把粮食买进卖出,这生意十拿九稳赚钱,以往的经验,行情总是看涨的。大米是南方的主食品,而面粉是北方的主食品,只要张开嘴吃饭,不照顾庆丰,就得照顾永丰。穿衣吃饭是人生两件大事,办这种实业,没有风险,利润也厚,并且还可以替国家争口气。如全国几亿人口当中有一半人吃饭穿衣都照顾潘家,那潘信诚便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富翁,而且还可以和各国大资本家较量较量,说不定通达的货色在国际市场上还可以插一脚,那前途就更加远大而又灿烂了。这个美丽的梦想像黄浦江的水一样流去了。
潘宏福站在父亲旁边,见他沉思不语,自己也不好啧声,他想起父亲那天在马慕韩家里忽然那么积极,不仅赞成全市合营,而且要抢在天津和广州工商界的前头,叫他莫名其妙。他老想问父亲,可是没有适当的机会。现在正是一个好机会,船上没有外人,他大胆地问道:
“上海为啥要这样快全市合营?”
“北京全市合营了,上海能够不全市合营吗?”
“迟一点不行吗?”
“不行。”潘信诚摇摇头,声音突然低了下来,向汽艇四面看看,没有人,他便用英文对儿子说:
“好比下棋,和共产党下棋下输了,只好做输的打算。现在是计划经济。我们要服从国家经济领导。原料,国家控制了。市场,国家管理了。私营企业生产也好,经营也好,单独维持很困难,只有依靠国家。公私合营企业,有了公家一份,生意好,生产也好,利润也不错,不走合营还走啥路子?”
“这个我了解。”儿子也用英文回答。
“乡下分了地主的田,农民当家了。经过雷厉风行的镇压,国民党的势力基本肃清了。美国力量虽然强大,可是在朝鲜给共产党打败了。‘五反’以后,资产阶级搞臭了,孤单了。现在工人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吃不开了。我们的处境,好比上了这条船。”潘信诚指着破浪前进的小汽艇,无可奈何地说,“船已经到了江心中,后悔已经晚了,不跟着走,难道要跳水不成?共产党网开一面,给私营企业安排了一条出路,只好跟着走,就是你们常说的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人家把我们的财产共走,心里怎么会愉快?从你爷爷手里创办了这份家当,我数十年经之营之,好不容易才有今天的规模,现在可好,全付诸东流!”
潘信诚的手指着哗哗流去的江水,儿子这才听到父亲的心声,但越发迷糊了,不解地问:
“你在马慕韩家,为啥主张上海要赶在天津和广州工商界的前头呢?”
“傻孩子!”潘信诚想起那天确是讲了这句话,他轻轻叹了一口气,说,“凡是共产党要办的事,只有拥护,不能反对。古人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大家都要走这一条路,我们怎么能够不走呢?人家走十步,我们就要走十一步,不然,人家要说我们落后哩!”
“哦!”潘宏福懂了,他说,“到社会主义,大家都好哇。”
潘信诚瞪了儿子一眼。
“用不着你来给我上政治课。我一辈子好不容易办的这些企业,原本是为儿孙做马牛,给你们谋幸福,我自己并不需要。现在要过渡到社会主义,把财产交给国家,交给社会主义社会了。”
“合营以后不是还有定息吗?”
“现在政府还没有公布,我看拿不了几年,就啥也没有了。”潘信诚回过头来,一眼看见一只小轮船搁浅在沙滩上,船身半歪着,船底有一半露在外边,烟囱像是躺在江面上的一个大油桶。这船是通达纺织公司的,年久失修,早已报废了。十多年来就搁浅在潘家厂子后面的沙滩上,再也没人过问。今天却引起潘信诚的注意,他自言自语地说,“哎,想当年这船在黄浦江上开来开去,多么活跃,多么神气,谁看到这条船不羡慕啊。可是现在呀:搁浅了,开不动了,完蛋了,在黄浦江上再也看不见它了!”
“爹,你过去不是说过这船已经使用的够本了,再修的话,还不如买一条新的便宜。”
“是呀!”
“这些旧东西别去想它吧!”
“旧东西也是钱买的呀!”
潘宏福不好再往下说,他放眼看着黄浦江蜿蜒而去,江上尽是中国船只,没有一只外国兵舰。屹立在江边的海关大楼,现在完全由中国人管理,没有一个洋人骑在中国人头上指挥。曾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英国汇丰银行,现在已是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大楼了,只留下一对铜狮子在守着大门。
他兴奋地指着江面一只中国大轮船说:
“爹,你看,这条船是上海新造的,我们现在也可以造万吨大轮船哩!”
潘信诚的眼光转到江中心那条出厂不久的万吨大轮船上,心头忍不住涌上喜悦的情绪,嘻着嘴说:
“共产党建设也有一套,这么大的轮船,中国从来没有造过。在黄浦江上也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中国船!”
“过去在江上停泊的都是外国兵舰!”
“对,”潘信诚陷入沉思里,租界时期的景象一幅又一幅在他眼前闪过,他站在操纵台上,手紧紧握着铁的栏杆傲视江面岸上的情景,觉得连呼吸也比从前舒服,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微笑地说:
“他们欺负中国一百多年,使得老大的中国抬不起头来。那时,他们在上海滩上可真威风,简直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只要工务局讲句话,就是法律。租界上啥事体都要听外国人的。虽说有华董,也是和外国人一鼻孔出气。办厂也得看外国人的脸色,有的人干脆用外国人的名义办厂。可怜偌大中国一点民族工业也叫洋商排挤得喘不过气来,倒闭的倒闭,并吞的并吞,就是勉强生存下来,也不过是苟延残喘,日本鬼子一来,干脆没收,通达的企业差点给弄得精光。幸亏抗战胜利了,走了点门路,这些企业才陆陆续续收回来,国民党不争气,贪污腐败,通货膨胀,失去人心,断送了江山……”
潘信诚说到这里,不禁黯然,望着流水,说不下去了。儿子接上去说:
“共产党一来,把帝国主义的势力全给赶走啦。
潘信诚点点头,从黯淡的心情中昂扬起来,眉宇间露出兴奋的神情说:
“共产党使中国人抬起头来了,不但中国的事体,外国人不能插手,连国际上的事体也要听听中国的意见哩!”
“那当然啦,国际上的事体,不得到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同意,老实说,就办不通!”
“现在作一个中国人比过去有意思多了,从前,我在英国留学,因为考试的成绩好,人家都拿我当日本人,和我很亲热。后来了解我是中国人,就不大和我来往了,有人还给我脸色看。你们很幸福,今后再也不会受那种欺负了。”潘信诚这时感到新中国的可爱了。他想起史步云曾经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到处受到外国人的热烈的欢迎,史步云回来对他说,到了国外,才真正了解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和崇高的威望。他希望有机会到国外看看。最好再到英国去一趟,看看前后不同的变化。政府方面也曾征求他的意见,要他参加代表团出去走走,就是因为身体不好,一直没有出去。现在这个愿望又在他的心头涌现了。
“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的时代永远过去了,我们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们别再想动我们一根毫毛!”
“过渡到社会主义?”潘信诚回过头去,眼光又落在通达的厂房上了。
潘宏福没有留心爹的眼光。他的眼睛出神地望着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大楼上的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润湿的海风中飘扬。他扬起眉毛说:
“是呀,过渡到社会主义,有计划地发展农业工业和科学文化,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书念,国家富强了,谁敢再欺负中国?”
潘信诚意味深长地说:
“但愿如此!”
说话之间,那只小汽艇慢慢靠拢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大楼前面的码头,潘宏福发现爹的面孔还对着江对面的厂房。他轻轻说道:
“到了,上岸吧。”
潘信诚慢慢转过头去,看见码头,看见从十六铺开来的有轨电车向南京路疾驶而去,看见宽阔的柏油路上熙来攘往的人群,看见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大楼和沿着外滩马路一排排矗立云霄的高大建筑群,对岸的厂房显得十分矮小,几乎看不大清楚了,他点点头说:
“上岸?就上岸吧!”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