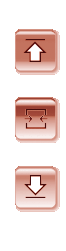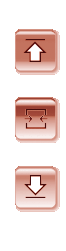|
|
|
|
40
|
韩云程回到家里,很早就上床睡觉了。他虽然躺在床上,可是一点睡意也没有,思索余静意味深长的话:“等你研究完了,我们聊聊。”平常余静找他谈话,总是事先约好,这次突然而来,显然知道他的问题了。他明天一早到厂里去,应该亲自向余静交代,不能再犹豫了。余静要和他聊聊,在民主改革的运动中,不是聊他那个问题,还聊啥问题呢?他不把这个包袱放下,怎能安心工作?也不能安心休息,连走路仿佛也很吃力,在人们面前更抬不起头来,总感到有人在他背后指手划脚,议短论长。
他下了决心,明天向余静交代自己的问题。
他闭上眼睛,准备好好休息一下,明天谈话有精神。可是清清楚楚听到太阳穴那里跳动,他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更没法入睡。沪江纱厂“五反”工作检查总结大会那一幕在他眼前出现了。他代表职员,在会上发言。他说:“我很惭愧,归队以后,得到大家的信任,我一定要好好工作,来报答党和工会。我代表全体职员表示:一定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在工会的领导下,做好工作,搞好生产。”这一段像是誓词的话,经常在他的脑海里翻腾。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誓词,而且是代表全厂职员的誓词。他受到党和工会的信任,在厂里,荣誉的事体都有他一份。大家都羡慕他,有技术,有本事,“五反”以后又比过去进步,厂里的生产离不了他。他如果把自己的问题交代出去,人们知道了,都会奇怪地问:韩工程师原来是这样的人呀!他的面子搁在啥地方去?他怎么有脸见人?他能在试验室里工作下去吗?党和工会以后再也不会信任他了。他受不了百口嘲谤,也忍不下万目睚眦。他这一生全完了!他不能交代。不能,绝对不能!他宁可背着包袱到棺材里去,也不能丢掉这个面子。
他身上感到沉重,好像给啥东西压着,连翻个身也很吃力。他心里很烦躁,老是要翻身,辗转反侧,宁静不下来。他怀疑地问自己:“真的背着包袱到棺材里去吗?”今后的工作怎么做呢?今后的日子又怎么过呢?他寻找不到一个正确的答案。他后悔在一九四六年一月跨错了一步。如果不走那一步,做个无党无派的工程师,现在多么轻松啊!他不能把时间拨倒过来,也没法把七年前的历史一笔抹掉。他无可挽回地陷在罪恶的泥坑里,不能自拔。
他睡不着,干脆睁开眼睛,向窗口一望:天已经蒙蒙亮了。一眨眼的工夫,蔷薇色的曙光照着窗户,房间里的陈设逐渐看清楚了。他接连打了两个哈欠,霍地跳下床来,匆匆洗了一个脸,便到厂里去了。
像往常一样,他一进厂,就低着头直奔试验室。还没有跨进车间大门,他忽然听见有人叫他,抬头一看,不是别人,却是余静。她笑嘻嘻地问:
“昨天晚上回去,休息的好吗?”
“休息?”他一听余静的问话,浑身毛骨悚然了。他昨天回家以后,没有任何人去看他,也没和任何人谈过问题,他的心事更没人知道,不用说,早上出来也没碰见熟人。余静怎么知道他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呢?他不动声色说道,“休息的还好。”
“昨天你回去很晚了,又研究棉纱检验计分方法,太累了,怕你休息不好。”
“哦,”他心里释然了,知道是一般的问候,心定了一些,镇静地说,“习惯了,也没啥。”
“怎么这么早就来上班?”
“还早?”他看了一下手表,才七点,恍然地说道,“哎哟,看错了一个钟点。”
“离上班还有一个钟点,我们聊聊,好不好?”
“好,当然好。”
余静把他引到俱乐部办公室,那里一个人也没有,早晨的阳光照着墙上各种锦旗红艳艳的发光,和南面墙角落那边堆得整整齐齐的红色腰鼓互相辉映。东面墙边放着一张办公桌。余静和韩云程在那张桌子前面坐了下来。她开门见山地说:
“我早想找你聊聊,因为忙,一直没有空,恰巧今天你来了,我们可以随便谈谈。”
“可以,可以。”
“汤阿英和谭招弟她们诉苦,好不好?”
“太好了。她们放下了包袱,又教育了大家,我就是受教育的一个。”
“这样诉苦也不容易,她们做了出色的典型示范,特别是汤阿英,应该成为大家的表率。”她伸出大拇指晃了晃,赞赏地说,“她是我们的榜样。”
“是呀,汤阿英是我们的榜样。”
“不过,有些人不是完全懂得这个道理,在重要关头犹犹豫豫,包袱越背越重,最后自己吃亏。”
“最后自己吃亏?”韩云程思索余静这一句很有斤两的话。
他坐在她的对面,没法躲闪。他说:
“如果一个人受到党和工会的信任,他却犯了错误,余静同志,你看怎么办才好?”
“把错误讲出来,克服它!”
“今后怎么做人呢?”
“有错误,不讲,又怎么做人呢?”
“这当然也是一个问题。”韩云程接着又问,“讲出来,党和工会仍然信任这个人吗?”
“不讲的辰光,党和工会都信任他,给他工作,给他荣誉。
讲出来,当然更信任他。这一点不必顾虑。”
韩云程见余静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他,心里有些胆怯。那眼光好像可以洞察幽微,仿佛啥事体也蒙混不过。她的眼睛从来没有这样明亮过,今天一直看到他内心的秘密。他再也不能隐瞒下去,看上去,今天非讲出来不可了。特别是最后那句话,简直是对他讲的。“这一点不必顾虑,”还有比这再明确的话吗!他的脖子红了,耳朵有点儿发烧,准备干脆和盘托出,但嘴上却说:
“余静同志说的对,我也认为不必顾虑,党和工会总是帮助每一个犯了错误的人。”
“主要靠自己。自己有了觉悟,党和工会才好帮助他。
“是呀,靠自己。”
“要是大家都像韩工程师这样认识问题,事体就好办了。”余静昨天晚上见试验室里有很多人,韩云程又不打算谈,没有深问下去。她和杨健商量:准备今天约好韩云程,下班以后谈一谈。不料在车间大门那里碰上,看他行色仓皇,便抓住机会约到俱乐部来谈。果然韩云程提了上面那些问题,恰是火候,不能放过。她说,“你有事找党支部,现在可以谈。”
他没有啧声。他暗中瞟了一下俱乐部办公室的门,屋子里除了他以外,只有余静一个人,现在是再理想不过的时刻。
她察觉他顾虑的眼光,便说:
“不要紧,有话,你说好了。现在没有人来。”
“哦。”他说不下去,他问自己:余静怎么知道他的心事呢?他暗自考虑她的话:“现在没有人来”,断定余静知道他的事。工人们说的好:国民党把人拉到泥坑里,越陷越深;共产党把人从泥坑里拉出来,洗洗清爽,重新作人。他低声地说:
“余静同志,我有一件事想告诉你,你可不可以给我保守秘密?”
“可以。”
“不告诉任何人。”
“行。”
“那你答应我了。”
“你说吧。”她觉得他忽然变成小孩子似的,忍不住要笑出声来,说,“我答应你。”
箭在弦上,话在嘴边。他不能不说了,可是这桩事体怎么好开口呢?党和工会待他那么好,他把这事隐瞒了这么久,怎么对得起党和工会?他没有这个脸开口。但现在不说,更不对了。他两眼发酸,泪光模糊,按捺住激动的心情,说:
“我做了对不起党和工会的事……”
讲到这里,他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哭了,眼泪簌簌落下,一直流到他深蓝色的人民装上。
余静悄悄的注视着他。等他呜呜地哭了一阵,她低声地说:
“不管做了啥错事,只要讲出来,改正错误就好了。”
“我做了这件事,没有脸见人……”说着说着,他又嘤嘤地哭泣了。
余静等他说下去。他情绪很乱,像是一堆紊乱的麻,找不到一个头,不知道从何说起。一提到这件事,他忍不住要哭。在重要关头,总是她挽救自己,受到她无微不至的关怀。
余静见他哭哭啼啼,快上班了,就说:
“下班以后再谈也可以。”
他觉得对不起余静,在她面前难于启齿,话到嘴边又缩回去了。可是也只有在她面前,自己才愿意谈这件事。他想了一个办法,说:
“我写给你,好不好?”
“也好。”
当天回到家里,等家里的人都睡了,弄堂里五香茶叶蛋的叫卖声消逝了,他才提起笔来。单是开头,他就写了七遍,别的更不用说了。改了又涂,涂了又改,比他写大学的毕业论文还要艰难十倍光景。他生平头一遭儿遇到这样难作的文章。好容易写好了,他在灯下仔细地再三斟酌每一个字,然后又用毛笔楷书端端正正抄了一遍。他把报告装进信封,放在口袋里,才安心躺到床上去睡。
第二天下班,在俱乐部的办公室里,他又见到了余静。按照他的要求,屋子里没有别的人。他一进去,就把门关好,生怕有人闯了进来。他坐到余静对面的木板凳上,伸手到口袋里,拿出写好的那封信。那上面写着:呈交党支部余静同志亲启;左上角另外有两个字:绝密,旁边画了四个圈。他双手把信封捧到她面前,忸怩地说:
“就是这个,你看吧。”
他的头慢慢低了下去。她接过那封信,仔细看了,字迹端正,一笔不苟,可见得写的十分认真。她抽出里面的报告来看:
余静同志:
伟大的民主改革运动在我们厂里展开了。听了杨部长和你的报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每一个有包袱的人都应该在这次运动中放下,不然越背越重,最后对自己不利。
现在,我想向你报告我自己的事——我恳求你给我绝对保密,否则,厂里的人知道我的事,我就无脸在厂里工作下去了。这一点,请你务必注意。
我也有一个包袱。过去,我不认识它是一个包袱,以为这是个人的私事。所以反动党团登记时,我没有告诉你。这次运动开始,我想这也许是个包袱,但是一个“滑稽”包袱,已经过去的事,谈它做啥哩!
听了大家诉苦,我日日夜夜想到我自己的事,虽然是一个“滑稽”包袱,也应该向你交代。我不应该失去组织上再一次给我的机会。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即一九四六年一月,我参加了国民党。你知道,我对政治和政党没有兴趣。但我为啥要参加呢?因为那辰光,不是国民党员,我这个工程师的饭碗就保不住。为了生活,我不得已才参加的。起初以为参加,不做事,不卷入政党的纠纷,对我工程技术工作也没有妨碍的。谁知参加以后,每半个月要开一次会,我心里就有点不安。不久,又要我注意厂里和里弄有没有共产党,这使我思想模糊了。我想起了古人说的“君子不党”那句话。我不幸卷入了政党纠纷的漩涡。当时,我真想退出国民党,可是失业的危险又在威胁我。我徘徊在十字路口。我希望和谈成功,两党合作,我们学技术的人不再卷入政党的纠纷中,好给国家多做点事。
和谈破裂,内战的炮声响了。我在上海亲眼看到国民党的腐败政治,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我很惭愧我是国民党的一个党员,人民受这些灾难,我感到也有一份责任。
上海解放,使我对国民党有了进一步认识:是误国误民的反动派。而共产党为国为民的高尚精神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从此,我怕人在我面前提到国民党,我也不敢在任何人面前提到我和国民党有啥关系。我是国民党的特别党员,厂里没有人知道我的。所以,反动党团登记的辰光,我没有勇气去办登记手续。理由是自己决定不再和国民党有关系就好了。我私下断绝了这个关系,实际上是背着沉重的臭包袱过日子,一天到晚都提心吊胆。
五反运动中,大家欢迎我回到工人阶级的队伍,给了我很大荣誉,又吸收我当工会会员,更增加了内疚。我曾经想把这件事告诉你,又怕讲出来会断送自己的前途。
通过这次民主改革,听谭招弟和汤阿英她们吐苦水,挖苦根,放下包袱,想到解放战争时期,上海人民所受的灾难,自己也不能幸免,全亏共产党和解放军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解放了上海,不然,人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我呢,做了他们的帮凶。应该说,我是一个犯了罪的人。这次,我认识了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政策,不但要交代自己问题,放下包袱,控诉反动派,还要批评自己,重新做人。
从此以后,我坚决与反动派一刀两断,永远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
我衷心感谢党对我的挽救。
最后,再一次请求不要把我的事告诉旁人。
此致
敬礼
韩云程上
“你的报告很好。”余静看完了,说。
他一直低着头,不敢抬起来。担心余静看了,不知道自己的前途怎么样。
他不敢往下想。但是把报告交给了余静,心里反而安定了,一切问题交给余静去处理吧。在静悄悄中,忽然听了余静这句赞扬的话,他猛的抬起头来,望着她,许久说不出话来。她站起来,走过去,紧紧握着他的手,说:
“我一定给你保密。”
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一股热泪簌簌流下。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