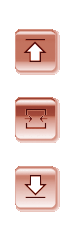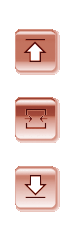|
|
|
|
第七章 仇恨
|
清洋江离肖家镇仅有二十里地,夜间,肖家镇这一带一高一低蹿起来的火苗,在清洋江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入夜好久了,同志们谁也不回去吃晚饭,都在这清洋江岸,默默地望着这罪恶的大火。清洋江的水哗哗啦啦无止境地向东北流去,可是它洗不掉同志们心上的仇恨。
马英踱到一棵树下,见建梅在地下坐着,双手抱着膝盖,低着头想心事。要在从前,建梅会忽然跳起来热情地招呼他,可是现在她没有动,就象没有人来似的。马英也没有做声,靠在树上,扯下一片树叶子,在手里揉成碎块,抛在地下。“建梅,你在想什么呢?”好久,马英才问道。
“我是想宝堂大爷,他躲了没有呢?万一他要被敌人捉住了,他受得住吗?……”
“如果要是你呢?”马英没有正面回答她。
“我……”建梅有些生气了,“我在入党志愿书上不是写清楚了吗?你还不相信我?”
“为什么不相信?”马英解释说,“我是说,如果我们能经受得住,宝堂大爷不也可以受得住吗?”
“我想也是的。”
老孟坐在沙滩上抽烟,抽啊,抽啊,抽了一袋再装上一袋,他的思想在肖家镇上跟着杨百顺奔跑:他仿佛看见杨百顺领着鬼子到处抓人,邦着鬼子打人、杀人,马宝堂好象已被捉住,杨百顺打他耳光,这家伙是最爱打人耳光的,马宝堂咀里流血了,杨百顺还在拚命抽打,这耳光就象打在他的脸上,直觉得脸上热辣辣的……他的思想不知不觉就从肖家镇跑出来,跑到去吉祥镇路上那块坟地里,他好象又听到杨百顺向他求饶的声音。唉,我为什么只打了他几下呢?我为什么打得那么不吃劲呢?我为什么没把他打死呢?……今天队长批评我,我还往大年身上推,我还强调这个毒蛇太狡猾,我………。猛抬头,看见马英立在他身边,他站起来抓住马英的胳膊,眼内浸出泪花说:“队长,我接受。我错啦,我错啦,我错了呀!……”
马英心里无限激动,许多老人浮现在他的眼前:父亲,早就死了;宝堂大爷,留下了;只有他,跟着他们出来了,五十岁的人了啊,容易的吗?……他声音沉痛地说:“老孟大爷,让我们接受教训吧!”
老孟用他那破皮袄袖子沾了沾眼角。
“日本鬼子,我操你八辈老祖宗!你们烧吧,烧吧,老子捉住你们大卸八块!”忽然王二虎跳着对着河西岸骂起来。马英走过去对他说道:“你骂什么呢?”
二虎不做声了。老孟在旁边说:“叫他骂吧,骂骂心里痛快些。”
马英忽然见赵振江一个人睡在沙滩上,就在他身边坐下来,推了推他说:“想什么,想家吗?”
赵振江没有回答,抓起一把沙子,又慢慢撒在地上。马英安慰道:“不要紧,不要紧的。”可是说了这两句,就再也找不到别的话了。再看那边的小董,一个人只顾拿着两块砖头对着敲呢,咀里不知还喃喃些什么。
“同志们,你们是跟鬼子生气,还是跟肚子生气呢?这样总不吃饭怎么能行?回去,回去。”杜平从村子里跑来,向大家喊道。接着他走到马英跟前,拍着他的肩膀说:“队长带头生气呢!”
“你不知道,大家都有情绪!”马英噘着咀说。
“这不怕,不过我们要注意把大家这种情绪引到积极方面来。”杜平推着马英说,“先回去吃饭,工作等会再研究。”“都回去吃饭!”马英无可奈何地向大家喊道。
“走,走!”老孟第一个跳起来,“不吃留给鬼子吗?”“吃,多吃点,好揍他个王八旦!”王二虎也附和着骂道。大家都起来往回走,只听小董嘟囔道:“光知道叫人家吃饭,自己不吃饭!”
“你说什么啊,小鬼?”杜平拉住他道,“谁说我没吃饭,刚才我在村里吃的饱饱的。”不想刚说到这里,他那肚子空得咕咕叫起来,他哄着小董道:“你听,它都在向你表示态度呢!”小董憋不住,笑了,接着又噘起咀说:“只怕它是对你提意见吧!”说罢拽住杜平的手,非硬拉他走不行。
“小董,我懂得吃饭的重要。能吃,我就会自觉地抢着吃。”杜平严肃地说道。
“唉!你怎么得了那样个怪病呢?”小董把手一甩,向马英他们追去了。
沙滩上只留下杜平一个人,对岸的大火还在熊熊地燃烧,清洋江的水还在无止境地流,他的思绪也在一起一伏地漫无边际地奔跑……
深夜,杜平把下一步工作想妥之后,才转回去,路上顺便查了一下岗。走到屋门口,他见小董坐在门坎上,双手撑着脑袋一点一点地打瞌睡。听到脚步声,忽然腾地站了起来,揉揉眼睛。
“还不睡?”杜平爱怜地摸了摸他的脑瓜。
“等你哩。”
“等我做什么?快睡去。”
杜平走到炕边,见王二虎仰面朝天躺在窗根,左手直伸,右手弯曲,做出一个拉弓的姿势,脑袋下枕着一口五寸宽的大刀。杜平才和他认识两天功夫,就深深爱上这个猛小子。靠王二虎睡的是老孟,蜷曲着他那高大的身躯,使劲地打着呼噜,白胡子仿佛还在颤抖着。挨着老孟睡的是建梅,这个爽朗活泼的姑娘把她那双一向闪耀着的大眼睛合上了,长长的睫毛弯成一个月牙形,她的脸是那样文静,她睡得那样安详。杜平暗暗感叹:这姑娘纯洁的真象是瀑布下的一块玉石,被水冲洗得愈加完美、干净、坚硬了。他的视线不觉又转到马英身上,他那两道粗眉显得更浓更黑了,这说明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可是杜平总觉得他脸上有那么一点孩子气。他忽然发觉苏建才翻来复去好象睡不着,就躺在他身边轻声问道:“没有睡?”
“嗯。”
“想什么?”
“不知道。”
的确,苏建才此时也不知道在想的什么。他的脑子里钻进了许多人,浮起了许多事,这些人在他脑子里打架,这些事在他的脑子里搅动,他只觉得眼花缭乱、昏昏沉沉……杜平忽然觉得一付沉重的担子落在他的肩上。现在同志们有两种情绪:一种是徬徨、恐惧,集中表现在苏建才身上;一种是急躁、轻敌,集中表现在王二虎身上。这些同志都是好同志,问题是看你怎么领了,领不好就要出漏子。第一步工作就是要抓紧做好思想工作,思想统一了才能有统一的行动。而更重要的是必须马上派人和县委取得联系,没有县委的指示,怎样行动呢?对当前的情况和对策,连他也弄不很清啊!……
“鬼子!鬼子!……”老孟突然惊叫道。
大家都从梦中惊醒,坐起来,王二虎抄起大刀就往炕下蹦。老孟揉揉眼睛说:“我梦见杨大王八领着鬼子来了。”建梅说:“你就会自己吓唬自己。”
老孟说:“我想,这回我可要把这王八羔子砸死!”二虎说:“又吹哩,又吹哩!”
大家哄笑了一阵,又睡了。
杜平推了推马英说:“明天想叫你化装回去和县委联系一下。”
“行啊。”马英激动地说。
“先到肖家镇看看,顺便把那里的情况了解了解,然后再到县委去。”
“…………”
马英接受了这个任务,兴奋得再也睡不着了。
第二天上午,肖家镇那边有人过来说,鬼子今早都进城了,好走。这时马英正在东套间里化装,建梅一边邦着他扣袍子扣,一边问道:“你这回去,得几天啊?”
“刚才开会不是早决定了吗?最多两三天,你怎么又问呢?”马英奇怪地反问道。
“嫌我问多了吗?好吧,以后你就是到天边我也不管不问了。”建梅故作生气地说。
“生气了吗?”马英开玩笑地说,“好,问吧,问一百遍我也不嫌多!”
建梅哧地一声笑了,“叫我问也不问了,咱高攀不上人家队长!”
“队长有你宣传部长厉害?”马英说罢,两个人不由都笑起来。
马英化装好了,头戴帽垫,身穿长袍,肩上背了个钱搭子,外挂一付茶色眼镜,他向前走了两步,转过身来对建梅说:“你看我象不象个做生意的?”
建梅歪着头看了看,笑起来:“我看呀,倒象个……”“你们两个小鬼又在谈什么心啊?”杜平带着老大哥的口气说道。建梅见他进来,忙跳起来说:“杜书记,你来检验检验,合不合格?”
“啥合不合格,又不是卖我?”马英一说,逗得大家都笑了。杜平叫马英朝前走几步看看,马英走了几步,杜平大笑起来:“不行,不行,你那样雄赳赳地干什么?把你那个队长忘掉吧。腰弯一点,步子迈小一点……”马英一一照办。“行了,行了,你看呢?”杜平回头对建梅说。
“右手应该撩起袍子。”建梅正经地说道。
马英只好按着她说的做,接着对她说:“行了吗?”“行了。”建梅说。
马英这时才松了一口气,往椅子上一坐说道:“可把我憋的不轻!”
这时小董跑进来,忽然又向外喊道:“都来看,掌柜的来了!”
大家听说,一拥而进,接着便七咀八舌地开玩笑。乱了一阵,杜平对大家说:“不要闹了,赶紧走吧。”马英把枪挂在腰里,又带了一个手榴弹,杜平把他送到门口嘱咐道:“切记,小心谨慎,头脑要冷静,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暴露自己的身分。”
“知道了。”马英答应了一声,急急朝村外走去。每当他到县委去的时候,他都有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这一次更加强烈,他三天前才在县委开过会,可是仿佛觉得有好长时间了;他们和县委相隔也不过几十里地,但他总觉县委好象在非常遥远的地方。当他一想到今天晚上就可以见到县委,就可以从那里取得新的斗争计划,心里便充满了喜悦,他不知不觉便想到县委书记兼县大队长李朝东身上,这个无忧无虑有本领的人,他一定有对付鬼子的办法!……他忽然低头看了看自己这一身穿戴,不觉好笑起来,他本来是最讨厌生意人的,现在倒装起生意人了。……
一过清洋江,他的心情完全变了,脚步也显得沉重起来,越往前走心里越觉得空虚,好象失掉了什么似的。现在他已遥望见涧里村废墟上仍然冒着白烟,走近一看,是烧掉了的四五家人家,有个女人坐在废墟上“我的天呀……”地哭,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扯着她的衣裳,直叫:“娘!娘!”
马英走进大亍,见一家门里一位老大爷惊疑地望了望他,赶紧把门关上了。他走出村口,不知是由于烟灰呛的,还是走的时间长了,咀里感到渴的要命。他见路旁有一口井,辘轳上还挂着一个木桶,他过去哗啦啦啦地把水桶放了下去,往下一看,忽然见一个披散着头发的十八九岁的大闺女脱得赤条条地躺在井底,井里的水已经染红了。马英觉得脑子一阵昏眩,赶紧趴在辘轳上,日本鬼子一件一件的罪证,象是在用一把锋利的刀子往他的心上雕刻,他的心感到剧烈的疼痛。过了涧里村,就清楚地看见马庄了,马庄的上空弥漫着烟雾,除了村西北角那一片房子被丁字亍隔住外,其余的房子全烧了。马英走到村口,迎面走来一个老太婆,手里拄着一根棍子,披头散发,咀里不住喃喃地说道:“我的老头子上天了,玉皇大帝都请他客呢!”
马英一惊:这不是马宝堂的老伴吗?这样说,老头子是死了?马英急忙问道:“大娘,宝堂大爷他……”
“他上天了,你们年轻人不知道,他的心好,连玉皇大帝都感动了,专请他去的。哈哈哈……”老婆子说着狂笑起来。她疯了!她疯了!马英想把她拦回去,可是她推开了马英,朝着肖家镇走了,咀里又在说:“他上天了,他上天了,哎呀,我要找玉皇大帝要人哪!”
“……你们凯旋归来,我带领乡亲们到十里开外去迎接!”这声音是那样清晰地在马英耳边回旋,就象马宝堂抖动着白胡子在他面前讲似的。昨天还是好好的人,一夜之间,就不见了。宝堂大爷,放心吧,这笔血债我记下了!
马英走进村里,他几乎认不出自己的家了,房子塌了,院墙倒了,瓦砾堆里一个碗柜子还在燃烧着,从空子里钻出一股白烟。满院子是烧焦了的木炭、纸灰,一阵风吹来,卷得在空中乱午。只有南墙脚下那块光溜溜的捶布石头,依然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马英坐到上面,凝视着这一切,父亲、母亲……他忽然看到那根烧剩下的半截门框,昨天母亲还靠在那根门框上擦着眼泪,送他走啊!……他不敢再想下去。马英忽忽悠悠朝肖家镇走去。进了北亍,听到远远的废墟上发出丁丁当当的响声,转脸看去,见二虎娘还在废墟里拾那些破碗破罐,马英跑过去叫道:“大娘,我回来了。”二虎娘直楞楞地瞅着他,马英摘下眼镜,她突然揪住他的长袍子说:“你回来啦,你把我儿子领到哪去啦!鬼子把我的房子都烧了,全村人都被害!”她喘了一口气,瞪着眼睛又说道:“马老先生叫鬼子用马拖死了,你娘叫鬼子抓走了,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马英脑子胀得象要爆炸了似的,几乎失去了知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二虎娘发了一阵脾气,出出气,解解恨,突然象是成了另外一个人,扑在马英身上哭起来。马英说道:“大娘,我们总有一天会打回来的!”
“你们回来做啥?只要能在外边平安无事就行了。”二虎娘说着从身上掏出两块干饼塞在马英手里,“你还没吃饭吧,孩子,拿去。”说罢又去翻拾那些破碗破罐了。
宝堂大爷,宝堂大爷,莫非你就这样惨死在敌人的手里了?母亲,母亲,你在什么地方?你那一颗善良的心还在跳动吗?……乡亲们,我们对不起你们,我们还没有保卫你们的力量;但是……马英把牙咬的咯咯响,那颗复仇的心,就象压在枪膛里的一粒子弹,随时都要射出去!
马英绕着胡同往赵振江家走去,亍上和胡同里到处是一堆一堆的火灰。罐头合子、酒瓶子,还有老百姓的锅碗飘勺扔得满亍都是。马英走到赵振江家门口,见门倒扣着,正在犹予,听到背后有脚步声,他警觉地把头扭过来,一看正是赵大爷回来了,手里掂着把铁锹,满身是土。一见马英,忙说:“屋里坐。作恶!作恶!”
“做什么去了?”马英问。
“埋孩子们去了。”赵大爷长叹了一声。马英说不出话来。赵大爷接着道:“孙子、媳妇,全死了。”
“宝堂大爷咋死的?”仃了半晌马英问。
“老人死的有骨气。”赵大爷赞赏地说,“他把杨大王八骂了个狗血淋头,还唾了他一脸,好不痛快!”
“杨大王八?”马英惊疑地问道。
“都是这王八小子坏的事!”赵大爷忿忿地说,“鬼子一来,他就领着挨家捉人。”
哧——地一声,马英掏出手枪就往外跑。赵大爷上去拉住他道:“你上哪去,他早跟着鬼子进城了。”这时马英耳边忽然又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头脑千万要冷静!”他把枪收回去,接着打听镇上的情况。赵大爷把他走后的变化一五一十讲了一遍,讲一句叹息一声,嗓子里不住打哽。马英咬着咀唇听完了,站起来说:“我这就走,以后有事还要托付你啊。”“这种时候了,还用交代什么。你告诉振江,不要叫他惦记家里。”
马英告别了赵大爷,忙着赶路了。
他走到城东的七里营,天已傍黑。忽然村西传来汽车的呜呜声,亍上的老百姓乱跑,因为天快黑了,都往地里跑,马英也跟着跑起来,刚跑出村,他猛然想道:瞎跑什么呢?趁着天快黑了,不如找个地方隐蔽起来看个究竟,鬼子也不是三头六臂!想着,他便转身往回跑。到了村西口,看好旁边不远有一间塌了的房子,躲在后面从门缝里往外瞧,路上的动静都能看得清清楚楚。马英找了块砖头,坐在门后,憋住气,专等着鬼子来哩!
呜呜的汽车声愈来愈响,已经看到了,汽车上满载着鬼子,个个都戴着又元又亮的钢盔,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装着一车西瓜呢!过去三辆汽车,接着是一百多个骑兵,再后面是四路纵队的步兵。忽然有个鬼子站住,朝这边瞄准,叭!叭!打来两枪,子弹穿透门扇,从马英身边擦过:落在废墟上变成两个小铅块。他以为鬼子发觉了,抽出手榴弹就要和鬼子拚,又听当的一声响,接着是鬼子一阵狂笑,他明白了,这是鬼子拿门环打靶哩!步兵过去,是九匹马拉的大野炮,一共四门,走到村边四吊角架开,轰!轰!轰!……连打了十几发进行示威,多么疯狂猖獗的敌人!鬼子终于都过完了,他们没有仃留,穿过村子一直向东去了。马英想,他们去做什么呢?是过清洋江,还是在这一带“扫荡”?……忽然又听到唧哩哇啦地有人在唱歌,他往马路上一瞧:有个日本鬼子,东摇西摆地瞎唱,看样子是掉了队的。马英的心突然紧张起来,脑子里浮起一个念头:“打死他!”一个鬼子算得了什么?鬼子不也是肉长的吗?看着看着,那个鬼子已经走近了。一不做,二不休,马英掏出手榴弹,拉出线,照准那个鬼子扔过去。“轰!”的一声,鬼子不声不响地倒下了,马英还在发楞,莫非鬼子就这样死了?这时,突然有个人拦腰将他抱住,他用手去掏枪,可是已经动不得了;正在这万分紧急之时,忽听身后那人哈哈大笑起来,声音是这样熟悉,可是一时想不起来,那人终于把手松开了,马英转脸一看,是李朝东,心里真是又惊又喜,忙问:“李政委,你怎么来到这里了?”“我来吉祥区检查工作。”李朝东严肃地说道,“太冒失了,小伙子!来,把鬼子弄过来。”说着指挥马英一起把鬼子的死尸拖在墙后,又把地下的血迹用土盖了盖。刚刚搞好,敌人三个骑兵拐回来了,查看了一下,见没有动静,又打着马走了。
李朝东教育马英说:“在紧张的情况下,一定要沉着,沉着就是把问题想一想,想好了就不紧张啦;迂事不动脑子,不紧张也要紧张起来,一紧张就要出漏子!……”
马英听着他耐心的教育,自然便想起他和李朝东初次相识的那段故事:
那是“七七”事变前两年,马英还在县城师范读书的时候,李朝东来县里检查地下党的工作,敌人发觉了要抓他,大亍上的巡警乱跑。马英奉杜平的指示到一个党员的家里去通知他,他还坐在椅子上喝茶,一见马英就说:“你是马英,对吗?情况我已经知道了。”
“那还不赶快走,敌人马上就要来了!”马英说着拉他就走。
“等一等,”李朝东甩开他的手,“房后这个小胡同能不能通出去?”
“能。”马英说。
李朝东倒拉着他来到后墙根下,噌的一声,便骑上墙头,然后伸给马英一只胳膊,说:“来!”那时马英个子小,身轻,一下子便被他掂过墙去。李朝东说:“小鬼,你前边走,碰上巡警就咳嗽一声。”马英应了一声“行”,就也学着李朝东的神情,坦然镇定地向前走去。
他们一前一后绕着胡同走,很顺利的来到北城墙根。这段城墙很高,地方也荒僻,没人守卫,他们悄悄上了城墙。李朝东从腰里取下绳子,马英正在想法如何把李朝东吊下去呢,只见李朝东将一头拴在城垛口上,顺着绳子一溜,便溜到城下,回头还笑着说了声:“再见。”马英都看呆了,不由感叹道:“这人真了不起!”
从那一天起,马英就对李朝东十分敬仰,把他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他发现在他身上除了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无穷的智慧以外,还有着熟练的战斗技巧,这样在他身上就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力量,再软弱的人跟他在一起,胆子也就大了。李朝东对同志们的工作要求,是严格的,对缺点的批评是直率的,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场合,对什么人,都是一样。可是一批评完,就恢复了他那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同志们说笑起来。他把鬼子身上的刺刀、水壶解下来向马英说:“太不走运了,没有枪。”
“就这也不错。”马英笑着说,“闹了半天,鬼子的脑袋也是肉长的啊!”
“可不,还没有我们的结实哩,哈哈……”两个人说说笑笑,消失在这黑夜的路上……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