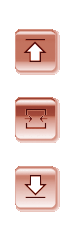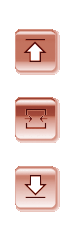|
|
|
|
第一章 肖家镇上
|
老槐树上吊着一个人。
这老槐树长在肖家镇的南亍口,谁也说不上有多少年代了,它那满是皱纹的干裂了的树皮,就象一个受尽折磨的老人的面孔。如今已经是深秋了,它那不多的树叶子也落尽了,光秃秃的,更显得干枯、凄凉、悲惨。
被吊着的人看上去只有二十多岁,穿一身白色的符衣符帽,从这里可以断定他是城东吉祥镇白吉会的人。他的双手反缚着,腰勾下来,两条腿垂成一条线,一只露出脚趾头的破鞋挂在脚上,看样子已经不能支持了。他勉强把头抬起来,用那乞求的眼光望着众人道:“叔叔大爷,婶子大娘们,你们行行好救我一命吧,我也是安分守己的庄户人家……”
“不准嚷嚷,再嚷嚷我马上捅了你!”一个虎实实的小伙子拿苗子枪在他脸前一晃,厉声喝道,声如巨雷。这小伙子胸前戴一个红兜肚,穿一条红裤子,在这秋凉的天气,他却光着膀子,露出那古铜色的皮肤,脊梁上背一口五寸来宽的明晃晃的砍刀。他叫王二虎,是肖家镇红枪会里有名的一员战将,昨夜单刀独身闯进吉祥镇,生俘七个白吉会的人。原来昨天不知为了什么,肖家镇的红枪会和吉祥镇的白吉会发生了一场恶战。白吉会勾结城里的民军,用机关枪扫死红枪会三十九个人,占了上风。红枪会吃了败仗,为了解气,决定拿这七个俘虏祭灵,一个村分一个。今天午时三刻开刀。一早,斋家镇的男女老少便来到老槐树下看究竟,霎时说长道短,议论纷纷。
“他娘的,白吉会没有好人!”
“哼!自作自受。”
“才二十多岁,还是个孩子啊!”
“唉!谁家不生儿养女,别残害这孩子了。谁去讲个情,留人家一条活命吧。”这是一位老大娘,说着拿衣襟捂在脸上。那被吊着的人看见这情景,又用那乞求的眼光扫着大家道:“叔叔大爷,婶子大娘们,替俺讲个情,俺一家老小五口人就托大家的福了……”
“你再嚷嚷!……”王二虎又一喝,全场顿时鸦雀无声。忽然一阵马蹄声响,一辆木轮大马车在背后仃了下来,车上跳下一老一少。那老头是个瘦高挑个儿,一脸花白胡子,手里拿着长长的鞭杆,头前分开众人挤了进来。他忽然望着那被吊着的人楞住了,结结巴巴地说不成句子:“你,你……你不是小陈家店的,陈……陈宝义吗?”
那被吊着的人眼睛慢慢闪亮起来,豆大的泪珠顺脸滚下:“老孟大爷,救救我……”
原来老孟赶车到过城东的小陈家店,认识陈宝义。这几天他给东家往城里捣腾东西,在城里住了两天,不了解乡里的情况。于是双手一摊,用他那颤抖着的声音向众人说道:“乡亲们,这是为了什么?这孩子是老实人!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啊!”
王二虎把眼一瞪:“他是种地的,别家的粮食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二虎子!”老孟吃了一惊,接着用长辈的口吻说:“你和你大爷要什么野蛮?都是种地的庄户人家,这是为了什么?”王二虎瞪着眼睛吼道:“为什么?为了给我们红枪会的三十九个人报仇!”
一提起红枪会,老孟的脸刷地变成一张白纸,不由倒退了两步。这红枪会的头子是谁呢?就是他侍候了一辈子的东家,就是在肖家镇一跺脚全县地皮要颤三颤的苏金荣!
王二虎上前一步,继续说道:“仇有沅,树有根,我王二虎凭白杀过人没有?”
老孟被问得哑口无言,大张着咀说不出话来。这时在老孟身后突然闪出一个英俊的青年人,浓眉毛,大眼睛,他伸出左手把二虎一挡,用他洪钟般的声音喝道:“不对!你们仇的沅在哪里?你们仇的根在哪里?难道就在他身上吗?”青年人把手向陈宝义一指,“他为什么要杀你们红枪会的人?是为了他脚上那一双破鞋吗?还是为了家里那两亩地呢?你说,他为什么?”
王二虎一开始还理直气壮地用眼睛瞪着那青年人,在青年人一连串的发问下,他慢慢把眼光避开了。那青年人用手向北一指,把脸转向大家说:“乡亲们,你们听!”
顷刻,全场又鸦雀无声,北边传来了轰轰的炮声。这炮声人们已经听了一个多月了,可是仿佛今天才听到似的,心又嗵嗵地跳起来。青年人接着讲道:“乡亲们,战火已经烧到我们家门口了!可是,我们在干什么呢?在互相残杀,杀我们自己的同胞,这不等于给日本鬼子邦忙吗?乡亲们,我们不要受坏人操纵,我们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犹如一声霹雳,把人们闭塞的、沉闷的脑壳炸开了,霎时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了明朗的青天,一个个都用敬佩的、希望的眼光,望着那个青年人。
忽然人群外一声尖叫:“谁家的叫驴跑到戏台上啦,在这充数!”
人们闻声,急忙让开一条道,中间闪出一人,但见他贼眉鼠眼,一个干瘦的脑袋象是用筷子插在肩膀上。这就是肖家镇上有名的无赖杨百顺,仗着他老婆“红牡丹”和苏金荣睡觉,便狐假虎威,成了肖家镇上一霸,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杨大王八”。
杨百顺把脑袋一歪,冲着那年轻人奸笑了一声,说道:“我当是谁哩,认识认识,这不是马庄马老山的儿子吗?马英,听说你到南宫共产党那里留洋去了,怎么样,弄了个什么官?带回来多少人马?多少杆枪?”
马英用那两道深沉的眼光丁住杨百顺,严肃地说:“没有人,也没有枪,我带回来的是共产党抗日的主张,冀南人民和全中国人民抗日的意志!”
“哈哈哈……”杨百顺一阵奸笑,“共产党这一套我早就领教过了,就是会卖膏药,胡弄老百姓还可以,东洋人可是不听这一套。”说到这里,他突然把脸一变,眉眼鼻子拧在一起:“我老实告诉你,这里没你的戏唱,少管闲事!”
马英用手朝杨百顺一指,喝道:“什么闲事!难道你们就可以拿着穷人的命开玩笑吗?这是大家的事,这是群众的事,你杨百顺当的什么家!”
在场的群众对杨百顺早已恨之入骨,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这时见马英将他抢白了,心里暗暗高兴,都替马英助劲,用那不平的眼光瞪着杨百顺。
杨百顺见风头不对,顺势一把将马英的手腕抓住,喝道:“你不要在这里逞能,有本事去见苏会长!”
马英一听,怒火万丈,把胳膊一抡,吓得杨百顺倒退几步。刹那间,多年积压在这个年轻人心中的仇恨,就象要从他的胸腔里一齐爆发出来!
原来马英家是苏金荣的佃户,因为积年累月借下苏家的债还不清,就把马英的姐姐——十七岁的兰妮送到苏家去邦工,工钱虽说寥寥无几,可家里总算少了一口人吃饭。
一天,马英的父亲马老山给苏金荣到衡水拉洋货去了,家里就剩下马大娘和马英母子两个。一场巨大的暴风雨来了,风卷着雨在猛烈地冲击着这个村子,象要把这村子洗平似的,窗纸被打破了,雨点涮打在炕上,马大娘一手抱着马英,一手拿被单子就去堵。轰隆一声,一个巨雷在他们的院空响起,屋里照得通亮,马英吓得哇哇哭起来。俗话说:“巨雷报信必有灾!”马大娘心惊肉跳起来,莫非他爹在外出了什么事?……就在这一霎时,兰妮披散着头发,浑身湿淋淋地从雨水中跑进来,脸色惨白……。“娘,娘……”她一下扑到马大娘的身上便哭成泪人一样。
“怎么啦,孩子?你又受委屈啦,你说啊!”马大娘紧紧抱住自己的两个孩子,马英也不哭了,瞪着两只元溜溜的小眼睛望着姐姐。
“娘,她,我……我叫他家的二……东家……”兰妮哭着说不出口,她把头埋在娘的怀里。
“孩子,孩子,你……你叫他……”马大娘的声音颤抖着,嚎啕起来。
“娘,”兰妮把头紧紧贴在娘的胸上,低声说,“我没脸见人了。你是我的亲娘,我才对你说,你不要对别人说,人活在世上,总要有脸,我虽说死了,一家大小还要活着……”马大娘不哭了,女儿的每句话,都象是一根根的钢针刺在她的心上:“孩子,你说的是啥啊!”
“娘,不要告诉我爹,就说我病死的,他老人家脾气倔,不要闹出乱子,只希望你们能过个平安日子就好了。等马英长大,他要有出头日子,再告诉他替我报仇!”兰妮说罢,抱住马英,在他的小脸旦上亲了两下,就往外走;马大娘丢下怀中的马英,一把将女儿拉住:“孩子,你上哪去?你不能……”这时她才发觉女儿的手这样滚烫,再一摸她的额头,烧得要命。兰妮被母亲拉回来,一头栽到炕上,马大娘扑到女儿身上,摇着她问道:“孩子,你到底怎么啦?”
“我……我吞了烟土啦。”
“啊!——”一声辟雷,马大娘摇着女儿哭!喊!叫!……雷鸣!闪电!暴雨!可怜十七岁的少女,在她对这世界还茫然的时候,便结束了她短短的一生。
仇恨!仇恨!暴风雨能把这世界洗平,可是也洗不清这仇恨啊!……第二天,马老山回来了,问女儿怎么死的。“病死的。”马大娘转过脸去说。
“好好的怎么会病死,准是在他家折磨死的!”马老山瞪着那满布血丝的眼吼道,“你告诉我,孩子究竟是怎么死的!”马大娘被逼不过,只得将实情原原本本告诉了他。马大爷头上的青筋立刻暴起来,拍着桌子骂道:“祖祖辈辈给他种地,到头落不了好死,不过啦!”
第二天,马老山请人写了一张状子,在县衙门告下了苏家的二东家苏金荣。那县官说没有真凭实据;苏金荣在大堂上还一口咬定自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说马老山败坏了他的名声。最后马老山被判了个“诬告好人”,在监狱里关了两个月。
马老山气得晕过去好几次。出狱那天,一直挨到天黑才回家。在月光下,他望着老婆孩子流下两滴泪,摸了一把菜刀,便又奔回城里来了。
马老出走到县商会门口,朝里望了望那辉煌的灯光,在一个角落里藏起来。苏金荣当时是县商务会长,正在里边打麻将,直到下一点钟才散伙。
马老山听得苏金荣在过道里讲话,浑身的血立刻沸腾起来,双手握紧了菜刀。忽然眼前一闪,走出一人,马老出赶上一步,用尽全身之力将菜刀劈将下去。那人忽觉脑后一阵风,急忙把头偏过,菜刀正劈在他的右肩,“啊呀!”一声,跌倒在地。此时走在后边的苏金荣掏出手枪照马老山叭的一声,击中马老山的胳膊,菜刀掉在地下。顷刻来了满亍巡警,将马老山捆了。
这正是一九二七年的白色恐怖时期,反动派正在残酷地镇压革命。他们给马老山安上个“共产党暴动”的罪名,判处了死刑。马老山在就义前,一边在亍上走着,一边昂然地诉说自己的冤屈,揭露苏家的罪恶,沿亍的人听了,无不落泪。
那时马英刚刚八岁,一颗仇恨的种子便种在他那幼小的心灵上。马大娘为了母子活下去,为了给男人、女儿报仇,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马英的身上,她到处跑着给人家邦工,什么活儿都干,忍饥受冻,积下几个钱供马英上学。
马英好容易上了几年小学,可是再往上巴结,那是无论如何也上不起了。他说:“娘,咱上不起学不上了,我去当兵去!”
马大娘一听,气得浑身直哆嗦,拉住他的手说:“傻孩子,你说这话不怕你娘生气吗?好铁不打丁,好人不当兵啊!”“娘,不当兵,咱怎么报仇?”
“当了兵还不是在他苏家手心里握着。听娘的话,孩子,好好上学,将来当个大官,管住他苏家。”马大娘说到这里,咀角上露出一丝微笑,接着又愁苦地说:“后晌我到你姨父家看看。”
马英的姨父在肖家镇天主堂里当长老,也算一个富户,因为马英家里穷,两家很少往来,马大娘也是个有骨气的人,只有到这节骨眼上,才去求人。
天黑,马大娘高高兴兴地从镇上回来了,她说姨父答应邦助,还随身带来一块现大洋,说是给马英作进城考学的盘费。不过有个条件:如果考上了,这盘费就算奉送;考不上呢,必须照数偿还。她把这块现大洋交到马英手里,千嘱咐、万丁宁道:“孩子,你可要给咱娘俩争这口气啊!”
马英就是怀着这颗屈辱、复仇的心,走进了县立师范学校。就在这一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马英也被卷进这次大风暴里,从这里他才认清了斗争的方向,革命的道理,一次又一次地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并且认识了这个学校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地下党员杜平老师。
抗日战争一开始,杜平便派马英到南宫八路军东进纵队里去受训,在那里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回来,县委便派他到肖家区开辟工作。肖家镇在县城的正北,离城十八里地,是衡水通往县城的要道,这里的情况最复杂,苏金荣又十分刁猾。所以县委才把马英派到这里,他是本地人,熟悉情况;但县委也考虑到他和苏金荣的关系,当他临走时,县委付书记杜平对他交代完任务,特别强调说:“记住党的政策,千万不要感情冲动。”
马英懂得领导的意图,也知道这付担子的份量。苏金荣是全县最大的地主,是一个最阴险最狡猾的家伙,又是他最大的仇人!如果叫马英去跟他干仗,那是比较容易的,仇恨会给他带来巨大的勇气和力量;可是叫他去和他打交道,去争取团结他抗日,这首先在精神上要忍受巨大的痛苦。而苏金荣这个家伙将会怎样对付他呢?……
马英在回来的路上,坐在老孟的马车上就反复考虑着对策。如今听杨百顺提起苏金荣,不由怒火万丈,又一想,这正是和苏金荣谈判的好机会,就忿忿地说道:“我正要见他!”老孟听了,慌忙凑上去拉了拉马英的衣角。马英一甩手,便大步朝前走去。杨百顺晃着个脑袋跟在后边。群众也随着拥进镇去,为马英助劲,可是又为他捏着一把汗。
肖家镇是县里头一个大镇子,足有五百户人家,一条南北大亍贯穿市镇。大亍的南段是些生意门面,以前十分兴隆,只是眼下肖条了;大亍的北段住的都是财主,尽是些高门楼,苏家的大门最高,坐西朝东,门口还有两个旗杆墩子。杨百顺把马英领进大门,让他在客厅坐了,又命两个红枪会的人暗地监视着,便直奔后院去见苏金荣。
苏金荣正坐在太师椅上抽水烟。他四十多岁年纪,穿一件绸袍子,戴一顶缎子帽垫,脸瘦而黄,蓄着八字胡,故意表现得很气派、威严。他见杨百顺进来,微微欠了欠身子。杨百顺深深鞠了一躬,便挤眉弄眼地报告道:“苏会长,马英回来了。”
“哪个马英?”苏金荣的眉毛动了动。
“就是马老山的儿子。听说到南宫共产党那里留了几天洋,一回来就在镇口卖起膏药来,还想把白吉会的人放了哩!……”
杨百顺一口气讲个不休,苏金荣一句话也没说,呼噜噜、呼噜噜地一股劲抽着水烟。如今时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八路军东进纵队开到冀南了,那些败退下来的中央军也老实了,有的被收编了,各县都在纷纷成立“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昨天他收到八路军东进工作团的一封信,邀请他商讨成立“战委会”的事,他正在为这事打着算盘:不参加,这天下暂时是共产党的,那自己一点地位也没有;参加了,谁知道共产党安的什么心,还不是借着抗日的牌子弄他的钱!如今马英又回来了,他来干什么?我们是仇人……
杨百顺跟苏金荣在一起混了多年,知道凡是他一股劲抽水烟的时候,就是要下毒手了,所以便自作聪明地献计道:“会长,我看把这小子扣起来吧,你知道你们两家……”苏金荣一挥手,打断了杨百顺的话,又狠狠地抽了两口水烟,啪的一声,把烟袋往桌子上一放,脸上露出一丝阴笑,接着在杨百顺耳边低声几咕了几句什么。杨百顺连声称是,一溜烟朝镇北的龙王庙去了。
苏金荣整了整衣帽,朝前院客厅走去。马英正在客厅里不耐烦地来回踱着,忽听脚步声响,一转脸,见苏金荣已经走进客厅,二人的眼光碰在一起……仇人!仇人!仇人来到眼前,马英眼睛里冒出忿怒的火光,两只拳头也不由自主地握紧了。这时他耳边忽然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记住……党的政策……抗日统一战线……千万不要感情冲动。”
在苏金荣的印象里,马英只不过是一个笨头笨脑的穷孩子,可是现在站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气宇轩昂的青年,特别是他那炯炯逼人的目光,使他倒抽了一口冷气。但他立刻镇静下来,堆起一脸假笑,客气地说:“马同志回来,有失远迎,请多多原谅。”
马英往太师椅上一坐,把一只握紧拳头的胳膊往八仙桌上一落,不客气地说:“不敢劳你的大驾。”
苏金荣接着让伙计沏茶拿烟,忙活了一阵,然后才落坐,慢条斯理地说道:“苏某虽不才,也深明大义,当前国难临头,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中共提出联合抗日主张,我苏某举双手拥护。……”
这些话要是出自别人之口,马英也许不会怎么介意;但出自苏金荣之口,他就有一种特有的敏感和警惕。他心里暗暗说道:“别他妈胡弄我,我早就看透了你!”
苏金荣只管空谈他的抗日道理,对于马英的来意,他十分明白,却故意避而不谈。这是因为如果把白吉会的人放了,他就不能以此来笼络和迷惑人心;而更主要的是,这是他和共产党走的第一步棋,这一步棋的输赢,关系着全局的胜败。要是这步棋走输了,共产党就会赢得人心,人们就会逐渐认清他的真面目,红枪会就有瓦解的危险,他的统治地位也就不巩固了。所以他想用这些进步道理来迷惑马英,转移马英的视线,从思想上解除这个青年人的武装。
马英对他这一套早已听得不耐烦了,便打断他的话,直截了当地说道:“既然你深明大义,这就好说。当前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对自己人就不应该互相残杀,所以我要求你把白吉会的人放了,这也是广大群众的要求。”苏金荣听罢,心里暗暗骂道:“好个不知厉害的东西,既然想见识见识,就给你点厉害看看!”他心里这样想着,脸上却仍堆着假笑说:“这事我不当家,仇也不是给我苏金荣报的,这还不是大家的仇。如果要放人,你得到龙王庙对会里的弟兄们讲讲,只要大家同意了,我万分欢迎。”
马英正想借此机会向群众作一次宣传,便追问道:“讲通了怎么办?”
“我马上放人。”但他随即也反问道:“要是讲不通呢?”“任凭大家处理。”
“好吧,一言为定。”
二人说罢,一齐走出大门,朝龙王庙走来。大门外的群众又一拥随在身后,都想去看个究竟。老远老远,就听到庙里红枪会的人乱叫唤,声音又直又硬,一高一低,听了叫人心里不舒服。马英暗想:这些反动家伙把农民愚弄成什么样了啊!
走上庙门口的大石桥,苏金荣转脸对马英说:“请少等一等,我先到里边让大家安静一下。”径自朝庙里走去。
这时来看动静的群众一齐围在桥头,议论纷纷。有的说:“这也不知又要的什么手段?”有的说:“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老孟三挤两挤,挤到人前,对马英说:“你,你回去吧,慢慢再争这口气,这伙人喝了符,六亲不认啊!”
马英笑着说:“老孟大爷,不要紧,都是自己的乡亲,怕什么?”
这时庙里安静下来,苏金荣走出庙门,把手一扬,说道:“请吧!”
马英没有答话,昂然走入庙内。
这是一坐老古庙,宽大的院落,高高的围墙,四周有十多棵大杨树,插入云霄,把天空密封起来。红枪会的人个个赤膊卷腿,磨刀擦枪,横眉瞪眼地注视着马英。也分不清哪是泥像,哪是真人,阴森森的寒气逼人。马英不由打了个冷颤,可是他马上警惕起来:这是在和会道门进行斗争!全镇的人都在望着我,全区的人都在望着我,决不能动摇;坚定,坚定,坚定就是胜利!
苏金荣倒背着手向大家介绍说:“现在有共产党的代表给大家讲话。”
马英上前跨进一步,用他那炯炯的目光把所有的人扫了一遍,严肃地说道:“乡亲们……”
一句话未了,平地跳出两个恶狠狠的家伙,用苗子枪逼住马英喝道:“哪里来的野猫子,我们会里的事情不要你管!”马英一见,勃然大怒,元睁着眼睛厉声喝道:“这是你们会长请我来的!”
人群中有人乱吼怪叫:“赶走他!赶走他!“捆起来!捆起来!”那两个家伙听了,把枪一扔,从腰里解下绳子就来捆马英。
忽然人群中走出一人,把两只胳膊左右一伸,就象使着一根杠子,把那两个家伙拦得倒退了好几步。这人就是王二虎,他用雷一样的嗓门吼道:“不能不让人家讲话嘛!”瘦高个儿赵振江也在后边挥着手说:“有话也得等人家讲完了再说。”
“客气点,客气点。”
“都是自己乡亲嘛!”人群中有人附和。
那两个家伙只好坐下了。苏金荣的阴谋破了产,没有吓唬住马英,只好装佯说:“都是自己人,不得无礼。”
马英把手一挥,精神焕发地讲道:“乡亲们,报告给你们一个好消息:八路军东进纵队开到我们冀南啦!……”
这时杨百顺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上前一拱手,牛头不对马咀地称呼道:“马先生,我请教。”接着摇头晃脑地假充圣人说:“什么东进纵队,西进纵队,我们没见过;可是正牌队伍我们看到不少,哪一个不糟害老百姓,我算是小舅子!”杨百顺的话立刻博得不少人喝采,乱附和着:
“什么正牌军,都是土匪兵!”
“都是牛皮大王!”
“老子什么也不信,就信我手里的大刀片!”
马英暗想:必须先把杨百顺打下去。于是避开大家说:“杨百顺,你可不要跳到秤盘里——拿自己来量别人,八路军不但不抢人,也不偷不摸,就是借老百姓一针一线,也要原物归还。”
这一下揭了杨百顺的底,谁都知道他是善于偷鸡摸狗的,顷刻院子里响起一阵哗笑。杨百顺的黄脸皮上顿时泛起一块块的红斑,他老羞成怒,正要出口还击,王二虎站起来说:“是听人家的,还是听你的,少说两句也不会把你当哑巴卖了!”
杨百顺虽然能巴结苏金荣说几句话,但因名声太坏,苏金荣不重用他,根子不硬,碰到王二虎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就草鸡了,只好溜到一边不说话。
马英接着说:“八路军是咱穷苦老百姓的子弟兵,你们说,自己人怎么会抢自己人呢?”
赵振江腾的站起来,对大家说:“昨日我进城看见两个八路军,人家就是不含胡,说话都和和气气,就象咱们亲哥们一样。”
这一来立刻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个个惊喜非常。马英趁机把八路军大大介绍了一番,从八路军的组成一直讲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给他们讲了一个八路军英勇善战的故事。接着从这里讲到敌我力量,国际形势。又渐渐扯到统一战线、团结抗日,最后才引到放人的问题上。
红枪会的人从来没听过这些新鲜事儿,听得入了神,有的暗里几咕道:“人家就是有两下子。”“说的头头是道。”苏金荣在一旁听得火辣辣的,又不好制止,气得直翻白眼珠子。马英讲完话,赵振江首先站起来说道:“把人家放了算啦,反正杀了人家,我兄弟也不能起死还阳。”
王二虎说:“都是中国人,多留一条命打鬼子!”
一个老头说:“救人一命,多积一分德。”
“放了算啦。”“放吧,放吧。”“……”人们嚷成一片。苏金荣见大势已去,假笑着对马英说:“兄弟们没有意见,我更没说的,我苏某生平是主张行善的,放吧。”当他看着马英满怀胜利微笑走出大庙时,他的上眼皮往下磕,阴沉地嘟囔道:“让你这一步,走着瞧吧!”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