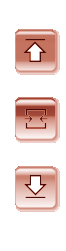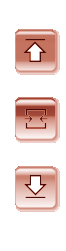|
|
|
|
第十一章
|
四五
蒋介石在各个战场上连吃败仗。在三月里,虽然攻占了延安,但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城和几千个窑洞,而付出的代价却是损兵折将。在东北战场上,已经丧失了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七个美械师,在冀鲁豫战场,也不断地遭到惨重的失败。在这个碰得头破血流的当儿,又重新在华东战场上打起算盘来。他们在四月里,曾以汤恩伯、欧震、王敬久三个兵团计三十四个旅的兵力,向蒙阴、新泰地区进犯,结果,遭到了我军的猛烈反击。驻守泰安城的整编七十二师全部连同整编十一师(蒋军五大主力之一)的一个侦察营,共二万四千多人被我歼灭。
紧接着泰安战役之后,蒋介石又投下了一笔巨大的赌注。他的骄子、御林军七十四师,也是他的五大主力当中的主力,被当着必胜无疑的一张王牌摊了出来。
蒋介石以七十四师作为核心和中坚,再加上汤恩伯、欧震、王敬久这三个兵团和另外的一些人马,摆成一个龟形阵势,再一次地向华东人民解放军控制的战略要点--费县、新泰、蒙阴一带沂蒙山区①开始新的大举进攻。
①沂蒙山区系毗连的沂山、蒙山的总称,在山东的东南部。
炮声又渐渐地稠密起来。山岳、平原,山上和地上的一切生物、无生物跟?战争,巨大规模的战争现象又显现在人们的眼前。
华东野战军各个部队,奉命在沂蒙山区和它的周围展开,制造和捕捉战机。
沈丁部队的两万多人,经过两个多月的战后休整,从淄川、博山地区,向沂蒙山区的西侧行进。
走在路上的队伍,因为连续八天山地行军,感到疲累得很。他们的背包越背越重,虽然不断地精掉一些东西,腿脚的抬动还是越来越感到吃力,部队尾后的收容队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增多起来。许多人腿脚肿痛,脚趾上磨起了水泡,说故事、讲笑话的人越来越稀少,就是有人讲呀说的,也很少有人爱听爱笑了。
“到什么地方才宿营?”
“情况不明,就地宿营!”
“不是'天亮庄',就是'日出村'!”
“天为什么老不亮啊?太阳躲起来啦?”
“这叫打仗吗?”
“是脚板跟石头块子战斗!”
……
战士们一边走着黑夜的山路,一边说着怪话。
连长石东根也忍耐不住,在一个山坡上休息的时候,他把身子倒躺在坡子上,让头部向下,两脚向上,竭力地使两条肿痛的腿上的血,向他的上身倒流,嘴里“咕噜咕噜”地说:
“再拖几天,不打死也拖死了!”
头部伤口刚好,第一天归队第二天就出发行军的指导员罗光,抚摸着脑袋,象是伤口发痛的样子。
“背包给我吧!”他望着石东根低声地说。
“要你这个伤号替我背背包?”石东根把背包垫在头底下,身子依旧倒挂在山坡上,两腿不住地摇动着说。
骑兵通讯员们纷纷地从面前跑过去,马蹄子踏着不平坦的山道,发出“咯咯叮叮”的响声,他们脸上流着汗水,枪托子在他们背后颠抖着,嘴里不住地吆喝着,驱使着马匹快跑。
有人羡慕地、但又嫉妒地说:
“当骑兵真是惬意!我们两条腿!他们六条腿!”
一个骑兵通讯员在团长刘胜的背后,高声叫道:
“团长!团长!”
刘胜在马上回头望望,骑兵通讯员跳下马来,递给他一个折皱了的纸片。他勒住马,看了看,旋即跳下他的乌骓,喊住在后面来的团政委陈坚。同时告诉作战参谋,通知部队马上停止前进。
蒋介石的包括七十四师在内的一个兵团深入了沂蒙山区,军部奉到野战军司令部的命令,通知所属部队就地停止前进,听候命令行动。
“七十四师真的来了!”这消息象战斗的捷报似的,在部队里传告着。
所有的指挥员、战斗员们立即欢腾起来,动荡起来,八天来连续行军的疲劳,一下子消退了一大半。山上、山下漾起了喜悦的笑声,展开了热烈的谈论:
“心里正在想他,他就来了!”秦守本搓着手掌说。
“嘴说曹操,曹操就到!”熟悉戏文的安兆丰接着说。
“七十四师是蒋介石亲生亲养的儿子,真舍得拿出来送死吗?”在黑暗中的远处,另一个班的一个战士问道。
“蒋纬国是他的真儿子,还给他赶上战场哩!在鲁南,不是险险乎当了俘虏!”另一个班的又一个战士说。
听来是石东根的声音:
“告诉他们不要嚷!赶快睡一觉!留点精神赶路、打仗!”
李全象只小松鼠似的,跳到这个排,窜到那个班,急急忙忙地传达着命令,由于心情兴奋,他把连长的话加多了内容,也加重了语气说:
“连长命令你们不要嚷!眼闭紧,腿伸直,就地睡觉!七十四师要请你们吃红烧肉,露水少喝一点,留个肚子好多吃几块肥肉!”
“小鬼!我听到连长的话不是这样说的!”秦守本抓住李全的膀子,用力地勒了一下说。
李全歪嘴促鼻子,故意过火地喊叫起来:
“哎哟!哎哟!疼死了!”
他挣脱了秦守本的手,跑走开去。
“杨班长这一仗又赶不上了!伤口还没有好?”秦守本走到张华峰跟前,低声地说。
“连个信也没有。”张华峰头枕在背包上斜躺着,眼睛望着天空的星星,带着怀念和忧虑的神情说。
“给他的小娘子扯住腿了!”和张华峰头抵着头的洪东才,转过脸来,在张华峰耳边哼着鼻音说。
“他不是那种人!”张华峰摇摇手,断然地说。
“就怕伤口复发!”秦守本担心地说。他躺倒在张华峰身边,两条笨重的腿压在洪东才的肚子上。
洪东才用力地掀动秦守本的两条腿,秦守本的两条腿象木头杠子似的,更加沉重地压服着他,他掀它不动,便抡起拳头死命地捶了两下;而秦守本却愉快地叫道:
“对!捶得好!就是这个地方又酸又麻!捶两下舒服!”
洪东才把身子猛然地向旁边一滚,秦守本的两条腿便重重地掼在硬绷绷的石地上。
他吃了亏,连忙爬起身来,去追逐洪东才,洪东才哈哈地笑着跑到远处去了。
石东根正好走到他们身边,他的眼睛在黑暗中发着亮光,亮光炯炯地落在秦守本和洪东才的身上。秦守本跑回到自己班里,不声不响地躺下去,紧紧地闭上眼睛,装做睡着了。洪东才却走到连长身边,装作很正经的神气向连长问道:
“连长!七十四师到了哪里?我们打得上吗?”
洪东才这一着,果然有了效用。
石东根本想训他几句,给他这么一问,只得冷冷地说:
“我怎么知道?你去问团长去!”
说了,石东根蹬了洪东才一眼。
尽管连长要大家争取时间休息一阵,班、排干部和战士们还是“嘁嘁喳喳”地咬着耳朵边子谈论着。
渴望战斗已经好久,渴望打七十四师已经大半年了,涟水城外淤河滩上的战斗,在他们心胸里刻上了不能磨灭的痕印。许多人的肌体上有着七十四师炮弹、枪弹的伤疤,许多人记得他们的前任团长苏国英牺牲在七十四师的炮弹下面,许多人记得七十四师那股疯狂劲儿,那股蔑视一切的骄纵骠悍的气焰,他们早就有着这个心愿:给这个狂妄的逞过一时威风的敌人,以最有力最坚强的报复性的打击。
“给打击者以双倍的打击!”
“叫七十四师在我们的面前消灭!”
这是在部队中自然发生的长久以来的战斗口号。
在涟水战役以后参军的和解放来的战士们,也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干部们和老战士们的深刻感染,有着和干部们、老战士们同样的心理感情。就是张华峰班那个曾经替七十四师吹嘘过的名叫马步生的新解放战士吧,前两天也说过这样一句话:
“说不定七十四师要死在我们这个队伍手里!”
“说不定?我说,七十四师一定要死在我们手里!”不大说话的副班长金立忠,斩钉截铁地对马步生说。
马步生没有再说什么。马步生--有人叫他“马路灯”,因为字音顺口,又因为他是个瘦高长子,额头前迎得厉害,和他的鼻尖子几乎垂直,两片嘴唇特别厚,走路的样子也不好看,外八字脚。从这些地方看起来,他是个很蠢笨、但又令人可笑的一副模样。因为他常常鼓吹七十四师的威风,同时又不喜爱他这副可笑的蠢样子,曾经有人对张华峰说:“向连长建议调他出去吧!”张华峰不同意,他说这个人有不少好处:第一,他直爽,心里有话搁不住,总是说出来叫别人知道。他刚到班里来的时候,不少人担心他要逃跑,他拍着胸口对张华峰保证说:“我姓马的不会开小差,我要是开小差,就不是我妈妈养的!”两三个月来,从他的各种表现上看,他说的话是可靠的。第二,他力气大,跑得动,背得起。第三,他在广西军里当兵以前,在七十四师里干过,他懂得不少七十四师的部队情形。张华峰早有这个打算:迟早要跟七十四师交手,多一个了解敌情的人是有用处的。
这几天,部队里酝酿着打七十四师的事,他讲了不少关于七十四师内部的情况,据他自己前些日子的自白,他是自愿到七十四师当兵抗日的,后来因为每天三操两讲吃不消,便开小差开到广西军四十六军。他认为广西军也很重视军事教练,但是比不上七十四师。他形容七十四师部队的容貌说:“有一回,美国顾问来检阅,在南京中山门里的大操场上,全师两万多人,戴的一律钢盔,穿的一律力士鞋,眉毛不动,眼皮不眨,排列得整整齐齐,队伍的行列象刀削似的,没有一个人磋前一分,磋后一厘。美国顾问检阅以后,不住地翘着大拇指,说着中国话,连口称赞:'好!好!'广西军就吃不开,从来没有美国顾问去检阅过。”
刚才,队伍得到通知,在原地停止前进,大家又谈起打七十四师的时候,他说:
“要是真把七十四师消灭掉,蒋介石的天下就完了蛋!别的队伍就不用打了!”
“照你这么说,蒋介石有七十四师,就能坐牢南京的金銮宝殿,没有七十四师,他的金銮宝殿就坐不成?”洪东才这样问道。
“正是!正是!”他毫不含糊地回答说。
“好吧!这一回就叫他下台!”秦守本拍着手里的枪杆子说。
马步生的话不是完全可信,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在蒋家军里,七十四师的确是有威名的一个队伍,蒋介石把最优良的装备给了它,发给它的给养是上等军米和洋面粉,别的部队的军饷,常常被克扣或者迟发十天半月,甚至更长的时日,对七十四师则从来没有扣发、迟发的情况。国民党蒋介石用许多的言语和文字来宣传他们这支部队,把这支部队说成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天将神兵,当成是他们整个军队的灵魂和胜利的象征。
正是这样,解放军的战士们对消灭七十四师就感到更大更浓郁的兴趣,仿佛只要是打七十四师,他们可以不吃饭,不睡觉,哪怕前面是汪洋大海也能越过,是重迭的刀山也能攀爬上去。如果一个钟头要赶三十里路,他们的两只脚就可以象《封神榜》上的哪吒,装上风火轮驾空飞走。又仿佛只要把七十四师消灭,他们就一切仇恨皆消,也才算得是革命英雄似的。
在连队里巡查了一遍的石东根,只是叫大家休息养神,自己回到休息的山坡上的时候,却怎么也合不上眼皮,心头总象有一群蚂蚁在爬似的,痒糯糯,热蒸蒸的。他的脑子里,象波涛滚滚似的,在翻腾着在涟水城外淤河滩上跟七十回师血战苦斗的影子。他突然地拍拍身边田原的大腿,大声地说:
“文化教员,编个打七十四师的歌子唱唱!”
“他已经编了好几句了!”李全告诉他说。
石东根当是田原睡着了,贴近田原的脸看看,田原的眼睛睁得挺圆,直望着前面的蓝空和紫褐色的山,嘴唇不住地弹动着,正在用心出神地想着、默念着。罗光和田原并头躺着,膀肘支撑在背包上,手掌托着下颏,眉头微微皱着,和田原同时地想着歌词。
天空象一片茫茫大海,碧澄澄的,繁星象银珠一般,在海水里荡漾着闪灼的亮光,仿佛是无数只的眼睛,向躺卧在山道上的战士们传送深情厚意似的,和战士们眼光亲切地对望着。战士们睡不着,它们也就有心地陪伴着,共同地度着这个初夏的深夜。一些不知名的虫子,“唧唧”地细声地叫着,象是帮同田原在哼着还没有想定的歌曲似的。
“这样好不好?”田原坐起身来精神奋发地说。
“念给我听听!”罗光轻声地说。
田原轻轻地亮亮嗓子,低声地念诵道:
同志们!勇敢前进!
同志们!顽强作战!
端起雪亮的刺刀,
刺进敌人的胸膛!
射出无情的子弹,
把敌人的脑袋打烂!
叫疯狂的敌人,
消灭在沂蒙山!
他念完以后补充说:
“最后两句唱的时候重复一遍。”
罗光把田原的歌词重念一遍,修正着说:
“'无情的子弹'改成'仇恨的子弹','叫疯狂的敌人,消灭在沂蒙山!'改成'叫蒋介石的御林军,消灭在沂蒙山!'
你看好不好?”
“御林军?我不懂!什么叫御林军?”李全歪过头来问道。
石东根接过口来说:
“干脆改成'叫七十四师,消灭在沂蒙山!'前面两句'同志们勇敢呀,顽强啊',哪个歌子上都有,不要!”
“那太短了!只有六句!”田原不同意地说。
“我说呀!所有的歌子都嫌过长,唱半个月二十天也记不住!六句,短而精,容易记又容易唱,我是老粗,没有文化,就是这个意见!”
“那就变成这样啦!”田原快速地念道:
端起雪亮的刺刀,
刺进敌人的胸膛!
射出仇恨的子弹,
把敌人的胸袋打烂!
叫七十四师,
消灭在沂蒙山!
“就这样!正合我的口味!嫌短,再昌一遍两遍!”石东根拍着田原的肩膀决断地说。
罗光表示同意石东根的见解,田原便在口边哼起曲谱子来。
田原哼着,李全跟着哼着,两手各拿一个小石片敲着节拍。哼着,哼着,田原唱出声来,唱起歌词来,接着便坐在一块大面的他的脸色,渐渐地胀红起来,涌上了兴奋激越的神情。他的声音虽然低而轻,却很清彻地在夜空里播荡着,袭入到战士们的耳朵里。
战士们也就自然地哼唱起自己爱唱的歌子来:
“前进!前进!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打得好来,打得好来打得好!四面八方传捷报来传捷报!………”
农历四月的山间的夜晚,含着香气的凉爽的风,从山峡口吹拂过来,在山谷里留恋地回旋着。山间的小松和野花野草,摆动着强劲的身姿,发出“窸窸嗦嗦”的有节奏的声音,象是给战士们的歌唱配着和声似的。
战士们的心,象火一样的热烈。他们睡不着,他们在歌唱,他们在星光下面擦拭着枪、刀,等候着和蒋介石皇朝的御林军七十四师接战的行动使命。四六
队伍现在的位置在沂蒙山区的西北角上,炮声在队伍的东南方“轰轰隆隆”地吼着。
歇在山道上的队伍,在焦盼热望中得到了行动命令。急忙地爬起身来,背包和武器轻飘飘地飞到身上,精神焕发地向前行进。
在练赛跑的运动员,一旦解去腿上沉重的沙袋,两腿觉得非常轻快,缚在身上的疲劳,全部解除尽净。
大概走了七、八里路,队伍下了山坡,踏上丘陵地的田野大路,不知是谁,望望上空的北斗星,突然地疑问道:
“这不是向西走了吗?”
这么一问,提醒了许多人。
“对呀!敌人在东边,我们怎么向西走呀?”秦守本没有说出声来,心里暗自地疑问着。
向西,向南,又向西,又向南,炮声确是越来越远了。
队伍离开了沂蒙山区,进入到半丘陵半平原地带。
“敌人又跑了?”
“回华中去吗?”
“到鲁西南跟第二野战军①会师?”
①第二野战军即冀鲁豫人民解放军。西北人民解放军为第一野战军,东北人民解放军为第四野战军,华东人民解放军为第三野战军。
“许是叫我们去摸敌人屁股的!”
“十成八成是去攻临沂!”
有些干部和战士提出了自己和别人都无法回答的问题,也有的在作着自以为满有把握的估计和判断,象是诸葛亮似的。
脚步越走越慢,仿佛腿上又缚上了沙袋,落下去很沉重,提起来很吃力。
又有人在开玩笑、说怪话了:
“当官的一张嘴,小兵癞子两条腿!”
出乎大家意外,走了约摸三十来里,天刚夜半,就进庄子宿营了。
“排长!解背包不解?”秦守本向二排长林平问道。
“不解!天一亮就出发!”站在连部门口的林平回答说。
秦守本察觉到林平的神情有些不愉快。林平在回了他一句以后,就走开了。
秦守本正要回转身子,忙着抱禾草打铺的田原从屋里出来,他迎上去说:
“文化教员!你做的新歌,打七十四师的,抄给我好不好?”
“新歌?打七十四师?”田原咕噜着说,忽而他觉得自己的语气神情不对,又连忙转过口来,强笑着说:
“还没有做好,隔两天教你们唱!”
说着,他匆匆地走到草堆边去。
从田原的话里,秦守本感觉到味道不对。“隔两天教你们唱!”难道不打七十四师了吗?他很想走到连部去问问连长、指导员,正犹疑着,抱着一大捆禾草的李全和惊吓的语气对他说:
“秦班长!还不赶快去睡觉?明天的路程……”
李全截断下面的话,向屋里走去。秦守全赶上去拉住李全,亲热地低声哄问道:
“我们两个感情不错,告诉我,明天的路程怎么样?”
“我不能自由主义!”李全拒绝他的要求,板着脸说。
“等一会,我还能不知道?不说拉倒!”秦守全装作不乐意的样子说。
李全觉得这倒也对,他是班长,又是莱芜战役的一等功臣,明天走多少路,还能不让他知道?于是抬起手来,用拇指和食指在秦守本眼前晃了个“八”字。
“八十里?”秦守本吃惊地低声问道。
“唔!”
“向东向西?”
李全的手朝西南角上一指,便抱着禾草捆子跑进屋里去。
秦守本的眼睛朝西南角上黑洞洞的天空,呆望了许久,心里很是惶惑不安。会上西南去吗?上那里干什么呢?他离开连部门口,默默地盘算着,默默地走回到班里去。
他摇摇脑袋,“这个小鬼!定是胡指乱划,弄不清东、西、南、北!”他心里怀疑着说。
遇到问题,他总是去找张华峰、张华峰和他的全班的人都已经睡了。那个大长个子马步生的鼾声,象是从肚子底下抽吸出来似的,又长又响,使他吃了一惊,退了出来。
他自己班里的人也睡了,副班长王茂生用一条毛巾复在脸上,遮着灯光,沉沉地睡着。只有一个张德来,在灯光底下抚摸着脚板上指头大的水泡。
张德来在吐丝口战斗里受了惊吓,当时有点神经失常,近来好了。可是,本来是个闷雷性子,不爱说话,这些天来却是很爱说话了,仿佛心上的窍门给炮弹震开了似的。
“班长!你看!一门榴弹炮!打七十四师用得上吧?”张德来指着脚板上的大水炮,粗声粗气地说。
秦守本制止着他,叫他不要弄破了水泡。
“弄破了,走路痛得很!”秦守本瞧瞧张德来又阔又肥的脚掌上的水泡,摇摇手说。
“明天还要走?”张德来苦恼地问道。
“要走!秦守本躺下身子回答说。
“多远?”
“多不到一百,少不下六、七十!”
“走这多?”
“不要紧!走不动,背包给我!”
睡了,张德来吹熄了灯火。
秦守本睡不着。他心里的问题没有解决,上西南干什么呢?一下子就下去八十里!这个人的心里盛不住什么东西,有个问题,总是要求马上解决,不然,脑子里就日夜打架吵闹,弄得自己神魂不安。
王茂生翻了个身子,他当是王茂生醒了,想和王茂生聊聊,王茂生却还是舒坦自如地睡着。
外面起了大风,原就是隐隐约约的炮声,给风声完全压服下去了。
接着是猛然来到的一阵暴雨,院子里的瓦缶、瓦盆,给雨点打得发着“当当”的响声,象敲小镗锣似的。接着,屋后沟里的水,“哗哗”地响起来,随后,又突然响起“喀喳喀喳”的闪电磨擦声和震天动地的雷鸣。
整个的天仿佛要倒塌下来似的。
许多人给风、雨、雷、电惊醒过来。
秦守本却反而睡着了。他的心思给风声、雨声、雷声卷走了。他根据长久以来的经验,认为这样的天气,没有紧急的战斗任务,是不会行军的。
可是,他没有算准。这一回,事情出乎寻常的,队伍不但要冒雨行军,而且出发八九天来一直不用的军号声,突然在潮湿阴暗的天空里抖荡起来。
前后左右的村庄上,紧接着响起号声,仿佛在部队休整的地区一样。
秦守本和许多人一致地作了这样肯定的判断:离敌人远了,七十四师是打不成了。
雨势减弱,但还没有放晴的意思,天空里一片暗糊糊的阴森气象,雨还在落着。
说情况紧张吧,吹军号,白天行军,不怕暴露部队的行动秘密。说仗打不成了,情况不紧吧,要冒雨行军。而且连长公开宣布:“今天行程是八十里!”许多“诸葛亮”象秦守本、洪东才他们都默不作声,感到茫然。
队伍披着绿色油布雨衣,走在向西南去的路上。
这里的路,奇怪得有时候叫人高兴,有时候却又叫人苦恼。
忽而一段黄里发红的油泥地,一脚踩下去,就拔不起来,这只脚快拔起来的时候,那一只脚又深陷下去,必须两只脚在泥窟里歪转好久,把泥窟歪转大了,才能拔出脚来。正因为要用力摇晃歪转,泥窟也就越深,有的人就几乎连膝盖子都陷没到泥窟里去,这样,腿脚就象上了油漆似的,沾满着黄里带红的油泥。忽而又是一段稀松的黑土路,脚板简直不敢踩落上去,一踩上去,就陷得很深很深,一拔起来,腿脚就钉满了黑土;弄得腿不象腿,脚不象脚,粗肿得象个冬天的柳树干。忽而又是一段平平板板的黄沙土路,赤脚踩上去,象是踩着呢绒地毯,使人产生一种舒适的快感。可是,这样的路在这一带很少遇到,最多的是难走难行的黑土路和黄油泥路。
有人在咒骂,也有人在说笑。
因为雨还在落,手就不能不沾上雨水,同时也不免要沾上些泥土,脸上有了雨水,手便要去揩抹揩抹,因而,脸上就抹上了泥痕土迹。往往在休息的时候,大家心情舒散,便把脸上的泥痕土迹,用各种相似的形象比拟着互相嘻笑起来。你向他笑,笑他的腮上伏着一条黑毛毛虫,他又向我笑,笑我的嘴上长了黄胡髭,我又笑你的脑袋上化了妆,象戏台上的小丑。
“嘻嘻哈哈”的笑声,象沟里的水声似的迸发出来。
在一个小村子上,队伍休息下来搞午饭吃。
雨不落了,村口的水沟边坐着、站着一大排人在洗手摆脚,连长石东根坐在一家门口的小木椹子上,吃力地吸着浸湿了的香烟。
“团长来了!”有人叫了一声。
团长刘胜披着发着光亮的披风式黑漆布雨衣,雨衣上布满了许多泥水点子,象一颗一颗黄星似的。他的乌骓给泥水点子喷溅得变成了花斑鹿。四条马腿的下半截涂满了泥浆,仿佛是天生长成的黄毛腿。
这一段是沙土路,马的脚步走得很轻快,骑在马上的刘胜的身子和脑后的雨帽,微微地抖动着。
刘胜来到面前的时候,石东根立在路旁向他敬礼。
刘胜还了礼,勒住马缰,停在路上。
“你们怎么样?”刘胜骑在马上问道。
“情绪不好,怪话不少!”石东根用夸大的语调回答说。
刘胜下了马,向正在嘻笑吵闹的战士们看看,说道:
“不错嘛,有说有笑的呀!”
“歇下来说说笑笑,上了路愁上眉梢”。石东根象念快板似的,苦着脸说。
“有些什么意见?”
“为什么不开上去打七十四师?一股劲上四南,大家不明白!”
“政治工作不好做!行动意图、目的,战士不明白,我们也是糊里糊涂!”罗光接着石东根的话说。
“你们糊涂,我跟你们一样糊涂!”
刘胜苦笑着说。他徒步地向前走去,走了几步以后,忽又回过头来,向石东根和罗光招招手。
两个人赶到刘胜的身边。
“开到鲁南敌人屁股后面去,牵制敌人的兵力。我们这个团可能跟军部、师部分开,单独行动。行动意图、部署,明天到了那边,得到上级明确的指示以后,要跟你们谈的!”刘胜避着战士们,低声地对石东根和罗光说。
“正面没有我们打的?”石东根咕噜着问道。
“管它正面、侧面?坚决执行命令!”刘胜在石东根的肩膀上拍拍,也有几分感慨似地说。
从来都很乐观的罗光,这时候叹了一声,说:
“说上天,打七十四师没有我们的分,我也不舒服!”“我们给七十四师打败过的,有什么资格配打七十四师?”
石东根愤懑地鼓着嘴巴说。
“部队巩固好!别带头说怪话!”
刘胜交代两句,迈开步子走了。
石东根和罗光冷冰冰地回到小屋子门口,咽着炒高粱粉,嚼着又咸又苦的罗卜干子。
小屋的主人是个七十来岁的老大爷,端了一小盆腌辣椒给他们两个,感叹着说:
“你们真辛苦啊!”
仿佛知道这位老大爷是大聋子,石东根大声喊着说:
“心不苦,命苦啊!”
不知老大爷真的是耳聋,还是听不懂石东根的外地话,扬扬毛尖直竖的白眉走了开去。
小鬼李全呆呆地坐在门口的路边,看着从面前经过的团部的队伍,同时留心听着屋子里两位连首长的谈话:
“有一次,还是在华中,铁路南,我听野战军组织部谢部长告诉我,他说粟司令跟沈军长说过:'以后,要就不打七十四师,打七十四师,总不会忘了叫你们参加!'”罗光告诉石东根说。
“一年以前说的一句话,现在还算数?”石东根抹着嘴上的炒高粱粉,愤懑地说,他认为这是完全无望的事。
“我们部队的战斗力,陈司令、粟司令都很了解。”
“你是聋子!有人说我们莱芜战役缴获大,是碰巧,是运气!”
“让他们碰碰巧看!”
“不要痴心妄想!到鲁南打游击去吧!”
“我想写封信给粟司令,他开的支票应当兑现!”
“赶你的信还没送到,仗都打过了!再说,他会为你一封信改变作战部署?没有我们参加,七十四师还消灭不掉?我们又不是神兵神将!”
本来怀着一线希望的罗光,给石东根这么一说,也表现无望了。他的脸色,因为是刚刚伤愈之后,血色本就不怎么旺盛,现在,就更显得阴沉抑郁。
他为了排遣心里的郁闷,走到门外,到战士们聚集的地方去参加谈笑了。
李全跟着他走到人群里去,拾起小石片子,在水沟里打着水撇撇。薄薄的石片子,在水面上跳跃着,发着“唧唧”的响声,喷着小小的水花。
秦守本走到李全身边,并肩地蹲着,一边向水里抛着石子,一边低声地问李全道:
“听到什么吗?”
“我又不是你的情报员!”李全笑着说。
“团长跟连长、指导员谈些什么,你没听见说?”
“没有。”
“我看连长有点不高兴的样子。”
“我也不高兴!”
“怎么的?”
“七十四师打不成,要我们去打游击!”
秦守本的心突然地沉落下去,就象手里的石子沉落到水底下去一样。
他呆楞了一阵,把一个拳大的石块,使力地扔到水里,迈开步子跑回到班里去。
“不要说是我说的!秦班长!”
李全赶忙追上去,低声地关照他说。
心情恼闷的石东根,嘴里在哼着什么小调,突然嗅到一股强烈的气味,转头一瞧,老大爷抓着一把小小的鸡形的黑瓦壶,从小房间里走出来,笑着说:
“同志!吃一杯!淋了雨,退退寒气!”
“不吃!”石东根闷声地说。
“我旁的不好,就好吃两杯酒。自家做的,来!我们同吃!”
老大爷把酒壶放到桌上,斟着酒,指着桌边的凳子说。
“不吃!不吃!”
石东根口说不吃,眼却瞟着杯里的烧酒。酒的香气寻衅似的向他的鼻孔袭来,他的嘴唇不禁咋动起来。
他真想吃几杯解解恼闷。但是,他下过戒酒令,向军长、团长、团政委和连里的同志们发誓地宣布过“再也不吃酒了!”他站起身来,转脸朝向门外,打算出去。老大爷却好似故意地捉弄他,跟上两步,把一杯烧酒端到他的面前,笑呵呵地望着他,连声地说:
“吃了罢!吃了罢!”
“我不会吃!老大爷!”他推托着说。
“没事!一杯酒,醉不了!吃一杯,暖和。”老大爷亲切地说,还是端着杯子,笑着候着他。
石东根感到窘困,好象已经吃了酒似的,脸上发起烧来。
仿佛为了老大爷的盛情难却,他把老大爷拥向屋子里边,回头朝外面瞥了一眼,终于皱皱眉头,接过杯子,把满杯烧酒一口呷进肚去。
“会吃呀!再吃一杯!”老大爷又斟了一个满杯,笑着说。
“不吃了!不吃了!”他连连地摆着手,回身走向门外。
小鬼李全一头闯了进来,看到连长口唇润湿,闻到酒味,迎头大声地说:
“连长!你又吃……”
石东根猛力抓住他的膀子,瞪起眼睛,吓唬着,但又带着笑意地说:
“不许你乱说乱嚷!”
他嚼着腌辣椒,急步地走到门外,对司号员大声地说:
“吹号!开路!”
队伍又开始行军。
天色还是阴沉沉的,灰暗的云朵,缓缓无力地移动着,有时候现出一块蓝天,但立即又给云朵遮盖下去。
当张华峰和前后两个战士距离远了一些的时候,秦守本快步地赶到张华峰身边,神秘地告诉张华峰说:
“我们是开到西南上打游击的!”
张华峰一楞,惊讶地问道:
“谁说的?”
秦守本默不作声。他本想告诉张华峰,又怕说了,李全要吃批评,同时,他就再也不能从李全那里听到什么消息。
“你的消息真灵通!是你自己估计的,还是听来的谣言?
谣言!谣言!”张华峰一面问着,一面否定着说。
“不是谣言!”秦守本肯定地说。
“你不要信这些话!不是谣言也是假'诸葛亮'的瞎估计!”
“是连部的人说的!”
“李全?是那个小家伙说的?”
秦守本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但在神情上表现着给张华峰猜中了,掩饰不住地笑了笑。
“领导上的决定,不会错的!”张华峰了解到秦守本的心情不安,沉思了一下,拍拍秦守本的肩头,严肃地继续说道:
“庆功祝捷大会上,军长、军政委的讲话,你没听到?我们是运动战、丢了涟水、郯城、临沂,换了莱芜大捷,敌人一家伙就报销了五六万。不要乱打听,服从命令听指挥!”
秦守本听了张华峰的话,心里混沌的波动的水,渐渐地澄清、平静下来。
他回到自己班里,把腰皮带束束紧,向前走着。看来他的脚步比饭后刚上路的时候,似乎轻快得多。四七
第二天中午,队伍进入到沂蒙山区西南侧的鲁南白彦、城前一带地区。这里分布着敌军三个旅的兵力,构筑了大小十七个据点。许多村镇变成了无人区,树木给砍伐得精光,沟边、田坎、小山洼里,都是白惨惨的尺把高的树根,象是都市里桥边的水泥栏杆似的。除去穿梭不息的敌机以外,天空里连一只飞鸟也难得看到。麦子发黄了,穗子低垂着头,在风里战栗地摇摆着,“沙啦沙啦”的声音象是沉痛的悲诉。
麦子、小谷子长得很繁茂,可是谁也没有喜悦的感觉。
看不见什么人烟,看不见牛、羊、鸡、犬。令人感到寥落、荒凉。
团长刘胜和团政治委员陈坚沉闷地坐在军长沈振新的屋子里。那条长凳又瘦又矮,而且缺了一只腿,身体的重心只能偏放到凳子一这,担心地坐着。
他们是奉到师部的命令,直接到军部来领受任务的。
军政治委员坐在一个小矮凳上,军长站着,踱着平缓的脚步,副军长梁波倒坐在石门限上。只有梁波的脸上有点微微的笑容,从沈振新和丁元善的脸色上看不出什么表情来。
“是苦肉计?把我们放在这块鬼地方受苦打游击,转移敌人的目标,好让人家抓住敌人小辫子打大仗!吃肥肉!”刘胜忿然不满地猜测着说。
“可能是这样!”梁波冷冷地说,瞥了刘胜一眼。
“看我们在莱芜战役里吃了一点油水,一定要我们泻泻肚子!不怪队伍里说怪话!”
“说什么怪话?”梁波问道。
“说我们命苦呀!”
“这是你自己说的!”
梁波笑笑,安闲地抽起烟来。
他觉得这位团长有时候快乐得跳跳蹦蹦,有时候苦恼得愁眉皱脸,简直象个大孩子。
“你不去,我派别人去!”沈振新立定脚步,轻淡地说。
刘胜眨眨眼,没有作声,又有好几天没有修刮的黑胡腮,抖动了一下,转头看看沈振新的脸色。
“陈坚,你们两个人的意见一致吗?都不愿意接受这个任务?”丁元善带笑地问道,他的眼光望着屋外,仿佛随便说说似的。
“我没有说不接受任务!”刘胜沉楞了一下,看看陈坚,陈坚没有表示,也不开口,他便这样申明着说。
陈坚随即笑着说:
“我们是一致的,接受军首长给的任务!”
“七十四师上钩不上钩还不一定!上了钩,别的部队能把它钩上手,吃下去,还不是一样?依我想,蒋介石这张王牌到底摊不摊出来,还很难说!”沈振新的指头向空中点划着说。“我是蒋介石,就不干这种蠢事!把两个主力部队拚光了,还有什么本钱做买卖?跟共产党打山地战,有什么好果子给他吃?”
梁波理会到沈振新的话意,竭力地把刘胜一心想打七十四师的兴头冲淡,有意地强调七十四师不一定能打得成。如果用强光透视镜透进他和沈振新、丁元善的内心里面,可以看到他们和刘胜的内心一样,热望能够打到七十四师,并且迫切地要求着自己的部队能够参加到和七十四师的正面作战。一个说:“七十四师上钩不上钩还不一定。”一个说:“我是蒋介石就不干这种蠢事!”两个人的话骨子里,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的质素,--担心和恐怕七十四师不上钩,担心和恐怕蒋介石忽然聪明起来。其实,他们从野战军首长命令他们冒雨插到鲁南敌后来的决策,已经料想到,蒋介石正在干着愚蠢的事情,七十四师正象一条贪食的鱼,张大着嘴巴,伸向尖利的鱼钩子。只是因为战机还没有成熟,又为的使刘胜他们不致过于懊恼,才作了这样的设想和估计。
“我看,七十四师是打不成了!”陈坚天真地判断着说。他看看刘胜,他的语气和眼光都希望刘胜放弃打七十四师的念头。
“好吧!那就走啊!”刘胜无奈地说。
“给你一部电台,跟我们同你们师部同时通报!”沈振新交代着说。
“注意跟地方党、政、地方武装、人民群众取得密切联系,积极展开活动!要灵活!要保持部队旺盛的士气!是要吃几天苦的!是锻炼、考验你们!不是叫你们泻肚子!知道这个意思吗?”军政治委员丁元善严肃而又恳切地说。他和沈振新、梁波同时地走到墙壁上临时挂着的地图前面,把刘胜、陈坚他们活动的地区,指给刘胜、陈坚看着,扬起淡淡的眉梢,加重语气继续地说:
“野战军前委①把我们放到这个地区,我估计是一着棋呀!我们军党委决定把你们放到沙河边上这条狭长地带,同志!这也是一着棋呀!”
①“前委”是野战军党的前线委员会的简称,是野战军党的集体领导机构。
刘胜似乎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质,不住地摸着胡髭,但对?领会得到。他茫然地看看陈坚,用眼光问着:
“一着棋!一着什么棋?”
陈坚没有明白他的意思,还在看着地图。
“下了几天雨。山东的河道就是这样,一下雨,就流大水深,睛上几天,就干得河底朝天!估计这条沙河现在有水。”
梁波指着图上的沙河说。
沈振新接着指点着说:
“控制这条河!在河西岸活动。控制三十里长的河面,不让敌人越过河东。这里有敌人,这里也有敌人,这个据点是敌人的团部带两个营,旅部住在这里。这个地带,敌人全部兵力是一个旅,把他的牛鼻子牵住!”
“背水作战!”刘胜哼声地说。
“这个,我们算计到的!包管不叫你下河喝褪牵绷翰ㄅ淖帕跏さ募绨蛩怠?
刘胜咋咋嘴舌,辨味着梁波的话的含意。
“好吧!当一名不过河的小卒!”
刘胜下了决心,承担起想来是个艰苦而又严重的任务。但从他的语意和神情上看,他的内心对这个任务落到身上,依然是不痛快的。
“小卒有时候也有大用!”梁波笑着说。
刘胜知道这位副军长的性格和风趣。在吐丝口的师指挥所里,他领受过梁波的教导。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用眼光在梁波的脸上闪动了一下,接着就抽起烟来。
黄达走进来说,电台已经准备妥当,政治部派了一个新闻记者和一个宣传科长跟着到团里去帮助工作。
“这个地方买几个鸡蛋也买不到,没有招待你呀!'胡子'!”沈振新笑着说。
“到沙河摸鱼吃去!”
刘胜憨笑着,说了,便和陈坚辞别了军首长。
他们骑在马上,缓缓地走了一段路。
“军部为什么叫我们担负这个任务呢?”刘胜回头问陈坚道。
“是看重我们啦!”陈坚笑着回答说。
这样的话,使刘胜感到快慰,但他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他摇摇手里的马鞭子说:
“因为我们老实!老实人总是干吃亏的事。”
“爱讨便宜的调皮鬼,常常讨到的是小便宜,吃的是大亏!
我看,还是老实一点好!”陈坚带笑地说。
“我不好还价,你也不还口!”
“不是你先说'没有说不接受任务'的吗?我怎么好再还口呢?”
“我看看你,等你开口,你呀!一言不发!我不承担下来怎么办?还能真的拒绝任务、违抗命令吗?”
陈坚放声地大笑起来,说道:
“你是老实人?原来想叫我犯错误!你不能拒绝任务、违抗命令,我就能拒绝任务、违抗命令吗?好个老实人!”
刘胜的话柄给陈坚抓住了,找不出什么话来反辩,只好跟着陈坚大声地“哈哈哈哈”地笑着。
跟在他们后面的宣传科长处新闻记者,听了他们有趣的谈话和笑声,也不禁“嘁嘁嗤嗤”地笑了起来。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