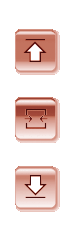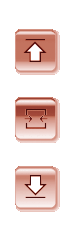|
|
|
|
七一 老书记
|
周天虹他们,又在青纱帐里苦挨了整整一天。
黄昏后,他和徐偏就在村边一棵大柳树下隐伏起来,这是同邢盼儿约定会面的地方。
等到夜静时分,才见村口飘动着一个白色的人影、那人一路走来,脚步轻捷,悄然无声。待走到近前,借着淡淡的月光一看,果然就是邢盼儿。
“他们来了!”她低声地说。
“在哪里?”天虹急问。
“就在俺家。”
说过,她头前带路,天虹和徐偏远远跟在后面,不一时就来到她家门前。邢盼儿把房前房后察看了一番,听听四外没有动静,才推开虚掩着的小黑门,让他们进去。随后又立刻插上了门。
周天虹进了北屋,一揭门帘,看见灯下坐着两个人,李捧大娘正陪他们说话。其中一个年纪稍大,生得方面大耳,满脸黑胡楂子,头上蒙着一块说白不白说黑不黑的毛巾,一副庄稼汉的派头。只是他那双明亮机警的眼睛和沉着坚毅的神态,还有怀里斜插着的一支光屁股驳壳枪,显出一种威力和神采。另一个面孔白皙的人,看去却显得文弱,且精神疲惫,无精打采。
周天虹和徐偏一进来,大娘就指着那个方面大耳的壮汉说:“这个大胡子,就是咱县的刘书记。鬼子、汉奸天天要抓的就是他。他这个头可值个万儿八干的哩!”大家呵呵地笑起来。接着,大娘又指了指另一个说:“这也是头儿,是咱们的县长傅萍同志。”说过,又介绍了徐、周二人,然后就下了炕,和邢盼儿一起到小东屋去了。
徐偏上前拉着刘书记的手亲热地说:
“刘书记!你是个大干部,我是个小兵崽儿;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我参军不久,还听过你的报告哩!那一次你讲的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刘书记哈哈大笑起来,说:“徐偏,看你说的!我不认识你,也听说过你嘛!你这个骑兵连长打得很不错嘛!”
徐偏也高兴地笑了。刘书记停了停,长长地叹了口气,感情深沉地说:
“说心里话,你们一走,我确实就像失去了靠山似的。说是度日如年,一点都不假。你们这一回来,我就有了主心骨了。……”
“刘书记,我们找到你也很不容易啊!”周天虹用尊敬的目光望着对方,“这次大家回来,可以说憋足了劲儿,都想大干一场。可是情况不熟,方针不明,斗争策略也还没有掌握住,这些都要向你讨教哩!”
刘书记名叫刘展,是个乡村的知识分子,卢沟桥事变前就入党了。在本县许多地方当过小学教师、小学校长。八路军来了以后,又在本县当过教育科长、副县长多年。对本县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阶级关系,自然环境,以及村干部的门都是冲哪里开的,他都了如指掌。今晚他介绍的敌情,使周天虹、涂偏深为满意。他把全县敌人一共修了多少据点和碉堡,以及这些据点碉堡里敌伪军的数目和武器装备,都说得清清楚楚,使他们心里亮堂多了。
“徐偏,这同你们在的时候,可大不相同了!”刘书记叹了口气说,“现在,敌人已经完成了面的占领,伪政权也普遍地建立起来。群众现在过的就是亡国奴的生活!真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啊!”
“那么,群众的情绪呢?”徐偏问。
“你们走后,是群众最难受的时期。当时流传着这么一首歌谣:
八路军进了山了,
儿童团也不撒欢了,
妇女们也不上识字班了,
鬼子和汉奸翻了天了。”
周天虹叹了口气,问:
“这个时期,你们怎么活动呢?”
刘展苦笑了一下,从腰里摸出一个烟袋荷包,装了满满一锅子烟,说:
“过去我们说,共产党的字典没有‘难’字;可是说实在话,那时候要开展工作,可真是难啊!……前半夜还好说,你去找维持会长谈话,找伪保长谈话,找伪军家属谈话,教育他们,叫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这还好说;一到后半夜,该找住处了,这就难了。因为不管是谁,他留你住下了,如果有人报告,他整个的身家性命都是非常危险的。”
“这是自然。”天虹说。
“从群众的角度说,这是自然;可是我们的同志有些人就觉得委屈了。他们说,我们舍生忘死出来抗战,连个住处都没有。我就给他们说,不要这样,谁让我们是共产党人呢!我们既当了共产党就应该多吃些苦。因此,我在高粱地里,铺上高粱叶,再弄点高粱叶一捆当作枕头,就睡得蛮舒坦。公家一天只给一斤多小米,刚够吃;一年一套单衣,挂得破破烂烂,不够穿,还得从家里拿。日久天长,老百姓看在眼里,有一天就问我:刘书记,你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一天到晚在外面跑,吃不上,喝不上。敌人还到处捉拿你,你到底为的是什么呢?群众提出这样的问题,我高兴了,这说明,我们的上帝受感动了,至少是感到了兴趣。我就利用这机会,宣传我们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意义,以及将来光明的前途。这以后我就有了住的地方,群众甘愿为我保守秘密,注意保护我的安全,自觉自愿地承担风险和牺牲。”
周天虹、徐偏不知不觉间也为这位老党员的精神所感动。周天虹问:
“刘书记,在当前情况下,你看我们怎样才能站住脚跟,打开局面呢?”
刘展略一沉思,一面抽烟,一面回答道:
“在我看,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教育群众,依靠群众,并且以武装斗争开路,把现有的伪政权改变成革命的两面政权,局面就会慢慢打开了。”
“什么,革命的两面政权?”
“是的。”刘展解释道,“就是表面上是支应敌人的政权,而实质上仍然是我们的政权,抗日的政权和革命的政权。过去一段时间,对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我们怎么能赞成两面政权呢,这不是迁就、妥协和投降吗?实际上不是这样。因为整个地区被敌人占领了,如果村政权一点也不支应敌人,群众天天都会饱尝烧杀之苦,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但是,这个地区过去毕竟是我们的根据地,党的基础和群众的基础都是相当好的,依靠我们的武装斗争和群众的支持,将这个政权改变成革命的两面政权是完全可能的。这就是当前党的指示。”
周天虹和徐偏听了觉得很开窍,真是斗争出智慧,使人感到又新鲜又有趣。周天虹又问:
“你看,我们当前军事斗争的焦点放在什么地方?”
“单打一政策。”
“什么,单打一?”
“就是镇压最凶恶、最疯狂、人民最痛恨的敌人。也就是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敌人。另外对夜间敢于出来骚扰的敌人,也要痛打。把夜间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
周天虹闷着头沉思了一番,觉得他的话很有策略性,现出赞赏的微笑点了点头。接着他把部队最近遇到的困难也讲了一遍。刘展听后,摸摸胡子笑道:
“我看,这样不行。好几百人在一起活动,就当前的情况说,太大了,太集中了。先说吃住就有问题,再说暴露了目标,打起来也不好脱离。你们研究一下,是否先分散一些,必要时再集中。我们带的那个游击队,不过二十多人,行动起来就很灵活。每个村都有可靠的堡垒户,就像李大娘家这样。这样,你这个鱼儿就游起来了。”
从老书记的话,周天虹进一步领会到毛主席说的“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的道理。同时他觉得经过全党整风,干部们很注意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真是思想作风大大提高了一步。他望望徐偏,徐偏也点头称是。周天虹问:
“这里不是住了一个日军中队吗,他的头目是谁,有什么特点?”
一提这个,刘展眉头皱成一个疙瘩,牙根咬得连下巴骨都凸起来。他把烟袋锅子乓地一磕:
“这个家伙,可真是头顶长疮,脚跟流脓——坏透了!他叫酒井武夫,是个极端残忍的家伙。杀了人,取出苦胆,用油纸包着吊在房檐上,晾干,每天切一小块儿用米纸包着吃……”
“你说什么,吃人的苦胆?”周天虹惊问。
“是的,杀了人,他就取出苦胆来。”
“这是为什么呢?”
“开始我也不明白。后来我请教一个老中医,他说,《本草纲目》上讲:有等残忍武夫,杀人即取其胆和酒饮之,说是能令人勇,此乃军中谬术,君子不为也。”
“哦,原来这些武士还是胆小啊!”
天虹轻蔑地一笑。刘展继续说道:
“要说这个人的特点,只有一个,就是无尽无休地强奸妇女。过去,他在山西盂县上社一带驻过,每天都要强奸三四个妇女。当地人恨透了他,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他‘毛驴太君’。这人长得高而瘦,长脸,样子也像个驴。他的胡子总是刮得精光,嘴边和两腮呈蓝色,样子很怕人。他一出来,妇女们就像大难临头似的鬼哭神嚎地躲藏。他还偏爱串门。在上社,他命令全村老百姓把房屋院落打通。他从炮楼下来以前,先通知全村妇女把衣服脱光,然后才下来任意奸淫。奸淫以后,还让全村男女在一起光着屁股跳舞,他搬把椅子坐在那里哈哈大笑地观看取乐。你说,这样的人还像个人吗?”
“真他妈比畜牲还要畜牲!”周天虹咬着牙齿狠狠地骂道。
“这头毛驴连他的亲信也不放过。”刘展继续说,“有一个汉奸想讨好,请毛驴到家里吃饭,没想到酒菜都摆到桌上了,毛驴倒没有看他的酒菜,而一眼看上了他的漂亮媳妇,马上拉她就要上炕。汉奸一看慌了,连忙跪下来哀求,毛驴哪管这个,把手一摆:‘这个,没有的关系!’就在炕上当面宣淫了。……”
“叫我看,这个王八蛋是自找!”徐偏说。
“最叫人可恨的,”刘展接着说,“是有一次毛驴强奸了一个十三四岁的闺女,他还用指挥刀逼着少女的父亲与女儿当面性交。你说这个王八蛋究竟是什么心理呢?”
“在北岳区,我常常听到这样的事。”天虹说,“有一年敌人扫荡,在阜平一个地方就发生了六起。这些兽类,让婶母同侄子,叔叔同侄女,爷爷同孙女,甚至父亲同女儿,当着他们的面性交,看着取乐。这些王八蛋究竟是什么心理,实在叫人不可理解,也无法理解。这种心理,无非是加别人以最大的痛苦,最大的羞辱为最大的愉快。我只能说这是一种超兽性的兽性心理。因为野兽最多不过把你吃掉完事,决不至于如此卑鄙。但是这种卑鄙的心理,是从什么条件,什么卑鄙的文化培养成功的,我实在想不清楚,只能请将来的历史学家细细研究。至少,在我看这不仅是加到中华民族身上的耻辱,也是日本民族的耻辱。”
刘展点点头,又接着说:
“这个‘毛驴’自调到这里,兽性更加猖狂了。他先是在沙河桥据点,每天向周围的村庄索要三个妇女,如果送不到,他就要出来放火杀人。最后驻在城里,又发展到专门索要十三四、十四五岁的少女,这一来,周围的百姓可就受了苦了。毛驴现在常常出来讨伐、扫荡,除了抢粮、抢物,抢掠妇女也是他的重要目的之一。
听了这番话,周天虹和徐偏,牙齿都咬得嘎蹦响。徐偏说:
“这样的兽类,如果我不亲手打死他,真是死不瞑目!”
沉了沉,周天虹问:
“这地方的伪军头目是什么人?”
“咳,臭鱼碰上臭虾,这个家伙更坏得出奇。”刘展说,“据说他是今年春天投降过来的叛徒。在冀西曾当过八路军的什么副支队长,以后犯了错误,受了处分,嫌给他的官小,跑过来了。敌人就给了他一个‘反共救国军’支队司令的名义。在附近两三个县活动。这个家伙无恶不作,我看比一般的汉奸要厉害得多!”
周天虹心中一惊,忙问:
“他叫什么名字?”
“高凤岗。”
“哦,果然是他!”
“你认得他吗?”
“认得,还是我的同学呢。”周天虹点点头说,“这家伙个人英雄主义十足,但我没想到他会走到这一步。”
“嘿,他可不同于一般的伪军。”刘展说,“这里的伪军,一般有这样几种类型:一种是过去的土匪,没有什么政治头脑和政治背景,只图吃喝玩乐。他们所以投靠敌人,主要是保住地盘和权势。再一种是土豪恶霸,借日本人的势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勒索群众,鱼肉乡民。而高凤岗和这两种都不同。据说,他到北平秘密加入了国民党,决心同共产党对抗到底。这种伪军比其他伪军都难争取,因为他是内心里仇恨共产党的。因此群众管他叫‘铁杆汉奸’。”
“他在这里都干了些什么?”
“这可多了。”刘展说,“他来这里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所有的抗日军人家属,门口都要挂上一个灯笼。……”
“挂这个干什么?”
“那意思就是,凡是挂灯笼的人家就是‘匪属’,而既是匪属,所有的伪军、汉奸都可以进去强奸。这是合法的,不犯罪的!”
“哦!”周天虹惊奇地瞪大了眼睛。
“他干的第二件事,就是残酷地捕杀、活埋抗日干部。因为他熟悉我方的情况,熟悉抗日干部的活动规律,常常出其不意地偷袭、捕捉,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咱县的区村干部就被捕被杀近百人,县里的干部也损失不小。第三,他还严密地监视、控制伪组织和伪军,切断他们与我们的联系。原来在伪组织和伪军里,我们做过不少工作,也有不少人同我们有联系。他来以后,杀掉了一些,其余的就不敢动了。为了彻底切断这种联系,他把城外的伪军家属也迁到县城。第四,他还利用毛驴太君的淫欲向他献媚,随时掳掠妇女……”
听了刘展的谈话,周天虹不平静了。一个高而瘦、长着驴脸、两颊和嘴窝发着蓝色的“毛驴”,一个他熟悉的目空一切、自命不凡、自我扩张的狂徒,这两个面目狰狞的恶魔,都活脱脱地站在他的面前。他的心感到极度的压抑、愤恨,有一种要爆炸的感觉。他觉得当前,就是这两个恶魔站在人民的头上,如果不打死他们,消灭他们,怎么能对得起这里的人民呢?
刘展说过,就笑眯眯地以兄长的神情,望着这两位年轻的兄弟。对今晚的谈话,周天虹露出非常满足的神情,盘旋在脑海的模糊不清的问题,已经清爽了许多。真是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了。
“傅县长还有什么指教吧?”周天虹转过头问。
“没有,没有。”傅县长双手一推,淡淡地笑了一笑。他终席未发一语,仍然显得是那样的疲惫。
“老周,你今后就是咱们县委的成员了。”刘展笑着说,“今后大家就不要客气了吧!”
刘展说过,把烟袋荷包挂在腰带上;随后把那支光屁股驳壳枪掏出来擦抹了两下,又重新插到腰里。然后同大家握手告辞。看起来还有什么重要的事在等待着他。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