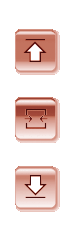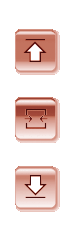|
|
|
|
四五 在生与死的边缘
|
漫长而单调的医院生活是很烦人的。周天虹经过大半年的休养,伤才渐渐痊愈。不料行将出院时,又患上了疟疾病。这种病俗称打摆子,冷起来如冰水浇头,浑身战栗不已,即使盖上两床棉被也不顶事;热起来高烧四十多度,烧得人昏昏迷迷,死去活来。而且这病每天或隔日必来一次。治这病的特效药倒有,名叫奎宁,但在敌人封锁下很不易得。边区自造的疟疾丸效果又不理想。这样,很快就把一个身强体壮的周天虹折磨得面黄肌瘦,衰弱不堪。正在这时,敌人对北岳区空前残酷的“扫荡”到来了。
这次大“扫荡”,是由新上任的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策划的。他一上台,就立刻集中五个师团、六个混成旅团,加上一部分伪军共七万之众,向晋察冀的北岳区开刀了。他把这次战役称为“百万大战”,意思是要报复八路军的“百团大战”。为了消灭边区的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他采取了“铁壁合围”、“梳蓖式清剿”、“马蹄形堡垒线”和“鱼鳞式包围阵”等战术。从一九四一年八月中旬开始,在平汉路保定至石家庄以西的这块数百里山区内,处处烈焰腾腾,烟火四起,枪声交织,血流遍地,人民陷于深重的灾难之中……
说起敌军的“铁壁合围”,那其实就是多路分进合击,不留任何空隙地将八路军主力严密包围加以聚歼。而八路军的中高级指挥员,都是多年打游击的能手,不管敌人如何来势汹汹,大致能不早不晚地跳出合击圈。当然这是极为凶险的事,不妨说也是一种艺术。如果时机掌握不当,跳得早了,就有被敌人发觉的可能;如果跳得晚了,就要陷入灭顶之灾。一般说,我们的部队多半能闯过这道险关。但是第二步敌人的“梳蓖式清剿”,对干后方机关、学校、医院等非战斗单位以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就很难度过了。
反扫荡开始以后,周天虹就随着医院的一个休养所行动。这样的单位,除了轻伤员就是重伤员,少数几个医护人员哪能照顾周全,只有靠大家相互扶持了;加上没有武装掩护,只能凭所部负责人的机警善断及时转移。
现在,周天虹他们正隐蔽在易县西北的玉皇山下。山下有一条险峻狭窄的山沟,名叫玉皇沟。一般越是偏僻险峻的地方,越容易成为敌人“梳蓖清剿”的目标。他们在这里暂时安顿了几天,眼看敌人就要把清剿的重点转到这里。于是所部决定向另一条山沟转移。
此刻时已近午,伤病员们提前吃了午饭,背起行装,在崎岖的山径上开始行进。可是出了玉皇沟门不远,侦察员回来报告,说从龙泉关下来的敌人,正在大路上运动,已经把路隔断了。所部当即决定,伤病员暂时拐进一条小沟里隐蔽起来。这时周天虹忽然觉得脊背上似有一股冰流悄然而下,显然这是疟疾袭来的征候。他急忙吞下几粒边区自制的黑药丸,然而已经迟了,何况没有水送下去,只停留在喉管里。果然,不一刻疟疾原虫的恶作剧就发作起来,剧冷剧热闹得不亦乐乎。周天虹只好闲着眼躺在山坡上默默承受。这状态持续了几个小时,迷迷糊糊间,只听耳边有人喊:“走了,走了,敌人已经过去了!”他睁开眼,果然所有的伤病员都背好了行装,准备转移。他挣扎着站起来,勉强随着队伍向前走去。队伍越走越快,显然要乘敌人大队过去的间隙穿过大路。周天虹跟不上了。两条腿像有千百斤重,每迈出一步都喘息不已。加上口渴如焚,嗓子眼儿像要生烟起火一般。幸好路边正有一条清澈的溪流,淙淙有声,格外诱人,他就全身伏倒在溪边痛饮起来。等到他站起来,抹抹嘴想再追赶队伍时,队伍已经无影无踪看不见了。
他坐在溪边一块大青石上,略想了想。此时已经暮色低垂,部队行动甚疾,又如何能赶得上呢?倒不如干脆休息一下,等疟疾过去,体力稍有恢复再作道理。抬头一望,在玉皇沟门的高坡上,有几户人家,他就站起来强打精神向高坡上爬去。
村里的老百姓大部分都到深山里逃难去了。周天虹进了一座农家小屋,空空落落,只有两个军人在那里坐着。他认得其中一个是卫生部的丁干事,人生得机警灵巧,能言善辩,会拉胡琴、唱京戏,还能画上几笔。平时常下来帮助开展文化娱乐工作。另一个是位副连长,名叫张宏,山东人,生得人高马大,外号张大个子,因长时间发疟子瘦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他生性木讷,见人只是笑一笑,不多说话。周天虹问他们为何掉队,丁干事用棍子指了指他的脚,说脚坏了;张大个子有气无力地说,他在打摆子,原来和周天虹同病相怜。最后,丁干事说,那咱们就在一起活动吧,大家也好有个照顾。
这时,天虹的的高烧未退,仍然浑身无力,在炕上一歪就睡着了。哪知刚睡下不久,就听外面响起了几声枪声。几个人出门一望,见沟外的老百姓纷纷向沟里逃难。有的扶老携幼,有的赶着毛驴耕牛。显然,已经发现了敌情。周天虹他们也不得不背起背包、米袋,沿着山径,走向玉皇沟的深处。
在狭窄的山谷里,夜色越来越浓,山岭黑得就像炭块一般。隐在深草中的山径已经模糊难辨。为了夜间行动有个助力,周天虹和张宏两人也学丁干事的样子,在路边折了两根树枝作为拐杖。三个人的拐杖在石头上发出笃笃的声音。彼此间有时交换一两句话。但是走着走着,两个人发现,既听不见丁干事说话,也听不见他的拐杖声。他们向后面喊了几声:“丁于事!丁干事!”后面并没有回应。不禁心里猜度:也许了干事顾虑重病号的拖累,已经躲到别处去了。
两个人相互扶持着向上攀登。老实说,在这样黑的夜间,走这样的山路,一半是凭微弱的星光,一半就是凭走山路的经验了。他们本来想爬到玉皇顶那个最险要的去处隐蔽起来,哪知刚刚爬到半山时,突然间,山顶上响起一梭子机枪声。这枪声,在这样的深夜,在这样的深山里,不知怎的显得这样惊人。“糟糕,走到敌人的枪口上来了!”周天虹吃了一惊,连忙招呼张大个子往回返。在回返途中两个人在夜色中失散。这时只剩下周天虹孤零零一个人了。
看来,敌人明天在这一带搜山是无疑的,只有找一个隐蔽的地方栖身才是。周天虹这样想着,就在山坡上寻寻觅觅地摸索起来。在巉岩石缝里,不是密匝匝的荆棘难以进入,就是悬崖壁立难以登攀。寻了好长时间,他的双手早已刺破多处,摔了几跤,还没有找好匿身之地。走着走着,在星光下忽然发现有一个好像蛤蟆嘴般的石崖,用手一摸,里面是一个石洞。天虹试试探探地爬进去,里面恰可容身。他从挎包里摸出火柴,用火光一照,洞里还有一块比较平的大石头,石头上毛毛烘烘,似乎有野兽卧过的痕迹。人说这条山沟里,狼虫虎豹都有,也就不足为怪了。
经过这番折腾,估摸已到后半夜了。山地的深秋之夜,近似冬日,一阵阵山风袭来,不禁全身瑟瑟战抖。天虹想,纵然遇到险境,如果不休息好,没有一点精力,还是难以应付的。这样想着,他就把被子打开,中间一折,穿过一条带子,像斗篷一样地披在身上。顿时觉得温暖了许多。可是这时又觉得饥渴难忍。本来早已饥肠辘辘,不过因为情况紧张没有注意罢了。他解开米袋,这里装的一半是小米,一半是干粮。所谓干粮,就是反扫荡前他的自制饼干,那是玉米窝窝头切成的云勾状的薄片晒制而成。他取出这些薄片送到嘴里,方才发现其坚固程度有如顽石,吃掉一片要花不少力气。何况更重要的是水,没有水那是难以下咽的。而要取水,必须下到深山下的河沟里,而喝过水,在如此漆黑的夜里,是否还能找到这个神秘的洞口,那就很难说了。想到此处,天虹只有望而止步。这时他对火烧火燎的焦渴,只有克制、克制再克制,仅勉强啃了几片他的自制饼干,就昏昏沉沉地入睡了。
这一夜竟睡得非常好。自然又做了许多的梦。大部分的梦都是找食物、找水,这无疑是过度饥渴的反应。其中当然又梦到高红,高红又到医院来看望他了,两个人在幽静的密林中说着甜蜜的话,最后是又长又深沉的吻。这自然是上次相见的印象太深刻了。天虹醒来时,晨光已经透进洞口,望望周围,那野兽的毛茸茸印迹和蹄痕更加清晰。此情此景,反而更加思念高红,不知在如此凶险的环境中她身在何处。
随着白天的到来,也就意味着凶险时刻的临近。一句话,生死存亡就决定在今天。周天虹很想走出洞口,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又怕暴露目标招致更大的灾祸;如果在洞里隐匿不动,岂不是干脆等死吗?想来想去,觉得难以抉择。在战场上固然随时都有生死的考验,但手中有武器,身边有战友,上级有指挥,主动权是操在自己手中。而现在却像圈中任人宰割的牛羊一般,不知何时饮刃而亡。想到这里他的心忐忑起来。他懊悔自己不该脱离部队、脱离集体,以致陷于这种难堪的境地。
他听听洞外,耳边只有呼呼的风声;望望洞外,只能望见洞口前山草不停地摆动。他判断外面的天色是阴沉的,不然洞里何以这样的阴暗呢?果然他的判断不错,不一时外面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来。他高兴了。把茶缸子伸出洞外迎接雨水,以便解除焦渴。同时想如果雨再大一点,也可以阻止敌人搜山。哪知道接了半天雨水,一口就喝完了。时间不大,雨也停了。他只好凝神谛听着外面的动静,静等着凶险时刻的来临。
突然间,山谷里传来几声枪响,接着是日本人特有的野里野气的叱骂声,随后便寂然了。又隔了好长时间,附近山坡上传来杂乱的脚步声,橐、橐、橐、橐地向山上走来。仔细听,很像是日军笨重的军靴在山石上发出的声音。脚步声愈来愈近。周天虹的心紧缩了一下,心想:“最后的时刻到了!”他伸手一摸,从挎包里拽出一颗手榴弹来。这是反扫荡前夕,休养所发给每一个伤病员的,而且只有一颗,一是为了防身,二是为了保全自己的革命气节。想不到现在真的用上它了。周天虹立刻将木把上的盖子咬开,将手榴弹紧紧握在手里。
可是,脚步声却没有继续靠近,而是转向山顶去了。不一刻就听见山顶上嘀里嘟噜地喊叫了一阵,声音十分粗野。接着是中国话的翻译:“太君说喽,把那两个八路带上来!”想来这是翻译官了,他的声音也很威严。过了一会儿,大约是人被带上来了。下面是生硬的中国话问:“你的什么名字?”没有回答。接着又问:“你的什么干部?”仍然没有回答。显然,“太君”急了,哇里哇啦地叫了一阵,又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你的不说话,死了死了的!”这时回答的只是一声冷笑,还有一句:“狗强盗,你们没有资格问我!”周天虹听出,不是别人,正是失散的副连长张宏的声音。想不到这个木讷少言的人说得这么利索。显然“太君”暴怒了,大声命令道:“挑了他!”接着只听张宏轻微地哎哟了一声,想来是被结果了。
周天虹在洞里轻轻地叹了口气,对这位战友不禁升起一种深深的敬意。接着,日本军官大概审问第二个人了:“你的什么名字?”只听下面接着回答:“我叫丁立。”声音是温顺而恭谨的。日军军官又问:“你的什么的干部?”又是一声温顺的回答:“干事,文化娱乐干事。”周天虹登时心里一惊,这不是昨天晚上见面的那个丁干事吗?他怎么也被捉住了?再往下听,日本军官又问:“这里八路藏的有?”丁立回答:“有,有。我可以领你们去找。”接着是日本军官一阵哈哈大笑:“真的?你肯帮我们的干活?”下面又是一句:“太君,我愿意为皇军效劳。”话音刚落,日本军官就嘎嘎地笑起来:“你的顶好,大大的良民!”听到这里,周天虹不禁怒火攻心,狠狠地骂道:“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当汉奸了!”与此同时,他感到,自己的处境更危险了;如果他要真正领着敌人一路搜来,自己无论如何是躲不过去的。这时,他忽地想起,自己的日记本上还记了些秘密的以及一些自己感情世界的东西,这些绝不能落到敌人手里。于是他立刻从上衣口袋里取出来,撕了个粉碎,埋入土中。同时为了让活着的同志们了解自己的忠贞,他取下钢笔,在金黄色的手榴弹把上写下了如下的文字:“为共产主义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周天虹。”然后用舌尖舐出雪白的手榴弹弦,套在手指上。此刻,他听见笨重的军靴声从山顶走下来,橐、橐、橐、橐,越来越近,而且听见那个名叫丁立的人尖尖的喊声:“皇军来搜山了,已经看见你们了,藏是藏不住的,快快出来投降吧!”周天虹把手榴弹攥得更紧了,心里狠狠地骂道:“来吧,来吧,你们这些汉奸,你们这些强盗……”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