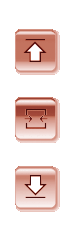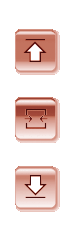|
|
|
|
三一 杏花营(一)
|
高红结束了慰问工作,回到专区妇救会;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就被找去参加地委书记召集的紧急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复查减租工作。地委书记神色严峻地说,现在边区的减租减息工作,虽然早已实行,但是有些地方水过地皮湿,贯彻得并不彻底。尤其是封建势力大的地方,还存在着明减暗不减的问题,贫苦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减轻。这样,广大农民群众就不能发动起来,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敌后抗战就不能坚持下去。因此要立即展开减租减息的复查工作。
会后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进行了分工。高红被分到一个叫杏花营的村庄。
杏花营是贴近山边的一个村庄,约有五六百户。高红虽然去过几次,但还不大熟悉。临走她特别请教了农会主席老常。老常嘱告她:那村子地主势力颇大,过去政权一直把持在地主手里;现在几经改选,村干部虽是中农出身,但看风使舵,常常看地主的眼色行事。要她到那里特别当心。
一切准备妥当,高红就煞上她的皮腰带,背上小背包,挎着小挎包出发了。她现在穿的是便装,但是仍保持着洒脱的军人风度。走起路来,步伐轻捷,二三十里路像玩儿似的就赶到了。
杏花营从房舍看,是一个阶级相当分明的村庄。村东头是地主李大官人家的庄园,高大的院墙,清堂瓦舍,几乎占了小半道街。再往西来,则是较一般的房舍,多半是中农和富裕中农,最西头边边沿沿,房舍低矮而破败,那自然是贫农和佃户们的穷窝窝了。高红一面走一面盘算:这次的任务不同寻常;如果住到富裕农民的家里,那就难以了解到真实情况了。她这样想着,就在村西头一家柴门前停住了脚步。
她手攀柴门一望,院子里有棵大枣树,树底下坐着一个驼背老人,正守着一大堆荆条子,在那里低着头编制筐篓。她知道这人名叫周二,是这村最穷苦的人家之一,家里只有两间北房,一间小东屋,全歪歪扭扭,破旧得不像样子。高红轻轻地叫了一声:“周大伯,您在家呀!”那老人这才抬起头来,向这边望了一望,接着站起身咯咯吱吱地开了柴门,柴门上挂着的小铜铃,也丁丁零零地响了一阵。
“大伯,您认识我吧?”高红带着笑和蔼地问。
“啊?面熟熟的,您是区里来的吧?”那老人猜度着,一面把她让了进来。
高红打量这老人,实际并不太老;因为背驼得厉害,同高红说话还得仰着脸儿。他穿着一件破布衫,露着半个肩头。两只老山鞋踢里踏拉也破得不像样子。高红从心底里腾起一种怜悯之情。
听见院子里有人讲话,女主人也从小北屋里走出来。她看去有四十多岁,人长得很清爽,一只手端着簸箕,一只手握着一把新掐下来的还在发青的麦穗在簸箕里揉搓着。
“大娘,您还认识我吗?”
“咋不认识?”她笑盈盈地说,“我还听你在戏楼前面讲过话哩!”
“大娘,您看我在您这儿住几天行吗?”
“啊哟!在我这儿?”大娘有点意外,以为是玩笑话,也笑着说,“你看我这个老鸹窝能住得下你这个金凤凰吗?”
“金窝,银窝,我都不住,我就是要住在你这个穷窝儿。”高红呲着一口白牙笑着。
“你只要说行,那就行。”大娘说着,就帮着她取下背包,然后拎到屋里放在炕上。一边唠叨着说,“你看我这穷窝脏的!我这家只有八路军住过两次,地方干部一次也没有来过,一到村里就到高门大户去了。”
高红眼往四下一扫,屋子里确实又脏又乱。土炕上放着的两床破印花被,说蓝不蓝,说黑不黑,不知道有多少年没有拆洗了。屋里除了一张小木桌,一张条凳,墙角里一口破缸,几个破旧瓦罐,几乎没有什么东西,真是一贫如洗啊!高红到这样的人家并不多,今天看到这些,不禁惊叹中国农村的贫穷。
大娘是个热心肠,见高红决意留下,就立时上了炕。她习惯地跪在炕沿上把两只半大脚一磕,然后把一些杂七麻八的杂物和自家的脏被窝归拢在一头;接着抄起笤帚扫起炕来。高红也连忙下手,打扫屋子,归拢东西,不一时就把一间小屋子拾掇得干干净净。大娘把高红的背包打开,铺在一边,亲热地说:“闺女,你跟我就伴吧,到晚上我把那老东西还有我那小子都赶到小东屋去。晚上睡不着了,咱们娘俩还可以拉个闲篇儿呢!”
这时,柴门上的小铜铃响了两声,院子里走进两个人来。高红走到院子里一看,原来是本村的村长,后面跟着一个小伙子。
“哎呀,高同志,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这个四十多岁,略略有些秃顶的汉子一脸埋怨地说。
“我随便找个宿儿。”高红笑着说。
“快跟我走吧,房子我早就给您找好了,那地方儿宽敞,吃喝、找人谈话也方便。”村长一边说,一边跟那小伙子丢眼色,“你还不快去,把高同志的东西拿上!”
“不,不,我就在这儿住了。”高红连忙拦住,口气很坚定。
“那怎么行?”村长皱着眉头,“这个地方……”下面的话村长没有说出来,停顿一会儿才接上说,“过去,上面下来的人,不是住在东头,就是住在街中间,那里离村公所也近。”
“村长,你就不要说了。”高红脸色严肃了,一面从口袋里取出十天的粮票,“请你帮我领出十天的粮食送到这里。有事我再找你。”
村长只好接过粮票,涨红着脸敷衍了几句,走出去了。
说实在话,现在最令这个农家主妇犯难的问题,就是吃饭问题。她不时地抬起头望望太阳,太阳已经转到正南方去了,是该做饭的时候。可是做什么饭呢?能让上边下来的人吃自家那种不像样的饭食吗?别说违背待客之道,自己心里也过不去。可是,现在正值春荒季节,瓦罐里的米只剩下不多几把,穷人赖以为生的瓜菜也没有下来。她望望墙头的北瓜,正开着一片黄花,结出的小瓜还不如小孩的拳头大。又怕客人看出自己为难的样子,只在心里叹气。
这妇女盘算了一阵,假托有事就拿起一个小簸箕走出去了。待了好大一阵子,才见她借来了二斤白面端了回来。
“大娘,你弄这个干什么?”高红惊愕地问。
“这个你就不要管啦!”大娘说着喜滋滋地做饭去了。
正午时分,饭做好了,周二的儿子也回来了。这孩子看去已有十七八岁,蒙着一块白毛巾,显得甚是英俊。原来他一大早起就背着几个筐篓前去赶集,也是为了换几个钱度过春荒。
开饭时,大娘给高红搬了一个小炕桌放到里间屋炕上,两张圆圆的白面饼放在算帘里。不一时又打了两个鸡蛋放在小铜勺里炒了炒也端上来。高红一看,周二一家则每个人捧着一大碗黑糊糊的东西蹲在外屋里。看见这情景,高红立时涨红了脸,说:“这怎么行?”一面说,一面跳下炕来,把两张白面饼掰成四份,一人一份放在他们的碗里,一小盘鸡蛋也强行给他们分了。大家争争让让,还掉到地上很大一块。
“闺女,你怎么能这样?这是待客,怎么能每个人都一样呢?”大娘显然带着不满责备地说。
“我不是客,”高红带着笑说,“你就把我当成你的闺女看吧!”
高红说着就抄起一个大黑碗,从锅里盛了满满一碗吃起来。说实在话,开头儿只看见碗里黑糊糊的,并没有看出是什么东西。吃了一阵儿,才辨出是山药干、萝卜干、胡萝卜缨子和玉米面搀和成的糊糊。那种味道和气息都是令人难以下咽的。高红生来并没有吃过这样的饭食,甚至觉得难以承受。但是在群众面前,她还必须装作乐呵呵的样子,使人觉得她吃得很香甜。而在这同时,这一家贫农,尤其是家庭主妇则怀着一种深深的负疚的心情。
“我不过偶尔吃了一顿这样的饭食,而他们,长年累月不就是吃这样的‘饭’吗?他们是怎样忍受的呢?”高红边吃边默默地想,油然生出一种深深的同情。
她一边嚼着那涩巴巴的萝卜干,一面偷眼望着周二,望着他那满是粗茧的大手,那苍老的面颜和深深的驼背,问道:
“周大伯,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我今年四十三了。”周二说。
“四十三?”高红不禁眉毛一扬,吃惊地说,“你的背怎么驼成这样了?”
“你不知道,同志。”周二停住筷子缓缓地说,“我从小就受苦。租种李大官人家几亩地,到我是第五辈了。年年都不够吃。我从十岁起,就腰里捆着绳子上山割荆条子。天不亮就动身,到晚上才回来。荆条子这东西沉哪,我一背就是五六十斤,走的又是山道。还不到二十岁,我这背就开始驼了。以后一背就是一二百斤,我这背就压得再也直不起来了。”
高红叹息了一声,又问:
“你家祖种了李大官人家多少土地?”
“就算二十亩吧!”
“每年出产多少?”
“碰上好年头儿,能打十三石五斗谷子。”
“要拿多少租子呢?”
“要拿十石五斗。”
“咦!要是坏年头儿呢?”
“坏年头也不能少。你当了裤子,卖了儿女也得缴租。”
高红愣住,不言语了。停了半晌,才问:
“八路军来了以后,不是实行二五减租了吗?就是说从原有的地租中减去百分之二十五,你们按规定减了吗?”
“这个……减了吧。”周二神情惶惑,支支吾吾地说。
高红看见他这个样子,忙追问了一句:
“是按规定减了吗?”
“是,是,按规定减了……”
“减了多少?”
“我记不大清楚了。”
周二刚说到这里,儿子瞪了他一眼,把筷子往碗沿上乓地一摔,说:
“爹,你怎么不说实话?谁给我们减了?”
周二当场红着脸,嗫嗫嚅嚅地说:
“是他们要我这样说嘛!”
“大伯,是谁让你这样说呢?”
“是李大官人家传下了话:上面如果来问,就说按规定减了;要是谁说露了嘴,就把地立时收回……”
高红听到这里,才知道问题果然严重。心里想道:我们的基本群众,如果仍然呻吟在封建剥削的重压之下,怎么能抬起头来抗战呢?她沉吟了一会儿,接着问周二的儿子:
“其他佃户也都是这样的吗?”
“国强,你知道你就给高同志说说。”大娘发言了。
这个青年人没有接触过女人,一直低着头抱着大黑碗吃饭。听见高红问他,才略略抬起眼望了望她,温顺地答道:
“是的。”
“你能找三五家佃户,到我这里谈一谈吗?”
“行。”国强说。
晚上,周二把小东屋的柴草、杂物收拾到一边,露出一铺小炕,父儿俩睡在小东屋里。高红就在大娘身边睡了。两个人越拉越亲热,大娘就把自己一切不便告人的家世都对高红说了。她说,她原来是外乡人,因为年景荒旱,丈夫活活地饿死了。从此自己无依无靠,不得不㧟着要饭的篮子外出逃荒。有一天晚上,就住在本村的破庙里。周二见她十分可怜,就把她领回家,两个人跪到地上磕了三个头,就算成了亲。她给他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因为荒年交不上租子,就把两个女儿卖了。大娘说到这里,抽抽搭搭哭了好大一阵子才渐渐睡去。
高红却一直没有睡着。想起自己生活在人世间这么多年,对于穷苦人的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深的感受。她想起自己的地主家庭,想起自己每年暑假回到家里,过的是何等富裕的生活!虽然也到穷人家去过,看的却比较表面,哪里会想到挨饿是什么滋味?卖儿卖女又是什么滋味呢?即如今天吃的饭食,简直还比不上自己家里喂猪喂狗的饭食!而他们这些朴实可敬的人,却是真正为这世界生产财富的人,流血流汗维系这个世界得以生存发展的人!自己能够活得这么大,不正是靠了他们的血汗吗!她想到这里,从内心深处感到深深的愧疚。直到今天的夜晚,她觉得自己在延安学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才算真正在自己的血肉和生命裹扎根了。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