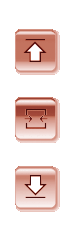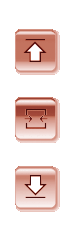|
|
|
|
二五 来到晋察冀(二)
|
那人领着周天虹他们进村不远,就看见小土地庙前面,有七八个老头儿正坐在大石头上聊天。中间有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军人,正兴致勃勃地向他们讲着什么,人群里不时扬起一阵阵笑声。一个白胡子老头儿站起来兴奋地说:
“老马,听了你这话,我这心就有了底了。以前老觉着洋鬼子厉害,现在看只要打持久战就行。咱们中国这么多人,干吗叫几个洋鬼子骑着脖拉屎呢!”
老人说过,把长杆烟袋往老山鞋底上乓乓一磕,从烟荷包里满满地装了一锅烟,用手掌把玉石烟嘴儿一抹拉就递给那个军人。周天虹注意到,那个叫“老马”的军人,既不推辞也不犹豫,恭恭敬敬地接过,立刻含在嘴里抽起来。巴哒巴哒,烟锅里冒着一股悠然的青烟。
“他就是你们找的马社长了。”那个中年汉子一指,同时高喊了一声:“老马!”
老马应声回过头来,也习惯地把烟锅子往鞋底上一磕,奉还给那个老者,然后走过来。
周天虹注视着这位老马,蓦然一惊,心想:“这不就是我的老师欧阳行吗?他怎么又姓马了呢?”天虹想起以前他那黄皮寡瘦的模样,那破毡帽低低压着眉际受压抑的神气,跟现在可大不一样了。现在,他脸颊红润,脚步轻快,真潇洒得多了。
这时,对方也似乎注意到他,远远地叫了一声“天虹!”接着就快步走过来把他拥抱住了;还不断地拍着他的肩背。周天虹不禁一阵激动,嗓子眼热辣辣的,“欧阳先生,要不是你引导我,我怎么会来到这里呢!”说着,止不住流下了两行热泪。
“我不是说过吗,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欧阳行亲切地笑着。
接着,周天虹把来者一一作了介绍,并再次指着欧阳行说:
“这是我常向你们提到的欧阳先生,他就是引导我参加革命的人!”
“不要再提什么先生了,我们都是同志,今后我们就在一起干吧!”
欧阳摆摆手,笑声朗朗地说: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现在部队正像滚雪球似的发展,到处都喊着要人。我这里人也缺得很哪!听说你们来了,我跟聂司令员好说歹说,才分给我一个!”
他一面说,一面带着大家向一家农舍走去。
“欧阳先生,”天虹一时改不过口来,仍旧这样称呼他,“您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噢,这地方光许你们来,就不许我来?”欧阳幽默地说,“天虹,请你原谅,我跟你实说,当你从家乡出走的时候,我也有心同你一起到延安去。可是一想我离开党多年,寸功未立,又有何颜面见江东父老?我总想组织一支游击队,拉到党的队伍里来。你走以后,我就跑到一个偏僻的县城里,没有想到我组织的游击队刚刚有点眉目,就被国民党县党部的老爷们知道了,他们就要抓我。幸亏有人透露了消息,我才连夜逃出来。这些人就是这样,他们不抗日,还不许别人抗日……”
“以后呢,以后您到哪儿去了?”
“接着我就到了山西前线。很快太原又失守了。听说聂司令员到了五台山,要在这里开辟根据地,我就集合了几个流亡学生赶到五台。聂司令员了解了我们的来意,表示非常欢迎。但是他说:‘在敌后创建根据地,这是十分艰苦的事,你们是些文人,能够吃得下这个苦吗?’我就说:‘聂司令员,你就放心吧,对于未来的艰苦和风险,我是有充分准备的。一路来的路上,我尝试了各种野草,哪一种是能吃的,哪一种是不能吃的,我已经辨认出十几种能吃的野草了。聂司令,我来你这里是准备着吃草的!’聂司令听了很感动,不止一次在会议上表扬我。他说:‘我告诉你们,我这里有一个准备吃草的干部!’……”
说话间,来到一个小院门前。刚踏进院子就听见一匹马咴咴地嘶叫起来。大家凝视槽头,见一头老黄牛旁边,拴着一匹棕红色的高头大洋马,它一边嘶叫还望着欧阳行打着响鼻。“老伙计,你饿了吧!”欧阳行说着,顺手丢了一把草在马槽里,一面笑着说:
“这是去年反敌人八路围攻的战利品。聂司令员见我跑来跑去太辛苦,就把它送给我了。现在我每天写好社论,就骑上它到聂司令那里,方便多了。”欧阳行说着还拍了拍皮带上的手枪,“这也是司令员送给我的。”
这时从屋子里出来一个农家妇女,带着笑对欧阳说:
“我一听见马叫,就知道你回来了。哟,来了这么多客人,我给你们烧点开水吧!”
“不用了,大嫂,早晨的开水还有呢!”
欧阳把大家让进一个堆满文稿的小房间里,从小桶里给每人舀了一缸子凉开水算作招待。小房间里,除了一铺大炕,一张八仙桌子,已经无处插足,周天虹几个只好坐在炕沿上。
晨曦把他的行政介绍信和党的介绍信取出来,恭恭敬敬地递给欧阳。他的入党问题是在抗大最后的时日里解决的。欧阳仔细看了看;又微笑地望着晨曦,把他端详了一番,慈祥地问:
“你愿意到我这里工作吗?”
晨曦把他的近视镜往上托了托,腼腼腆腆地说:
“我本来也是准备到前方去的。”
“哈哈,前方?我们这里也是前方嘛!”欧阳朗朗地笑着说,“现在敌后进行的战争,正像毛主席说的是一种犬牙交错的战争。这也许是一种新形式的战争。敌人包围着我们,我们也包围着敌人。一打起来,双方就交织在一起,更分不清前后方了。现在我们离敌人远者五六十里,近者三四十里,聂荣臻的总部竟敢在此巍然而立,历史上哪有这样的战争呢?……”
欧阳越说越兴奋,特意望着晨曦说:
“你看我们这个报社,不过是些文弱书生,但打起仗来,都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去年敌人八路围攻,我这个报社,就同敌人打起游击来。敌人在山那边活动,我们就在山这边印报。我们有几个记者还真表现得很不错呢!晨曦,我看你就下决心在报社干吧,你一来就知道了。”
高红忽闪着一双黑眼睛,一直望着欧阳。这时,她笑微微地插话说:
“马社长,你只要多给他点时间写诗就行。他写诗都入迷了。”
“哈哈,原来是位诗人!”欧阳望着晨曦笑道,“这个没有问题。我们的报纸也可以发表你的诗作。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田间、邵子南最近也来了,他们正计划着出诗刊。”
“田间、邵子南同志我也认识。”展曦微微红着脸说,“我们在延安一起搞过街头诗运动。你看,边区也可以搞街头诗吗?”
“当然可以!”欧阳果断地说,“我们的文化迫切需要同劳苦大众结合起来。”
“现在我一进村庄,就察看那里的墙壁,我心里想,如果在那上边写一些短小有力的诗句,对人民群众不也是一种鼓舞吗!”
“对,你的想法很对。”欧阳充分肯定地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缺点,就是还没有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起来。左翼文化运动也有这个缺点。现在我们到乡村来了,革命更深入了,我们吃着老百姓的小米,住着老百姓的房子,我们应当把革命的新文化深入到穷乡僻壤才行。”
晨曦像是一下遇到难得的知音似的,心情格外舒畅,脸上放着红光,一点拘束也没有了。他亲切地望着欧阳,像对老朋友一样敞开了心扉。
“我过去在家乡也到过乡村。乡村给我的印象是贫穷的、悲惨的、愁苦的和没有希望的。我这次来到边区,处处都有一种新鲜的感觉。从村头查路条的孩子,大树底下纺线线的老太太,村边大场上操练的青年妇女,冬学里飘出来的歌声,我都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新鲜感。虽然人们生活得并不富裕,我看他们的眉眼间似乎都充满希望。就是晋察冀的山呀,水呀,也仿佛包含着一种力量,披着一种灵光似的。我这脑子里一天到晚骚动不安,老想写诗。高红说我被诗迷住了,其实我是被新的生活迷住了,我觉得就好像来到一个新世界似的。……”
欧阳一直眯着眼听着,好像他也进入到晨曦的情感世界中去了,他把桌子兴奋地一拍:
“晨曦,就凭这一点,我也要说你是个诗人!不错,一点不错,不仅仅是抗日,我们的确是在创造一个新世界!”
大家都兴奋起来,沉入到一种光荣和神圣的使命感中。
“马社长,现在边区的形势怎么样?”高凤岗插话问。
“你就别叫社长社长了,你没听到全村大小都叫我老马哩!”欧阳嘿嘿笑着说,“现在我们的脚跟总算站定了。你们要早来一年,那可是热闹得很呢。正像人们说的,‘主任赛牛毛,司令遍天下’。因为国民党的军队逃到南边去了,国民党的官儿也跟着跑了,这就造成一个真空地带。这时候,各种力量,三五十人一股,百儿八十人一股,千把人一股,都纷纷揭竿而起,自立旗号,自封司令。这里有真正抗日的,也有地痞流氓,散兵游勇,假借抗日之名企图浑水摸鱼。还有跟日本人暗中勾结作威作福的。他们整天鱼肉乡里,派捐派款,加重了人民的苦难。当时就有民谣说:‘穷八路,富七路,要找媳妇到高部。’……”
“这是什么意思?”高凤岗问。
“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自然是穷的。还有个七路军,抢老百姓的金银元宝;把老百姓的土炕都压塌了,你说富不富?易县有个高宏飞部,司令部门前经常停着三乘花轿,见到有些姿色的农家女子,就抢过来成亲,作践够了就赏给他的部下;所以到高部找媳妇就比较容易了。群众对这种状况自然是不能忍受的。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那些真正抗日的,就同他们团结起来;那些同日本人暗中勾结的,就干脆将它消灭;那些为非作歹不走正路的,就加以改造;这样根据地的秩序才渐渐地稳定了。去年敌人的战略是‘南取广州,中取武汉,北围五台’,经过去年粉碎敌人的八路围攻,现在可以说晋察冀根据地已经站稳脚跟了。”
“现在这块根据地已经巩固了吗?”周天虹问。
“应当说,基本上是巩固了,但是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欧阳沉思着说,“我们同国民党抗战路线的根本不同之处,就是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只要把群众真正地发动起来了,我们的根据地就可以说立于不败之地了。而要把群众真正地发动起来,一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二要给他们民主。而国民党是不给人民这些的。你看国民党地区,一片死气沉沉;由于抗战,一些官僚乘机发国难财,人民的负担反而加重了;人民抬不起头来,要他们当兵就抓壮丁,绳捆索绑赶上前线,这种办法怎么能赢得抗战胜利呢?我们这里就大不相同:到处是一片勃勃生机,到处是一片歌声,人人眉开眼笑,晨曦说是来到了一个新世界,不就是从这里来的吗!但是,我们的减租减息工作,还可能有做得不彻底的地方。这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
讲到这里,外面响起了几声长长的哨音。欧阳笑着说:
“开饭了。你们回去也是小米饭,就在这里吃吧。我叫他们加一个菜,我这里还有一点过年时老乡送的枣酒呢!”
大家并不推辞。仿佛很愿意在这里多留一点时间,因为这位报社社长的才情、意志和说不出的魅力早已经把他们征服了。
吃饭中间,周天虹忽然想起有一个问题还没有问,就说:
“欧阳同志,您为什么又改姓马呢?”
“这个很简单。”欧阳笑着说,“这个村子的名字叫马兰村。聂司令员题写过一句话:‘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我以村名为笔名,取名马南,今后这里就是我安身立命之地,或者也可说是我生死之地了!”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