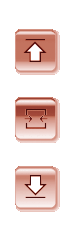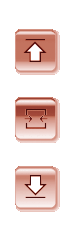|
|
|
|
二一 清清延河边
|
接着的一周是紧张的军事演习。
抗大四大队的学员们,全副武装整齐,从斥候兵的搜索动作开始,其次是班进攻、排进攻和连进攻,一路向九十里外的瓦窑堡攻击前进。周天虹和他的同学们,英姿勃勃,头上戴着用长长的野草扎成的像车轮一样的伪装盔,脚蹬草鞋,手持步枪,在黄土高原的沟壑坡坎间,上下跳跃,纵横飞驰。高凤岗因为上过几天军校,尤其显得训练有素,大出风头。即使晨曦也一扫文弱之气,有了几分军人的样子。这次演习,往返一百八十里,途中汗水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回到延安时,大家几乎成了泥猴,浑身军衣已经布满汗碱结成的霜花了。
好在眼前延河的流水,正是他们洗去征尘的好地方。入夏以来,下了几场雨,这条细瘦的河流,已经变得丰盈碧绿,满当当的,十分可爱。河边的青草也都长起来,绣成了宽敞的绿毯。一到星期天,数不清的男女青年们就被吸引到这里来了;他们在河边上洗衣呀,谈笑呀,散步呀,歌唱呀,看书呀,闹吵吵的,仿佛树林间的鸟儿一般。
延河的水并不深。它由北而南,在嘉陵山下打了一个转弯向东去了。由于经年累月的冲击,在嘉陵山下便汇成了深潭,成了一个天然的游泳场。尽管刚刚立夏,水还很凉,那些略识些水性的男青年便耐不住性子,纷纷跳进水里,像鱼儿一般畅游起来。女孩子多把裤腿高高地挽起来,站在浅水处弯着腰儿洗头。还有一些坐在大石头上静静地看书。周天虹不会水,在河边洗完衣服,便把它晒在草地上,穿着白衬衣在河边散步。他步态悠闲,望着嘉陵山上的宝塔,凤凰山和延安城,以及这湾碧绿的流水和河边充满青春朝气的男女,觉得简直像一幅动人的油画,心里感到十分惬意。
“周天虹!”
一个女同志的声音在喊他。
他停住脚步,循声望去,见河边几棵高大的柳树下,青草地上坐着一个女孩子,怀里抱着一本书,正在望着他笑。
他向前走了几步,才看清那是高红。
“高红,是你呀!”
“不是我,是谁?”高红笑着说。
他走到高红身边:
“你在看什么书?”
高红随手一翻,露出封面《被开垦的处女地》,说:“这书写得很有趣。你看过吗?”
“没有。你看完借我看看吧!”
高红点点头,仰起下巴颏笑着问:
“你怎么爱站着讲话?”
周天虹红红脸,不好意思地在她身边坐下来,稍稍保持了一点距离。他望望高红,也许她刚刚洗过头,黑油油的头发闪着亮光,显得非常舒展,脸似乎晒黑了一点,比前更健壮了。
“这次大演习,你们女生队怎么样?”周天虹匆忙间找到这样一个话题。
“真出了不少洋相。”高红仿佛回忆起什么有趣的事情,笑着说,“一出发整整齐齐,还很带劲;可是没有走出二十里路,有的绑带开了,有的背包散了,有的掉队了。气得队长说:‘你们这些小资产该(阶)级!’回来的路上,有的人满脚血泡,最后二十里,硬是走不动了。队长派我当收容队,我就帮她们挑泡呀,包扎呀,搀扶着她们呀,身上还背着两支枪呢!”
“你哥哥表现得也不错,他是这次演习的标兵。”
在他们前面不远的河边上,有一个年岁稍长的女同志正在洗衣,她旁边摞着一大堆洗出的衣服。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正光着腿弯着腰立在浅水处洗头。周天虹颇觉面熟,就随口问:
“那也是你们女生队的吗?”
“是的。”高红说,“那个是我们全队最年长的吴大姐,另一个叫小广东,是全队最小的小妹妹。两个人在一起就像母女似的,可有意思了。小妹做什么事都要同吴大姐商量。那一大摞衣服,你不用问,准是吴大姐帮她洗的。这个小姑娘,真逗!有一次我问她,你为什么参加革命,她就说,以前,我听说陕北有骆驼,我就想象我骑上它在西北高原上漫行,唱着我心爱的歌儿多浪漫呀!”
说到这里,高红笑得咯咯的,逗得天虹也笑起来。
“这个吴大姐,在外面就是律师了。她待人真好。我初到延安,生过一场大病,发烧到四十度,人烧得昏昏迷迷。吴大姐半夜从校部牵了一匹马来,驮上我到了桥儿沟给我看病。刚好了些,她又牵着马去接我。我真忘不了她。她有一件很漂亮的浅蓝色的呢子大衣,把它裁成一条条的,都给大家做草鞋用了。我一看,也把自己的红毛衣拆了,分给大家做草鞋上的红缨缨。你看这草鞋多漂亮!”高红说着,把她蜷着的一条腿伸出来,她的赤脚上套着非常合脚的淡蓝的草鞋,大拇趾处翘起的红缨,在青草地上就像一朵红花一般。
“真的,我们是在过另一种样式的生活!”她越说越兴奋,“在我们队里不管谁家里寄了钱来,没有人把它看作是自己的,都分给同学们用了。给这个人买点儿这个,给那个人买点儿那个,要不就到合作社里打牙祭。真的,我觉得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才是人的正常关系,才是真正人的生活!未来的共产主义,我不知道什么样子,但人类不就应该这样相处么?……所以,我一到了延安,觉得简直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崭新的世界;一天到晚,老是想唱,想跳,真是快乐极了,这真是我一生的黄金时代!”
这时她那双乌亮的猫眼,忽闪忽闪地放着光彩,又似乎在询问:“你不觉得是这样的吗?”
“是的,我们的确是来到一个崭新的世界。大家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都认为自私、利己是一种很可耻的东西。”
说到这里,周天虹望着高虹,像忽地想起了什么,笑着问道:
“高红,我听你哥哥说,你家里好像是个大地主吧?”
高红坦然一笑:
“大地主也许算不上。反正总有两三百亩田地,在北平城里还有一爿商店。总之算个典型的地主兼商业资产阶级,剥削阶级。”
周天虹笑着说:
“那么,你的生活一定是相当优裕啰!”
“什么优裕!”高红憎恶地说,“我和我妈在家里简直像奴隶。我妈是个贫家女,娶到他家里,一天挨骂受气,见了我父亲就像老鼠见了猫似的。我父亲一向重男轻女,拿着我哥哥当宝贝,把我不当人看。从小就让我念女儿经、四书五经,搞三从四德那一套。把我管得严极了,连门都不让我出,我家简直就像个太监狱。后来我坚持到北平上学,才算离开这个讨厌的地方,只有寒暑假才回去。就是这样,我父亲还追到学校去,给我约法三章:不准我参加学生运动;不准我结交男朋友;还不准我参加运动会。我真讨厌死这个家了!”
周天虹哈哈笑着说:
“这三条恐怕你一条也没执行吧!”
“你算猜对了,我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
两个人笑了一阵。周天虹似乎想起了什么,试试探探地笑着问:
“我总纳闷,像你们这些剥削阶级家庭的小姐——”
“什么?小姐?你要再说这个词儿,我可就要恼了!”
周天虹一见高红涨红了脸,连忙改口说:
“我的意思是说,像你们这样的人,怎么会跑到革命队伍里来呢?”
高红稍微平静了一下,拍拍怀里的书说:
“这首先是因为我接受了革命的思想。我从小就爱读书,尤其爱读鲁迅的书。看他的书真带劲!他说过去的历史就是两个字:吃人!还说什么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什么在这可咒诅的地方击退可咒诅的时代,等等,真写得好极了。看到这些句子,我的整个灵魂都要燃烧起来。这个老人死了,我捧着给他送葬的报纸还趴在床上哭了好半天呢!郭沫若、茅盾的作品我也看了不少,还有邹韬奋和他编的《大众生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及曹培华翻译的苏联小说,他们都塑造了我的灵魂,都是引导我前进的导师,我真感激他们!……”
“是的,他们对我们这一代青年,实在帮助太大了。”天虹也深有所感地说。
“另外一个对我起作用的,恐怕就是旧制度本身了。那个社会实在太黑暗了,穷富太悬殊了。每逢寒暑假,我回到家里,总到穷亲戚家去转转。那些农民们生活真是苦啊!真是一贫如洗啊!吃没吃的,穿没穿的,孩子夏天在泥里爬,冬天十冬腊月还光着腚;茅草房子四外透风,连点糊窗户的纸都没有;屋子里暗得像地洞,进去什么也看不见。唉,简直不是人的生活!这时我就想:我是人,他们也是人;为什么我住得富丽堂皇,他们却这样受苦呢?为什么世道这么不公道呢?记得有一年,天大旱,收成很不好,他们交了租子就两手空空了。有一天,一个穷老汉领着两个孩子来到我家,一进门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哀求我父亲少交一点租子。老汉说,不是不愿交,实在是老天不落雨没有收成;如果再交,全家就要饿死了。我父亲听了这话,冷冷地说,这事儿你别找我,老天不下雨,你去找老天爷算账去!说过扭头就进去了。我当时在旁边,气得浑身打战。后来我读了点马列的书,才知道这就叫剥削。那个社会真是太丑恶了!我想,我决不能站在他们一边。……”
在周天虹眼里,高红不过是一个天真纯洁的女孩子,今天听了她的这番谈话,才发现她的觉悟竟是这样高,不由得从心眼里暗暗赞服。
太阳已经偏到凤凰山方向去了。河边上的人渐渐少起来。吴大姐和小广东也站起身来,收起晒干的衣服,准备回去。临走前看见高红,远远地打着招呼:
“高红,我们先回去了!你也不要误了吃晚饭哪!”
高红连忙站起身来,有礼貌地笑着说:
“大姐,我们也快回去了!”
但是,周天虹意犹未尽,望着高红说:
“高红,你毕了业到哪里去呢?”
“我早下决心了,到前线去,到敌后去。”高红回答得很干脆,“毛主席不是说了吗,要我们同工农群众相结合。他还说,过去是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现在是聂荣臻大闹五台山。那里已经建立起一块根据地了,我很想到那里去。”
“你说的是晋察冀呀!我也很想到那里去。”周天虹热情地说,“我早在志愿书上填了‘愿做八路军的下级干部’。”
他们在草地上收起晒着的军衣。这些军衣早就干了,而且因为吸收了过多的阳光,热得烫手。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