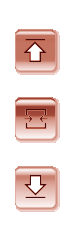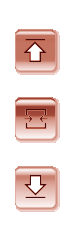|
|
|
|
第六回 周恩来病重陈赓抬 毛泽东挥兵毛儿盖
|
沙窝会议后,红军全军改为执行夏洪战役计划,即北上甘肃南部,在夏河至洮河流域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采纳了张国焘提出的意见:一、四方面军分别由各地向毛儿盖和卓克基两地逐渐集中,然后分左、右两路军北上。右路军以毛儿盖为目标,左路以阿坝为目标,然后在班佑、巴西会合。
张国焘临离开沙窝前,毛泽东在王稼祥的陪同下主动找到他进行了一次谈话,希望交换一下意见,可两人没说几句话又谈崩了。
张国焘关心似地说道:“我说润之呀,你要注意影响哟!
有很多人都在背后议论你,说你的闲话呢!”
“议论些什么?”
“说你是曹操,党中央成了汉献帝。”
“哈哈,有人看《三国》也演义到我身上来了。那意思是说我挟天子以令诸侯!”
“是这个意思。难道不是吗?”张国焘步步紧逼,突然来了一个反问。
“我说国焘,这些闲话是听不得的。我毛泽东行的端,走的正,不怕别人说这种闲话。只是现在我提醒你不要听有些人的挑拨离间,还是以解决当前红军的出路为第一大事。”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张国焘的话,怕的是引起更大争论,但张国焘却寸步不让,几乎把毛泽东逼向谈话的死角。
张国焘得意地抬起头,直视毛泽东,说道:“你不是最喜欢讲政治路线吗?我也这样认为,路线是一个大问题。路线不对,一切都等于白费。我们当前应首先解决路线问题,可我提了上百遍,你就是不听。”
毛泽东停顿了一会,可看出他心中十分难过,猛吸了一口烟后才缓缓回答张国焘的逼问:“有些政治路线问题,看来现在我们争论不清,等将来环境许可后我们再从从容容去争论吧。我们吃饱了饭,再说《三国》,争论几个月也没问题。”
“说《三国》,我比不过你。可我知道诸葛亮有个既定国策……”
“欲北伐必先南征。”毛泽东替张国焘说道:“我的国焘同志呀!说到底,你还是要南下。那是诸葛亮巩固蜀国的方法,我们现在连根据地都没有了,哪里还有什么后方?”
“那么,你就认准过草地这条路了?这条路可要耗尽我们的全部体力,蒋介石也不傻,早在草地那边放上兵力,不用说多了,就是一个连,我们这些连走路都迈不动腿的人,只能是到一个被敌人捆一个。”张国焘说得很玄乎,使毛泽东和王稼祥都感到过分。
毛泽东仍语气平稳地说:“目前的形势对红军来说是很严峻的。尾追我们的川军刘文辉部已经占领懋功,我们在两河口召开会议的大门口已经飘扬起青天白日旗;蒋军的周浑元、吴奇伟纵队集结在雅安;胡宗南集结了4个师的兵力,位于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座一带,川军刘湘部已经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敌情越来越严重。敌人估计我们会东出四川,却不敢向北冒险横跨草地,走出甘陕这一着棋。我们呢,硬是要走敌人认为我们不敢走的这条路!”
“润之兄!这川西北的水草地可不是你们湖南的水田地哟!水草地纵横数百里,渺无人烟,神秘莫测,很不好过。”
毛泽东明白张国焘的话既有讽刺他毛泽东是乡巴佬的意思,又表明了不同意过草地的客观困难,他强压心中的不愉快说道:“很不好过,那说明还是可以过的嘛!红军纵横数省,冲破了敌人的道道封锁线,是不会被这点困难挡住的。”
“明明是过不去嘛,可你硬是要一条道走到黑!”张国焘的火气也冲上来了。
毛泽东和张国焘的思想交锋,又发展到面红耳赤的激烈争执。
王稼祥见毛泽东和张国焘又顶起了牛,连忙在一边打圆场,说:“草地的确不好过,国焘同志说的有道理。但是,草地是可以过的,泽东同志已经派叶剑英同志到草地探查过了,那里还是可以过去的。国焘同志,你看,这是叶剑英同志根据实地考察画出的路线图。”
张国焘被王稼祥这番巧妙的话说得一会儿脸露喜色,一会儿又沉下脸。但他是不能对刚刚恭维过他的人发火的。可王稼祥的话最终却是倒向毛泽东的。
“这个王稼祥真把人弄糊涂了。”张国焘心中暗自叫苦,接过王稼祥递过来的地图,瞄了一眼。如果是毛泽东递过来的地图,他会立刻撕碎扔到毛泽东的脸上去。
“哼!你们对草地是不了解的。请不要忘记,这里有胡宗南的部队和马家骑兵,还有川军的各路军阀。我的意见还是南下为好,在川康一带站住脚再作另外考虑嘛!”张国焘的话不可能再引起毛泽东、王稼祥的共鸣。
毛、张之间的谈话只能是不欢而散,这是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最后一次面对面的交谈。
“国焘同志,我们就要暂时分手了。你和朱总司令,还有刘伯承同志,共同携起手来。我们在草地那边再见。”毛泽东扬起了右手,表示送客。
毛泽东这一声“再见”,本意是在半个月或20多天后再见,但他和王稼祥及张国焘都未曾想到,这一声“再见”的间隔时间竟然长达1年之久,而且其中又折腾出许许多多中央与张国焘的恩恩怨怨来。
朱德和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去左路军后,8月15日,党中央鉴于敌情又有了新的变化,致电张国焘,准备改变原定主力经阿坝北上的方案,指出: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并强调目前应专力北向,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
但是,张国焘置中央指示于不顾,仍率部队坚持西出阿坝,以期造成北打阿坝的既成事实,行其原来提出的深入青海、宁夏、新疆的主张。8月18日,陈昌浩、徐向前见张国焘率部仍向阿坝进发,连忙发电致张国焘,指出:“不应深入阿坝,应速靠紧右路,速齐并进,以免力分。”
次日,张国焘回电,以“财粮策源”、“多辟北进路”、“后方根据地”为理由,坚持“阿坝仍需取得”。并说:“事实上右路军与左路军联络困难,左路若不向阿坝攻击,将无粮并多番骑扰害。”反而劝说右路军也向阿坝进发。
“我们头里先走,为他们开路!我就不信草地如魔毯会把红军全部卷进去。”毛泽东把张国焘的回电一扔,表示自己坚决北上的决心。
右路红军为过草地北上,紧张地作着一切准备。8月中旬,毛泽东在沙窝听取叶剑英关于草地情况的汇报,随即与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等人开会研究右路军北上的问题,确定了经草地到班佑、拉卜楞寺的行军路线,由叶剑英率两个团组成右路军先遣队。
毛儿盖以北,当时统称作松潘草地,包含若尔盖、红原、阿坝和壤塘部分地区,为丘状高原和山原地带。丘状高原呈坡状起伏,境内草原辽阔,水草丰茂,海拔一般在3000~4000米。草地气候寒冷多变,风、霜、雪、雹日日皆有。草地中的沼泽是“一片茫茫泽国”,是“人陷不见头,马陷不见颈”的险恶地段,被称作是“鸟儿也飞不过”的地方,这种沼泽、半沼泽区域广达2500平方公里。
8月17日,毛泽东通知林彪,让红4团政委杨成武亲自来接受任务。
杨成武当面从毛泽东这里接受任务这还是第一次,他激动地问毛泽东:“主席,军团长让我亲自到你这里来接受任务,是不是有很重要的任务?”
“先坐下。这一次还是让你们4团当先头团。”
“是。”
毛泽东深深吸了一口用大黄叶子土制的烟,说道:“这草地是一片泽国,很不好走。原想要6团去,但试了一下,没有奏效。我看他们没有奏效的原因有3点:粮食准备不足,思想准备不充分,敌人骑兵的伏击。”
杨成武把毛泽东所说的话复述了一遍,深深记在脑子里。
毛泽东又指着地图说:“你们团必须从这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现在,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座一带集结了几个师,东面的川军也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已占领了岷江西岸的杂谷脑。追击我们的刘文辉部已赶到懋功,并向抚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则集结于雅安。如果我们掉头向南是没有出路的,就会断送革命。我们现在只有向北,所以说,你们团的任务重大呀!”
“我明白了,主席。坚决完成任务。”杨成武表示自己的决心。
毛泽东指在地图上的右手用力一挥,接着说道:“我们只有前进。蒋介石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这一着棋。但是,蒋介石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蒋介石认为不敢走的道路。当然,这条路上的困难很多,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是,我们要教育部队,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透彻。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能挡得住红军指战员的。”毛泽东还说道:“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搞好团结,同时要搞好一、四方面军的团结。”
杨成武接受任务后飞奔回团。
为了进一步落实北进的各项计划,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沙窝召开。这时,周恩来的病仍很重,在前几天他所缺席的沙窝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争论进入白热化程度时,连续的发高烧正使他昏迷不醒。现在,他虽在沙窝,但仍参加不了常委会。
毛泽东为自己的支持者周恩来多次不能出席会议感到焦虑,谁又能保证哪次会议会不出现关键时刻就差关键一票的情况呢!
“周副主席肯定是不能参加会议的,高烧不见退,现在说话都很困难,烧得太厉害,40度了。”医生手持体温计,介绍病情说。
毛泽东把手按在周恩来的头上,立刻感到如同摸到一块热炭,脱口说道:“烧得这么烫,千万注意不要把人烧坏了。
赶快想办法降温。”
“我们现在什么药也没有,只有依靠病人自身的抵抗力。”
医生表示无可奈何。
“无论如何先把体温降下来,否则会把人的大脑烧糊涂的。弄些冰来!”毛泽东向着不远处的雪山呼喊。
警卫员从山上背回来一筐冰雪,用毛巾包裹一些冰块,放在周恩来的额头上,辅助降温。邓颖超谢绝了一切来访的客人,时刻守护在床边。直到3天后,周恩来高烧的体温才缓缓下降,但人犹如从死里走了一遭。他的身体状况降低到了生命的最低点。
周恩来因病重不能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常委全到会也就仅有4人,他们是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和王稼祥。会议议程有两个,一是研究常委的分工,二是研究宣传问题。会议决定,王稼祥负责政治部工作,张闻天、李维汉(罗迈)负责组织部工作,博古负责宣传部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
会上,博古提出对张国焘的闹分裂思想倾向作斗争的问题,毛泽东表示不同意,说:“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现在应采取教育的方式。可写文章,但不能指名,不能引证。我建议在这非常时期,政治局每周要召开一次常委会。”
“还开什么会,耍嘴皮子干什么,有什么用?张国焘仍然自恃兵多,不把中央放在眼中。”
“会还是要开的,集思广益嘛!”毛泽东说。
会议最后还是接受了毛泽东关于“每周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的建议。
沙窝常委会议后当天下午,毛泽东等人继续北行,到达毛儿盖。
周恩来因身体状况极差,中央在沙窝召开的两次会议他都没有能出席。
在整个8月,周恩来都病得很厉害,有人甚至估计到他的生命已是危在旦夕。离开沙窝时,毛泽东为此非常着急,一再嘱咐彭德怀,说:“无论如何要照顾好周副主席,他不能再骑马了,要组织力量抬着他行军。这件事就由你来负责!”
彭德怀立刻把办事一向认真的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找了来,命令道:“抬着周副主席行军的任务就交给你,从现在起你就是担架队的队长,我给你分配40名战士来。”“是,我可以亲自抬!”年方31岁的陈赓爽快地答应道。他与徐向前、胡宗南都是黄埔军校的同期同学,整10年前,他在东征战斗中曾背起绝望中欲自杀的蒋介石,撤到安全地带。现在,他又担负起救护黄埔军校时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重任。
川西北高原,辽阔的地域在地势上东南明显低于西北,海拔由780米逐步升高到3000米以上,由南向北走,基本上呈上坡。陈赓抬起周恩来的担架,稳健地踏向新的征途。他的队员是彭德怀下决心扔掉红3军团唯一还保留下来的两门迫击炮,腾出40名战士来轮流抬周恩来的担架的。彭德怀算了一笔大帐:“别说是两门迫击炮,就是200门、2000门大炮也不能换我们1个周副主席。”
从沙窝到毛儿盖,担架在行走着,昏迷中的周恩来在暖融融的阳光照射下苏醒过来,他面朝青天睁眼看到的是一张熟悉的圆圆的娃娃脸,认出了是陈赓,说道:“原来是你呀!”
“周副主席!你醒了……”
“你救过蒋介石的命。现在你又要救我的命了……”周恩来讲话仍很吃力,他太虚弱了。
“马上就到毛儿盖了。”陈赓说。
周恩来勉强地微笑着,又闭上了眼睛。陈赓把草帽遮在周恩来的脸上,免得强光照射,影响周恩来的休息。
再有4天就是处暑的节气,草原上的气候不像内地那么热,但走在直射的阳光中,仍然浑身燥热。陈赓身上已经被汗水湿透了。
“看着远处的雪山,也就不会感到热了。”陈赓对战士们说,他采取的是心理驱热法。
“还真管用。”战士们望上一眼冰雪覆盖的高山,心里好像有块冰在融化,渐渐感到比刚才凉快些。
此地高原东南部是高山峡谷地带,峰岭耸峙,起伏绵亘,河流纵横。整个地区的气候呈垂直分布,从河谷到高山形成温暖带——温带——寒温带——寒带——冻原带的立体气候。其间九顶山、雪隆包、巴朗山、夹金山和中部的梦笔山、虹桥山、亚克夏山(又称垭口山、长板山)、昌德山、打古山等,海拔都在4300米以上。山顶终年积雪,故统有雪山之称。
“古有曹操望梅止渴,今有陈赓望冰止热。”周恩来不知什么时候醒了过来,也加入这望山活动。
“你们看,前面就是毛儿盖。嗬,真是个美丽的地方啊!”
陈赓赞不绝口。
毛儿盖周围,是个农牧区,土地肥沃,牛羊结群于草丛中。这里的青稞比较多,蚕豆开着紫色的花,有的已经结满豆荚。
周恩来的担架进了毛儿盖。毛泽东等人也刚到不久,在街道上四处望着。
经过战斗后的毛儿盖,有许多房屋被烧毁。
红军到了毛儿盖后,缺粮情况虽有所缓和。但对这么多的红军大队来说,也只能救一时之急,必须尽快离开这里。因此,毛泽东等人于8月20日中午到达毛儿盖后,下午,即在索花寺内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夏洮战役和以后的行动方针。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共12人。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首先作了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我们向北行动以后,目前存在着两个方向,一个是执行夏洮战役计划,积极占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东岸,然后依托这一地区向陕甘边发展,以实现创造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的;另一个是向黄河以西的青海、新疆、宁夏方向发展。我认为,向东是转入进攻,向西则是退却。蒋敌之部署,正是迫使我军向黄河以西。如果向西去,无论从敌情、地理、民族、经济、政治等条件,都对我们极其不利;而向东发展,则可以洮河流域作为革命根据地的基础。这一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而北靠黄河,便于作战。同时,又可以黄河之西为退路。因此,红军主力应向黄河以东,支队可以向黄河以西去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所以说,洮河作战步骤,极大关系着将来的行动。”
会议对毛泽东的报告展开了讨论。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徐向前相继发言,一致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
陈昌浩在会上明确阐述自己看法说:“原则上的问题,以前已经决定,当无可争。我们应坚决先从洮河左岸向东突击。
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
徐向前在发言中也表示:“我们必须快速北进,集中最大兵力,以实现中央的既定方针。红军北出甘南后,应该坚决沿洮河右岸向东,突破岷州国民党军王均部的防线,向东发展。万一不成,再从河左岸向东突击。”
毛泽东当即对陈昌浩和徐向前的意见表示称赞。
王稼祥、博古、凯丰在发言中着重强调:不应把向东向西看成是一个小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向东是转入反攻,转入新的形势,是创造苏维埃新中国;向西不仅是军事上的退却,而且是政治上的退却,是缩小苏维埃运动,是另行其事,创造新疆人民共和国。因此,应该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向东发展。
最后,毛泽东总结大家的发言,讲道:“今天大家讨论的意见是一致的。概括起来有4点:第一,敌人的企图是逼迫我们向西,我们则应采取积极的向东的方针,这是一个关键问题;第二,为配合全国红军租全国的革命运动,也应该向东发展,而不是向相反的方向;第三,东进北上的路线应该采取包座至岷州的路线,而占领西宁的提法,很不现实,民族政策上不应该,红军当前的兵力也不够;第四,左路军应该向右路军靠拢。”
会议最后明确决定,左路军的行动应统一于右路军的进展。并委托毛泽东起草一个决议以补充两河口会议的决议。
这次会议因为没有像前几次会议那样有张国焘从中作梗,开得很顺利。
毛泽东的兴致很高,他立刻根据上述报告内容,亲笔起草了一个会议决议,即《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作为正式文件,下发部队执行。
《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明确指出:企图使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它正好适应敌人希望把红军赶到人烟稀少的西部边陲地区的需要。《决定》要求红军迅速夺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向东发展,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决定变右路军为打开北上通道的主力,左路军应立即向右路军靠拢。
会后,毛泽东挥兵北进,迈向草地,这是关系到红军主力能否北上关键性的一步。
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前敌指挥部立刻率领右路军开始了艰难的草地行军。同时,将毛儿盖会议的决定电告张国焘和朱德。随右路军前进的徐向前和陈昌浩也几次致电催促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以便集中向夏、洮前进。
然而,张国焘公然无视中央的决定,坚持两路军分而不合,分兵北进。徐向前及陈昌浩殷言致电张国焘:“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但张国焘把中央的决定和徐向前等人的劝告全当作了耳旁风。
进入草地前,红一、四方面军在毛儿盖召开联欢晚会,会场很简陋,就在河坝中搭了个台子。演出前,博古在作“革命到底”的讲话。大家认真听着,但也有不认真听讲的,在台下互相交头接耳,谈论着新闻趣事,也有人在互相开玩笑。
“你给我烟抽,我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个浓重的四川口音。此人是时任红1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的邓小平。“什么好消息?又要骗我的烟抽。”答话者是红1军第1师师长李聚奎,他与邓小平的关系很熟,所以“欲擒故纵”,把衣袋故意捂得紧紧的。
“你不给我烟抽,我就不告诉你。”
“这很简单,不就是一点烟丝嘛,早晚都会被你盘剥光的,早抽晚不抽。”李聚奎从衣袋里摸出个小铁盒递了出去:“抽吧。”
两人之间顿时腾起烟雾。
邓小平深深吸了一口烟,才笑着说道:“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升官了!”
“开什么玩笑,这个时候升什么官?”
“军委决定调你到红四方面军去担任第31军参谋长。”
“我不相信,怎么会把我弄到四方面军去呢,我对那里的情况不熟。”李聚奎对中革军委已经颁布的命令显然是真的不知道。
“真的,命令已经下来了,我看到了。”
“我去问一问聂政委再说。”李聚奎见邓小平不像开玩笑的样子,也认真起来。一片掌声在他们身边响起,博古的讲话完了。可邓小平和李聚奎是一大半没有听清楚。
李聚奎在红1军军部没有找到聂荣臻,等到半夜也没有见到聂荣臻的影子。有个参谋进来说:“聂政委大概是在陈政委那里喝醉了。”李聚奎这才知道聂荣臻是到陈昌浩那里去了。”
这天,聂荣臻和林彪在右路军指挥部开了一整天的会,留下来吃晚饭后,大家又在一起磕了很多胡豆,天南海北地闲聊了一通。
其实,这时右路军的政治委员陈昌浩一直挽留聂荣臻等人过一会再走,原来他是根据张国焘的来电旨意,要想方设法做好争取聂荣臻的工作。磕了一盘胡豆后天还没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总政委有话让我对你讲。我们还要谈一谈。”
聂荣臻留下后,陈昌浩说道:“总政委对中央改变沙窝会议定的作战方案很不满意,毛泽东这个人也的确太专权了些,总司令、总政委都不在,就这样随随便便改变了原来的计划。”
“前天的会议上你不是也发言表示同意嘛。怎么现在又变卦了呢?”
陈昌浩没有回答聂荣臻的问话,反问道:“你对遵义会议的态度怎样?”
“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聂荣臻简捷地回答。
到此时,聂荣臻心中已经明白,张国焘仍是要动员他反对毛泽东。林彪看来是不成问题了,现在要做的是聂荣臻的思想工作。
房间内,徐向前站在大地图前,划着标记,计划着作战方面的事。尽管陈昌浩在房间里高谈阔论,滔滔不绝,徐向前却没出声。
聂荣臻静静地听着,心中感到砰砰直跳。
一直谈到晚上10时过,陈昌浩还似乎有许多话要讲。聂荣臻说道:“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
“好吧,你走吧。你对总政委的话要考虑到后果。”陈昌浩见聂荣臻迟迟没有表明态度,很不高兴地表示送客,话语中充满警告。
如释重负的聂荣臻带着两个警卫员,牵上骡子,离开了右路军指挥部。
聂荣臻翻身上了骡子,黑洞洞的夜空下,他的身影很明显。
“停!我下来步行。”聂荣臻跳下骡子,在这时他已分明感到危机四伏,说不定今晚就有杀身之祸。回去的路还较远,但现在他有骡子也不敢骑了。
聂荣臻让一个警卫员牵着骡子走在前面,让另一个警卫员殿后,自己走在中间,并把手枪顶上了子弹。在过去的作战中,聂荣臻还从来没这样紧张过,来自内部的子弹难防呀!
几天前,红2师参谋长李棠萼就是走在路上被冷枪击中牺牲的。聂荣臻思索着,李参谋长的死是谁干的呢?
张国焘的面容在聂荣臻脑海中转着圈,他真担心张国焘会指使陈昌浩在背后动手,也怕遇上当地土匪劫径打冷枪。
聂荣臻一路跌跌撞撞,走了大半夜,才摸回一军军部。
林彪还没有睡,见聂荣臻回来了,关心似地问道:“怎么这么晚才回来,谈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
“都谈了些什么?”
“陈昌浩同志告诉我,张总政委向西走后,总是说阿坝如何如何好,强调种种理由,就是不向这边来,企图以既成事实,让我们右路军也向西进。”
“你是怎么对陈昌浩同志说的。”林彪关心的是聂荣臻的态度。
“真是奇谈怪论!阿坝再好,也只有那么大一块地方。我们仅在毛儿盖附近,前后就耽误了近1个月,再不能在这高原上拖了。还是照毛泽东同志讲的,出甘肃,不然,我们就要完蛋了。”聂荣臻说。
林彪沉默着,没有表态。
聂荣臻告诫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很可能要把我们吃掉。”
林彪疑惑地看着聂荣臻,表示不可理解。
“据我所知,张国焘现在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红31军去当政治委员,李聚奎去当参谋长,把你调到另一个军去任军长。总之,要把我们调离原部队。”聂荣臻说。
“不可能吧?”
“什么不可能!只不过是现在张国焘还没有发出关于我们两个的命令,听说副军职的命令已经下达了。”
“你这是宗派主义,我们去四方面军有什么不好。”林彪显然有自己的立场。
“什么?这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警惕。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我说这是路线大问题。”
“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的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哪?我们现在才剩几个人?”林彪的口气里带着反驳。
“是这样,我们一方面军的确只剩下1万多人。可蒋介石的人多呀,难道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聂荣臻的嗓门也越来越高。
聂荣臻和林彪两人争吵起来。左权和朱瑞听到争吵声,也赶了过来,但他们一听争吵的又是“政治路线”问题,也就不敢插话,更不敢表态。左权有着自己的苦衷,他知道当时王明等人怀疑他是托派,这完全是冤枉,因此他在长征途中说话始终都非常谨慎。朱瑞是在长征途中才接替李卓然任红1军政治部主任的,在聂、林争论中,他既不好表态支持聂荣臻,也不好表态支持林彪。
林彪的脸色开始大变,聂荣臻的脸也气成了紫青色。两个人各不相让,“啪”的一声,不知是谁先用巴掌拍向桌面。两个人的拳头都挥动在空中,桌面变成了鼓面。木桌在摇晃着,桌子上的盘子滚落在地。
这是红1军团最高领导人之间在长征路上争吵最激烈的一次,给他们留下的印象也最深,多年后,聂荣臻和林彪都还就此事谈论当时自己的想法。由此可见,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不仅是在红四方面军中大有支持的人在,在红一方面军中的支持者、至少是“骑墙者”也是有不少人的。否则,他是不敢如此胆大妄为地向毛泽东、张闻天等大多数中央领导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起挑战和进攻的。尽管在数年后张国焘因倒台而成“破鼓乱人捶”,但在当时有些人的砝码确实是加在张国焘的天平称盘中的。这种政坛中的微妙之事,大概除当事人的良心知道外,只有毛泽东和张国焘两人最知晓。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