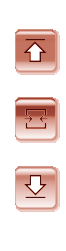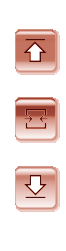|
|
|
|
第四章 大沙漠(一)
|
一天,夜里两点钟,哨子声把战士们从梦中扳醒来。时值盛夏,可是这高原上的夜晚,还是冷嗖嗖的。巷道里,各个院落里,到处都挤满了人。只有偶尔闪亮的手电光和炊事员做饭的灶房里吐露出的灯光,才划破了这漆黑的夜。
开饭了。有的战士还没有完全清醒,便摸着把饭舀到碗里,一连就吃好几碗饭。一锅饭吃完了,另一锅还没有抬出来,就在这一两分钟的间隙中,有人便靠在墙上呼噜呼噜地拉起鼾声,可是饭一来他立刻又吃起来。好像,这样吃饭不是因为肚子需要,倒是为了完成任务。
夜里三点钟部队出发了。骑兵、炮兵,纵横交错的步兵行列,远处手电的闪光,深夜战马的嘶叫声。……
这一带是陕西、甘肃交界的一条险峻高耸的山脉。西北野战军的战士们在这人烟稀少的山地前进,向万里长城进军。当年刘志丹同志曾经率领陕北红军,在这里进行过长期而艰苦的斗争。一九三五年初冬,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首先到达这里;后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在这里英勇奋战。这里留下了毛主席、周副主席和许多巨人的足迹。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中国革命历史的新篇章,实际上是从吴旗镇周围这一带山区开始写起的。战士们沿着红军当年开辟的道路,奋勇前进。大大小小的山头,一直起伏着伸展到天边去了,像是永世也走不完。战士们爬上爬下,一个山头闪过去,一个又突然横挡在面前。仿佛,一个个迎面扑来的山头,是陡然从平地冒起来的。
太阳喷火,战士们身上汗像瓢泼,汗从头顶直灌到脚底下;呼气吸气,嗓子都热辣辣的。他们的舌头粘在嘴里转动不灵,唾沫早就吐不出来了;两条腿除了酸痛还有些粗肿。战士们一步一滴汗,艰难地行进着。
行军第五日的下半天,战士们好像又走到山和水的尽头了。大山,渐渐变成了起伏的丘陵;大河变成细流,眼看着细流也渗到地下去了。
这些干巴巴的红土丘陵地带,很难找到指头粗的一棵树。当地老乡们叫它“八百里火焰山”。人们在这“八百里火焰山”上掏下去四十丈,掏不出水,反倒能掏出老辈子的炉灶的灰烬。
这里靠近沙漠了,水很缺,战士们即使找来一点水也是苦水。
六月末尾的那一天,部队宿在沙漠边沿的小村。
下晚刚一宿营,团参谋长卫毅就紧急地派出二十多个骑兵侦察员,到方圆二十里去找水。
第一营还算机遇不坏,他们驻的村子下面,有一眼小泉子。宿营后,二三十个炊事员,有的抬着大行军锅,有的提着灌水的葫芦,有的提着木桶,在那里等水。泉眼里麻绳粗的一股水往外流着,炊事员们都眼巴巴地瞧着它。啊,这一股清淙淙的细流系着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哩!
第一连一直闹腾了多半夜,才凑合着吃了一顿饭。吃罢饭,有的人还没放下碗,便躺在地下睡着了。
夜里一点钟,王成德召开了支部大会,大伙儿研究了怎样通过沙漠的行军问题。
开罢会,王成德困得站下就睡着了。
周大勇望着王成德,只见他脸黄瘦,眼里网满血丝。他说:“你瞌睡?给眼里放辣面子吧!”
“真是穷开心,你总有气力!”
周大勇的脸色黑黝黝的,两道粗黑眉毛下的一双大眼睛,闪着渴望猛烈斗争的光。他那钢一样结实的身体里,像是蕴藏着使用不尽的力量。他这副样子,让人觉得:不管遇见什么敌人,他一伸手就能掐死他;黄河在他眼里只是一条小水渠,无际的沙漠只是一把沙土;要是上级有命令,他像是可以用刺刀把山削平似的。
王成德看看周大勇,劲头又来了,像是周大勇身上的力量传到他身上了。他说:“大勇!来,咱们把水的问题再捉摸捉摸。团政治处指示,要我们沿途收买老乡的葫芦,用它装水。我们才买到十七个葫芦,这管什么用?”
战士们都睡了,炊事班长孙全厚还在烧水。他烧好最后一锅开水,就把战士们的水葫芦收集起来,一个个地灌满水。过后,他又舀了两碗水,给周连长跟王指导员送去。连长跟指导员,趴在灶火台上头顶头睡着了。看样子,大约他们是正在商量事情中间睡去的。他们头边放着一盏小小的麻油灯。
灯焰噗晃噗晃地闪着。
老孙把嘴放在周大勇耳朵边,想喊:“连长,起来喝水!”
可是话到口边,又留住了。他一手端水,一手扶住灶火台子,微微弯下身子望着连长,那种老父亲疼爱子女的感情在他心里浮起来。
老孙的眼光落到周大勇那又黑又厚的头发上,只见那头发上有几根很小很小的草棍。这草棍大约是昨天晚上部队行军中大休息的时候,连长躺在路旁睡觉落上的。老孙像拿绣花针似的,把连长头上的小草,一根一根轻轻地取掉。他还想端来一盆水,亲自给连长把头洗一洗。哦,如今哪里能用水洗头?连长喝水还没喝够哩!一想起水,老孙的注意力又移到自己手里端的那碗开水上了。他鼓起很大的决心,叫了连长一声。
周大勇猛一睁眼,只见自己口边有一碗水。他嘴唇都干得浮肿起来了,真想把这碗水一下倒在口里。
周大勇从老孙手里把开水碗接过来,悄悄地说:“别吭声!
让指导员好好休息一阵,给他留点水,到他醒来的时候再喝。我喝过几口水了。我这碗水让连部的两个小鬼喝。”
老孙照着灯,只见卫生员三牛和通讯员小成挤在一块睡觉。小成枕着三牛的肚子,睡得可甜啦。卫生员三牛还说些什么梦话。小成的嘴在动弹,莫非他梦见自己正在喝水?老孙心疼起来:“孩儿们准是渴得厉害!”老孙想叫醒他们,可又不忍心打扰他们睡觉;不叫醒他们,又怕他们没喝上水身上出毛病。他的口跟心合计了好几回,还是把水端到他们口边去叫他们。
老孙把三牛推过去,叫不醒,拉一把还不醒;抱在怀里,睡得更实在了。小成呢,老孙叫一声,他哼一声,叫得紧了,他脚乱蹬手乱抡,口里瞎嘟哝。……
天将拂晓的时候,周大勇醒来了,揉了揉眼,身子舒展了一下,走出房子。他双臂帮在胸前,抵挡寒冷。多怪呀:白天晒得身上流油,晚上像是数九寒天,冷得抽筋。难怪老乡们说这里气候是:早穿皮袄午穿纱,抱上火炉吃西瓜。
他巡查了一趟哨岗,回来路过伙房,就顺便走进去。
孙全厚坐在火炉跟前,抱住膝盖睡定了。火光把他油渍渍的灰军服,照得发亮。他一阵一阵打冷颤,轻声慢气的在梦中呻唤。
周大勇蹲下去,左手慢慢地搭在老孙肩上,头挨着头,把全身力量集中在耳朵上,听老孙长一口短一口地呼吸。过了一阵,他又轻轻地摸老孙那枣树皮一样的手,摸那浮肿而烫烧的脚。……
老孙打了个冷颤醒来了。他用衣袖擦脸上的汗。嗨!连长这样严肃地瞅他哩!他说:“误了开饭时间?这……这……”他慌乱地左瞧右看。周大勇压住他的肩胛,要他坐下。
老孙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说:“啊,连长,你要好好睡一觉,你和指导员总是劳累的!!忙,忙,叫人心疼!
周大勇说:“先说你吧,老孙。我看你的病不轻!”
“连长,我,没有甚么病……算不了甚么病!”
周大勇知道,老孙五六天来就闹痢疾,今天行军中,还晕倒了一次。岂止老孙是这样?很多战士喝了苦水都拉肚子。
为了不耽误行程,夜行军中不少战士都是把裤子脱下来搭在肩膀上,让粪便顺腿往下流吧,反正连队里也没有女同志。周大勇想着老孙这几天行军中的艰难,再看看老孙那因睡眠不足而发炎的眼睛和那肿得穿不上鞋的脚,说:“老孙,你是老战士,有什么话尽能给我谈呀!你有病,可又不吭气,这还成呀?”
老孙说:“连长,你不是说要咬紧牙嘛?……咱们炊事班人人脚肿,都有点小病。我能挺住,他们也能挺住。咦!我是个应名的党员,没有啥能耐,吃点苦可还行啊!”周大勇用木棒拨弄火,眉头拧起,长久地满怀深情地望着老孙。他说:“你好好休息。明天晚上十二点才出发;咱们要抽时间准备水,要不,部队就过不了沙漠。这么,你还能得空到卫生队看病。老孙,保重身体,千万保重身体。在这艰难的日子里,老战士比什么也宝贵!”
老孙说:“连长!你快去歇息,看你跟指导员熬累的……,教人心疼!
上级指示,部队在原地不动,抽出一天时间准备水。因此,团司令部命令:各营各连,派人到方圆三十里去找水。到处部队都驻得满满堂堂的,找水不容易,找水的人员跑了多半天,搞回来的水,全团每人还匀不到一茶碗。
团长赵劲准备派三百个战士,再去搞些水回来,可是第二批找水的人员还没动身,就来了出发的命令。命令上写着:
三边分区的敌人准备沿长城向西逃跑,因此,部队提前出发。艰难的行军开始了。当地有谚语:“过了八百里火焰山,一眼望不尽的老沙滩。”一点不假啊!
战士们在沙漠中走路,是走一步退半步,而且每走一步,鞋子里就灌满沙子。因此,他们从昨天下午六点钟出发,走了一个通夜,才走了四十里路。夜里又刮大风,作向导的老乡是过惯沙漠地带的生活的,但是连他们也迷失了方向。部队首长只能按指北针定方向,指挥部队前进。
第二个通夜行军过去了。
天亮了,太阳好像突然从沙漠中跳出来爬上了天空。
天边无际的沙漠像黄色的大海,太阳照在上面,万点光亮闪耀。战士们朝远处望,远处海天相连。战士们朝四面望,天像一口大锅倒扣在广阔的大海上。
一路路的部队行列,望不见头望不见尾,在广漠漠的黄沙中像浮游一样前进。
虽然说经过一天两夜的行军后,疲劳煎熬人,可是离开了大风沙的黑夜,战士们都精神一振。
政治工作人员、共产党员们,前呼后应地鼓动:
“发扬互助精神,战胜沙漠!”
“通过沙漠就是胜利!”
宣传员们站在队伍旁边,嗓子沙哑地讲着今天沙漠行军中大伙要注意的事情。
正晌午,蓝蓝的天上没一丝云彩,挂在天空的太阳猛烈地喷火,沙漠被烧得滚烫,空气灼热。人像跳到蒸笼里一样难受。没有一点水,没有一棵树,没有一丝风,战士们渴得嘴唇都裂口了,喉咙里直要生烟冒火,头昏眼花。很多人流鼻血。马尿下来,人们都眼红地瞅,生怕那混浊的马尿被沙漠汲去。
战士们把烫热的步枪,从这个肩上移到那个肩上,迈着沉重的脚步向前走去。
突然,天空传来轰轰的响声,战士们都习惯地向左右看,到处都是平漠漠的黄沙,没处隐蔽。
周大勇抬头看,只见一架飞机飞得很慢。他想:“侦察机!”
过了一会,敌人三架飞机来袭击。敌人飞机绕了一个圈子,就怪叫着向战士们俯冲扫射,千百条火箭从战士们前后左右穿过,沙子被打得扬起来。
战士们忽地散开,卧倒。只有周大勇直挺地站在那里,气汹汹地掏出手枪,准备朝飞机打。王成德跳起来把他按倒,说:
“干什么?那有卵用!战士们早忍不住了,你一打响,战士们也要无秩序地射击起来了。”
周大勇气狠狠地把枪塞在枪套里。
周大勇拍拍身上的沙土,跟王成德一块走着。他气鼓鼓的,一句话也不说。
王成德问:“你刚才发什么妖风?”
“老王,我什么时候看见了我们的飞机,哪怕是一架,我立刻去死也情愿!”
王成德说:“大勇,你想邪了!飞机我们很快也会有的。一九四一年,我带二百多民兵,把日本鬼子的炮楼围住,攻打了两天两夜,还是啃不动。那会,我们也想过:什么时候有了大批迫击炮、小型平射炮就好了。看,现在我们不是山炮、野炮也很多吗?”
周大勇眼睛盯着前方,紧绷着嘴,不吭声地向前走去。
王成德问:“大勇,想什么哪?气还没消?”
周大勇说:“老王,伤脑筋真是伤够了!有一天我们要有了现代化的装备,我打破头也要掌握它。”
远处刮来大黄风。那黄风,就像平地起了洪水,浪头有几十丈高,从远处流来。战士们盘算:“这许凉快点!”他们把帽檐往下扯扯,让帽檐遮着眼睛,等候黄风刮来。
大黄风裹住了战士们。天地间灰蒙蒙的,太阳黄惨惨地挂在天空。战士们一点也不觉得凉快,反倒像从火炕跳到开水锅里了。这呀,是沙漠地的热风啊!战士们闷热得喘不过气,沙粒把脸打得生痛。他们睁不开眼,迎头风顶住,衣服被吹得鼓胀胀的。大伙定定地站稳,像是脚一动,人就会被风卷到天空去。
热风过去了,太阳又发泼地喷火。暴热、口渴、疲劳在折磨人!
有一个战士跑上来向周大勇报告:“炊事班老孙又昏倒了!”
周大勇急急地离开队伍行列向后跑去。通讯员小成也跟着连长向后跑去。周大勇通红的脸上汗水混着沙土。他浑身是汗,衣服透湿,像刚从河里跳出来一样。
周大勇跑到老孙跟前,看见一个炊事员抱着老孙。
他一条腿跪下去,从炊事员怀里把老孙抱过来,紧紧地搂到胸前。
那个炊事员站起来,说:“连长!老孙,老孙不行啦!”
周大勇说:“去!快去帮助指导员。看,那不是指导员?他又扶着谁!”
那个炊事员望着老孙,迟迟疑疑停了好久才走开。
老孙眼发直,干枯的嘴唇咧开,脸涨得通红,脖子上暴起发紫的血管。他的嘴唇动着,仿佛要给自己的同志和这世界留句什么话,但是说不出来。不大一阵工夫,他的呼吸由急促变得微弱了,脸由通红变成灰白……蜡黄……
周大勇紧紧地搂着老孙,眼珠子一动也不动地盯着老孙那半闭的眼睛,心神错乱地嘟哝:“有一口水就好了!有一口水……”通讯员小成也机械地重复:“有一口水就好了!”
一口水一条命呀!
敌人三架飞机,绕过来又栽下来,一条条的火箭,穿在周大勇周围的沙子里爆炸了。炸起的沙土扑在周大勇和老孙的脸上。周大勇用自己的胸膛遮掩住老孙。
周大勇望着那俯冲扫射的敌机,眼里喷火。他心里猛烈的仇恨混合着撕心的痛苦;浑身颤动,嘴唇发抖。哪怕他周大勇一分钟以后就死去,但是在这一分钟以内,他也要把那美国走狗的心肝挖出来!
团卫生队队长,骑着马赶来了。他跳下马,喊:“有办法,有办法,这针药有效。”
卫生队长拼命地把注射器的针尖往老孙胳膊上的血管里扎,可是扎不进去。生命离开了老孙,血管,筋肉都僵硬了!周大勇把老孙轻轻放到地下,站起来。他把自己的破衣袖子撕下一片,想盖在老孙脸上,免得沙子吹进老孙眼里。可是周大勇拿上那块破布,呆呆地站在那里,像是他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像是他的心脏停止跳动,血液停止循环,思想也木然不动了!
老孙啊,老孙!同志们走路你走路,同志们睡觉你作饭。为了同志们能吃饱,你三番五次勒裤带。你背上一面行军锅,走在部队行列里,风里来雨里去,日日夜夜,三年五载。你什么也不埋怨,什么也不计较;悄悄地活着,悄悄地死去。你呀,你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啊!
小成摸摸老孙衣服兜儿,看有什么遗物可以给老孙家里寄去。他从老孙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一个小本子。小盒里装着针线、破布、铅笔头跟炊事班的立功计划。那上小本子是麻纸订的,因为怕雨淋湿还用油布做了个皮子。那小本子的每一页上都留着老孙的黑指印,每一页上都歪歪扭扭地用铅笔写着核桃大的字:毛主席。
老孙不识字,可是他看见同志们都给毛主席写信,他也想写。他想把自己满肚子的话,写给自己的领袖毛主席。这样,他开始学字。他这上了年纪的战士,宿营后烧行军锅煮饭的时候,在这小本子上花了多少气力!他在紧张行军后的深夜里,在这小本子上写下了多少愿望!他在跟敌人拼死拼活的空隙中,面对着这卷了角的破本子,又有多少次看见了自己的亲人毛主席!如今,他永远不能写这封信了!
周大勇从通讯员手里把老孙的小本一把夺过去,塞在口袋里。他想,他一定要设法把这小本子寄给毛主席。因为这是老孙生前的愿望、死后的遗言。
部队哗哗哗地前进着:战士们,担架队员们……走啊!走啊!老孙没有走完的路,同志们要走完!
战士们用眼光向倒下去的同志致敬。听不见长嘘短叹,看不见愁眉苦脸,只有一种沉重而又严肃的空气,充满在天地之间。
周大勇双手撑在腰里,再一次地望望老孙那老诚忠厚的脸相。啊,这个跟他周大勇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士,永远放下了自己的行军锅,永远再不会向他说:“连长,我没啥能耐,吃点苦总还行……我好赖是个党员。唉,我做的事太少……连长,你跟指导员劳累的,教人心疼!”周大勇心里绞痛:有多少英雄好汉倒下去了啊!有多少热血浇在中国的土地上了啊!
周大勇和小成,用黄沙掩埋了老孙的尸体。团供给处的队伍过来的工夫,周大勇要了一片炮弹箱子上的木板,用刺刀削了削。他从文书手里接过来毛笔,在木板上写着:
共产党员孙全厚,五十七岁,山西孝义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光荣牺牲!
周大勇把这个木牌插在老孙的墓前,望着它,望着它!
周大勇擦了擦头上的汗,背上老孙留下的行军锅,正要去赶自己的连队,团政治委员李诚上来了。李诚满脸是沙土,嘴唇干得裂开小口子,鼻孔里塞了一团棉花,上嘴唇还有干了的鼻血。他的马满身是汗,口里流着白沫。
李诚跳下马,看了看墓牌;站在坟墓旁边,脸上一条条的皱纹像刀子刻的一样。他抬起头,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着前进着的战士。
突然,李诚向战士呼喊:
“同志们!一个战士倒下了,千百个战士要勇敢前进!一个共产党员倒下了,千百个共产党员要勇敢前进!大山沙漠挡不住我们;血汗死亡吓不倒我们。前进!哪里有人民,我们就到哪里去;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更需要我们。前进,勇敢前进!战胜一切困难。”
这用全部生命力量喊出的声音,掠过战士们的心头,在无边无际的沙漠上空雷也似地滚动。
战士们踏着沙窝,急急地向前走去。他们那黑瘦的脸膛上,眼窝里,耳朵里,嘴唇上,都是厚厚的一层沙土;两腿沉重得像灌满了铅。但是,他们都挺起胸脯扬起头,加快脚步,一直向前走去。他们都坚毅地凝视迎面移来的沙漠,凝视远方。
沙漠的远方,一阵旋风卷起了顶住天的黄沙柱。就算它是风暴吧,就让它排山倒海地卷来吧!
周大勇赶上自己的连队。王成德把一个昏倒的战士交给卫生队,也刚赶上来了。他俩肩并肩走去。周大勇敞着衣服,衣袖子卷到肘子以上,两手撑在腰里,肩上搭着米袋子,他扬起头迈着大步,向前走去。他现在的神气,就像每次部队在战斗中快要出击时的神气一样。他瞅了王成德一眼,像要说什么,可没说出来。
太阳快把人烧焦了。渴,渴,渴,渴得要命,任何人都感觉不到自己嘴里还有舌头和牙齿。心脏在猛烈地跳动,但是血液仿佛却越来越稠,越来越流得缓慢了。人们身上手上和脖子里的血管,都发紫地暴起来了!战士们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意志力量,可是不能休息,不敢休息,因为有人坐下去就会永远起不来!部队行进着,加快速度地行进着。战士们都眼巴巴他望着前边,希望前边就是乡村、市镇、草地和流水。往日他们走过千百个市镇、乡村,穿过许多草原,涉过许多河流。那时候,他们很少注意这些时常见惯了的人烟万物。现在,当战士们远远看见一个黑点的时候,就有说不出的欢腾。可是,他们走近那黑点,一看,原来是一堆蒿草。多少次希望变成了失望!慢慢的,战士们也不看了,闷着头走吧!总会走到沙漠的尽头,走到希望的边沿。……三
再次打击了胡宗南重要的帮凶马鸿逵匪徒,收复三边分区以后,西北野战军在长城沿线作短期的休息、整训。旅司令部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布置休息、整训期间的练兵工作。会议一直开到晚上九点钟才结束。
旅长陈兴允在房子里来回踱着,像在筹思什么问题。
紧张艰苦的战斗生活,向革命战士要求旺盛的精力。陈旅长在作战的时候,几天几夜不睡觉;端上一支蜡烛,站在地图下,从上灯时光站到鸡叫,从鸡叫站到更深夜静。现在,部队虽然在休息、整训,从表面上看来军队生活是平静得多了,但是摆在陈旅长这些干部面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比行军作战中遇到的问题复杂得多了。
他浑身充沛着力量,眼睛光芒四射,络腮胡子半个月没有剃又长得黑茬茬的了。人说胡子是衰老的记号,可是他的胡子更增加了他的英雄气概。
有些个中年人,虽然经过很多磨炼,可是他年青时候的性情或嗜好,总以某种形式显露在他的举动上,哪怕这些显露常是很难察觉的。陈兴允现在的举动,显露出他一九三○年还是一个工农红军的连长时,定是正直、勇敢、愉快而又刚烈的人。
旅政治委员杨克文躺在地下铺的马褡子上,头边放着洋磁碗做的灯盏,灯焰一跳一跳地晃着。他借着灯光,看毛主席写的书:《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房子中的墙角,放着一张破方桌。桌边有两个参谋和一个政治部宣传科的干事,在抄写什么材料。陈旅长有时候走在他们跟前,伸头看他们手里舞动的笔尖。
杨克文坐起来,机敏地看了旅长一眼,把书本卷起在膝盖上敲着,自言自语地说:“许多人参加了同样一个会议,听了同样一个报告,看了同样的一本书,可是各人有各人独特的心得!”
陈旅长没听清旅政治委员的话,他扭转身正要问,杨政委又说:“毛主席这本著作,我几年来看了至少有几十遍,可是现在读起来像是第一次才读,觉得书里每一句话都特别亲切、宝贵。怎么搞的?有些道理毛主席早就说过咯,自己也多次听过咯,可是自己在实际工作中花费了很多力气以后才能比较深刻地领会一点。老陈,人,有时候可真笨得出奇啊!”
他急急地把书翻过几页,说:“好久以来,我脑子里有些片断的体会,闪呀闪的,可是把它收拢不起来。看,老陈,看!我读了这一段,突然脑子里像是起了一种变化:一切片断的体会都联贯起来了,明确了。看!这一段:关于集中使用兵力的问题,尤其是这一句话,我看了,一下子就兜出来很多问题,像是自己的脑子里突然豁亮咯。”
陈旅长意味深长地说:“这说明任何一点道理要真正变成自己的,确实是很不容易。不要说你没有体验过的事情,就是你拿全部心血体验过的事情,也要反复多少次,那你才真正算在斗争生活中,学习了一点东西。也许经验主义还在我脑子里作怪,我总觉得人是按照自己的经历走路的。”
杨政委把膝盖猛地拍了一下,说:“一句话,你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理和实际工作结合一点,你就进步一点;结合得多,你就进步得快;但是每一点结合都是不容易的。老陈--”陈旅长用手势打断杨政委的话,说:“瞧,小伙子们打瞌睡咯!”
杨政委说:“年纪越轻瞌睡越多。我背机关枪的时候,部队一宿营,躺下立刻就睡得呼呼叫。”
陈旅长走过去,轻手轻脚地把自己的棉衣给一个年青的参谋披上。
那个参谋醒来了。他又疲乏又不好意思地说:“旅长!我不瞌睡,你倒应该睡一阵。”
陈旅长大声笑了。他把烟卷的一头在桌子上磕了磕,说:
“乱弹琴,睡得咕咕的,还说不瞌睡!”
他坐在那些青年人旁边,看着他们孩子式的脸膛,谈说贺龙将军的工作精神(他有很长时期跟随贺龙将军战斗),谈说战士们的英雄气概跟克服困难的事迹。
一个干事说:“旅长!人要常常想到战士们的英雄行为,就觉得自己有使不尽的力气!”
陈旅长说:“对呀,对呀!身体需要营养,思想也需要营养。身体不营养就要垮,思想不营养就要枯竭。不同的是:一顿不吃饭肚子就闹意见;十日半月不营养思想,人还不一定能感觉到。可是当一个人感觉到思想枯竭了的时候,同志,那他的生命就完结了--死咯,彻底地死咯!而且世界上没有比这种死亡更可怕。”
一个参谋把桌子上的纸张收拾了一下,说:“说来说去,反正我看到战士们的英雄行为,就觉得惭愧!”
“惭愧?”陈旅长举起头,回忆思索着。“我很少有这种感情。战士们的英雄行为总是强有力地鼓舞我前进。是鼓舞而不是惭愧。你不同意?咱们可以辩论呀!”
那个参谋说:“我们不能和你比。你为党做了很多事情,可是我们--”陈旅长打断他的话,说:“你这不是成心说颠倒话么?同志!战士们,我们的战士,才是为党做了很多事情的人,才是为党的事业冲锋陷阵、赴汤蹈火的人。”
夜深了。一阵阵的风从沙漠中吹来,沙子打得窗户纸沙沙响。远处传来骆驼的铃铛声。隔壁房子里,老乡的孩子从梦中哭醒来,母亲悠然爱抚地乖哄孩子。孩子的哭声慢慢地消失了。
陈旅长看着那些参谋们抄写起的东西,一句一句地修改,掂量每一个字的轻重。有时候,他为一句话、一个字,捉摸几十分钟。有时候,他抬起头责备地说:“搞什么嘛!你完全写错了。文化教养差,还不开动脑筋学习。思想懒汉,是最没有出息的!”说着,他就在床头上翻出一包书:有几本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有一本《孙子兵法》,两本写战争的小说,还有五六本描写爱情故事的外国文学译本。
陈旅长讲着各种书的内容。他讲得兴奋了,就放声大笑。
他笑得那样纯真、愉快,简直像一个毫无挂牵的青年似的。
叮--当--叮--当--夜深人静,远处传来的骆驼铃铛声,听得更真切了。这种持续不断的声音,在广阔的沙漠上空波荡,听来是深远的静穆的。这种声音,让人想起坚韧的生命力量和沉重的劳动;也勾起了人的回忆。
杨克文把书放在一边,平躺着,用手垫着头。他静静地听着骆驼的铃铛声。过了好一阵,他说:“今天下午我和周大勇谈了谈。奇怪!我看见他,就想起自己刚参加部队时候的情形。”
陈旅长说:“周大勇总是尽量避免跟我碰头。有闲空子,我要好好整治他!”
“你对他太严厉咯!”
“那是喜爱他呀!”
叮--当--叮--当--骆驼铃铛声渐渐的远了。夜深了,这声音虽然很远,但是听来还非常清晰。
陈旅长侧起耳朵听了好一阵,说:“老杨,骆驼在咱们南方真是稀罕东西。我小时候,那些卖艺的人拉上骆驼在我们乡下转。我跟一群小孩子去看骆驼,好玩得很。有一次,我跑了四五十里路去看骆驼,家里人找不见我急得要死,你说好笑不好笑!”
陈旅长仿佛因为骆驼的铃铛声,勾起了他久远的回忆而觉得奇怪。他慢慢地磕着烟灰,说:“一下子就想到这样遥远的过去!”他背靠着墙,眯缝着眼注视手指间夹的烟卷,烟卷冒起一股很细的白烟柱。他像是又沉入到回忆中去了。
他的生活是复杂的,也是简单的。说复杂,是因为他像千千万万的革命战士一样,经历了艰难困苦与曲折的斗争;说简单,是因为他也像每一个普通的中国劳动人民一样,一出世,饥饿、痛苦、不幸就像身影一样不离他。
三十七年前他出生在湖南浏阳县一个雇农的家里。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给人家做工,担起成年人劳动的担子。
像俗语说的一样:“受的牛马苦,吃的猪狗饭。”穷苦的生活折磨人,穷苦的生活又能琢磨出倔强的性情。
就仗着这种性情,他一九二七年逃出了家门,参加了“秋收暴动”,当了一名红军战士,上了井冈山。从此,他和他的战友,以革命为职业,以部队为家庭,以同志为兄弟,以武器为伙伴。从此,他和他的战友,转战在大江以南的红色根据地;征战了二万五千里;经历了八年的抗日战争,目前又投入到这空前艰难的爱国解放战争中。
一天,吃罢早饭的时光,团长赵劲跟团政治委员李诚,向旅司令部走去。
他俩通过平坦的草滩,跳过一条水渠,到了旅部门口,碰见了陈旅长的警卫员。
旅长的警卫员粗胖高大。说起他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可是提起“老资格”或“大个子”来,全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是有八年军龄的老战士。战斗紧急,子弹乱飞的时光,只有他敢把旅长挡住,不让他到危险的地方去。为这,他常挨旅长的骂,可也常得到师政治部保卫科的夸奖。
李诚喊:“老资格!”
警卫员轻巧地转过身子,很正规地敬了礼,说:“李政委,你不是来开会就是来和旅首长讨论问题。玩的事,你不参加。”
赵劲说:“老资格!李政委今天专门是来玩的。因为,他侦察到你给旅首长准备了好吃的东西。”
警卫员挺高兴,因为赵劲这样有趣的对他讲话还是第一次。他有时候跟别的团首长还可以说说笑笑,可是对赵劲总是敬畏的。赵劲在他印象中,是严厉而很少说话的。他说:
“赵团长,你愿意吃东西,我一定想办法,可是当真没有什么好吃喝!昨天,旅长领上我们满地跑,说是找什么野菜,其实哩,给老乡割了一天麦子。旅长一边割麦子一边和老乡拉话。太阳晒得人身上脱皮,我们想早点回来又不敢催他。看,我手上打了四个血泡!”
李诚说:“旅长找什么野菜?现在粮食并不缺呀!”
警卫员抱怨地说:“旅长说他认识几十种野菜,又说野菜怎么好吃。他呀,首长们都知道,那是说不来的!我们向陇东进军的工夫,有一天在洛河川里宿营,旅长就下到河里去摸鱼,一摸就摸两三个钟头!”
赵劲说:“他一定摸得很多鱼,可惜我们不知道这个消息!”
警卫员说:“什么呀!他摸了老半天才摸到大拇指头粗的五条鱼。就是那呀,他还说他要做几个菜哩。还没等到他做什么菜,老乡的猫就偷偷把鱼吃光,连一根鱼刺也没剩下。旅长把我骂得好惨啊!要不是群众纪律管着,我非宰掉老乡的猫不可!”
赵劲跟李诚向前走去。
警卫员说:“旅首长不在呀!”
李诚问:“到哪里去了?”
警卫员说:“杨政委到城内给地方干部讲话去了。旅长,刚才还在房子里,可是眨眼就不见了。我现在正找他。”
赵劲说:“你这个警卫员真是乱弹琴,连首长也看不住。
要是旅首长碰到特务出了差错,保卫科会砍你的头!”
突然院子里送出了歌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李诚说:“这不是旅长的声音?他在家。”
赵劲一进门就冷冰冰地说:“旅长,你的嗓子确实不行!”
陈旅长说:“要唱得好,我就不必关住门唱咯!”说罢,他从床头摸出了照相机,兴头蛮大地讲,他的照相技术怎样好,会洗印还会放大,好像,谁不会照相就是了不得的憾事。
赵劲不感兴趣地说:“旅长,你照相技术再好,我也不羡慕!”
李诚说:“旅长,这简直是给你泼凉水!”
陈旅长把照相机往铺上一扔,故意生气地说:“赵劲,我照相的积极性叫你一脚踢光咯!”
赵劲嘿嘿嘿地笑了。
他们谈了一阵,李诚说:“下午两点钟我们团党委会要开会,请你和杨政委去参加。”
陈旅长问:“怎么,刘邓大军进入反攻的消息,你们还没传达?”
赵劲说:“早传达咯。今天开会是总结传达工作,布置练兵工作。”
陈旅长说:“战士们听到我军进入战略反攻,高兴得很吧?
我刚听到这消息,整夜都睡不宁!”他看着墙壁上的一张中原地图又说:“你们要随时把刘邓大军反攻的情形,向战士们报告。这样,战士们便知道刘邓大军带头反攻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的转折,就是直接援助我们西北战场,援助我们全国各战场。这是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事件啊!”
赵劲说:“从今天消息看,刘邓大军进展非常迅速。”
陈旅长说:“反动派,是一帮饭桶!他们招架不住刘邓大军的打击噢。”四
团首长们住在长城边一家老乡的上房里。傍黑,赵劲从连队里回来。他的裤子扯开了几绽,绑带上还沾着沙土。大概,他和战士们一块练习战术动作了。李诚背朝门坐在桌子跟前,正看二营的一个工作报告。他看了一阵,把报告轻轻地往旁边一堆,说:“毫无头绪,简直连问题的性质还没闹清!”从本子上撕下一页纸,低下头唰唰地写着什么。
赵劲放轻脚步,用两手把李诚的肩膀猛地按着。李诚肩膀摆了一下没摆脱,说:“别捣鬼!”他想回头看,赵劲两条胳膊使劲推着他的肩膀,躲着不让他看见。李诚说:“老赵,我知道是你。”
赵劲两手松开,望着李诚,说:“你怎么知道是我?”
李诚说:“由你的手劲上我感觉到是你,由你呼吸的声音我听到是你。”
赵劲不出声地笑着。
李诚问:“莫非我说得不对?”
赵劲摇头,眼睛调皮有趣地闪着光,说:“对。我也有这经验:夜战中,有好多回我在阵地上喊你,你准答应。其实,并不是我看清了你,我感觉到那是你。”
两人眼对眼笑了。
赵劲转过身,坐在床边,迅速地解下绑带,又使劲地缠着,缠得非常整齐。他的帽子、绑带、皮带,都整齐而有次序地放在枕头左边。他到现在还保持着这样习惯:晚上睡觉的时候,数着身上脱下的东西,而且记着数目。比方说,解下来的东西是七件,晚上如果有事,他一爬起来,把七件东西数着带上,头也不回就走出去了,准不会丢东拉西。
赵劲两手托在脑后,身子往后仰着靠在铺盖卷儿上。他在回想着这几天练兵的情形。
赵劲的警卫员真够麻烦。一阵,他进来报告:“团长,水打好了,洗脸吧!”赵劲根本没听见。警卫员轻手轻脚地走出去。一阵,他又进来说:“饭搞好了!”赵劲不耐烦地摆着头,让他走开。警卫员摸不着头脑,又不敢多问。他走出去,对李诚的警卫员说:“咱们这些首长,我看等不到四十岁,头发都要落光的!”
“首长们哪里能像咱们,干罢工作就吃饱喝足,扳倒睡觉。他们肩上的担子重!”
李诚说:“赵劲!我要政治处所有干部赶快把'评纪律'的工作结束。然后,他们好集中力量搞练兵工作。”
赵劲没有回答。
李诚走过去,看见赵劲躺在床上,眼睛望着天棚发愣。他笑着说:“赵劲,你像是得了什么病?”赵劲坐起来,一字一板地说:“不是害病的时候啊!”
李诚问:“你今天到第一连去了吗?我下午到六连去了一趟,听六连战士说:第一连练兵工作搞得挺不错。”
赵劲伸了个懒腰站起来,像是要摆脱疲劳似的。他想起今天的练兵情形,想起战士们在练兵中的创造,想起他从连队上带回来的启示和心得。他觉得浑身都是力量,脸上闪过兴奋的光。
赵劲把两个大拇指头挂在腰间的皮带上,来回走着,讲着第一连练兵的情形。李诚听着,寻思着。
八点钟了,熄灯号吹过了。沙漠中刮来的大风,摇着门窗,撞击着长城。
卫毅闪进门来,说:“好大的风哟!”他揉着眼睛,唾着口内的沙土。他眼窝、鼻孔都是沙土。从他朴实稳厚和精力饱满的样子看来,像是他也从连队上带回来很多启示、心得和劲头。他向赵劲和李诚摆了一下手,说:“你们谈什么?一定是谈练兵。嘿!战士们想了很多办法,真是越练劲头越大!”
他盘腿坐在床上,立刻把参谋们都找来,要他们汇报今天参加各连队练兵时光了解到的情况。
卫毅带来满房子的工作热情。
一天,太阳快落山的时光,在野外练习战术动作的战士们,都集合起来,回到小村里去了。周大勇和一营教导员张培,从练兵场走到一块草地上。他俩周围是一片肥沃的田野和草地--沙漠中的绿洲。
目下看来,沙漠中的绿洲便是世上最如意的地方。绿茸茸的草地像绒毯子一样铺在地上。成熟了的麦子散放着香味。
骆驼在远处的沙漠中浮游。放羊的人赶着一群群的牛羊回来了。他们边走边唱“信天游”小调:
人都说三边有三宝,牛羊咸盐甜甘草哟!
这一切在经过连续行军连续战斗以后的战士们看来,格外清爽,格外美好。
张培的旧灰军衣,整齐而清洁;破烂的地方,他都一针一针缝补过了。他慢慢地走着,不停的低下头瞧自己移动着的脚步,看来很清闲。有时候他望着远方的沙漠,像是很有趣味地想算什么。
他上了一个土堆,两条胳膊向前平伸,让风吹进袖筒。回头望望周大勇,笑了笑,像是说:“这样挺舒坦,你也试试!”
周大勇觉着,张培这样谦逊、沉静、诚挚的性情挺好,连最毛躁的人见了他也会心平气和。张培打完仗,到什么学校当个教员,真是太好啦!
“战争考验人,严格地考验着人。这多时,艰苦的生活,唬倒了不少的人啊!”张培望着远处的沙漠,手指轻轻在空中弹着。“营部的刘副官,哎,这个人!他以前是我们的同志,可是现在变成我们前进路子上的障碍物了。”他的头轻轻地摇了摇。“那些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不管他的本质曾经怎样好,功劳怎样大,才能怎样高,都会丧失自己的一切变成精神空虚的人,一直到毁掉自己!”
周大勇说:“上级批准开除他的党籍了。依我说,早就应当开除了!刘副官这样人,他就不知道他为什么活着。一天吃饱喝胀就满足了,让他干点子工作,他就佯佯吾吾混日子。胡搞乱来,……还说什么革命有前途他没前途!我最恨这种人……一个人没有思想,怎么可以活下去呢?一个人逃避生活的担子,逃避斗争的责任,那不就是一块废料吗?”激愤的情绪使得他的脸色更加刚毅。“像我们党的那些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人民的领导人,像我们的英勇而无私的战士,像那许许多多为劳动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他们硬是把历史向前推进了。人难道不应该像他们一样生活吗?”
张培说:“是呀!人都应该像他们那样生活、斗争。”他望望周大勇纯真的脸膛和那喷发着热情的眼睛。停了一阵,他又把周大勇打量了一番,像是从周大勇那魁梧的身材上得到了什么启示。他掉转话头,说:“政治工作做久了,就会觉着:
人的力量是不能估量的,是无穷无尽的。像我们的战士们,你大胆地去估量,他们的力量也比你的估量高出一百倍。”
周大勇说:“我们有不少同志,很年青就牺牲了。他们要活着,那该还有多少力量可以发挥!”
张培轻轻地喊了一声,说:“我们在斗争的道路上,是负着很大的痛苦向前进的!他们有的人只活了二十多岁,有的还没活到二十岁……当然,生命的价值是不能拿时间长短来衡量的。”
周大勇折了根小蒿枝,在口里嚼着,顽强地思量着张培说的话。
张培说:“周大勇,我们的战士们,在旧社会是一钱不值的人。可是他们到了革命队伍以后,就发挥了伟大的力量,成了顶天立地的人。我常想,要是将来我们走到共产主义社会,那所有的人更该发挥多么难以想象的力量啊!”
周大勇说:“教导员,我也想过:我要好好处发挥自己的力量,还得住住什么军事学校。我参加部队以后,只住过几次教导队,知道的东西太少!”
张培望着周大勇的豁亮而愉快的面容,说:“太阳一落,可真凉快啊!--周大勇同志,能有这样机会更好,不过你不要把一个人的学习、锻炼的范围看得太狭小。--看,看,周大勇。那种鸟儿,你见过吗?啊,你没见过。据说,它是沙漠地特有的一种鸟儿。多好看呀!--像你已经比普通人升高了一截。笑什么?你不是战斗英雄吗?告诉你,我们在战斗生活中学到了别人得不到的东西。比方,平时同志们批评你,上级教育你,劳动、学习、锻炼……一句话:你得经过千辛万苦才能懂得那么一点点道理,学得那么一点点知识。可是在战斗中,猛烈的炮火、生死的斗争、艰苦的考验、英雄们壮烈的事迹、同志们的鼓舞,这一切很快地就把人那些庸俗的想法烧掉了!战斗中一个人会很快获得纯洁、高尚的品质。是吗?”
周大勇很少看见过张培这样的热情流露。他很感动,他仿佛看到思想在闪光。这种思想的闪光,让周大勇又一次清楚地看到了人生的道路。
“大勇,我常想,我们的军队不仅是一支军事力量,而且是一支政治力量、思想力量和新道德的伟大力量。你想想看,我们军队到了哪里,我们就把党的声音带到哪里。而且我们的战士拿自己勇敢和无私的行为,给人们建立了这样的榜样:
每一个人应该怎样爱自己的人民,应该怎样生活、斗争,应该怎样一直向前。这就是说:我们军队不但是消灭敌人、打碎旧社会的力量,而且是移风易俗的力量!我说得对吗?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周大勇说:“教导员,我懂得你的意思。党让我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呢,也有决心成为一个对人民事业有用的人。”
张培说:“这是个很好的志愿。能这样,我们就不会辜负这英雄的时代;能这样,我们就能用自己有限的岁月,创造出无限的光辉事业。”他两条胳膊前后晃悠,脚在柔软的土地上轻轻地踏着,自言自语地说:“光辉的事业,光辉的事业……”他转过身来,手托在周大勇肩膀上,望着天和沙漠相接之处,说:“大勇同志,要是世界上没有那一帮剥削人压迫人的畜生,那人生会变得多么美好啊!”
周大勇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着张培那因兴奋而更加光彩的脸色,身心沉浸在一种庄严的向往中。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