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秦可卿:神性与奴性的完美结合(1)
|
薛遒
试看一部《红楼》,将滴滴血泪,却为谁而流?
在第一回中,作者开宗明义: 为闺阁立传!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谓宝玉: “爱博而心劳。”闺阁女子,历历数十人,分而立传,不亦滥乎!其实闺阁女子的群像,共同完成着曹雪芹心中情人的有机组合。贾宝玉的至理名言“女儿是水做的”便是对这一有机组合的旁白。
那么,谁有幸成为这一“有机组合的偶像?”是秦可卿!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第一回)
作者痴,痴在一个“情”字。不难看出,在《红楼梦》的庞大结构中,有一座立体袖珍模型,那就是第五回的“小红楼”。“小红楼”写得扑朔迷离,委婉曲折,却又惊心动魄,酣畅淋漓,道尽了作者衷肠:
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第五回)
在这场幽梦中,宝玉“同谁近”呢?是秦可卿!
那宝玉恍恍惚惚,依警幻所嘱之言,未免有儿女之事,难以尽述。至次日,便柔情缱绻,软语温存,与可卿难解难分。(第五回)
尼尔唐纳德瓦尔施在《与上帝交谈》中写道: “每个人都知道,性体验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惟一的最可爱、最令人振奋、最有力量、最新鲜、 最有活力、最确实、最亲密、最富娱乐性的身体体验。”
作者赋予宝玉充满激情的性体验的伴侣是谁?是秦可卿!
这性体验便是被作者予以豪情礼赞的“意淫”之果。即两颗热烈地爱着的心灵驱动着同样热烈的躯体。这是灵与肉的合一,是在忘我中的融化。而在与秦可卿梦交之后,现实中的宝玉曾“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第六回)。这种带有强迫性的性实验,则已经是世俗的男女间事,“淫”则淫矣,却绝无“意”的灵魂。这也是与宝钗“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的原因。
[]这样说是有根据的。第十三回,可卿死,宝玉“只觉心中似戳了一刀,哇的一声,直奔出一口血来”。淡淡写来,却痛心如此,可见秦可卿这一艺术形象,凝结着作者痴情的块垒。 那么,作者是怎样写秦可卿的呢?
“那宝玉刚合上眼,便惚惚的睡去,犹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荡荡,随了秦氏。”接着,警幻仙姑出现,问宝玉“试随吾一游否?”于是,“宝玉忘了秦氏在何处,竟随了仙姑,至一所在。”即太虚幻境。二者衔接如此之紧,先随秦氏游,转瞬“随了仙姑”,使人物在梦中幻化无痕,诚如端木蕻良所论: 秦氏 、警幻,一体而两形。周汝昌亦认为警幻仙姑是可卿的幻影(见《红楼艺术——红楼之写人》)。“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固然是贯穿全书的旨要,但其引子,却在秦可卿与警幻仙姑于真假有无中的同一。 秦可卿是何等样人?有赋为证:
方离柳坞,乍出花房。但行处,鸟惊庭树;将到时,影度回廊。仙袂乍飘兮,闻麝兰之馥郁;荷衣欲动兮,听环佩之铿镪。靥笑春桃兮,云堆翠髻,唇绽樱颗兮,榴齿含香。纤腰之楚楚兮,回风舞雪;珠翠之辉辉兮,满额鹅黄。出没花间兮,宜嗔宜喜;徘徊池上兮,若飞若扬。蛾眉颦笑兮,将言而未语;莲步乍移兮,待止而欲行。羡彼之良质兮,冰清玉润;慕彼之华服兮,闪灼文章。爱彼之貌容兮,香培玉琢;美彼之态度兮,凤翥龙翔。其素若何,春梅绽雪。其洁若何,秋菊被霜。其静若何,松生空谷。其艳若何,霞映澄塘。其文若何,龙游曲沼。其神若何,月射寒江。应惭西子,实愧王嫱。奇矣哉,生于孰地,来自何方;信矣乎,瑶池不二,紫府无双。果何人哉?如斯之美也。(第五回)
天上人间,独一无二。超过西施、王昭君等千古美女。曹雪芹把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情人写得溢彩流芳,光华四射。端木蕻良惊叹: “作者未给任何人作赋,惟有给秦可卿作赋,赋中道‘其文若何,龙游曲沼。其神若何,月射寒江。’……把可卿的体态比作龙游曲沼,把她的神韵比如月射寒江,集华丽与冷艳于一身,把不可再得的美态和不可思议的神情融合在一起,这才是兼美的意思。”(《说不完的红楼梦》)端木蕻良的惊叹不无道理。请看针对此赋的甲戌本眉批: “按此书凡例,本无赞赋闲文。前有宝玉二词,今复见此一赋,何也?盖此二人乃通部大纲,不得不用此套。” 曹公作赋,用心良苦。“通部大纲”,足以引领全书。
“一声也而两歌”(戚序)。曹公心目中的情人“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第五回)。她兼钗黛之美,兼众钗之美,经过《红楼梦》的全方位衬托与充分理想化,升华为人类之魂,女神的再造;同时,这一艺术形象又具有了千古情人的普遍意义(正所谓“情人眼中出西施”),从而完成了对真、 善、美的执著追求与形象化定型。
但是,这只是作者一往情深的心灵抒发,是写虚,虚写秦可卿神性的一面。秦可卿俗性的一面,作者是如何写的呢?在第五回中,“贾母素知秦氏是个极妥当的人,生的袅娜纤巧,行事又温柔和平,乃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这是对秦可卿之神性在俗性中的照应。第十三回,“‘东府里蓉大奶奶没了。’……那长一辈的想他素日孝顺,平辈的想他素日和睦亲密,下一辈的想他素日慈爱,以及家中仆从老小想他素日怜贫惜贱、慈老爱幼之恩,莫不悲号痛哭者”。
这短短不足百字,写尽了俗生活中秦可卿的几乎全部: 孝长爱幼,尊老怜下,平等待人,慈悲为怀。这评语与其说树起了封建闺秀的道德楷模,更可视为揭示了人类真、善、 美的追求神性在俗生活中的光辉。
神性与俗性,在秦可卿身上得到完美结合。然而,这种对在俗性中的神性之光的礼赞,仍然是写虚。在全书,我们几乎看不到与秦可卿评语相照应的具体事例。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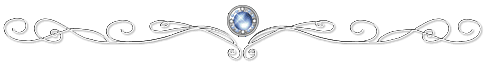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