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是谁把红学引入不归路?(2)
|
三、 陈独秀道破《红楼梦》却无人喝彩
1921年4月,陈独秀在广州为《红楼梦》写“新叙”,陈独秀比较中西方小说,发现中国小说有一个致命问题: 就是写小说既写“人情”,又写“故事”,同时发展,看小说时你却隐约看出了“历史”,你把它当历史看时,你会发现它不过是一部小说!“这种不分工的结果,至于两败俱伤”!岂止是两败,三败俱伤!历史伤了人情,人情又伤了历史,研究者伤了小说,小说又伤了研究者,以至于研究者成了小说的伤害者,也成了读者的伤害者!《红楼梦》最终成了各色人等的智力玩具与各种意图的博弈场!
陈独秀一方面反对用高深思想来批评小说旨趣,又批评把《石头记》当史实考据: “至于考据《石头记》是指何代何人的事迹,这也是把《石头记》当做善述故事的历史,不把它当做善写人情的小说。我尝以为如有名手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可以算做中国近代语的文学作品中代表著作。”①
陈独秀已经批了胡适把小说当历史来考据,可胡适却仍执迷不悟!其实,胡适本人对《红楼梦》一书文学价值一直评价不高,甚至在晚年的一次讲演中把《红楼梦》说成是“狗屁”。既然不是文学至高精品,为何要穷究其背后的似是而非的所谓的问题呢?
不仅不要考据学,陈独秀甚至希望有文学高手把《红楼梦》中缠脚布尽皆斩除,使它成为清纯的文学作品,可惜,胡适没有与同僚们按独秀先生意志去做,如果遵循独秀思路,也就没有了百年红学,我们后人欣赏到的可能是真正的“洁本”《红楼梦》!
陈独秀的这篇“新叙”短短千余字,可谓是独上高楼,望尽了红学天涯之路!他不愧为中国20世纪初思想领袖,可惜,真正的思想者总是发出不合时宜的孤独的声音,人们更多地愿意去捉文化迷藏,看文坛热闹。
四、 李希凡、蓝翎引出毛泽东关注《红楼梦》
1954年,刚刚从山东大学毕业的李希凡与蓝翎在《文史哲》第九期上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使优秀的祖国文学真正为祖国人民所有,成为全体人民的精神财富”是文艺工作者光荣使命,所以要“正确地分析,评价《红楼梦》,使它从各种谬误中解放出来,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欣赏它,让文艺工作者正确地去学习它,也就成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
李、蓝革命性的学术意义在于: 他们把《红楼梦》这部文学著作引入到社会生活场中来讨论,他们深刻地看出,这部名著折射出一个封建时代的瓦解崩溃之征兆。这种宏大的学术视野俯视传统红学与《红楼梦》小说,惊世骇俗,非同凡响。
他们的遗憾也随之同生: 他们把曹雪芹自然而为之文,看成是“革命者”有意而为之文,他们把《红楼梦》从文化场直接引入到政治角斗场,最终成为文化界思想斗争的学术工具!毛泽东亲自批阅“二位小人物”文章,使红学学术之争成为国家文化革命之大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批红学,既是反右之前兆,又是“文化大革命”之前奏,通过红学之争,毛泽东洞悉了文化界隐存的问题以及文化群体的可操纵性。毛泽东的批语: “共青团员,一个二十三岁,一个三十六岁。”并在“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一句旁加上: “不过是小人物”。
这份研究于10月16日被提上中共中央政治局议事日程,毛泽东为此致函中央高层及文化界高层人士: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彭真等等。毛泽东这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提到: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的《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红学”被毛泽东提到政治局议题上来,红楼政治学、红学阶级斗争学也就随之成立并一点点实施起来。中国文化界又失去了研究《红楼梦》主体文本的机会,阶级的批判代替了严肃的学术研究与批评,李、蓝也因此成为文化界风口浪尖上的“小人物”。红学第二次走上学术之歧途,无法回归学术本身。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又是一场红学热潮,红学界有影响力的人物一方面回顾几年红学之争,一方面还在版本、作者身世、祖籍,及一系列似真似伪的“出土文物”问题上大动干戈。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认为,真正的红学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四大支②,除此之物,都不属红学。周汝昌先生所云红学,不过是在《红楼梦》文本外打转圈的“红外学”!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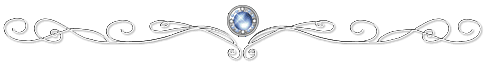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