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辛辣地解剖人情事理
|
我们更应该赞美的是曹雪芹,谈论《红楼梦》的人有福了,这书提供了近于无所不包的话题和机遇。闫红能从中读出的远远不仅是青春和时尚。比如闫红说薛宝钗,就“山中高士晶莹雪”这个判词,论起高士来,她说:
见好就收,点到为止,宝钗从来没有得意洋洋……这种姿态,虽不是欲擒故纵,却无意中增加了她的分量。相形之下,黛玉就显得过于要强,用力太过,不似宝钗那般优裕从容。
当年谢安盘桓东山,也是一点也没耽误他推销自己,不然怎会有“谢安不出,将如苍生何”的说法,所谓的退隐不过是退一步进两步,炒作也分热炒和冷炒两种。
宝钗的志向,其实是不明确的,就像谢安逍遥东山,诸葛亮草堂高卧,并不曾琢磨着要奔着怎样一个官衔。他们志向远大,大到空茫,不复是一官半职,当然更不是皇帝老儿的江山,而是必要成就一番事业的抱负。《诗经》里谢安最喜欢的一句是:銙谟定命,远犹辰告,意思是:把宏伟的规划审查制定,把远大的谋略宣告于众。他认为这里面有一种雅人深致,他不是寻常俗吏,所追求的不是高官厚禄,正是这样一种雅人深致。
但另一方面,造化弄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苦苦追求可能会适得其反,苦心经营也许是弄巧成拙,所以他们不把目标定死,只要方向不错,可以随机应变。他们积极争取的,只是做一个有准备的人,使突如其来的机遇变成花环,一丝不错地落在自己的脖子上。
姜子牙钓鱼,愿者上钩,这是行为艺术,他摆出等待的姿态,却不做过于积极的争取,手持鱼竿立于江岸,他知道命运神秘莫测,他只静静地等待着,命运将要透给他的一点信息。
还了得吗?闫红居然能说出一套高妙的入世入仕宝鉴箴言!现在的年轻人照样能成精!但闫红又说得刻薄了,说下大天来,谢安也罢,姜子牙也罢,宝钗也罢,境界与小红贾芸(被《误读》一书称为职场精英的人)大有不同。用我的习惯用语,他们是有所不为的。有所不为的是好人,无所不为的小红与贾芸则不是好人,是坏人。写刘备仁而近伪,写诸葛智而近妖,人们有时候太仰视了,自己给自己造神,人有时候又确实理解不了比自己高三尺三的境界,也许最多理解到二尺二高,见了三尺三更不要说一丈二了,反而起火,叫做以权谋之尺度境界之腹。
作者对贾雨村的想像也极风格,似是深谙世事。她说:
目睹着贾雨村从清寒的布衣才子,学而优则仕……彻底失去本色,只觉得顺理成章。才子不是君子,有的是聪明而非智慧,他的思想框架如同平行四边形,容易变形,容易妥协,容易为自己找到借口,不但可以无耻,还可以享受自己的无耻。
只是,我常想像,贾雨村是否也会在某一个洁净的月夜,试着寻找一条回到从前的路,隔着苍茫时光,隔着欲望的灰网,望向庙里的多情少年,是否会有一丝惆怅,冰裂纹一般,从那颗藏污纳垢的心灵中炸开,文人的旧习,就像还没进化完的尾巴骨,在官袍下面,隐隐地作痛,他于是摇摇头,自嘲地笑了。
我想告诉闫红的是,文人是文人,也有三六九等,也有各种劣根性,把官场与文人绝对对立起来的依据可能是少不更事的一厢情愿与自说自话。
作者敢说话,既能女性地体贴地谈情说情,也能老到地辛辣地解剖人情事理。对于曹雪芹,对于各派红学大家前辈,她都平视,都敢抡招。当也有说得不够谦恭之处,乃至她说得露了怯,说明她对“红”是知其一二,而不明其三四五六七。“红”是小说,也是文献,对红的研究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文化。“红”是立体的,全息的,不能看到一面就不顾乃至抛弃另一面。谈红正如谈文学,谈政治,忌瞎子摸象。我许多年前就爱说,王麻子卖刀,自卖自夸是可以理解的,搞成“王麻子剪刀,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是不可以的。同样,我喜读闫红的误读,不等于我不喜爱各种正读、(考)证读、深读、探读。大矣哉,红楼梦!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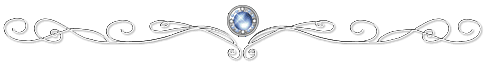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