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第四章 诗词曲赋的隐喻意味和叙事功能(6)
|
柳絮词之填使大观园诗社舞台上的灯光骤然暗转,到了七十六回,黛玉湘云在中秋夜的即景联句使人物从诗的黄昏坠入了令人瑟瑟作抖的寒夜。这次联句不仅诗句本身冷不堪言,而且其背景亦已形成黑云压城之势,大观园世界危在旦夕。联系到整个叙事运势,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湘云偶填柳絮词”,前有“情小妹耻情归地府”和“觉大限吞金自逝”的二尤之死,后有“惑奸谗抄检大观园”的狂风暴雨和“开夜宴异兆发悲音”的鬼哭狼嚎,致使这七十回的填词如同一个幕间插曲,死亡的阴影由此从大观园外过渡到大观园内;而此刻的七十六回联句,又正好就发生在抄检大观园之后,“俏丫环抱屈夭风流,美优伶斩情归水月”之前。虽然残酷的命运还没有直接降临到小姐们头上,但林黛玉的处境已经相当凄惨。一场中秋赏月,花木飘零。宝玉探春因为抄检之事心中烦恼,早早离去;迎春惜春胆小自顾,与黛玉也不大甚合;薛宝钗早已躲避出去与家人团聚了,只剩下湘云一个人宽慰她。而且,似乎是出于湘云宽慰她的一片好意,才有了这篇即景联句。整篇联句由“三五中秋夕,清游拟上元”平平而起,然后铺开,先极写中秋之夜的欢闹,及至“酒尽情犹在,更残乐已缓”一转,开始“渐闻语笑寂,空剩雪霜痕”的丝丝寒意,就连作者林黛玉自己都感叹:“这时候,可知一步难似一步了”。她们一面渲染景象,“阶露团朝菌,庭烟敛文棔。秋湍泻石髓,风叶聚云根。”一面将诗情朝空灵处推:“药催灵兔捣,人向广寒奔。犯斗邀牛女,乘槎访帝孙。盈虚轮莫定,晦朔魂空存”。但是死亡毕竟无可回避,二位少女在天上盘旋了一阵之后,最后不得不落向“壶漏声将涸,盲灯焰已昏”。时间停止,灯烛渐微,然后死的景象惊心动魄地由此呈现:“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
由于后四十回的阙如,湘去和黛玉二人最后结局的细节无从猜度,但我想这篇联句的最后二句便是这二位少女的末日写照。“寒塘渡鹤影”勾勒出一个孤单的形象策应第五回中预言的“云散高塘,水涸湘江”;“冷月葬诗魂”则意味着诀别人们,且是在寒冷的月夜。这种死亡景象在林黛玉的其他诗句中曾屡屡出现,诸如咏白海棠诗中的“月窟仙人缝缟袂”、这次中秋夜联句中的“人向广寒奔”之类。可见,林黛玉死亡场面的设计,在原作者的构思中是与嫦娥奔月的神话有关的,正如晴雯之死被诉诸芙蓉花神一样。遗憾的只是,读者没有能够读到这样凄美的绝唱。
从大观园题咏到中秋夜即景联句,这部分主要有诗会和联句组成的人物韵文,既是整个小说叙事的路标,又以各种不同的隐喻意味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承担了小说的叙事。而且,这些韵文本身又自成系统,前后照应,互相关联,在吟咏基调上有着独立的冷暖调性转换;从大观园题咏和灯谜制作的缕缕晨曦,到咏白海棠的一轮朝阳,再到菊花诗会的如日中天,然后跌入芦雪庭即景联句的牧神午后似的朦胧倘佯,最后经由填写柳絮词的暮霭沉沉,进入中秋夜即景联句的凄切寒夜,这种转换在其象征意味上标记着小说诗神的升起和陨落,而林黛玉则是这一诗神的灵魂。“冷月葬诗魂”既是诗魂的归宿也是诗神的终结。这一终结与贾宝玉的最终出走亦即悬崖撒手互相唱和又互为因果,因为在一个丧失了诗神连同诗魂的世界上,贾宝玉只能作出遗弃这个世界的选择。正如爱情和泪水是大观园世界的血肉部分一样,诗歌和诗才乃是大观园世界的灵魂部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在小说叙事部分中,整个叙述由贾宝玉作引导;在小说的人物韵文部分中,其全部诗意以林黛玉为灵魂。相比之下,每次诗会中,贾宝玉只是一个有力的配角,并且每每评比总是落第。但即便是这么一个落第者,在大观园外的世界里却是首屈一指的人物,这在小说中不仅特意在贾宝玉跟着贾政题对偶时点明,而且还在他和贾环贾兰一起作诗的场面上屡屡呈现,致使即便顽固如贾政内心深处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诗才。整个小说的诗歌设计由此可依次排出三个层次:一个是大观园外男人世界的诗歌,一个是大观园内贾宝玉的诗歌,一个是大观园内少女的诗歌,由浊至清,则低劣到高洁,经由贾宝玉这个中介环节,铺写了诗神连同诗魂同男人是泥和女儿如水这两个世界的区别。面对一个男权世界和一部男性统治的历史,小说将诗歌的高贵和骄傲断然留给了那些美丽纯洁的少女们,并且由那颗晶莹的诗魂成为这个女儿世界的皇后。我想,这也许就是这部分人物韵文在总体造型和总体结构上的隐喻意味。
人物韵文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一系列即兴吟唱。只消稍许留意一下,人们就可以发现在贾宝玉的参禅诗、四时即事诗、访妙玉乞红梅诗、姽婳诗、芙蓉女儿诔、紫菱词这一系列抒发和林黛玉的葬花辞、题帕诗、秋窗风雨夕、五美吟、桃花行这一系列悲鸣之间在情感变化和叙事轨迹上的微妙异同。尽管作为一个小说的叙事灵魂,贾宝玉呼吸领会着一片悲凉之雾,但在诗情上成为导引的却是林黛玉这颗孤傲的诗魂。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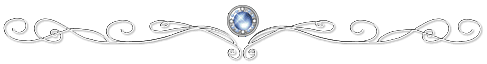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