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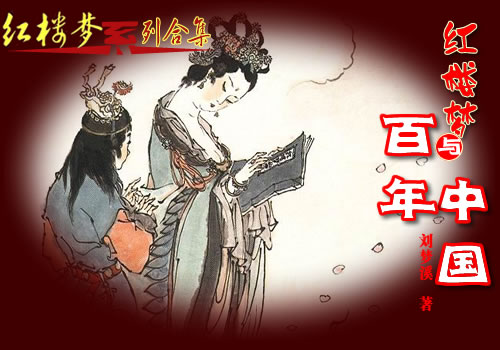
|
|
考证派红学笼罩下的小说批评派红学(1)
|
王国维开其端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命途多舛,刚一诞生,便有王梦阮和沈瓶庵以及蔡元培、邓狂言等索隐派著作相继问世,接着便是胡、蔡论战,考证派红学的压倒优势于是形成。所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多大反响。俞平伯的红学研究,因为代表的是小说批评与文学考证的结合,虽然在社会上有影响,人们却没有理解他的特殊研究方法,误认为与胡适的考证毫无二致,尽管如此,他似乎还感受到一定的压力,因而在《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中自为回护。可见受考证派红学笼罩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处境是何等艰窘。
当然在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之前,梁启超倡导小说界之革命,谈论小说一时蔚为风气,有的专论《红楼梦》的文章,已与我们所说的小说批评非常相似。1915年《小说海》上刊载的季新的《红楼梦新评》参见《红楼梦卷》第一册,第301至第319页。,方法基本上还未能摆脱评点式,但持论甚深邃,对《红楼梦》的反封建的思想内涵多有阐发,论点相当大胆。即如文章在提出宝玉一生钟情于黛玉,而又往往滥及其情于旁人,此不足为训之后,对各种婚姻制度有一段爬罗剔抉的议论。先是挞伐一夫多妻制:“若一夫多妻之制,直视女子如饮食之物。八大八小,十二围碟,样样不同,各有适口充肠之美,下箸既频,又欲辨其味,大嚼之后,便已弃其余,直不视为人类,又何爱情之有?”然后泛论婚姻制度本身:
推而极之,则婚姻之制度亦为爱情之障碍。盖多妻之制,以女子为饮食物,固是私心;一妻之制,以女子为珍宝,亦是私心。西人斥多妻者之言日:“汝有钻石如此,将以之嵌戒指乎?抑将捶为无数之碎颗乎?”此以喻爱情之宜专也。殊不知视妇女为珍宝之心,皎然如见,此不可为讳者也。中国之俗,结婚不得自由。西国之俗,结婚得自由矣,而离婚不得自由……诚以婚姻者以爱情为结合,爱情既渝,为婚姻自然当离也。于是社会学者,倡为废去婚姻制度之说……以余论之,男女相合之事约可分为四期。草昧之世,榛榛狂狂,男女杂媾,无所谓夫妇,此一期也。定以法制,以防淫纵,然野蛮故态,仍未尽去,于是有一夫多妻之制,又有一妻多夫之制,此为二期也。一夫一妻,著于法律,至于情夫情妇狎妓等事,只能以道德相规,不能以法律相绳,此第三期也。为离为合,纯任爱情,此第四期也。以理言之,自以第四期为最宜;然必俟其男女道德皆已臻于纯美,又知以卫生为念,然后可行,否则将复返于榛狂之世矣。法制者,道德之最低级,使不肖者歧而及之者也。因世界多不肖之人,不得已设为法律以制之,使不肖不绝迹于世,则法制终不可废。故今日为计,仍以一夫一妻制最为合宜。
此一系列观念,我们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可以找到依据,立说既大胆,又平实,放在七十年后的今天,也没有过时之感,反证出中国社会发展之缓慢。作者随后又提倡,爱情一是要自由,一是要平等,须“自重其爱情,尤当知重他人之爱情”。因此他联系《红楼梦》的有关描写,认为宝玉的“滥用其情”,便不是以平等为根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季新的《红楼梦新评》,更多地是从社会改良的角度来剖解《红楼梦》,主观注入的思想多,客观分析作品不够。1914年《中华小说界》发表的成之的文章参见《红楼梦卷》第二册,第600至第620页。,在思想上多有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遗绪,也具有一定代表性;不过主要是解释第五回的一支支《红楼梦曲》,见地虽不乏有,可是又认为《红楼梦》中的人物各“代表主义”,则未免太凿。他们近似于小说批评,还不能说是完全的小说批评。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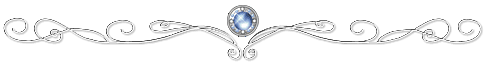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