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贾府的女权至上论者
|
在封建社会的森严氛围中,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格局是谁也不可动摇的,男尊女卑素来被奉为金科玉律。但在贾府这个小社会里,贾宝玉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女权至上论者,他同情女性、崇拜女性,讴歌女性,简直是不遗余力,而对于须眉浊物的男子,鄙夷、厌恶、痛恨,并为自己身在男子行列而深以为耻。
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2回)。
他“便料定,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可有可无”(第20回)。
宝玉这些思想颇有点“民主”意味,岂只是鼓吹男女平等,而是疾呼女尊男卑了,可说是对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信条的一种最为彻底的叛逆!
深居贾府的宝玉,既没有机会读过鼓吹民主思想的启蒙著作(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产生这种著作),又不可能走出重门大户去参加社会实践,以感受阶级压迫的残酷从而构建自己的思想大厦。那么他的这种重女轻男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罗素在《婚姻革命》一书中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所著的《维护妇女权利》(1792年),是那些造成法国革命并为法国革命所造成的思想的产品。从她那时直到现在,男女平等的要求越发受到重视。”
曹雪芹活在世上的时间(1715年或1724年生,1763年或是1764年卒),与法国的这场大革命的时间遥相对应。但中国当时仍笼罩着封建社会的浓云密雾,既不可能产生先进的启蒙思想,也不可能翻译进口国外的理论著作,曹雪芹通过宝玉所表述的这种“先进”观念,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不能不重视宝玉所存在的典型环境,在贾府这个名义上是男性作为主宰的小社会里,实质上是女性在调理一切事情,上有贾母的至高无上的威仪,中有凤姐的大权独揽,下有一大批由美丽的女性所构成的“泱泱大国”,贾宝玉由少及长,生活在这个天真、自由、美丽、温柔的环境里,陶醉在芳郁缠绵的脂粉香中,“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鬟们一起……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
试举女性中的人物,凤姐、秦可卿、黛玉、宝钗、湘云,探春、迎春、袭人、晴雯、妙玉、尤二姐、尤三姐、紫鹃、平儿……哪一个不是美丽、聪明、多情,尽管她们身上也有各种不同的缺陷,但宝玉一概略去不计,只是一味地称颂不已。
而贾府中的男性世界,留给他的却是一幅虚伪、刻板、愚蠢、庸俗、荒淫的图画。贾政的平庸和毫无生气,整日里把仕途经济、光宗耀祖当歌唱,对贾宝玉督促甚严,威赫可惧;贾敬“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余者一概不在他心上”(第2回);贾赦只知猎色,寡廉鲜耻,竟把自己沾染过的丫鬟秋桐,赏给贾琏为妾;贾珍、贾琏除了淫乱,别无他事;贾芹、贾蓉之流更是坏种;薛蟠胸无点墨,宠男色,嫖女妓,横行霸道,劣迹累累……至于那些男性奴才们,一个个相貌卑俗,操行不良。
女性世界与男性世界形成强烈的鲜明的对比,前者使宝玉感受到一种美的生活情趣,一种鲜活的性灵氛围,而后者却使他反感——从生理到心理。于是,宝玉从最切身的体验中,领悟了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的分野,很自然地便产生了“尊女抑男”的思想倾向。
他对男性的厌恶,甚至不排斥自己在内,常为自己的这个男儿之身抱憾不已,自贬为“浊物”,“浊玉”,“俗而又俗”。
在宝玉偷祭金钏儿时,深谙他心事的焙茗祷告说:“你在阴间保佑着二爷来生也变个女孩儿!”
当贾宝玉和甄宝玉见面时,虽相貌、身材、衣着尽皆相同,而心性却相去甚远。听了甄宝玉一番显亲扬名、立德立言之类的“禄蠹”之语,宝玉颇为不耐烦,回来后对宝钗说:“只可惜他也生了这样一个相貌,我想来,有了他,我竟要连我这个相貌都不要了。”(第115回)
宝玉的崇尚女性,也可说是出于一个年轻男子的性心理。宝玉的性心理正是在这个女性世界中开启的、发展的。当一个个美丽的女子,在宝玉面前,或香残玉殒,或远走高飞,或落入苦海,也就不断地破灭着他的梦幻,增添着他对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的憎恨。于是,他的出路也就只有遁入空门了。
欲与美丽而温柔的女性同生共死却不可能,同时又不愿与“浊物”男子在名利场上奔逐 ,惟空门之中可以安置宝玉的存在——远离情欲、物欲,摆脱一种精神的惶惑和绝望。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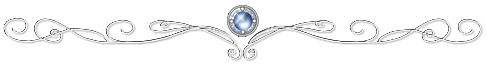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