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生活原型”其实是没有生命的生活实录
|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知所谓的“生活原型”是没有生命的生活实录。除此而外,整部《红楼梦》找不到一个“人物原型”、“事件原型”。首先,《红楼梦》将曹家家世与封建上流社会相融合,以个别显示一般。贾家虽然有曹家家世的投影,但更重要的是概括了封建上流社会许许多多类似贾家的共同特征,从而预示了整个封建社会末世的衰败。其次,曹雪芹将个人的情感与同时代的许多青年的追求和欲望相融合,写出了千千万万青年共同的苦恼与不幸,从而展示了人性向新的层面发展的趋势。再次,曹雪芹在回忆往事时,超越了家族和自我,从世道演变和人性本身,对自我评价,对流失岁月、秦淮旧梦进行思考,并坦诚地表明了自己的困惑和无奈。
而刘心武先生在谈“生活原型”的“虚构”、“想象”时说:“当然要虚构,当然要想像,但是都是从已经存在的活泼泼的生命基础之上去发展,去想像,去架构这个人物关系,去铺展情节。”倒值得我们认真的深思,它揭开了“生活原型”没有生命的生活实录,是如何获取血肉,获得生命的。我们对曹雪芹的创作,实在是知道的太少了,尽管红学家穷年累月地精心考证原型素材,再加上“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展开丰富的联想,但是我们还是难以据实素描似地勾勒曹雪芹的风貌。不过,正因为他写出了一部伟大的《红楼梦》,曹雪芹才成为伟大的人物,从而具有了研究的价值。我们虽然不能详知具体的过程,但清楚一点,曹雪芹是以巨大的情感力量创造这部伟大著作的。
苦难,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是一种精神财富。它涵养了人的气质,提升了精神境界,塑造了人的风骨。否则,无论其身世遭际如何,都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人物。曹雪芹与敦诚、敦敏和张宜泉,彼此唱和,留诗数首。从这珍贵的文字里,了解到他豪放不羁、才华横溢、高谈雄辩的风貌;了解到他叠遭大故、感愤时事、倾注笔端的创作情况;了解到他晚年生活困顿,流落京郊的生活概貌。除却曹家史料和脂评提供的若干信息而外,敦敏、敦诚等人的诗中关于曹雪芹的行状就是最有价值的了。凝缩的诗句,使我们感悟到了一种追求独立人格的精神,一种在人生的无奈中寻找个性至上的精神。
人不能有傲气,但不能没有傲骨。曹雪芹不阿权贵、不随流俗、超尘脱俗,几乎他的朋友都把他比作“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司业青钱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敦诚《赠曹雪芹》)阮籍是一个愤世疾俗的人,狂放不羁,脱略形骸,背叛礼教,曹雪芹引阮籍为同调,遗恨不能生于同时,无奈在梦中以求之,自号“梦阮”。在煌煌一部文学史上,阮籍成了继往开来的一座里程碑,再现了屈原沉痛幽深的心,重弹了《离骚》飘逸浪漫的调。屈原悲怆地呼喊: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阮籍读懂了屈原,他悲沉地写道:
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
曹雪芹很理解屈原和阮籍的心,屈原太“痴”了,为人格,为国家,竟投江自尽了;阮籍不痴吗?然而,谁又能晓得,这痴必是性情中人;这痴必是郁结之心;这痴必是大志难遂。曹雪芹没有像屈原和阮籍那样的官位,那样的名士地位,面向天地,呼天抢地的宣称,而他只是一介寒士,生前默默无闻,但内心的痛苦更加深广,情调更加低沉,用如椽的巨笔写下了调侃而凝重的诗: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人生的无奈,在无奈中寻找,这是一种独立人格的追求,是一种自由思想的追求,是一种众人独醉我独醒的精神!这种精神,不是视富贵如浮云,而是拒绝与功名相掺合的庸俗。
他像阮籍一样,地地道道用青白眼观察社会。他用青眼,看到了被侮辱、被压迫的青年女子悲惨的命运和人生;他用白眼看到“须眉浊物”般的贵族上流男子的卑劣和无耻。《红楼梦》是曹雪芹用青白眼辨析后的活生生的社会写实。
他像阮籍一样,敢于公开表示好色,喜欢他所喜欢的女人,好色而不淫。曹雪芹用一生的心血描写贾宝玉是一位情痴,是一个意淫的典型,嘲笑用封建礼教包装的市俗世界。
他像阮籍一样,穷得家中别无长物,除了书就是酒。他读书,平复他受伤的心灵,开拓他驰骋的思路,挥洒他创作的灵感。他嗜酒如狂,在酒醉朦胧的意态中远离世俗的黑暗和不幸,在酒醉亢奋的激情中走进创作的天地,恰如敦敏所题:
醉余奋扫如椽笔,
写出胸中块垒时。
曹雪芹少年时代一下子从“钟鸣鼎食之家”跌落到“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贫困境地,虽然受到巨大的打击,面对残酷的命运,他依然狂放不羁,抗争命运,不惧厄运,一股英气胆魄溢于言表。等到他晚年,体力渐渐不支,贫困对他的精神和生活的压迫,日见加著。敦诚说他“举家食粥酒常赊”;敦敏说他“卖画钱来付酒家”。人生只有在最艰难的境遇下,才能体会人格的伟大。曹雪芹的人格伟岸虽不减当年,但更多的是借酒浇愁,敦诚以诗劝慰:
劝君莫弹食客铗,
劝君莫叩富儿门。
残杯冷炙有德色,
不如著书黄叶村。
曹雪芹在朋友的鼓励下,愤发著书。他创作《红楼梦》的过程,我们几乎无所知之,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其心理动机的揣想。古今中外的作家们,其创作心态虽多种多样,但大抵离不开“发愤”二字。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段话道出了这些卓越人才的创作心理机制,一般都是从大得大失、大欢大悲、大起大落的生命体验中经历过,“意有郁结”而后产生巨大的悲愤的情感力量。它不再为个人的悲愤的处境而呼天喊地,而是指向了冥冥的上天、苍茫的大地,进行无穷的拷问;将自己溶于历史长河之中,思索兴荣衰败的答案;追问人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愈是拷问的执著,愈是思索的深刻,愈是趋向哲思,也就愈是远离芸芸众生,愈是不为世俗所理解。
这是天才的痛苦!天才的孤独!也是伟大的痛苦!伟大的孤独!
曹雪芹内心激荡的情感被岁月不断冲洗后,趋于淡泊。平静背后孕藏着巨大力量。身处末世,半生潦倒,一事无成,他只好立言,以“假语村言”,为“闺阁昭传”。出于这样一种创作动机,年年岁岁守着“蓬牖茅椽,绳床瓦灶”;日日月月伴着“晨风夕月,阶柳庭花”,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就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完整的梦,给世人一个清醒的梦,给后世一个理想的梦。在他的心中,不仅仅是八旗才子的“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而是透过悲凉之雾看到美丽可爱的女儿世界,激发了他“写出胸中块垒时”,“直追昌谷破篱樊”!他用生命在拼搏,同时向中国文学的顶峰冲刺!
曹雪芹正是用这种巨大的情感力量,创造和升华,才使得“原型素材”长入《红楼梦》的肌体之中,赋予“作品中的人物”以最鲜活的生命!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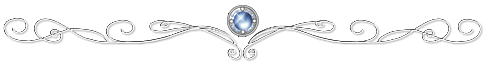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