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第十五章 明修暗度
|
脂砚在“诸奇书之秘法”中,提出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法。这个典故原本出自楚、汉相争时,刘邦将从汉中攻打项羽,故意明修栈道,暗中却绕道奔袭陈仓,取得胜利。脂砚意中所指以何为例?暂且不管,我如今借它来举示雪芹写《红楼》的一大关目,即他如何来写宝玉这个核心人物,真主角。我的领会是:他一面明修,一面暗度;明修是假,暗度为真。这与军事家用兵的策略本是两回事,但在写一个人,却从明暗两面一齐用笔,则实为小说文学中的首创之奇迹,别家也是再没有与之比肩望背的。
前章已曾略涉雪芹如何传宝玉之神的“描写”问题,那只是从一个题目或层次来讲论,如今则宜更从明暗两种笔法来重温续理。
如前所举,宝玉是何如人?他是通了灵性的一块未得补天之用的神石,因受屈抑歧视,不甘寂寞,要下世为人,经历红尘中的享受。但他赋气殊常,秉性特异。第一场冷子兴向贾雨村“介绍”,已把这个孩童说得十足的不成样子。王夫人向黛玉的“介绍”,更为“严重”可怕!真是天下难逢、人间罕见的一个“怪物”。此即明修是也。甚至还又加上了两首“显眼”的《西江月》,大书特书,将此宝玉直贬得是一无可取,浑身是病。甚至直到写了宝钗入府之后,大得人心,黛玉有所忿忿不平,那时方叙宝玉与黛玉的熟惯亲密,还是要给他加上一个“愚拙偏僻”的“考语”(“鉴定”也)。请看,雪芹在使用明笔时,不但不肯“省力”,不肯“留情”,而且是着实的加重渲染勾勒,绝不含糊。
可是,贾雨村听了冷子兴的话,就曾正言厉色地指点说:非也,你们都弄错了,不懂这孩童的“来历”——他的聪明灵秀,居于万人之上!
然后,那是到了第五回,宝玉在秦可卿房中午息,“神游”幻境,遇见了那位多情的“警幻”仙姑,从她口中也“援引”了宁荣二公先灵的话:“唯嫡孙宝玉一人,禀性乖张,生情怪谲。”又加重了一层明修之笔。这真是“一之为甚,岂可再乎?”岂可再三再四乎?
然而,石破天惊——仙姑所引宁荣二公之言,跟着又出现了一句——聪明灵慧,略可望成。
这已奇了。更奇的是仙姑自己又加上了一句: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
仙姑因而明白表示“吾所爱汝者”,此也。
这就是好例:在明笔中,猛不防给了一个暗笔!暗笔份量很微,而且中间又总带着明笔来“掩护”——如仙姑也说他“未免迂阔怪诡”,是也。
雪芹行文至此,到底读者领会的是什么?好还是坏?他就“悉听尊便”,不遑恤矣。
还有奇的,“知其子者莫若父”,读者以为贾政给人的“印象”,总离不开一条:见了宝玉就瞪眼,申斥,排揎,骂“畜生”、“孽障”——以为他对宝玉是“恨之入骨”的了。这真真是“被作者瞒过”(脂砚语)。今时人己不懂二三百年前八旗大家父子的关系,严厉至极,不能当众表现出一点儿抚爱之情——于是都大骂贾政“封建势力”。其实又弄错了。——怎么说?如何会错了?
我请你看看这一例:
第二十三回,元春怕园子荒闭,传命姊妹宝玉等可以入园居住。那贾政遂召集子女,都先到了,只宝玉不敢来(怕又是责斥),“一步挪不了三寸”。及至到了房门,赵姨娘打起簾子,宝玉低身挨入(也许是倚门而立。门口侧立,是旧时晚辈进屋后的侍立的“合法”地位)。那贾政举日一看,——
见宝玉站在跟前:神采飘逸,秀色夺人。
请看这八个斤两奇重的大字!这一种“描写”,又是诗的传神句法,画的“颊上三毫”。但这种夺人的神采,不由黛、钗或任何一位女儿心目中传来,却偏偏从严父的心臆中流露而出。那笔似乎轻轻一点即止,实则其力千钧,因为整部书中贾政也从不曾“假以词色”的,漫说如此着语了。
这又是一层似明而暗、似暗又明的写法。
以上,人人都说宝玉的禀性乖张奇僻,到底是怎么一个样子?书中又是在哪儿写的?这是直到第二十一回,袭人箴宝玉,这才首次“正”写;然而回目既标上一个“箴”字,可知雪芹是“又要蒙蔽读者”(脂砚语),他总是先从俗常“正统”观念的角度去“明”写宝玉之“短”之“病”,而只在“暗”里淡淡傅彩,轻轻勾线——透露的真情何在?让我们自去“参禅”,自寻悟境。
袭人为什么要“箴”他?所“箴”者皆是何纲何目?这就说来话长。在宝玉的原来秉赋上,从“神游”起,又更加上了新的乖僻、迂阔、荒诞……。所以在第五回回后,戚序本有一段总评,说得最好:将一部(书)全盘点出几个(人物),以陪衬宝玉,使宝玉从此倍偏,倍痴,倍聪明,倍潇洒,亦非突如其来。作者真妙心妙口,妙笔妙人!
这正是一位最懂得(理解)宝玉和雪芹的人,才批得出这样的妙语。你看他虽只用排句举出四点,也恰恰是世俗贬者的与知音见赏者的高层评赞的两大“对立面”这就可知,袭人之箴,大约不出那“偏”、“痴”的栏目之外了。
那是元春省亲既罢,史湘云首次见面——她总是在热闹繁华局面之后最末一个出场。她来后,立即有“四个人”的妙文(黛、钗、湘与玉)。湘宿黛处,宝玉恋恋,夜不知归屋,晨不待其梳洗;倩湘云为他打辫子,透露了押辫珍珠竟送了密友(至于要吃胭脂,被湘云打落,与前文见了鸳鸯便要吃她唇脂一脉相连,都不遑细论)……。这种“无晓夜地和姊妹们厮闹”,引起了袭人的不悦,掀起了小小一场风波。这又纯属明笔。若只认这些“不肖”行径,便会忽略了别的层次。原来这一回并非“初箴”,在第十九回“花解语”时早已“箴”过了一次了。那时所箴何条何款?何以要箴他?——
……袭人自幼见宝玉性格异常,其淘气憨顽自是出于众小儿之外;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儿。近来仗着祖母溺爱,父母亦不能十分严紧拘管,更觉放荡弛纵,任性恣情——最不喜务正。
此皆一个丫鬟的了解与理解。她之所箴者:
一,不许说“疯话”(如愿她们永守不离,直到化灰化烟、没了知觉形质为止……)。
二,假装喜欢“读书”(按:此特指八股文章的事情,不可误会),不许当众讥诮“读书上进”的是“禄蠢”,说前贤之书都不可信,……惹父亲生气、打嘴……。
三,不许再毁僧谤道。
四,不许调脂弄粉。
五,不许吃人嘴上搽的胭脂与那“爱红的毛病”。
凡此,尽属“明”的一面,是“暴露”和“揭发”的性质。
但是紧跟着下文是什么呢?是听曲文,喜得击节不已,几乎“唾壶尽碎”。又仿作,又作褐,还又“续《庄》”。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他何尝不喜读书?只不过“书”是不同的,《西厢》,《牡丹》,《庄》,《骚》,……他简直入迷了——也就是说:他有一面为俗常人诧讶难容的“不肖形景”,他又另有一面同样为世人不解的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探索,审美品味。但这一面,总是不用正笔,总带着“贬词”,或只“暗度”,——并且绝无孤芳自赏、骂世嫉俗的任何口锋,叹惜伤感的气味。
在这两三回书中,方是专写宝玉性情气质、天分才华的真正文章,而你已可看得分明,雪芹写人,毕竟都是怎么运笔传照的。这就是《红楼》艺术的一大绝技。
旧日的欣赏批点者,并不是用今天我们这种语文和方法来表达他们的感受的,他们用的是咱们中华传统的方式,且引一二则来,似乎也可以佐助浚发今日读者的灵智。第十九回之前有一绝句,写道是——
彩笔辉先若转环,心情魔态几千般。
写成浓淡兼深浅,活现痴人恋恋间。
同回回后又有一段总评云——
若〔欲〕知宝玉真性情者,当留心此回:其与袭人,何等留连;其与画美人事,何等古怪;其遇茗烟事,何等怜惜;其于黛玉,何等保护!再,袭人之痴忠,画(美〕人之惹事,茗烟之屈奉,黛玉之痴情,……千态万状,笔力劲尖,有水到渠成之象,无微不至——真画出一个上乘智慧之人,入于魔而不悟,……
批者的理解力是高级的,也正说明了《红楼》艺术的非凡超众,使他心折不已。(我略去的一些“警悟”语,其实也是当时为了公开,不得不周旋世俗的障跟法而已。)问题落到今日我们这一代人,是否也还能同样赏会那支劲(简净健举)尖(深刻锋利)而运掉自如的彩笔呢?
至于宝玉究为何等人?批者所指最为中肯:乃一上乘智慧之人。但本书旨在谈艺,不能多涉此义〔1〕;为晓雪芹笔法之妙,且再引二例,以为本章收束。一例是宝玉病起,出户行散,杏花谢尽之时;一例是他“不肖种种”挨打之后,莲叶尝羹之际。
那日正是清明佳节,天气甚好,宝玉饭后闷倦,袭人因劝他园内散散:宝玉听说,只得拄了一支杖,靸着鞋,步出院外。因近日将园中分与众婆子料理,各司各业,皆在忙时,也有修竹的,也有[乌刂]树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种豆的,池中又有驾娘们行着船夹泥种藕。香菱、湘云、宝琴与丫鬟等都坐在山石上,瞧他们取乐。宝玉也慢慢行来。湘云见了他来,忙笑说:“快把这船打出去,他们是接林妹妹的。”众人都笑起来。宝玉红了脸,也笑道:“人家的病,谁是好意的,你也形容着取笑儿。”湘云笑道:“病也比人家另一样,原招笑儿,反说起人来。”说着,宝玉便也坐下,看着众人忙乱了一回。湘云因说:“这里有风,石头上又冷,坐坐去罢。”
这已又是诗境了,中间还夹着湘云对他病中疯状的戏谑,也是一种暗笔“三染”,然后——
宝玉便也正要去瞧林黛玉,便起身拄拐辞了他们,从沁芳桥一带堤上走来。只见柳垂金线,桃吐丹霞,山石之后,一株大杏树,花已全落,叶稠阴翠,上面己结了豆子大小的许多小杏。宝玉因想道:“能病了几天,竟把杏花辜负了!不觉倒‘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舍。又想起邢岫烟已择了夫婿一事,虽说是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儿。不过两年,便也要”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再过几日,这杏树子落枝空,再几年,岫烟未免乌发如银,红颜似槁了,因此不免伤心,只管对杏流泪叹息。正悲叹时,忽有一个雀儿飞来,落于枝上乱啼。宝玉又发了呆性,心下想道:”这雀儿必定是杏花正开时他曾来过,今见无花空有子叶,故也乱啼。这声韵必是啼哭之声,可恨公冶长不在眼前,不能问他。但不知明年再发时,这个雀儿可还记得飞到这里来与杏花一会了?“这才真是“活画出一个上乘智慧之人”的“心情魔态”,令人不胜其感叹,为之震动,为之惆怅。
但是,正在这一点上,他与世俗的“价值观”、“利害观”都发生了冲突,世人如何能理解这么一个“怪物”?说他是疯,是呆,是愚拙乖僻,所谓“万目睚眦,百口嘲谤”了。他父亲不是不爱他,只是不“懂得”他;加上了诸事凑泊,最后贾环使坏,诬陷他“强奸母婢”,才激怒了贾政,誓欲置之死地——怕他今后会惹出“拭君”的大祸来!这怎怪得那时代的一位严父?宝玉吃了亏,死里逃生,卧床不起,这引出莲叶尝羹一段故事。这都“不算”,最妙的是偏偏此时傅秋芳女士家婆子来看望慰问,宝玉一段痴心,看在秋芳的面上,破例让婆子进来了。及婆子告辞,出了院门,四顾无人,她两个悄悄对话起来——那两个婆子见没人了,一行走,一行谈论。这一个笑道:“怪道有人说他家宝王是外像好里头糊涂、中看不中吃的,果然有些呆气。他自己烫了手,倒问人疼不疼,这可不是个呆子?”那一个又笑道:“我前一回来,听见他家里许多人抱怨,千真万真的有些呆气。大雨淋的水鸡似的,他反告诉别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罢。’你说可笑不可笑?时常没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且是连一点刚性也没有,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的。爱惜东西,连个线头儿都是好的;糟踏起来,那怕值千值万的都不管了。”两个人一而说,一面走出园来,辞别诸人回去,不在话下。
请你且慢开颜捧腹,请你掩卷一思:雪芹是何等样人?他怎么想出来的这个笔法?写一位全部书的核心主角的外貌内心,却让两个陌生的、无文化教养的婆子来给他下“考语”,写“鉴定”!你道奇也不奇?古今中外,小说如林,可有哪一部是这么用笔的?
这个,我真不知道在新的文艺理论上用什么术语来标名此一艺术奇迹?所以在孤陋寡学的无可奈何中,我只得借来了“明修暗度”的提法。
自然,你也会更为明白什么叫做“背面傅粉”了吧?
〔1〕请参看拙著《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中编,专论这个主题。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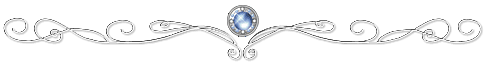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