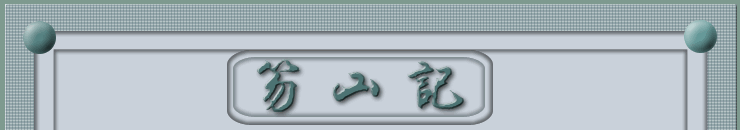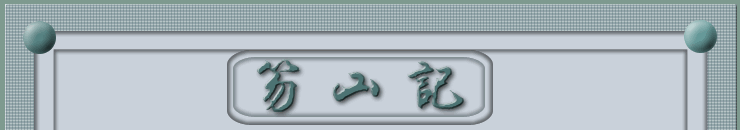|
无知自延秋亭留幸,已将花容四王子挂帅之议言于王。王哂之。无何,足足复奏曰:“丞相苦欲四王子出师,必有灼见。妾 与 白 真 妃,同 心 夹 辅 王 子,何 忧 战 不 克,虏 不擒。”王曰:“妃子何所恃以克敌?” 足足曰:“ 安不忘危,进不忘退,胜不忘败,朝夕恐惧,虚其心以采众议,妾所恃者此而已矣。”王喜曰:“娇鸾惟不知恐惧,故无功。今妃子能为此言,国之福也。往时妃子卤莽好杀人,自征韩火产王子,便精细有谋略,妃子此言,军国之福,亦妃子之福也,朕何忧。” 会玉鲸飞、玉鹏飞兄弟,从黄石逃至紫都,无知唤至相府问之,言三弟散布流言,谓王师欲尽诛玉氏,故玉氏子弟,人人自危,甘为之用。自恃城池深固,又有蓝眉妖术,用毒雾笼罩诸险要,故可贵妃不能进兵,反为纸兽所败。三弟自立为竹山大王,以婆胡弟子许小蛮为后,许粉儿、许朵儿为妃,皆传脂粉作女妆。凡竹山、黄石、瞿谷、圣姥诸处,择男子壮健而美者入宫,悉与淫乱。蓝眉仙又以妖术摄四城妇女。初犹以小惠,笼络百姓,自王师退后,益放恣。苛刑厚敛,日甚一日。今玉氏子弟,渐有知玉侯之冤而出怨言者。无知录其言,与花容谋。相与奏王,拟于未出师之前,为玉夫人韩吉姐作一檄文,明玉侯之死,实为蓝眉妖术所弑,以释玉氏子弟之疑。王然之。乃召指挥使张小微服私往黄石,将檄文遍贴四城。张小领旨,约结义兄弟张珍、张布、刘士刚同往。花容作就檄文,呈览,王大喜。缮写停当,张小等,领了檄文,即日起行。
张小居黄石久,其地多产苎,居人咸织苎为业,遂扮作贩苎客人。至黄石时,正值仲春天气,花天草地,街市繁华。百雉高城,十分完固。乃私议曰:“当年王为黄石侯造这城时,只防不坚,今日却嫌他太坚了。” 刘士刚曰:“ 妖焰不长,虽坚奚益。” 四人一面说,一面笑,正欲寻个客店安歇,忽有人从张小背后拍其肩曰:“ 张小哥别来无恙?”张小吃了一惊,回顾那人,正是旧日的博徒玉振之。振之曰:“闻小哥在紫霞做了高官,那得空到此。”张小曰:“虽曾做了不三不四的官儿,只是拘束得不耐烦,久矣被人参了。”又指着珍布等曰:“今与伙计们做些买卖,不知近来的苎价如何?” 玉振之曰:“买卖的事我不懂得,我家里有所空房子,可以安顿你四人。如你们舍馆未定时,可搬行李来权时住着,好早夜攀话。” 张小曰:“ 这个不须。我们做买卖的人,或一两月,或一两日,不能拿得定的。不如客店里行止自如,较便。” 振之曰:“ 恁地时,不强了。那西边榆树下这绿油招牌的客店,是有名的好客店。” 张小点点头曰:“我就在这里安歇罢。明日得空,到店里吃盏清茶,与足下慢慢的倾谈。”振之遂拱拱手去了。
这振之原是玉无敌侄儿。无敌自以为先世旧臣,王居黄石时,甚礼重之。凝命元年表求黄石太守,王不许,以为黄石参将军。及三弟称王,又受伪将军之职。然为人外;谦而内蒙暗,不达事体,亦罢归。生一子一女,子名敬之,眉目端好。三弟召至竹山,逼淫之,旋放出。媳许氏,牢阑邑人。女名翩翩,美而黠。时竹山黄石,凡有孕的,无贵贱限三月内,在平天圣母衙门报名,满八月,即将孕妇剖腹而取其胎,又剖胎而取胎之肝,以行邪术。如有隐匿不报,全家剥皮。玉敬之妻许氏,孕已五月,举家忧惧,敬之谋之振之,振之谋之张小。张小曰:“ 此易耳。敬之若亲来求我,必得当。” 振之以张小之言复敬之,敬之恐客店中谋事易泄,乃具酒密室,请张小至家跪而求之。张小曰:“ 易易耳,何不令尊奶娘诈病,请医请巫的闹将起来,佯言不愈而死,将棺穴一窍,令闭目卧棺中,举家假哭,送出西郊僻静处,先使人通知牢阑尊岳丈处,使精细人具软舆,豫伏在此,密将棺中人置舆中,承夜舁回牢阑,汝父子却将空棺葬了,假哭而回。神不知鬼不觉,你道此计妙么。” 敬之扑的拜在地下曰:“ 此真妙计,难为张大哥想得出。” 振之曰:“此计虽一时瞒过,终久却怎样呢。”张小曰:“悖天理的必亡,行妖术的必败,竹山黄石之灭,旦夕间耳。那时夫妻父子完聚,须无忘小可今日。” 敬之大喜,进内捧出纹银五十两谢张小,张小那里肯受。正推与间,忽闻嘤嘤的啼哭声,一女郎阑入,密室中哭拜于地曰:“两哥哥为嫂嫂谋,独不为妹子作地乎。”敬之曰:“翩翩有客在前,无作闹。” 翩翩曰:“哥哥,既请此客谋嫂嫂的事便不是外人,求贵客救儿一救。”张小惊曰: “ 汝处子亦有孕么?” 翩翩起而唾曰:“呸!这客人甚无赖来谑儿,只为黄眉好摄人家闺女,行采补术,若 想 到 儿 时,这 就 迟 了。贵 客 善 谋,当 亦 豫 为 儿地。”张小搔着头想了一回,笑曰:“这个更易,三十六界,走为上界。”翩翩曰:“儿又如何走法?” 张小曰:“ 汝有甚么姑母、姨母、妗母么?” 翩翩曰:“问他怎的?” 张小曰:“今时的风气,凡偷汉的妇女,多在姑母、姨母、妗母处做出来。那姑母、姨母、妗母又百般的向他父母处弥缝。男子欲勾搭妇女,亦先用钱财买通那姑母、姨母、妗母,暗做牵头,故有姑母、姨母、妗母的便好做事。” 翩翩曰:“ 呸,呸!这风话给谁听,儿的姑母、姨母、妗母并亡故了。” 张小曰:“你既无姑母、姨母、妗母,你的老公呢?” 翩翩曰:“呸,呸,呸!说甚么鬼话?” 以袖掩面又呜呜的哭。敬之见张小说这些话,又不敢恼,只得减着性子曰:“ 我这妹子,并未曾许亲的,不知张大哥有妻室么,如未娶妻时,可使渠跟着你走。” 张小曰:“某虽无妻室,只是这小姐某不要的。”振之笑曰:“张大哥想是发了些财,志气高些。我且问你我这妹子,千中不能选一的,论门户呵,却是一位千金的小姐,如何配你不过。” 张小曰:“ 有两件配某不过。”振之曰:“那两件呢?”张小曰:“第一件,是年岁。某今年四十有一,这小姐才得十余岁,如何配得某过?” 振之曰:“第二件呢?”张小曰:“这一件更难,某这相貌,生得头尖眼小,脸赭发黄,头脑儿、身手儿,比他人的多不合。小姐的眼如秋水,螓首凤鬟,与某的头儿、眼儿、发儿不对了。桃花的脸,杨柳的腰,粉捏就纤纤的十指,与某的脸儿身手儿又不对了,如何配得某过。” 言到这里,引得那翩翩,哑的笑将出来。正笑不迭,忽闻拐儿响,一白髯老者,踱进密室里来。张小大惊,旋点头作个揖曰:“ 这位就是老将军么?违教了许时,养得白发朱颜,阿小认不得了。” 老者曰:“老夫就是玉无敌。你们的言语,老夫在屏后一一听见了,至于 婚 姻 的 事,小 女 不 嫌 大 哥,大 哥 反 嫌 小 女,何也?”张小又作个揖曰:“老将军前不敢说谎,只因阿小年长貌陋,断不中小姐意,故此这般说。” 无敌向翩翩笑着曰:“我儿你中意他么?”翩翩不答,红着面走出去了。
时日已黄昏,张小亦拜辞无敌父子,回寓而去,将此事言知珍布等。刘士刚曰:“此段婚姻,不可推却。一来哥哥得了个慧美的嫂嫂,生个少爷,终身有靠。二来做了亲戚,便好讽无敌父子投降,做个内应。倘平了黄石,哥哥的功劳不小,不是初出紫霞第一功么。” 张小然之。明日,玉敬之、玉振之又来寓所,致无敌意。邀请小酌,并请珍布、士刚。张小猜着了几分儿,先佩了金玉兽环合欢宝为聘物。四人换了新鲜的衣服,随着敬之兄弟,到景泰坊。只见无敌已扶着拐在门前拱候了。四人进了玉府,坐定。张小曰:“屡次踵府,未曾请老夫人的安,今番不得无礼了。” 言着,便欲起身。无敌曰:“ 山妻已物故了。” 张小曰:“ 未聆训诲,那里晓得。少间,延入内厅,已摆下极丰美的酒筵。逊了一回坐位,各人坐定。酒三巡,无敌举杯,先饮珍布士刚曰:“老夫年迈,尚有一幼女未婚,今见张大哥,能慷慨急人难,愿以小女奉箕帚,烦三位大哥代老夫做个冰人。” 张珍曰:“老将军的命,那敢不遵。只恐我哥哥贫贱无门阀,有辱门楣。如老将军果不见嫌,敢不从命。” 无敌笑曰:“ 这主意出在老夫,不必太谦逊。”张小曰:“老将军虽不见嫌,恐小姐不豫意。与其他年琴瑟不调,不如此日葛藤先断。”张布曰:“儿女子允与不允,多羞涩不肯明言。如肯当筵奉酒,便愿俯就了。”无敌曰:“这是我笏山的古礼,即大哥等不言,老夫已排当定了。” 乃目敬之曰:“可唤汝妹子出来。”敬之带笑的进内去了。又饮了两巡酒,渐闻玎玎珰珰环佩响。敬之掀帘先出,即有几个丫头老媪捧着翩翩出来,花花翠翠好一个妙人儿,比初见时,又不同了。翩翩奉了酒,张小向身上解下金玉兽环合欢宝,交与敬之,敬之交与老媪。一时麝兰香散,步玎珰,进内去了。顷之,老媪捧出琥珀八棱杯一双答聘。男女席间交聘,是笏山的故事,不足怪的。
筵散后,四人辞回寓所,便择定三月初十日,招张小在玉府成了婚。明日,许氏即妆出病来,果然嚷嚷地请医请巫的闹着,敬之修一书,密令张小往牢阑邑,寻着丈人许宗照,言知此事。宗照看了书函,知张小系女儿的姑婿。遂令与儿子许钧,备快舆往接女儿。两家订了时刻,依计而行。果然作得周密,无一人知觉。无敌益信女婿作事可靠,自是翁婿十分相得。张小遂承间将实情说知无敌,讽无敌降。无敌叹曰:“今王,老夫故主之婿也。倘录前过,敢不为率土之臣。”于是修一待罪表文,使张小奏王,愿作内应,将功折罪。三月末旬,趁着月黑,张小吩咐张布带檄文二十张,潜入圣姥城,张珍,带檄文二十张潜入瞿谷城,自己带檄文五十张潜往竹山城,留五十张与刘士刚贴黄石。约定某时某刻,一齐张贴。各人换了黑衣,携了浆糊行事。又吩咐玉振之带书一封往寅邱投玉带侯韩腾,令人接应。玉敬之豫备行李马匹,先送妹子玉翩翩在紫藤城外白衣庙中相待。是夜甚寒冻,四城的居民闭户甚早。这四城,惟竹山为三弟所居,巡逻严密。张小先于是日,扮作黄石的公差,混进城中。天已晚了,见宣化街前,有所酒店,甚幽雅。踱进店中,先有一个公人打扮的,据住东边的坐位,见张小来,便拱拱手曰:“老兄何来?”张小曰:“某是黄石大军师的公差,姓平名贵,有紧急文书,投戚平章府里的。只是这雨如膏的,泞着街巷难走,天又寒,闻这店里好酒,借几杯暖暖手脚,才去投文哩。敢问足下何人?”其人曰:“我姓端木,名敦正。在戚平章府里,专管文书的。” 张小吃了一惊,曰:“ 足下偏得空在这里饮酒?” 其人笑曰:“我正奉本官的公文,往黄石投大军师的,大都都为着此事。” 言着,呼酒保:“ 不用另备平大哥的酒菜,有上好的酒肴,多搬些来。是我请这位平大哥的。”张小曰:“搅扰老兄,怎好意思呢。” 端木敦曰:“大家俱是吃官饭的人,况且两衙门甚耽干系,有甚么事,须照应些。这小意儿,说甚搅扰。” 张小惧他穷诘大军师衙里的事,对答不来,用甜话儿,拿酒向端木敦乱灌,看看的已有八九分醉意了。张小曰:“适才老兄言两处投文都为此事,到底甚么事呢?” 端木敦曰:“你在大军师衙里做个公差,韩水的事,你不知么?” 张小闻韩水二字,又吃一惊,只得笑着曰:“韩水的事,那里不知,只不信我们袋里的公文,专为此事。” 端木敦曰:“只为这韩水,晋王画影图形,捕拿甚急。前数日,带几个结义的兄弟,投你家大军师处,军师已奏闻天王。今天王要将他解回竹山,故我们戚相公,行文催取。难道军师回覆的公文,别有事么。” 张小曰:“ 这事尽知,但韩水好意来投,天王何苦定要害他。”端木敦曰:“ 你真个不懂此中机关,因天王闻韩水生得美貌,欲取回宫中受用的。又忌着大军师,不敢明言,故假说,”说到此处,<的吐将起来。张小趁势将壶中的余酒,灌他一回,已倒在桌上,不省人事了。时天已昏黑,酒保掌起灯来。张小曰:“我的结义哥哥饮醉了,天气寒冷,防冒着风。你这里可有铺盖,让我们睡一夜,明早,好干办公事。”这店主人,原认得端木敦,系平章府里的公人,遂与张小搀入客房里,放倒床上。店主人泡着一壶浓茶,亮着灯。张小曰:“自便罢。” 即关上房门,搜他的身上,搜出那文书袋来,浸湿封口,用口呵了十余下,慢慢的用竹刀解开封口,并不缺烂,取出那公文,向灯下细看,果然是催解韩水的事。翻来覆去,看至将韩水首从,即日解回竹山数字。不觉计上心来。原来笏山的纸有泠水、新泉两种,泠水造的薄而韧,新泉造的厚而松,凡官衙多用新泉纸。张小向身上取出小薄刀,将首从这从字轻轻的刮将起来,纸惟厚而松是以好刮。张小身上有自具的笔墨,取出笔墨来将刮去从字的字位,照原文笔法改作级字,改得甚是妥帖,照改的读去,是“将韩水首级即日解回竹山” 了。大喜,又取出些浆糊将原封的封口封固,回顾端木敦,尚呼呼的僵卧不醒,遂照旧放回端木敦身上。是时已打三更了。开房门出看,店主人犹摒挡东西未寝。张小曰:“求大哥看顾某的兄弟,呼茶呼水时,好好的给他。某趁这雨已息乘夜投这公文,免误大事。”言着跑出门去了。
张小原有飞檐走壁之术,这五十张缴文不一时贴完了。刚贴至末一张,不提防这墙角有个灯笼闪将过来,正照着张小。又有两个拿朴刀的随着提灯的,先喝曰:“你这厮深夜里贴甚么,拿去见巡城官。” 张小曰:“ 大哥,勿声张,只因我的妹子被人勾引逃去,不知下落,今出了这张谢贴,或者有人报信未可知。” 那人曰:“ 为何深夜才贴呢?” 张小曰:“这是没脸的事,白昼里防人嘲笑。” 那拿朴刀的哈哈的笑起来,曰:“有这等希奇的事?” 将朴刀支在墙角,夺那灯笼向壁上晃着。张小欲逃,又被前时拿灯笼的揪着。无计可脱,情急了,乃向怀中拔出七寸长的小刀儿,暗向揪他这个人的腹里只一戳,那人大叫一声便倒。原来张小这刀是用毒药浸炼,刺人见血,立死的。那个拿朴刀的昏邓邓倦眼麻茶,闻这一声叫,刚欲动手,张小手快已将那拿灯看檄文的戳倒,灯已灭了。张小眼明,提墙角支着的朴刀,向那拿朴刀的脑后尽力削了半个天灵盖,又向嗓里一刀。所谓说时迟那时快,其实只一齐事,俱呜呼了。张小杀死三人,即寻至僻静处,爬城而出。时四更将尽,走至白衣庙,天已明亮。张珍、张布、刘士刚及敬之、翩翩等,已在这里等候。张小辞别敬之,携了行李马匹及翩翩等,取路从寅邱回都复旨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