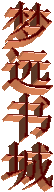
立体交叉桥 第六章
二十
北京站那两座对称的大钟敲响了九下,站前的广场上,毫无规则地布满了或立或坐、或倚或卧的人们,另一些流动的人们左躲右让地在他们之间穿行。在广场的人群中,可以看到侯锐的身影,他已经在这里游荡了半个多钟头。
家里的纠纷由侯勇的撤退而暂告休战以后,侯锐就一个人来到了这里。一开头,当轻柔的夜风吹拂着他的面颊,清凉的空气滋润阒他的鼻腔时,他产生了一种解脱感,就象一只被关在纸盒子里的甲虫,终于有机会从纸盒中飞出来一样,胸臆为之一宽。在地下铁道人口处,他买了一瓶新上市的“上海可乐”,用蜡管慢慢地吮吸着,回想起这天晚上回家后问侯勇之间的两次冲突,他主要不是为弟弟,而首先是为自己感到羞耻。他仿佛在对着一幅荧光屏,被迫观看自己在前一两个小时里的录相。他,一个读过不少中外古今典籍的人,一个自命能欣赏西洋交响乐和京剧流派唱腔的人,一个整天在学生们面前鼓吹道德与修养的人,遇到弟弟的粗暴无礼,却一筹莫展,只知道拍桌子、瞪眼、喝斥、掴耳光……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浅薄和庸俗的表现吗?
人,应当随时随处都是高尚的。可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作到这一点却如此困难?侯锐抽着一支烟,有意跑到广场上人群最稠密的地方逡巡。那里有两个人在伸长脖子互骂,一群人在那里围观。他们为什么不能想到,在这个星球上,他们起码属于同类,而在这个国度里,他们更属于同胞手足,他们又都在旅途中,这里的空间是如此之大,合不来他们尽可以各奔东西,为什么非要这样为一点点小事吵闹不休?为什么不能多多少少保留一点礼貌?他没有挤进人群围观,他往没有喧嚣声的方位走去,那声音小的地方,人却更多,他看见一些显然是从偏远的小地方来的男男女女,他们就那么随随便便地找个墙根,打开铺盖卷,横躺竖卧地蜷缩在那里。他们为什么来到北京?是否正准备乘火车回去?……有一位显然是从外地而来正准备返的妇女,她坐在那里,身边搁满了大包小包的行李,其中有一摞在木头搓衣板,足有二十块之多,为什么搓衣板这种最原始、最简陋、最易制作的东西,她要归去的地方竟不能制作,而需要来北京采买,并且要用这样辛劳的办法运载回去?我们这个国家究竟出了什么毛病,竟使得木头搓衣板也成了一种珍贵的物品?……侯锐又看到一个男子,不知为什么他决定不去旅店过夜,而是把一块塑料布卷成一个圆筒,把一头扎紧,人钻进去,用那圆筒包着自己,就在地下铁道入口侧面的窗根下睡觉。他的整个形象使人联想起蜗牛或钉螺,侯锐站在离他十步远的地方,望了他足有好几分钟。啊,原来一个人所需要的空间,可以减缩到同他本身体积相等的限度!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把对生存空间的渴求降低到这个程度,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相对纯洁起来,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相对美好起来呢?……
宣告已是晚上九点的钟声,把侯锐的思路从关于全人类的冥想中拉了回来,他不得不再想到自己的家,于是他的情结又黯淡了下来。他毕竟没有车站上那些席地而卧的人们的勇气,他势必还得回到那个狭窄而拥挤的家中去睡觉。是啊,究竟怎么睡呢?白树芬和弟弟吵了一场,却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侯勇仍是一枚定时炸弹,如果他深夜归来时,发现家里人的睡法不合他的意,他是敢把大家从被窝里薅起来的!
侯勇为什么变得这样蛮横?就如同白树芬变得那样冷峻,侯莹变得那样猥琐,自己变得如此易怒和粗俗一样,很重要的一条原因,便是缺乏自己的足够的生存空间。有了自己的足够的生存空间以后,比如说到下个世纪国家经济发达时,某些每人各有各的房间的家庭中,也许又会出现另外的问题,人们会变得互相很虚伪,很冷漠,很隔膜。就算是那样吧,但那也总比现在的局面好。我们不能因为生活发展到下一步仍会有缺憾,就拒绝去医治,排除眼前的痛苦啊!
侯锐拖着脚步,返回家里。当他行进在路灯光稀疏而暗淡的胡同中时,他不禁在心里对自己说:“你啊你啊,当你思考全人类的时候,你象个高尚的哲人;可是当你面对着家里的糟心事时,你就又成了个十足的窝囊废!我应当怎样才能摆脱庸俗卑琐的心理,使自己对生活充满坚实的信心?也许,我还应当立足于农村,在那里进行不懈的开拓……”
二十一/center>
院子里整个是幽暗的,北京市胡同里的不老少居民,在节约用电上堪称是世界大都会居民中的冠军。这并不是作为一个优良传统继承下来的。在“史无前例”的十年以前,那时候一般一个院子只有一个公用的电表,电费按灯头数目或灯泡总瓦数计算,人们在用电上很少费什么心计,院子里一到晚上总有种灯火灿烂的热乎劲,但人们也确能基本上做到随手关灯,真正意义上的浪费也并不严重。在“史无前例”的热潮过去,人们普遍产生了一种受骗感之后,北京市胡同院的居民们却似乎变得自私起来,互让互谅的淳朴民风变成了一种斤斤计较的风气,几年之中,每家自装电表成了一件必不可少之事,致使家用电表的供应一进紧张到如今;而未能安装上电表的家庭,便觉得低人一等,在计算电费时,也确实常常吃亏。按说,各家自己装了电表,院落中该出现灯火通明的景象了吧?恰恰相反,除少数的人家、少数的院落以外,普遍的状况,是流行开了一种吝啬到极点的用电方式:屋中只安一盏八瓦乃至于六瓦的日光灯,于是常常可以看到上小学的孩子搬着方凳子和小马扎,跑到大马路的路灯底下做功课,因为那灯光比家里的还强一点。人们一分钱一分钱地节省着电费,以便能把这份钱用到别处。这样的结果,便使得北京市胡同院的不老少居民更加不善于利用晚上的时间读报、看书,因而也就更加增长了庸俗与浅薄,并且使得越来越多的不得不在晚上做作业的孩子,成了近视眼。
侯锐从北京站蹓弯回来,进到院里时,整个院子里简直没有多少灯光。他家更是漆黑一片,掀开门帘进了屋,侯锐这才发现里外屋之所以没有开灯,是因为里屋开了电视,他家的电视机,属于他家最贵重的物品之一,由于没有地方安放,便搁在了大立柜里,需要看电视时,便把大立柜左边的一扇门打开,露出搁放在大立柜横隔板上的电视机,抽出电线,插到柜边墙上的插销里。这样安放电视机,天线不好使用,他们便干脆不用天线,好在附近高层建筑不多,离大马路又有一段距离,干扰也少,不用天线影象也算清晰,他们就那么看。屋里没有多少坐人的地方,看电视时,往往就爬到床上,倚着被窝垛看,倒也别有风味。
小琳琅一随妈妈回到家中,就吵着要看电视,当时因为大家都没吃饭,正忙乱中,所以没给她开。大人们的一场风波过后,妈妈让她吃了饭,她便又吵开了,可谁有心思开电视呢?她闹了好一阵,白树芬拗不过,这才去开了电视。
侯锐回到家里,首先看到的,便是倚在里屋床上看电视的白树芬和小琳琅。
他问:“爸爸呢?”
白树芬回答他:“去邮电所了,他说去替人家值班,好让咱们今晚上睡松快点。”
他又问:“妈吗?”
白树芬回答他:“到后院串门去了。”
侯锐忍不住叹口气说:“老毛病了!自己家出了乱子,在自己家唠叨还不够,还要跑到别人家唠叨去。”
白树芬呼应说:“可不,这样子她心里头也许能松快点。”
侯锐瞟了几眼电视,正播映一部编摄得极生硬的电视片,他便坐到床边说:“有什么好看的!你也真是,家里发生了这种事,你还能心平气和地看电视!”
白树芬不以为然地说:“不看电视又怎么着,坐到旮旯里哭去?躺到床上生闷气去?一头撞死去?”
侯锐说:“你别这么顶撞我,我也是为了你,为了咱们这三口人好。别人在场我也不这么说了,好在现在只有咱们在一块……”
白树芬打断他说:“这屋里还有别人呢!”
“别人?”侯锐四处望望,莫名其妙,“别人在哪儿?”
白树芬一点也不象开玩笑地说:“当然还有人,小莹回来了。”
“小莹回来了?她的事怎么样?你没问问她?”
“什么事?问什么?”
“小莹在哪儿呢?”
“她不看电视,她在下铺哩!”
侯锐站起身来,先拉开了灯,然后就弯下腰,把挡住床下铺位的布帘一拉,啊呀,侯莹直挺挺地躺在那儿,两只眼睛睁着,还在发愣。
“爸爸关灯!爸爸关灯!”小琳琅不喜欢开着灯看电视,蹬着腿嚷了起来。
候锐顾不上应付小琳琅,他把身子弯得更低,又纳闷又关切地招呼着侯莹:“你怎么回事儿?你们谈得怎么样?你干嘛躺在这儿发愣?”
直到侯莹把眼珠转向他,对他发出一个微笑,他才消除了疑惑与惊讶。
“哥,我累了,累极了。”侯莹说着,也就坐了起来,并且开始找鞋,要钻也来。
二十二
里屋只剩下小琳琅一个人看电视,侯锐、侯莹和白树芬都来到了外屋,拉开灯,开始了一场不可避免的谈话。
侯锐坐到方桌边,侯莹和白树芬并排坐在大床上。侯莹回来时,只有白树芬和小琳琅在家,她招呼了声“嫂子”,便说“累,真累”,钻到下铺休息去了。白树芬只当她是下了中班回来,也就没问她什么。现在白树芬才知道她是去搞对象回来,一种同情心和责任感促使她提起了精神,来问候锐一起询问她会面的情况。
侯莹坐在那里,仿佛参加完一场激烈的战斗,疲惫、倦怠,但从她嘴角淡淡的微笑上,又可以窥见她的内心,她对所见到的人是满意的,并充满了幻想。
“你们在一块谈了多久?”侯锐问她。
“嗯,有半拉多钟头吧。”
“都谈了些什么呢?”
侯莹低头微笑,只望着鞋尖;“我也不知道。”
“你呀,都这么大了,还这么幼稚。”侯锐叹口气说,“你告诉我们嘛,我们帮你分析分析。”
白树芬伸臂揽住小姑的肩膀,维护地说:“干嘛都告诉咱们。小莹,你拣能说的说嘛。”
侯莹羞涩地揉着衣角说:“谈看电影的事来着。”
“具体是怎么谈的呀?”侯锐有点着急。
“他问我最喜欢哪部片子。”
“你说是哪部呀?”
“《巴士奇遇结良缘》,我爱看,好。”
侯锐大失所望:“唉呀,你就不会拣点别的片子说吗?《简·爱》、《孤星血泪》、《马戏团》、《小花》、《归心似箭》……哪部不比这个强。人家是文学编辑,哪能喜欢这种香港的俗里巴唧的东西?”
白树芬反驳说:“小莹说的是实话嘛,干嘛非得照你教的这个说?搞对象,就得实话实说。《巴士奇遇结良缘》我看着也不错,说人家俗,咱们过的日子就不俗啦?我看咱们更俗!”
侯锐追问:“你问他了吗?他爱看什么电影呢?”
“我没问。”
“你干嘛不问呢?”
“……”
白树芬又帮着小姑辩解:“哪有女的问男的这个的?只有你才那么厚脸皮,跟我搞对象的时候,什么都敢问!”
侯锐觉得细致地询问没有什么意义了,便直截了当地问:“你觉得他对你怎么样?喜欢你吗?”
侯莹把头埋到胸前去了。白树芬抚爱地理着她鬓边的发髦,责备侯锐说:“你这叫什么话?先得问咱们小莹觉得他怎么样,喜不喜欢他啊!”
侯锐便间;“你觉得他怎么样?满意吗?”
侯莹连连地点着头,她怎么会不满意呢?
白树芬用温暖的臂膀把小姑子搂得更紧了。她衷心地盼望着侯莹能获得幸福。她问:“你们谈话的时候,蔡伯都到哪儿去了?”
侯莹抬起头来,满眼里闪着感激的泪光,“蔡大哥真好,蔡大哥陪着我们聊了一会儿,就一个人到王府井蹓弯去了……蔡大哥陪我去东单公园的时候,跟我说好了,他只管介绍我们俩认识,认识完了我们自己谈,谈多久都行,他今晚上还要上人家家去,人家愿意不愿意,他晚上就知道了。他说要是不太晚,兴许就给大哥你打电话……”
“是吗?”侯锐看看手表,已经九点二十几了:“今天他怕来不了电话了吧。是呀,伯都对咱们家的事,就跟对他自己的事一样上心。不过……人家跟你分手的时候,没约你下次再见吗?”
“没……。”
“没?怎么——”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白树芬分析说,“人家知道咱们小莹乐意不乐意呢!得等着蔡伯都跟你联系上了,才能知道人家的想法,也才能把咱们小莹的意思递过去……”
正说着,母亲回屋来了。她刚才到后院邻居家里,找一位跟她处境相仿的大妈聊了一阵,主题是议论媳妇的难处,以及再好的媳妇也难免在家里惹是生非,俩人很是共鸣,这使得她的心情稍许有所好转。她一进屋,见侯莹坐在那里,不禁惊呼起来:“小莹,你回来啦!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样呀,那人你中意吗?”
她的心思又全转移到侯莹身上去了。
白树芬主动向她介绍情况说:“妈,人家小莹挺可意的。俩人谈了半拉多钟头哩!”
白树芬的一声“妈”,使当婆婆的彻底消除了对媳妇的不满,她笑着说:“是吗?你瞧小莹,这有啥不好意思的呢?跟家里人,你还不能说说你们刚才是怎么搞的吗?”接着就走近前问:“你都问了他些啥呀?他的工资,是不是八十七块五呀?”
“那还能有错,伯都不是都跟咱们说了吗?”侯锐代为回答。
“工资八十七块五,也不算太多呀!他们那儿兴不兴奖金呢?一个月能拿多少哇?交通费、洗理费……都有吧?”
侯莹红着脸,偏过头去说;“不知道,我没问……”
“嗨,这有啥不能问的呢?他问你了吗?你跟他说了吗?咱们家不用你一个子儿,你们要成了家,逢年过节的,给你爸爸和我提个点心包儿来,我们就知足……”
“妈,头一回见面,哪有就谈这些个的……”侯锐插话道。
“不谈这些个谈什么?”作母亲的振振有词地说:“一个四十老几了,一个二十六七了,都是不能再拖的了,还用得着花前月下的,慢条斯理地去对它半年一年的象么?瞧上了,合得来,不吃亏,干脆就抓紧办事儿呗!”
正说着,二壮掀帘伸进了头,他对着侯锐开腔,眼睛却死盯了侯莹两眼;“侯大哥,电话!蔡大哥来的!”
侯家的四个人闻讯无不怦然心动,侯锐赶紧去接。
二十三
“伯都吗?你在哪儿呢?”
“就在他们楼下,也是公用电话。”
“怎么样?他愿意吗?”
“怎么说呢……好象是不大行……”
“怎么怎么,我们小莹怎么不行呢?”
“是呀是呀,我刚才还在跟他说,象小莹这么单纯、善良的姑娘,如今已经不多见了。”
“他不是要贤妻良母吗?如今北京城里象小莹这么大的姑娘,有几个够得上贤妻良母型呢?”
“他也说小莹可能是个贤妻良母,但是……他觉得小莹太无知,太没有常识……”
“才谈了半拉多钟头,怎么就见得呢?!”
“你别急,我也是这么跟他说,他说,小莹连香港是怎么回事都不清楚。小莹看了香港电影,觉得好,可小莹以为香港是台湾岛上的一个城市,是国民党统治着……”
“小莹是这么说的吗?……他该知道,小莹他们在学校根本就没上过地理课,不光小莹,小勇他们也没学过地理啊……”
“可他总觉得小莹的知识水平太差了一点,太缺乏共同语言……他说,他毕竟并不是想找个洗衣服做饭的保姆啊……”
“话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别生气,要生气就生我的气吧。都怪我,我应该考虑得周全点再牵线……小莹回家怎么说,她愿意吧?”
“你问这个还有什么意义呢?”
“是呀,真对不起。我发现我其实一点也不会办这类事,原谅我……”
“你就会编剧本,瞎编!”
“是呀,生活要复杂得多,微妙得多。我把握不住……别生我的气。我本想明天往你学校写信,告诉你,可那就得让小莹多幻想两天……我不该折磨她,所以这么晚了,我还是决定给你打电话,好在你们这电话方便,二壮他们也不是外人……”
“你当初就不该贸然牵这个线!”
“是呀,真对不起。你可得好好跟小莹说,别刺激她……”
“我怎么说?你来跟她说吧!你瞧你办的事……”
“我改天一定去你家,亲自跟小莹好好地说……你就说,这个不行,不算啥,蔡大哥以后再给你介绍个年轻点的……”
“我开不了口,你知道我们小莹这些日子对这种事儿犯过病……”
“所以得好好地跟她说,别说人家觉得她无知。”
“那怎么说?说人家对她满意,可就不想跟她结婚?”
“……嗯,就说人家一看,觉得自己大得太多,怕耽误了小莹的青春,所以……”
“那我们小莹要说,不怕他大,不怕耽误什么青春,我还怎么说呢?”
“是呀是呀……你就把责任全推在我身上吧,就说蔡大哥作事不细致,没把人家的想法摸清楚,人家原是想找个三十几岁的……”
“说不通,有更年轻的愿意跟他,他死不要?”
“唉,那你说怎么办呢?”
“我只能如实地告诉她,让她知道自己的无知,对她有‘好处’。也许今后她还能逼着自己读一点书。”
“那……也好,不过你应当婉转点,不要伤了她的自尊心。”
“伤她自尊心的罪魁祸首是你!”
“啊,我也是赌气才说这个话,你别介意。”
“我心里很不好受,我本想为你家做一件好事,没想到……”
“行了行了,我们还是都感谢你,你再接着帮忙。”
“我不灰心。经了这事,我更觉得对小莹负有特殊的责任……”
“以后别找这么高级的人物了,给她找个普普通通的人,不要求她把香港弄得那么清楚的人……能跟她一块好好过日子的,就行!”
“对,看来是得从这么个角度考虑。”
“我还是得谢谢你,谢谢你及时打来了这个电话。”
“这个讨厌的电话。”
“这样的电话越晚打就越让人讨厌。”
“也向你母亲道歉吧,你父亲还不知道吧?”
“怎么不知道?他刚才回了趟家,又折回单位值班去了,他听了很高兴,我父亲母亲都迷信你,认定你是我们家的福星……”
“你一定在他们面前为我美言几句,我不是什么福星,但我愿意为你家这些善良的人们效劳……”
“伯都,我的心软了。刚才我还怨恨你,现在我真的原谅你了。”
“可我自己并不能原谅我自己,我现在有一种空虚的感觉。我觉得我的剧本,我的名气,我的灵感,真是一钱不值!……”
“为什么?你可别这么想!”
“不能不这么想,我发觉我对实实在在的生活本身,还是那么无知,那么无力,那么无能……”
“别这么说。”
“好,就说到这儿吧。”
“你别灰溜溜的,我都不灰溜溜,你何必灰溜溜?”
“当然,我们要努力冲破灰溜溜,我们要顽强地开辟通向幸福的道路。”
“是呀是呀,伯都,你受累了,你还回家吗?还是就住在他那儿?”
“当然还要回家。”
“快十点了,你抓紧时间吧,谢谢你及时打来电话。”
“讨厌的,可又不能不打的电话。”
“好,我挂上了。欢迎你有工夫来我们家。”
“我会去的……挂上吧!”
二十四
侯锐接电话时,二壮在一旁耸起耳朵听,他听出侯莹没给人家看中时,心里头说不出来的痛快,那丫头养的谱儿真叫大,还得知道香港是怎么回事儿才能要人家,臭讲究!“没常识,”“就你们那号捏酸假酸耍笔杆子的有常识!……话说回来,香港究竟在哪儿?反正离北京特远特远,不在台湾,不归国民党管,那归谁?归小日本?归美国大鼻子?他妈的,我们没常识,可谁给我们讲过这些常识呢?”
侯大哥这人还算懂道理,听他说的这话:“以后别找这么高级的人物了,给她找个普普通通的人,不要求她把香港弄得那么清楚的人……”我就不要求她把香港弄得那么清楚,你们给她找我不就结啦!是呀,“能跟她一块好好过日子的”,我就是嘛,我能给她打出大立柜,打出捷克式酒柜(捷克又他妈的在哪儿?也不清楚,不清楚也一样能打出他们那号酒柜来,有图样子就行!)我还能让她少干活,陪她逛天坛,给她置件象样的呢子大衣,攒钱给她买块日本电子小坤表……
钱大爷到仓库上班去了,小弟弟到邻居家看电视去了,里屋的钱大妈和小妹妹已经入睡,大妹妹在单位值班没回来,二壮一个人呆在屋子里,关上灯,合衣靠在床上,正好凭他的素养和愿望去逻想……
他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才能得到侯莹呢?爸爸仗着酒胆去开过口,让侯大妈羞了回来;妈妈也曾在与侯大妈闲聊之中,透露过这层意思,人家侯大妈硬是装作没听出来,光拿别的话打岔……
也许,该写一封信给侯莹吧?可这信,该是怎么个写法呢?二壮活了这么大,除了看过一些小人书,几乎没读过任何一本文艺小说,象他这样缺知少识的胡同院落里的青年市民,北京城里真不老少,只不过他们象墙缝里的土鳖一样,不引人注意,常常被人们忘记其存在罢了。万万不要以为只有那些会用西班牙、夏威夷两种方式弹奏吉它琴、会背诵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并且也能写象征派诗歌、会搞抽象派绘画和会谈论克罗齐美学观点的青年,才值得我们去研究其存在价值,象二壮这样的活鲜鲜的京城青年,他们的生存价值,难道不是更值得我们去关心,去反映,去研究,去帮助他们自己领悟,获取吗?二壮现在想不出来该怎么写一封给侯莹的信,他脑海里甚至不知道有“情书”这个字眼。他只知道,那些不正经的流氓“拍婆子”时,也兴写条子的,但那样的条子他只听说过而并未见识过,所以也无法模仿……
啊,请原谅吧,如果我们如实地记录下汇涌在二壮那厚实茁壮的脸脯里的冲动——或者可以不原谅这支揭破他内心隐秘的笔,但一定要原谅象他这样的无数北京胡同里的青年市民……
二壮躺在那里,他生理上产生着一种燥热和骚动,他眼前活生生地浮现出侯莹的脸,侯莹的胸脯,侯莹的全身……他想,没法子,只好逮个机会……干脆,当她上夜班去的时候,在胡同当中那段路灯坏了长久没修、最黑最背的地方,冲过去搂住她……或许,不该那么粗鲁,那就一下子站到她面前,干干脆脆地告诉她:“我要你,你跟我了,准有你的好!”
……这是不是就犯法了呢?二壮眼前浮现出了“小锛子”的嘴脸,“小锛子”被剃成光秃,手上铐着“小镏子”,被推进了小轿车……呸,小轿车没他妈什么意思,划不来……二壮懂得犯罪不好,犯罪对不起爹妈,也对不起自己,并且也对不起侯莹;他并不是想把侯莹当“婆子”玩玩,他是实心实意地想娶她当媳妇啊!他究竟得怎么着行事,才能得到她呢?
忽然,二壮想到了一条路子,他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他拍着自己的脑袋,他笑自己笨,他为自己刚才的那种犯罪冲动而自愧。其实这事多么简单,多么保险——他该求蔡伯都给他传话呀!蔡伯都新编的话剧,他在电视上看过,那戏里不是写了讲恋爱的事儿吗?蔡伯都那戏里头的人和事,平常日子里谁见过?可既能编得有枝有叶,也就兴许真能出那样的事。他不是反对嫌贫爱富吗?他不是主张恋爱自由吗?只要他能说通侯莹,我们的事儿就能成!侯莹不讨厌我,从她那眼神里我还看不出来!都是她爹她妈,总想拿她再攀一个高枝儿,让她也迷了心窍;蔡伯都要给我们说成了,他还能再编一出新戏哩!
二壮真恨不能马上给蔡伯都打个电话,他知道蔡伯都住的那个楼区的公用电话号码,可这都什么时候了,人家那儿的传呼电话可不象这儿,早关门了,那就明天、明天、明天!
想这儿,二壮高兴起来。他哼着香港电影《三笑》里的调调,开始铺床展被,可就在这时,他忽然听到一种嚎啕大哭的声音,他立即判断出为是谁的声音,肝肠立即抽紧,心发疼,脑发闷——他咬咬牙,一跺脚,奔哭声响起的地方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