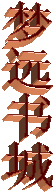
刘心武文集 洗 手
刘心武
每当我要洗手的时候,那水龙头就先伸手脖颈然后灵活的一甩自己打
上一个结儿。可是天哪,我怎么搞的呢?最最要命的是 我怎么那么神经质
那么精神失常那么反动透顶,我总想总想总想洗洗手。
这篇小说所写到的事情不是发生在上海。这一点很重要,这是我要郑重声明的
一点。另外我还要不郑那么郑重地声明一点,就是这篇小说所写到的人物全都不是
上海人,至少不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这一点不那么重要,可我也得说。
言归正传。我忽然想洗手。当然是用水洗。目的自然是使其干净。
“你的手不是挺干净的吗?”
传来一个声音。又像男人的声音,又像女人的声音,又像老人的声音,又像青
年人的声音。总之是一种中庸的声音。但很洪亮,很清晰,还带有回响。
可是我觉得我的手不干净。我相信自己的感觉。那訇的一声我没有听到,可是
我跑出来的时候,那尸体还没有僵硬,我只不过在别人起草别人抄写别人张贴的长
长的贴尽了一面墙又转个九十度贴到另一面墙还没完便又转个九十度贴到再一面墙
的那份大字报的末尾的空白部分别人都已经签满了名字的地方找了个小小的地方的
空隙颤颤巍巍地填上了自己那微不足道的名字。可是有訇的一声。然后有我挤在马
蹄铁形的人群中左右都是发着炎夏恶臭汗气的嘴里喷着消化不良引出的秽气的其实
心里也许同我一样惶悚或心里确实同我完全不一祥地充塞着义愤或鬼知道心里在怎
么想的男女所目睹的那一具还软绵绵的沾着粘稠紫红色液体的尸体。然后就有许多
公开的批判和私下的议论。轻如鸿毛和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是使用得最多的并扩大
胸腔以增阔共鸣箱猛颤声带以增强分贝值的两个语汇。而那只手表和那一堆零钱则
是窃议得最多并引出许多嘴角歪斜眉毛扭曲鼻翅翕动眼皮乱眨种种张狂的事物。
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想洗手。
在后来的平反追悼会上人们排成长长的一列很像那份大字报因为排了一行转九
十度再排一行再转九十度仍是一行我也很像当年那个签名嵌塞在挤得满满的行列中
广顶巍巍地期那遗孀以及遗孤伸出我微不足道的手去握住他们的手深致悼念之情。
然后就有若干公开的文章和私下的议论。事如泰山和高风亮节是分配稿费额最多的
八个字并且那八个字常随着印上它们的纸张包住一条活鱼或一斤傻子瓜子。而那只
手表和那一堆零钱则依旧是人们窃议得最多并引出许多嘴角抽搐眉毛上扬鼻脊打皱
眼珠圆睁种种张致的事物。
我忽然想洗手。因为刚走出灵堂他就对我说,“嘿,还不快去新街口,那儿的
菜市场每天这时候来螃蟹!”而他同他勾肩搭背,亲热得就如同当年他同他各带一
列敢死队把对方的“勤务组”砸得稀巴烂一样火火爆爆,而我自己也才深切地意识
到浮动在我思维之河中的那只大舟自始至终载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我那辆新买的
凤凰车该不会被人撬了锁吧?”我急匆匆走到存放自行车的地方,我的车没有丢,
这是桩天大的事,它没有被撬。如果訇的一声,我其实也会主要惦念这一条,我的
东西丢了没有?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重要是我的东西不能毛;如
果訇的一声,我也还是会这样么?所以,我忽然有点想洗手。
在沙龙的“派对”上我饱受嘲笑。双下巴的主人递我一杯兑了冰水的“人头马”
并拍着我的肩膀说:“心里是些什么逻辑?你以为我们都是肤浅之辈,把事情都往四
个上海人 其实女的那位算不上上海人——身上一推,就心安理得了?心安理得完全
不必那么个路数。你该知道各人有各人的命运。各民族有各民族的命运。冥冥中自
有主宰。“然后他就对我、对派对”中的众位,讲起了那訇的一声掉下去的那个东
西的命运。那家伙实在是很霸道的。他的那些著作其实有一大半根本不是他写的。
而是他的助手帮他写的,开头助手写了他还看看改改,后来爽性只坐在沙发上闭目
听听发发指示甚至没有具体指示只有哼哼哈哈,他在訇的一声以前写得最多的其实
只是他自己的名字,而他签名签得太多了以后他那签名让没见过的人见了任谁也猜
不出是几个什么中国字。所以他訇的一声主要是由于他的心理崩溃。而他的心理崩
溃实在是咎由自取的成分居多。双下巴没有讲完就被人频频打断。他终于讲完以后
几个人立时把他拉到一边。并且高级音响立即奏起丁维瓦尔带的《四季》。是从半
当间奏起,己经到了“夏”。人们极得再来嘲笑我的洗手欲。我得感谢双下巴主人,
毕竟他还针对我的冲动作出了正式的反应。我呻着“人头马”发愣。其实我早知道
双下巴讲的一切。那份贴满了一面墙再转九十度又贴满了一面墙再转九十度还几乎
贴满了一面墙的我也签上边名的大字报上就有他讲的这些内容。我很惊奇我听到双
下巴讲到这些内容时所产生的新鲜感。可是我还是想洗手。
我走到卫生间里。我拧开洗手他的水龙头,洗手。可是我觉得水龙头里流出来
的水还没有我的手本身干净。我拍打水龙头。水龙头忽然活动起来。先伸长了脖颈,
然后自己灵巧地一甩,给自己打了一个结儿。我再怎么拧开关也无济于事,连我认
为不洁的水也流不出来了。我照镜子。洗手他上方的镜子映出了我的脸。我的脸似
乎太干净了,亮亮光光的,像是用砂纸打磨过。我忽然发现我身边的人似乎都有一
张同我相似的十分十分洁净的脸,可是我们还热衷于洗脸。我们忌讳洗手。我忽然
觉得我的脸其实倒不必这么亮亮光光的。我用手沾着洗手池中的剩水往脸上抹。我
再照镜子,镜子却扭动着,调整着它的表面,或微西域微凹或微微波动,因此我无
论怎样细照,我的脸永远是亮亮光光的,并且十分美丽。我注意到镇子下面有MADE
INCHINA字样。可爱的镜子。可恨的管子。然而我还想洗手。
当我搂着我的恋人的时候,我心里头千不该万不该又飘过了洗手的念头。她不
要听关于訇的一声的事。确实对那件事我讲得也实在未免多了点儿。可我这回想洗
手倒并不是因为那訇的一声。我下午才在电视摄像机镜头前被碳精灯照得光亮亮明
晃晃来着。晚上这个城市家家户户的电视机荧光屏上部将出现我的特写镜头,人们
一般总是在吃晚餐的时候看这种特写镜头,人们的嘴巴咀嚼着,而我在特写镜头里
嘴巴翕动着,电视广播员特优我发出那义正辞严的声音。我向恋人预告了这个节目。
我的特写镜头也许将持续两至四秒。这是个不得了的待遇。就是到中国来进行国事
访问的总统或国王,一般也只给四秒的特写,这是有规定的。我又希望同恋人一起
看那荧光屏上的特写,又充满了洗手的欲望。我的心被分裂的地球切取西半。我想
洗手是因为我知道我对着电视摄像机时我脑子里充塞着最正确最堂皇最了不起的也
最要紧的东西。那就是好比那訇的一声他本是很霸道很糟糕的他有他的不可逆的命
运而且各个民族有各个民族谁也驾驭不了的命运而且唯有维瓦尔带的《四季》或梵
高的《向日葵》那样的东西才是至高无上的值得维护的再说散了会以后我那辆取代
凤凰自行车的铃木摩托该不会被人盗走那才是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
最最要紧的事再说与其让别人在镜头前来说不如让我来说我再不说谁还能说唯我来
说才分寸适当才有最佳效果这与訇的一声毫无关系而且谁以为有关系谁就有问题当
然我也不是说要找谁的问题但其实我是怕失去了比铃木摩托更要紧的东西那东西我
一时说不出口来但不久恋人哪你就能知晓就能理解……可到头来我还是有点想洗手。
在美国芝加哥我遇上了那个小伙子。他告诉我,他是在“你爸訇——訇”的嘲
笑中长大的。他对他爸的感情,原来究竟如何,他竟回想不清,但自从“革委会”
把他找去,将他爸留给他的那只手表和那堆零钱交给他时,他才突然感受到一种无
可形容的伟大的父爱。他妈那时也被隔离审查,不过没有訇的一声。他将那只手表
从腕上褪下来给我看了,是一只已显得相当陈旧的“欧米茄”。至于那零钱,他告
诉我只有柒块玖角肆分,不够买一只像样的骨灰盒,现在被他妈存在一只景泰蓝匣
子里,连同他爸的几本著作。我立即想到其实那著作里有一半并非出自他爸的手笔,
有的他爸甚至在付印前仅只是坐在沙发上饶着二郎腿闭着眼睛听助手朗诵过并仅只
是发出了一些哼哼哈哈的声音。我望着那小伙子。他嘴唇翕动着我却全然不知他还
在说些什么。我对他很失望。我原本以为他可以给我个哪怕是并不一定灵光的线索
帮我为急待来美国留学的恋人找到个经济担保人。这才知他其实是个穷光蛋并且完
全还没有开出一条路来。他戴着他爸留给他的那块表多半还并不是为了纪念他爸而
是除了最蹩脚的电子表以外他还买不起任何一块新的机械表更递论新的“欧米茄”,
“你爸訇——訇”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嘲弄。美国这地方不是几乎天天訇的一声从高
处跌下来么?而且美国有的是摩天楼,那訇的一声要气派多了,双下巴的沙龙主人说
得对极了,各人有各人的命运,各民族有各民族的命运,冥冥中自有主宰。不过不
知为什么我心里头总抹不掉我在那贴满一面墙拐九十度再贴满一面墙又拐九十度继
续贴下去快贴满另一面墙的那份大字报上所签下的那个微不足道的名字?真是的,那
算得了什么呢?我不是还在另外的大字报上也签过名吗?我还在批判会上举过我的拳
头,振动过我的声带,扩大过我的胸部共鸣箱,并且我还在外调材料上如实证明过
某某老同学崇拜托尔斯泰是个地地道道的封资修吹捧者男一位共过事的人与他的地
主婆母亲划不清界限为那地主婆祝寿时还请我在他家吃过寿面,这自然都算不了什
么,但就是在这美国的芝加哥,前天夜里做梦,梦见那总跟我漂着颈儿的矬子,我
幻想着他终于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我眼前像银幕上猛然变焦距从全景推成
大特写似的,出现了登出批判他罪行的报纸头版大标题,又出现了他惶惶然从领奖
台上被揪下来的狼狈相,随即,又有訇的一声,并且又有一具软绵绵的并不僵硬的
尸体,以及一摊粘粘糊糊的紫红色液体……而最过瘾的是我忽然成了双下巴,并且
在我的沙龙中充当主人,我为无知的年轻朋友兑好一杯加冰水的“人头马”,递给
他并拍拍他的肩膀,然后我轻声慢语地告诉他,以及沙龙中的其他朋友,那矬子所
写的作品中,很有几篇是模仿维吉尼亚·伍尔芙的!……然而那小伙子翕动的嘴唇
里逸出的声音又渐次飘进了我的耳中并清晰起来:“奇怪的是在这儿,在远离国内
的这个芝加哥的华人圈子里,我反而更深刻地理解了我爸訇的一声结束一切的心理……”
我愣愣地望着他。他不能给我恋人找经济担保人他不愿意把给他做经济担保人的名
字身份地址告诉我他戴着他爸的那块表其实多半只是出于穷酸,但我忽然想洗手。
我的恋人离我而去了。我痛苦我寂寞我空虚我虚无我颓废我颓唐我愤懑我要爆
炸可我没爆炸我反归于沉寂归于宁静归于淡泊归于原始。
我开始平心静气地琢磨洗手的事儿。一个人洗还不行。需要大家都来洗。我敢
说凡活下来的人手都是不干净的。也许正因为反正任谁的手也不能彻底干净所以大
家就都用不着洗手。那么谁爱说谁说吧。但这绝对不行。你洗手,不是在讥讽我们
的手不干净吗?你的手其实是干净的,同大家一样。手不干净的都死了,或关进监狱
了,或倒台了,或安放在不寻常的地方了。你来带头洗手是最滑稽不过的。首先你
设有那个资格。你算老几?其次你洗手只能证明你是隐藏在干净人中的污浊者。再说,
洗手根本进入不了审美层次。梵高就不洗手。毕加索洗手吗?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原则
里没有洗手这一条。对中国作家评不评得上诺贝尔文学奖有着最高发给权的瑞典皇
家科学院汉学家马悦然博士对洗手没有兴趣也不可能有兴趣,你洗手不是白洗吗?而
且洗手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毫无技巧可言,毫无形式美,属ABC之类,你洗最好到幼
稚园去洗。另外,你也该懂得,世上本无干净的手,脏手是必然的,因此脏是手的
本质,所以你洗手是最蠢不过的想法,你能把你的本质洗掉吗?除非訇的一声,不过
訇的一声也没有用,双下巴的沙龙主人就告诉了你,完全是事实,訇的一声那主儿
连脚带手都是不干净的。人的手是一辈子也洗不干净的。可我这是怎么了?天哪!我
就是摆脱不了洗手的欲望。
那个城的中心有一片湖很明净的一片湖倒映着四周景物很幽雅的一片湖我印象
很深刻并且当我刚刚走近它旁边时我不由得快乐地叫了一声:“嗬!”
可是当人们问我到过那个城没有我说没有他们告诉我那个城中心有一片湖很有
趣的湖可以把四周很有特点的房屋倒映在水中可以给我很深刻的印象这时候我就装
成很惊讶的样子发出一声,
“嗬!”
我明明去过那个城见过那个湖却不承认去过见过,因为我在那个城的时间是19
75年我去的目的是进行外调外调的对象是眼下很红很紫很了不起并且也是我的同行
还可以算是我的朋友的那么一个你大概也认识的人物,最要命的是我明明知道他无
辜明明知道不该进行那样的外调明明知道那是故意整他并且我心里头也同情邓小平
厌恶江青我私下里也传进“政治谣言”也学过江青的做派并逗得最信得过的朋友们
在拉紧了窗帘的屋子里捂住嘴笑,但是我还是很看重那次的任务很感激领导班子对
我的信任很愿意在那个时候入党并且我也确实是在完成那次外调任务回来以后就大
了党我的入党志愿书上写着我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要同还在走的走资派
血战到底我点了邓小平的名我自作多情地写上了要一辈子向江青学习我的入党申请
书至今仍然有效而且我要告诉你在1984年的整党当中我不仅算毫无问题的人我还参
加了审查“三种人”的专案组因为我们那儿的领导班子总是喜欢我的忠厚老实与甘
随人后,但现在单位里绝大多数人都调换了,领导调换了同事也大多调换了,看传
达室的老头也调换了,所以如果有人问我去过那个城看过那个湖没有,我就说没有,
并且当别人对我形容那个湖如何如何时我就微微张开嘴巴说,“嗬!”
这真是算不得什么。我跟我恋人不是从前的恋人现在得说是恋过的那个人说过
这桩事,她都懒得听完她说我是神经病,她并不问也并不关心我去过那个城看过那
个湖没有。有一回我实在想洗手,我见到了那个被我外调过的眼下很红很紫很了不
起并且也是我的同行还可以算是我的朋友的那么一个你大概也认识的人物,我凑拢
他身边脸上热辣辣的对他说我去过那个城见过那个湖因为我曾被派去进行过先有结
论后凑材料的外调,他设等我说完就脸儿飞红眼儿忽闪哼哼几声便装作有要事得找
别人商量离我而去,我觉得水池子上的水管又先伸长脖颈再灵活地一甩然后自己订
了一个结儿,我于是陷入最大的苦闷之中,然后不久我就从别人那里知道,在他那
回被隔离审查的过程当中他当然是被迫而确实是写下了若干揭发别人的材料,于是
引出了更多的外调,使更多像我一样的人见到了从前没见过的城没见过的湖没见过
的江河没见过的海洋没见过的山脉没去过的名胜。
现在我仍经常和那朋友出席宴会参加座谈并常常是同外宾在一起同台湾同胞在
一起我们谈易谈禅谈马斯洛谈布德罗斯基谈紊乱学谈气功疗法,我们常常一同去饭
店或餐厅的厕所并排站在白瓷的搁有消臭剂的小便器前排尿,然而我们却不能一起
洗手,每当我要洗手的时候,那水龙头就先伸手脖颈然后灵活的一甩自己打上一个
结儿,他呢大概根本不走近洗手池,我们就那么过得挺自在的并且会越来越自在。
可是天哪,我怎么搞的呢?最最要命的是我怎么那么神经质那么精神失常那么反动透
顶,我总想总想总想洗洗手。
这当然是梦境是只有我这种心智不健全的人才有的梦境。我接到一个通知让我
参加一个新的会议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并且也非常非常非常正确的会议,会议将宣布
一个我们都熟悉都清楚的人物的罪状,并发动我们揭发批判他的罪恶,因为这关系
到天也关系到地关系到宇宙也关系到人类前途。我将参加。我将发言。我将不参加。
我将不发言。反正无论我参加不参加发言不发言,我总是问心无愧的。因为那家伙
确实有若干令人讨厌的地方。因为这类事与我无关。因为反正我一个人也改变不了
事物运行的基本走向。因为这类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可笑的,因为我不愿意耽
搁工夫。因为我只做美的奴隶。因为我压根儿就不承认这个梦境。但最最要命的是
我明明知道他并无那样的罪孽。我明明知道。如果訇的一声,我会怎样呢?我要责怪
他脆弱,嘲笑他怯懦,叹息人各有命,感慨世道无常,并且我也许会欣赏他跌落时
所形成的抛物线的优美,因为对我来说这世界的一切都是形式而已,对于一种优美
的轨迹优美的定音鼓般的音响优美的横陈方式优美的浓稠的液体优美的带着海风般
腥味的气息我不能不进行冷挣的审美并达于物我两忘的境地。不过这个梦最精彩的
部分并不在这里,而在我接到那开会通知以后其实心底最最关心的是这回究竟都有
谁接到了这个通知我希望谁没接到这个通知我猜轮不到谁有这个通知。这当然是一
个荒唐透顶的梦拙劣的梦无聊的梦不该有的梦。然而其实我并没有做梦我只是非常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想洗手。
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