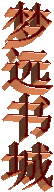
生命通道 第四章
事实上并没等到半个月,苏原便离开了莱阳城。不是逃走,而是跟随北野的部队向昆嵛山区扫荡。北野将与山本在海阳城北一个叫现石的地方会师,然后东犯。这是日军继秋季清乡又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同时也是一次强弩之末的军事行动。
时令已入初冬,中国黄河以北大半个版图已开始降雪。寒流渐次南侵,整个中原地区朔风凛冽,枯草瑟瑟。然而战争并未因季节之冷而冷,反而因临近终了而变得如火如荼。中国军队与日军在湘、桂、黔、豫、鄂诸区域的所谓“大陆决战”正激烈地进行。日军为扭转必败之局做殊死的“最后攻击”,以进为退,争取主动。十月下旬,几路敌军合围桂林、柳州,十一月初两城相继攻陷。此后,日军继续冒险西进,占取桂林外围龙胜、融县、南宁,又攻陷金城江、河池、南丹、六寨,直取贵州大门。其时,敌轻装部队一直向北追击,再占三合城、川寨、独山。至此中国军队开始反击,汤恩伯兵团从河南一路步行入黔,到达黔南前线,另一有力部队由美国航空队赶运抵黔增援,在八寨与敌军交火。一夜之间战局骤变,敌人迅速向南退却,中国军队尾后追击,先后克复三合、独山、荔波、六寨、南丹。迄月底,黔桂线战局送稳定。黔桂战事之转折趋向可视为当时整个中日战局之缩影。
出城后苏原不由回首一瞥。那瞬间他有一种预感:今生今世不会再回到这座小城了。他的回首自不是出于对小城的留恋,那里没有值得他留恋的东西。恰恰相反,往日的一切都不堪回首,那是他的牢狱,那里断送了他的一切。那最后的一瞥只是他无言的诅咒。
天空阴晦。寒风扫掠着空旷荒芜的原野。树木的叶子已经落光,站在那里如同一些赤裸的汉子,在冷风里簌簌发抖。途经的河流大都干枯,映入眼帘的是状如丝带的白亮河沙,风吹尘起,逶迤奔腾,流水一般。苏原油然记起老马所说他去的那个河里流淌白沙的“怪地场”,他的心不由一沉,他觉得此刻的。自己正在步老马的后尘踏进那个“怪地场”,只是老马已原路折回,自己却怕要一直往前走下去。如果无法脱身,也许会一直走到“死地”。
十天以前,他已将敌人这次行动的情报放在那个秘密树洞里,他相信抗日队伍会接到并已采取了相对措施。北野要他随部队行动,其目的已不同往前,这次是把他当作弈棋的对手,以便在战事的间隙随时对弈一局。自从与苏原对弈过,北野便对原来的对手龟田失去了兴趣。但因北野未占苏原的上风,因此耿耿于怀。
因为老马的缘故,高田借故留在城里。临走前高田关照他可利用这次机会脱离日军,如果逃脱不成也无妨,待回城后再从长计较。尽管高田没有明说,可他看出高田舍不得自己离去,希望能为“生命通道”计划再度合作。苏原心里也很矛盾。
北野的部队疾速东进。中午时分经过一个小村,村人已望风而逃,村里村外空空荡荡。北野下令在这里埋锅造饭。饭后又继续东进。道路渐渐向上倾斜,进入两县交界的丘陵地带。为防备抗日队伍的伏击,队伍的行进速度减缓。当再次途经一个村庄,天色向晚,部队不敢贸然前进,决定在村子宿营。是夜,无战事。如果说有,那便是北野和苏原的方格之战。第二天天亮部队继续行进。这时已踏进海阳地界,地形渐现陡峭。中午,部队经过一个状若蚌壳的谷地,四周是一圈山丘。骑在马上的北野神情惶惶,有一种不详的预感。果然当他的军队完全进入谷地,四面山头便骤然响起枪声。
这场后来被载入县志的谷地伏击战由此拉开序幕。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支抗日队伍对山本部队的伏击亦在十里之外的杨庄展开。
战斗打响之后,惊慌失措的日本兵和伪军各自寻找隐蔽物卧倒。苏原却出奇地冷静。他仍然站在原地,像个局外人,眼睛顾视着前面不断闪着亮火的山地,直到有一个上岁数的伪军向他大喝一声“卧倒!”他才下意识地蹲下身子。这时他感到有一股强烈而灼热的气流从头上呼啸而过,紧接身后不远的泥地飞起一串土花。
他仍然没有惊慌,只是向那个吆他的上岁数伪军靠过去,卧倒在他的身旁。前面的隐蔽物只是一块隆起的山岩,不时会听到子弹击中的砰砰声。
这是一块十分狭窄的谷地,长不过二里,宽不过一里,俨然是一个“口袋”。抗日队伍选中的是一块极佳的伏击地,居高临下的射击使未及散开的敌军伤亡惨重。北野的坐骑被枪弹击中毙命,他被龟田少尉和其他几名军曹掩护到谷地中间的一处凹地里,趴在地上用望远镜向周围的高地观察。对于一个征战已久的高级军官,他清楚自己已陷入在劫难逃之境地。
日伪军开始还击,这是条件反射般的盲目射击,造不成任何杀伤力。但无意中却产生出另一种效果,射击的烟尘弥漫,谷地地势低洼,又没有风,烟尘无法消散,便形成一种天然屏障。抗日队伍从山上看不清具体目标,杀伤力大大减弱。而谷地里的日、伪军在烟尘的掩护下,很快恢复起建制,各中队长指挥各自所属部队投入战斗,重机枪和掷弹筒猛烈向山上射击。
这里不是恋战之地,必须尽早突围出去。战斗僵持了一段时间,北野已选中了一个突围口,在谷地东南,两座山丘之间有一个百余米宽的豁口,由强大火力掩护从这里突围会有成功的可能。北野做了突围的部署,但没等下令,抗日队伍便发起对谷地的合围进攻,数不清的抗日战士从四面的山头上向下冲锋,枪声和喊声连成一片。
谷地里的日、伪军拼命抵抗,各种火力一齐向冲过来的抗日战士扫射。暴露在开阔地上的抗日战士不断有人倒地。日本兵的掷弹筒也发挥了威力,炮弹在抗日战士头上炸开,造成很大伤亡。这对抗日队伍离谷地边沿大约有二百米距离,合围基本完成,为避免过重伤亡,暂时停止冲锋,利用谷地四周的有利地形,对谷地形成了钳制之势。
苏原仍然卧在那个上岁数的伪军身旁。整个战斗过程都收入他的眼底。尽管他不具有军事眼光,但也看出北野的部队已陷入了“死地”。他想这是自己脱离敌营最后的时刻了。当敌人被歼灭之后,他会在抗日队伍中间找到老胡。老胡会将自己带到他的上级面前,向上级报告他就是送出情报的苏原医生。上级会握着他的手再三对他道谢。那时他会如释重负地长嘘一口气。他知道只要找到了老胡,后面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随着抗日队伍射向谷地的火力不断加强,谷地上的情势愈来愈混乱严峻,伪军们并不积极参战,只是应付,举枪朝半空胡乱射击,随时做好或逃或降的准备。日本人见状恶语咒骂,甚至以枪口相对。他们也知道关键时刻指望不上伪军,只得靠自己作战。他们一边射击,一边修筑临时掩体。军医队的军医和卫生兵在谷地中央设置了临时救护所,将受伤的日本兵抬过去包扎,敷药。重伤号疼得哭天号地,军医便往他们嘴里塞满纱布。一战地执行军官,阴沉着脸走来走去,对那些奄奄一息的伤兵补枪杀死。忽然一匹中弹的白马在谷地里疯狂奔腾,嘶叫不已,见人便踏便踢便咬,几次冲到北野面前。龟田少尉端冲锋枪向马头一阵猛射,直到那马倒地毙命为止。
为尽早实施突围,北野重新部署了据守谷地的兵力,并变换战术。他命令森日中队长带领一支冲锋队抢占谷地北面的山匠。这座山丘只有一百多米高,树木茂盛,这将给攻击带来便利。如果能抢占成功,陷入谷地的日军便可以此为依托向北突围出去。
森日中队长带领他的冲锋队跃出谷地,猫着腰边射击边穿越谷地与山丘间的开阔地带。这是一个死亡地带,然而却并未遭到抗日队伍的抗击,似乎抗日战士突然从阵地上消失。森日有些意外,脚步下意识地一停,突然迎面飞来一颗枪弹射中他的胸膛。森日倒下的瞬间一排手榴弹落在冲锋队中间,爆炸开来,冲锋队顿时死伤过半,抢占计划告吹。剩下的日军赶紧拖起同伴的尸体缩回谷地里。
当北野正欲再次组织冲锋时,一阵激烈枪声从谷地东南方向传来,谷地里的日军顿时慌张起来,一齐向枪响方向张望,终于看清,是一伙被追击的日军仓仓皇皇从豁口处向谷地拥来。枪声是豁口两边山头上抗日队伍的密集射击。谷地里的日军见是“自己人”连忙接应,将火力掉向东南,总算使那伙逃窜过来的日军进入了谷地。
豁口处的空地上留下一具具麦个子似的尸体。
这是山本部队在杨庄被抗日队伍打散的一支残部,不到三十个人。他们没想到费九牛二虎之力突围出去却又钻进新的包围圈,可谓在劫难逃。他们个个垂头丧气,一脸的晦气。
苏原仍卧在原处,听见那边的动静回头不经意地一瞥。他没看清什么,却闻到从那边飘过来的一股腥臭气味儿,就是当地鸡蛋黄花发出的那种恶劣的气味儿。他打了一个寒战,再次转回脸时,看见了八木那张又白又胖的脸,还有八木手下另外几个军医。白衣杀手。苏原只觉得一股血冲上头顶,耳朵嗡嗡叫,尔后,那股股臭味儿愈来愈浓烈地挟裹着他。他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症状,神智也变得迷离。这时他的思维十分简单,心中唯一所想便是实现一个誓愿:不能让这伙白衣杀手活着出去。他知道这个誓愿不是出自眼前,他和高田埋葬那个青年农民时这誓愿已萌生于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眼下就到了他们遭受报应的时候。他这么执著而迷离地想着,可对自己当前究竟该做些什么却模糊不清,只隐隐约约觉得手里该有一支枪。
双方的对射没有一刻间歇,烟尘从谷地缓缓向四外弥漫过去。当烟尘淹没了抗日队伍的阵地时,抗日队伍便开始又一轮冲锋。匍匐于谷地边沿的日、伪军只能朝烟尘里盲目射击,直到抗日战士冲到离谷地不远显露出身影来,日、伪军的射击才恢复了杀伤力。战斗就变得异常激烈,攻与守都同样殊死不怠。只是愈接近谷地,地面愈平坦,抗日队伍暴露得愈严重。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高昂代价。
苏原在身后拣到一支枪,是一个被打死的伪军丢弃的,那伪军很年轻,仰面躺在地上,他的头部被击中,血染红了他那张娃娃脸。苏原只看了一眼便赶紧将枪捡到手。他这是头一次触摸枪支,间一个感觉是枪的分量很重。
他回到那个上岁数伪军的身旁重新卧下,观察那伪军怎样射击。看了一会儿觉得很简单,他没想到可以将人致于死地的可怕事情做起来竟如此简单。
那上岁数伪军停止射击,侧头向他看看,脸上露出诧异神色。
“小老弟,临秋末晚了还捞家什干啥呢?”上岁数伪军说。
苏原不吭声。
“傻瓜,快把枪扔了!”上岁数伪军说。
苏原仍然不吭声。
上岁数伪军叹息一声,然后又开始射击。
苏原这时才发现他射击时将枪口仰得很高很高。
天渐渐黑下去了,射击的火花划破昏暗的天幕显得怪异而狰狞。
这是北野等候已久的时刻。
谷地里的局势已愈来愈严重,抗日战士已可以将手榴弹投进谷地。日、伪军伤亡惨重,不得不向中间收缩。掷弹筒已失去了效力,几挺重机枪成十字状摆在新挖掘的掩体内,不断向四下吐着火舌。
北野开始布置新的突围。这是一个新的突围计划,利用夜幕的掩护,从东北方向的豁口处向外突。北野将全部伪军和部分日军组成掩护队,他自己和其他军官们由余部日军保卫组成突围队。
北野竟然没有忘记苏原,他找人寻到他,将他叫到跟前。暮色中,苏原眼里的北野像一只苍老的狼。
北野见苏原手中提着一支枪,先怔了一下,却也没说什么。他看了一眼站在身旁替补卜乃堂的黄翻译官,便开始对苏原说话。黄曾担任山古队长的翻译,苏原和他稍有接触,知他的日语水平很一般。
北野说:“苏原君,现在不是叙谈的时候,这你知道的,可我得告诉你,又到了该你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这话由黄翻译官多余地翻译出来。
如果在以前,北野这句话又会吓得苏原心惊胆颤了,可这遭他十分的平静。只是定定地盯着北野。
“你说吧。”他说。
“跟我突围?还是将你留下来?这由你来决定。”北野说。
苏原的眼前出现了八木女人模样的脸。
“军医队的人一起突围吗?”苏原问。
“留几个卫生兵,其余的一块走。”北野说。
“山本部队的……八木队长?”苏原似不放心,又问。
“他是佐官,当然走。”
“那我也走。”
“这是好主意,留下落到抗日队伍手里可是要倒楣的。”北野说。
苏原在心里骂了北野一句。
“要是能活着出去,我非和你好好弃一局不可,死了,咱们就在阴间里从从容容地奔,争个高低输赢……”事到这般天地,北野竟还想来点小幽默。
只是苏原没响应。
天已完全黑下来,西天最后一抹晚霞早褪尽颜色,铅色的天幕不时被战火耀亮。夜风已起,从山口向谷地刮来,阴森森的。
战斗仍在僵持,这时苏原突然明白:日军所以能支撑下去,主要靠那几挺重机枪的火力。他有些担心,如果再拖下去,北野和八木他们很可能会逃之夭夭。
突围队已集中起来,聚拢在北野身边。虽然看不清这些人的面孔,可苏原凭那股腥臭气味儿知道八木和他的手下军医俱在。由于离得很近,这气味更为浓烈,苏原有一种要被窒息的感觉。他心里一直都疑惑不解,八木身上的气味究竟是真实存在还仅是自己的一种感觉?反正二者必居其一。但此刻他的思维已难于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他觉得头很胀疼,有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他唯一清晰的一点是,哪怕天再黑,凭自己的嗅觉会像猎犬那般跟紧八木的……
突围队无声无息转移到谷地东南与豁口相对的阵地前。
北野的突围计划简单而狡诈:他要率部像蛇样偷偷摸摸从豁口开阔地上“滑”过去。
这是一个酝酿阴谋的时刻。
突围队开始行动,几十个人匍匐着爬出谷地,那情景确像一条蛇小心翼翼地向前滑行。且很快便脱离了谷地。开阔地生长着茂盛的麦苗,像一条软毡铺向前方,队伍在上面爬行省力而无声。这是一个阴晦之夜,天上无星无月,天地间混沌一团,前面两座山丘的半腰不时有火光闪烁,那是射向谷地的火力,短促的光亮时时将山丘的轮廓显示,同时也威胁着向前运动的突围队,只要稍稍出现意外,后果将不可想象,可谓是千钧一发。苏原亦爬行在这支队伍中间,他警惕地嗅着那股恶劣的气味儿,以便弄清八木他们在队伍中所处的位置。他暗暗地“咬”紧。但那气味给他的头脑带来很大的损伤,他只能进行一种单向思维,那就是跟紧八木,不能让他逃走。而对于自己究竟将有怎样一番作为,仍然模糊一团。这时突围队已离开谷地很远,渐渐靠近抗日队伍占据的两座山丘。苏原两眼向前寻觅,他想看清到山丘还有多少距离。他忽然觉得面前的空间一下子变了模样,十分怪异,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他不难认出这是一个宽阔巨大的胸腔,他似乎觉得自己曾到过这里,但又记不清晰。他感到惊异,感到迷离。这瞬间他好像又记起了高田,记起了老马,还有他的妻子单青,但一切又是那么遥远,如同隔世。就像那些人和自己只有一面之识。胸腔里渐渐明亮起来,又像上次那样出现雷电天气,一道道耀眼的弧光照亮前面的景象,那巨如山峰的心、肺清晰地矗立,他看得见巨心在有节律地搏动,看得见巨肺在不停地收缩扩张。这是一幅生命蓬勃壮阔的景象。他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慢慢将视线压低,眼前又出现另一种景象,他看见一条宽阔平坦的道路从这些巨心巨肺中间穿越过去,一直通向那迷茫的远方。他冷丁觉悟:这就是他和高田军医寻找到的那条生命通道,人只要从这里走出去便会得以复生。这是一条神奇之路,是一条铺满光明的路。他突发奇想:假若在这条道路设下关卡,在这里将行人盘查,让好人通过,将坏人阻拦,善善恶恶都各得其所。这时他的眼光有些痴迷,他好像看见有一个人站在那座心山下面,向他张望,那人高高瘦瘦,脖子很长,啊,是老胡!他疑惑无比,老胡怎么会在这儿呢?莫非老胡已在这设下了关卡,一定是这样的,谢天谢地,老胡竟与自己不谋而合,他兴奋异常,失声高呼一声:老胡——
应着他的呼叫,是一阵炒豆般的强烈枪声……
第二天天亮,抗日队伍打扫战场。渐升的太阳驱散了弥漫于谷地上空的雾气,显现出这块弹丸之地经历过战事之后的悲凉。尸陈遍野,草木焦枯,几丛烧着的灌木还在冒着余烟,空气中飘散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怪异味儿。
抗日战士有条不紊地在清查并掩埋日、伪军尸体。一个抗日战士在两座山丘间的开阔地上发现了仍还活着的苏原。他的前胸和后背都有枪伤,全身的血几乎流尽,脸色苍白如纸。于弥留之际,他的神智尚清醒。他央那个发现他的抗日战士帮他找一个人。抗日战士问找谁,他说我老胡。抗日战士问老胡是谁,他说老胡是抗日队伍的敌工。抗日战士想了半天,最后告诉他这支队伍里没人姓胡,自然就不会有个姓胡的敌工。苏原不信,说老胡是他的联络人,怎会没有?他说他要见见部队上的长官。那个抗日战士尽管心里很不情愿,但还是找来了他们的连长。那位连长听完苏原的要求再次向他证实:这支队伍里确实没有一位姓胡的敌工。他说假如那人真是敌工的话,那他对外使用的便不会是真名真姓,是化名。化名便无定规,今天姓李,明天也可以姓王。苏原听了张嘴说不出话来。不过那位连长还是个很厚道的人,不想撒手不管。他问苏原那位自称姓胡的敌工长一副什么模样,苏原就一五一十地向他做了描述。这时站在连长身旁的一位抗日战士插言道:听他说的这情况倒与情报处的黄科长很相似。连长听了亦表示赞许,遂让那个战士立即去连部打电话与情报处的黄科长联系。那抗日战士飞奔而去。连长又喊来了连里的卫生员为苏原包扎。不久,去打电话的抗日战士又跑步回来,说那位姓黄的科长接了电话。连长问黄科长可有话说?抗日战士说那部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电话噪音很大,耳机里像在刮十级大风。可黄科长最后那句话还是听清了。他说他联系的人中没有一个姓苏的医生……此时苏原已气力不支,张口无声,只对着那位连长久久瞪着眼。
太阳从两座山丘间升高时,苏原死去。